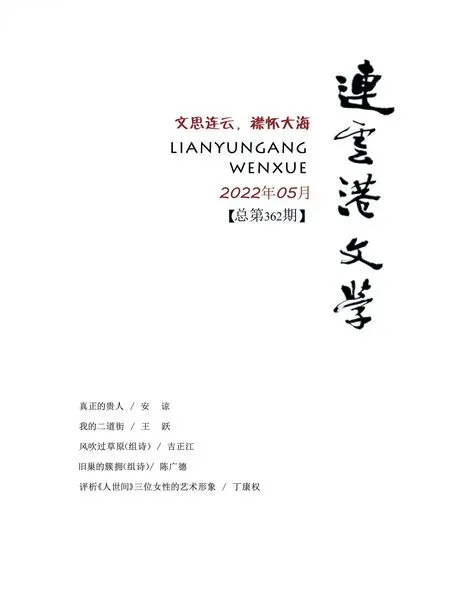年华似裳(外一篇)
陆大雁
回老宅整理旧衣物,在阁楼的柜顶上翻出一个土布包裹,里面是一件灰褐色底子姜黄色圆点的薄棉对襟小袄,瞬间,一个四岁的小丫头在生产队仓库场角落长凳上双脚悬空坐着的模样,就在这初冬午后阁楼的光线里铺陈开来。那是一九七八年,父亲还是生产队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而年幼的我,总是梳着齐整的小辫儿,穿着这件用母亲的衣裳改做的小袄,端正乖巧地跟随着我的父亲。生产队里的叔婶伯姨们免不了摸摸我的小辫,说道上一句:“哩个小细娘,一件灰不拉叽的小衣裳都能穿得这般标致。”那时的我不懂得这样讨好的赞美,但小袄子柔软体贴的棉布质感,带给幼小孩童的是最直接的安全感觉。
柜子角落里叠放齐整的是几件母亲的“的确良”衣裳,一看到“的确良”就能穿越时间的阻隔到达一九八〇年那座破旧的小学校。我很容易记起那些桌椅,歪歪扭扭,坑洼破旧,但粗糙得让人心疼,让人温暖。那个教我们所有课程的女老师姓陈,刚刚高中毕业,扎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子,眼睛细小狭长,习惯抿着嘴笑,挺括的灰罩衫里翻出灰蓝色“的确良”衬衣领子,齐整干净。她对我极温柔周到,以至于年少的我认为那是唯有我才能享有的独特待遇。如今念起便会有那样的画面浮现:低矮灰暗的屋顶下,略显局促的院场上站着一排排高高低低的孩子,围绕在他们四周的是数十棵要两人合抱得以环抱的梧桐,我站在那些掉落的梧桐叶片上,看着陈老师边念着口令,边不停地微笑着望向我。她灰蓝色的“的确良”领子,在早晨的光线里泛着唯一的光芒,而这种光芒成为一种无须言语的温暖交流,永远定格在一九八〇年。
旧衣物里有很多涤盖棉材质的衣裳,母亲一直舍不得扔,就都存在阁楼的柜子里。记得去镇上的学校上学后,便一直跟随着母亲,一九八七年左右,母亲在机械厂裁剪车间上班,那几年所有的衣裳都是用车间里裁坏的布料所制,一套紫色涤盖棉套装,超长开片的上装,同色的小喇叭口裤子,围一条母亲亲手编织的白色马海毛围巾,在校园里一走,会听到花树下少年喊出的那一句:看,穿紫衣的女孩!青春真好啊,那时的美丽不用精雕细琢就会散发在阳光中。
成年后极少穿紫色,这样充满想象的色彩,只能远望。恋爱时,被心仪的人拉到玻璃柜前,指着一件紫色的大衣说:这衣裳天生就是为你而设计。纯手工钩花的领子,A 字型宽大的下摆,旋转时有轻快的风声,那份好看的喜悦来自于甜蜜而又傻傻的恋爱。后来分手,衣裳就一直压在柜子的角落里,好几次想把它寄回去,物是人非,早已找不到新的地址。年华里应该有那些时光,是保存在柜底的一件衣裳,再也无法寄出。
柜子夹层的盒子里,是一件微微发黄的白色连身长裙。每年拿出来晒晒复又放进去,关于它的时光要追寻到工作后的一九九五年。那一年,在老街的拐角租下一间四十平方米的小屋,独自生活。彼时偏爱白色,这一袭棉布花边的白色长裙穿得最勤,空气里飘满桂花香气的时节,穿着它独自从老街的这头,走到老街的那头,不经意间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也成就了一段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姻缘。多年后,才猛然醒悟,一切的因果来缘居然和一件衣裳有着隐秘而晦涩的关联。而那个说着我就是看到你穿着白色裙子的样子,想一定要娶这个女孩的男人,也早已兜兜转转成为陌路。
午后的阳光从阁楼的窗户缝隙里斜射进来,仿佛能听得见岁月不管不顾,兀自流逝的声响。而很多衣裳,也只在华年,年轻时穿了好看,年长后再不能随意套上身。只有旗袍这样独特的衣,随着时间的沉淀,尽管容颜褪色,却会应着内心的丰盈而愈发穿得风生水起,楚楚动人。如今的衣柜里因此多了旗袍这个角色,平日里日日穿着也不再觉得刻意。我想,衣裳应该也有灵魂,而它们的灵魂依附于我们的身体和气息,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便能让它们鲜活。
人到中年,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状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学会忍耐与宽容,偏爱起宽大的袍子——这种有足够容纳度和想象空间的衣衫,能够把身体完全隐藏在里面。不管内心有多大的波澜,它令我们看起来总是默默的、平淡的、温和的。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各人住在各人的衣裳里。包容我们的衣裳,应该就是时间与记忆的载体。
回顾所来径,时光的柜子虽然落满尘埃,但我们的记忆总会随着一件旧物苏醒,那些尘封在我们记忆中的,不仅仅是一件衣裳,而是被这件衣裳所吸附的年华。它可能是一个孩童清澈的初心,一个少女或少年闪亮的憧憬,一个中年沉淀的风霜,一个正在风中赶来的未知。
豆浆 南瓜饼
王家的豆花是镇上做得最好的一家,位于大桥堍下的老街旁。清晨,下一点薄薄的雨,微凉又清澈,最适宜去紧靠河沿的大篷子底下要上一份热腾腾的豆花。
从我上班的地方,步行经过两个银行,走过一段既不热闹也不清冷的小街,稍一拐弯就能抵达那里。许是因为酝酿一场大雨的缘故,清晨在起初薄薄的雨雾里,有了一丝舒展的凉意,而这凉又洋洋洒洒地令季节有了秋的况味。
要上一杯热腾腾的豆浆和两个南瓜饼,在篷子底下的木桌前坐下来,双手捧着豆浆,将南瓜饼咬在嘴里。王家的南瓜饼也是做得极好,皮煎得薄而脆,豆沙的馅,柔糯香甜,每每吃豆沙馅或芝麻馅的吃食,脑子里总是自然而然地出现龙凤汤圆的广告画面,一枚纯白的瓷勺子里纯白的汤圆正滋滋地往外淌黑亮的馅,顺滑流淌的速度,仿佛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无休止,如同永远,是一个意境。
这些日子,平日里普通的事物,突然样样珍贵起来,哪怕是每天必经的一棵树、一堵墙,哪怕是手里的这杯热豆浆,和唇齿间留有余香的那个“永远”的意境。
很多彼此相爱的人,总是念叨过“永远”这个词,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永远相爱。那一刻,我们仿佛能够给“永远”丈量出一个确切的长度。
雨雾中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腆着个大肚子,男的穿着工作服,提着安全头盔。男人朗朗地喊:“来两个油蛋子、一杯热豆浆,再加一个南瓜饼。”听上去是安徽一带的口音,男人把要的东西都堆在女人面前,女人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他站着看她吃。女人吃了一口,把其中的一个油蛋子举到男人面前,说:“你也吃啊。”男人把女人的手按下去,说:“我不吃,你吃、你吃。”他们这样推来推去好几次,女人拗不过男人,坐下来吃一口就抬头望一眼她的男人,男人始终站在她的身侧,看着她和他还未出世的孩子吃得饱饱的,他就舒心。
我把南瓜饼咽下去,望向篷子外面通往老街的街,六十多岁的她撑一顶暗红格子的伞,在薄薄的雨雾里走过。穿了暗紫色的中式袄子,白皙的脸颊,盘得光洁的发,眼神柔和平缓地直视着前方。王家铺子的老板娘招呼她:“蒋老师,上街了啊。”她和她暗红格子的伞略微停顿了下,冲铺子这边轻浅地笑了下:“是咯,出来走走。”她是个传奇式的女人,年轻的时候丈夫去了台湾,在台湾谋了高官,又娶妻生子,她在这边守着四个儿女直到丈夫回来,四十年孤身一人。她堂堂地迎接丈夫一家归来,丈夫的第二任妻子一直尊敬地喊她蒋夫人。
紧靠河沿的杨柳在枯败的枝条间,早有了按捺不住的绿意,柳条们保持它千古不变下垂的姿势。在这样的姿势里我仿佛领略到了一种最最平淡持久的东西,比如一棵树、一堵墙,一杯热豆浆,和一个关于“幸福”的各自执守的细微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