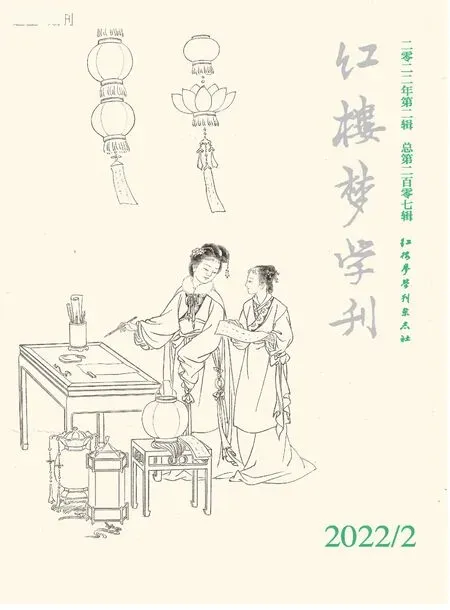论《金瓶梅》《红楼梦》中被侮辱谴责的下层女性形象
霍现俊
内容提要:《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长篇世情小说史上的两座高峰,两者的关系较其他小说更为密切。本文以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的下层女性为中心,从侮辱手段、被谴责的原因及结局、叙事立场、叙事态度等角度,探讨了《金瓶梅》《红楼梦》中下层女性书写之异同,进而探讨了《红楼梦》如何借鉴从而在整体上又超越了《金瓶梅》。
庚辰本脂批曾称《红楼梦》“深得《金瓶》之壸奥”,说明《红楼梦》深受《金瓶梅》的影响。很多红学研究者对两书之间的关系都做过系统深入的探讨,如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就从七个方面详尽论述了两者的继承发展关系。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综述》从“题旨、形象、叙事、价值”四个方面,对两书的比较研究作了较为详尽的述评,以期检视“金学”“红学”的共同成果。这些对笔者颇有启发,读者自可参看。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金瓶梅》首开长篇世情小说之先河,它以西门庆宅邸为中心,进而辐射整个社会,以西门庆及其妻妾的日常生活展现时代风貌,以西门庆的暴富死亡,揭示西门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红楼梦》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子,揭示了贾府如何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钟鸣鼎食”之家,一步步堕落到最后彻底衰败的历史规律。两书的关系较其他小说更为密切。《红楼梦》在借鉴《金瓶梅》艺术得失的基础上更为成熟,在思想、意蕴、艺术、技巧等多方面都超越了《金瓶梅》,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
两部小说之间的关系可探讨的话题很多,本文从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的下层女性角度入手,探讨《红楼梦》是如何借鉴并超越《金瓶梅》的。
一、被侮辱者阶层的固化和侮辱手段的多样性
中国小说史上写女子之不幸的篇章数不胜数,诸世情书中,集中写女性悲剧的,《金瓶梅》开其先,《林兰香》继其后,至《红楼梦》则始写出了众多女子不同的悲剧命运,其第五回所叙“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实际是悲悼“红楼”众女儿之不幸命运,她们都属于“薄命司”中人。而在这些女性中,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女奴、女仆、女艺人最为悲惨。在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处于被侮辱、被凌辱的地位,她们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反而被人站在传统道德的高度进行了种种谴责,她们作为被侮辱、被损害者又成为被谴责者。
中国封建大家族中蓄有大量奴婢,为维持家庭稳定和谐,严格恪守等级秩序,自宋以后,在传统各种礼仪规定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专为家庭而定的“家礼家规”,如司马光的《居家杂仪》、袁采的《袁氏世范》、徐三重的《明善全编》等,对家族中的男女主人、子女以及奴婢等各级成员,都有许多具体的规定,有力地维护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实际上,家礼对主子基本没有约束力,受惩处的往往还是那些身处底层的奴婢,被侮辱者的阶层是固化的。
西门宅邸中的女奴、仆妇等下层女性几乎都受过各色各样的欺辱、恐吓,或是言语上的羞辱、或是身体遭受暴力,更多的则是由言语攻击转化为身体的折磨,最后导致被卖甚至被逼死亡。“纵观历史,大多数的暴力事件是出于家庭之间或社群之间的仇恨”,西门府邸的主奴之间、妻妾之间、奴与奴之间的种种明争暗斗,可谓是形象的写照。第一回作者评论说:“世上惟有人心最歹,软的又欺,恶的又怕;太刚则折,太柔则废”,揭示了“人心不古”“人心不善”导致的家族成员之间的仇恨和倾轧,而其实质则源于森严的等级制度。
(一)言语羞辱恐吓
等级森严的社会,一旦奴仆僭越自己的身份,即使所说是正确的,如不符合主人的心意,也要遭到羞辱呵斥。《金瓶梅》第二十三回写吴月娘与孟玉楼等众人掷骰子玩耍,宋惠莲不知高低,一会指点月娘,一会又指点李瓶儿,结果孟玉楼恼羞成怒,厉声呵斥道:“你这媳妇子,俺每在这里掷骰儿,插嘴插舌,有你甚么说处!”把宋惠莲“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飞红了面皮,往下去了”。这种言语上的羞辱,那些下层的丫鬟仆妇几乎都曾遭遇过。
第六十四回“玉箫跪央潘金莲 合卫官祭富室娘”叙玉箫与书童苟合被潘金莲发现后,玉箫惊恐万分:
那玉箫跟到房中,打旋磨儿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万休对爹说。”……金莲道:“既要我饶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箫道:“娘饶了我,随问几件事,我也依娘。”金莲道:“一件,你娘房里但凡大小事儿,就来告我说。你不说,我打听出,定不饶你。第二件,我但问你要甚么,你就稍出来与我。第三件,你娘向来没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
玉箫固然有错,但潘金莲却不依不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竟以其他条件相要挟。动辄以“你看我对你爹说”恫吓他人,这几乎成为她的口头禅。
不仅主子羞辱奴才成为常态,即使同为奴才,也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那些地位高的奴才,往往对地位更低的同类羞辱恫吓。比如“心高气傲”的春梅对秋菊等其他女仆就经常指手画脚,支使她们做那些粗活、累活、脏活,稍不满意就非打即骂,其态度之恶劣,有时更甚于主子。《金瓶梅》中这样的描写很多。
经常到西门府说唱的女艺人,在传统社会中被称为“戏子”,社会地位更低,更被人轻蔑看不起,其遭遇甚至比家中女奴更为悲惨,申二姐被春梅百般辱骂就很能说明问题。《金瓶梅》第七十五回“春梅毁骂申二姐 玉箫愬言潘金莲”叙申二姐在西门府为吴大妗子、西门大姐等唱曲,春梅让小厮春鸿去叫申二姐来唱【挂真儿】,二姐不肯,坐着不动身,春鸿添油加醋,拨弄口舌,结果引起春梅大怒:
这春梅不听便罢,听了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一点红从耳畔起,须臾紫遍了双腮。……指着申二姐一顿大骂,道:“你怎么对着小厮说我,那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了,稀罕他,也敢来叫我?你是甚么总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你无非只是个走千家门、万家户,贼狗攮的瞎淫妇!……好不好,趁早儿去。贾妈妈——与我离门离户!”……把这申二姐骂的睁睁的,敢怒而不敢言。……春梅越发恼了……道:“赖在我家,教小厮把鬓毛都挦光了你的!”……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来,……往韩道国家去了。
春梅之所以如此,除了其本身的火爆性格外,究其实质,是由等级制度所造成的。反过来说,春梅对主子就不敢如此。
(二)由言语侮辱转为身体暴力
《金瓶梅》第十二回西门庆对李桂姐说过这样的话:“你还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这几个老婆、丫头,但打起来也不善,着紧二三十马鞭子,还打不下来,好不好还把头发都剪了。”“房下”指的是正妻吴月娘。西门庆的话说的很明白,除了吴月娘,其他女人都可以随意打骂。而最遭殃的自然还是那些下层的女性。
《金瓶梅》中对下层女性肉体的折磨可谓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所使用的处罚手段花样翻新,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诸如:“拧耳朵”(第十一回)、“打耳刮子、打嘴巴”(第二十八、九十四回)、“跪顶石头”(第二十八回)、“打板子”(第二十八回)、“用狼筋抽打”(第五十四回)、“用鞋底抽打”(第五十八回)、“用鞭子抽”(第五十八回)、“用指甲掐脸”(第五十八回)等。而在家里私用刑具则明显超出主子对家奴的惩罚。如第四十四回写“西门庆醉拶夏花儿”,因李娇儿房里丫头夏花儿偷了一锭金子,西门庆大怒,令琴童往前边去取拶子:
须臾把丫头拶起来,拶的杀猪也似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
拶子即“拶指”,古代审理犯人时使用的一种刑具——谓用绳联结的五根小木棍,行刑时套在手指上收紧绳索,令犯人疼痛难忍。接着又用“敲扑”这种古代鞭打犯人的刑具进行惩罚。
对家奴的肉体惩罚最严重的当为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春梅对待丫鬟秋菊。因李瓶儿生子夺爱,潘金莲借故打骂秋菊以泄愤:
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搽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教春梅:“与我采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乱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妇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点般鞭子轮起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
不仅如此,还“盖了十阑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又把他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
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中的相关描写。贾府虽说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百年望族,与暴发户西门家族有很大的不同,相较于西门家族,其等级秩序更为森严,可在表面“宽和仁慈”的背后,主子们对那些女奴、仆妇、丫鬟、艺人等下层女性的侮辱惩罚手段,与西门家族几无二致,甚至更为毒辣。我们以《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为例加以分析。该回叙凤姐生日,众女眷轮流劝酒,凤姐因不胜酒力,离席要往家里去歇歇:
才至穿廊下,只见他房里的一个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见他两个来了,回身就跑。凤姐儿便疑心,……凤姐儿坐在小院子的台矶上,命那丫头子跪了,喝命平儿:“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那小丫头子已经唬的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说着便扬手一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头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平儿忙劝:“奶奶仔细手疼。”凤姐便说:“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他再不说,把嘴撕烂了他的!”那小丫头子先还强嘴,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方哭道……凤姐儿见话中有文章,便又问道:“叫你瞧着我作什么?……你若不细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
凤姐听了,已气的浑身发软,忙立起身来一径来家。刚至院门,只见又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儿,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那丫头本来伶俐,见躲不过了,越性跑了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凤姐啐道:“你早作什么了?这会子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干净儿。”说着也扬手一下打的那丫头一个趔趄,便蹑手蹑脚的走至窗前。……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
从这段描写来看,凤姐惩罚丫头的手段与潘金莲一样,甚至更多更残忍,西门家族的主子还未使用烧红的烙铁烙嘴。对丫头而言,她们怎么做都不对,无论是告诉还是不告诉实情都要被惩罚挨打,她们被侮辱是必然的。
作为通房丫头的平儿,与春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虽说是丫头,实则是半个主子。当然,平儿的与人为善、洁身自好是春梅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在她的身上,等级观念、恪守本分亦时时体现出来,对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仆妇、丫鬟的越礼行为亦不能容忍:
探春见平儿来了,遂问:“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涂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们受这样的委屈。”平儿忙道:“姑娘怎么委屈?谁敢给姑娘气受,姑娘快吩咐我。”
当时住儿媳妇儿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坐下,让我说原故请听。”平儿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礼!你但凡知礼,只该在外头伺候。不叫你进不来的地方,几曾有外头的媳妇子们无故到姑娘们房里来的例。”……王住儿媳妇见平儿出了言,红了脸方退出去。
平儿的“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礼”,透视出其内心深处的“身份意识”。她不只是以礼规范他人,同时也以礼时时处处规约着自己。
而令人发指的是,贾府中那些小丫鬟们,她们大多纯真无邪、天真烂漫,但在主子的眼中往往被贴上“下作小娼妇”“狐狸精”“病西施”“轻狂样儿”“狐媚魇道”“妖精”等极具侮辱性的标签,她们时时面临王夫人“揭你的皮”的恫吓。如果说西门府的丫鬟们多少都沾染上一些恶习的话,贾府的丫鬟们大多却是玲珑剔透,没有染上恶习,但却遭受到同样的谴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被侮辱谴责的原因及结局
两部小说下层女性被侮辱谴责的原因不尽相同,但结局基本一样,或被卖、或配人,或被逼死亡,皆为悲剧。
奴仆对主人是否忠心,能否恪守本分,是仆人会否遭受侮辱谴责的最主要原因。
就西门府邸的女性仆人而言,夏花儿偷盗,春梅、玉箫偷情,宋惠莲“勾引”主子等行为都不符合女仆身份,未能严格恪守家礼之规定。从维护礼教的角度看,她们被谴责似乎是“必然”的。我们以宋惠莲为例加以分析。
宋惠莲在《金瓶梅》中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从第二十二回出场,到第二十六回上吊身亡,展示了其轻浮、爱慕虚荣、水性杨花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其良心并未完全泯灭的另一面。作品对她的身世做了这样的介绍:
那来旺儿,因他媳妇自家痨病死了,月娘新近与他娶了一房媳妇。娘家姓宋,乃是卖棺材宋仁的女儿。当先卖在蔡通判家,房里使唤,后因坏了事出来,嫁与厨役蒋聪为妻小。这蒋聪常在西门庆家做活答应。来旺儿早晚到蒋聪家叫蒋聪去,看见这个老婆,两个吃酒刮言,就把这个老婆刮上了。……把蒋聪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墙逃走了。……月娘使了五两银子,两套衣服,四匹青红布,并簪环之类,娶与他为妻。月娘因他叫金莲,不好称呼,遂改名惠莲。这个老婆属马的,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了。生的黄白净面,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性聪敏,善机变,会妆饰,龙江虎浪,就是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
从这段介绍来看,宋惠莲天生有几分姿色,但命运多舛,先是被卖在蔡通判家做丫鬟,后嫁厨子蒋聪,蒋聪死后再嫁来旺儿。她虽性格机灵,但生性轻浮,在进入西门府邸不久,就“被西门庆睃在眼里”,“安心早晚要调戏这老婆”,“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西门庆即以这样小恩小惠的手段,很快就奸占了她。后来事情败露后,她又想摆平她与丈夫与西门庆的关系,但结果却使来旺儿死的更惨。在得知真相后感觉被人暗算,便想一死了之。最后,在潘金莲的挑拨下,她与孙雪娥火并一场,忍愤不过,终于自缢身亡。其父宋仁鸣冤,反被李知县以“打网诈财,倚尸图赖”的罪名,夹了二十大板,不上几日,也呜呼哀哉了。
宋惠莲的遭际不过是封建社会大家族中众多丫鬟、仆妇下层女性的缩影,她被逼成为西门庆的情妇、性伙伴并导致二十五岁就“香消玉损”,已够悲惨,她本应得到起码的同情。相反,我们在作品中不但没有看到任何的怜悯同情,反而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西门庆就认为她没有“贞节之心”,不然,她当初就应该为蒋聪守节而不嫁来旺儿了。对于她的死,罪魁祸首西门庆就很不理解,归因于她是个“傻孩子”“拙妇”“没福”。这里,被侮辱者却成为了被谴责者。
但秋菊有些例外,她既没有姣好的容貌,又因“为人浊蠢,不任事体”,即不大会“做人”,往往成为潘金莲的出气筒。更多时候她本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却遭到潘金莲的多次侮辱,也得不到大家的喜欢,最后被吴月娘卖掉。秋菊在众丫鬟中最为弱势,本应最值得同情,但恰恰相反,她所遭受的谴责最为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其“天资愚钝”,不明事体,却又自以为是,做事往往不合人意。对这样的奴仆,即使传统的仪礼、家礼,也不主张过分苛刻,而应多宽恕厚待。袁采《袁氏世范》“待奴仆当宽恕”条就主张家长对所使唤不如意的奴仆“宜宽以处之”“多教诲”“省嗔怒”,因为他们“天资愚钝”,如此才能“仆者免罪”“主者安乐”,省却是非,家庭和谐。二是“不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传统的主仆之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奴仆应该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主人,是否有才干倒不那么重要。徐三重《明善全编》曰:“仆何必善干,第忠实不作奸足矣。”显而易见,忠诚比才干更为重要。如果奴仆没有忠心,往往会出卖主子,这是家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秋菊就是因为她“葬送主子”,多次向吴月娘告状潘金莲偷情,不仅潘金莲认为她“做奴才”没有做到“里言不出,外言不入”,就连同为丫鬟的小玉也严厉斥责她“张眼露睛奴才,又来葬送主子”。甚至吴月娘都谴责她“轻事重报”,是“葬送主子的奴才”。
《金瓶梅》中的仆妇、丫鬟们的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而主子为维护家族利益,不得不牺牲她们,当作商品礼物赠送他人。如迎春、玉箫,在西门庆死后,翟管家寄书索要,吴月娘为家庭计,迫不得已,派来保送往东京。在路上,来保却把迎春、玉箫都奸污了。(第八十一回)春梅因与陈经济通奸,事发后被月娘卖掉,净身出户,走时竟连一件衣服都不让带。(第八十五回)孙雪娥的结局更为悲惨,她在西门府中名为四娘,实为奴才,因与春梅发生矛盾,后遭到成为守备夫人的春梅报复,被卖为娼,不堪凌辱而自缢身亡。(第九十九回)
《红楼梦》中的丫鬟、仆妇等下层女性,其被侮辱谴责的原因及结局,与《金瓶梅》大同小异。相同者,如惜春对其丫鬟入画的态度冷漠至极——“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第七十四回)香菱的被卖,如同《金瓶梅》中的迎春、玉箫,她本身并无任何的过错,但薛姨妈为家庭计,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她卖掉:“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说着,命香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第八十回)其态度之冷漠无情跃然纸上。后在宝钗的劝说下,只好作罢。
但《红楼梦》毕竟不同于《金瓶梅》,比如同样写丫鬟偷盗,《金瓶梅》谴责的是偷盗的手段、方式愚笨,而《红楼梦》谴责的则是人的品质。夏花儿偷了一锭金子,李桂姐并没有谴责她偷盗本身的过错,而是谴责她做事不机密:“这里没人,你就拾了些东西,来屋里悄悄交与你娘(李娇儿)。似这等把出来,他在傍边也好救你。”还教唆她“不拘拿了甚么,交付与他”。同时也数落李娇儿软弱:“你也忒不长俊”,“前边几个房里丫头怎的不拶,只拶你房里丫头?你是好欺负的,就鼻子口里没些气儿。”
而《红楼梦》中丫鬟坠儿偷金子——就是那件名为“虾须镯”的首饰后,众人对偷盗的态度与西门府相较是截然不同的:“俏平儿”为人和善,先是自己承担了责任,再悄悄叮嘱麝月:“你们以后防着他些,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麝月的态度就稍激烈些,骂坠儿“小娼妇、眼皮子浅”。而最不能容忍偷盗行为的是晴雯,如让她知道,“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了,或打或骂”。果然,晴雯知道后,“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后得机会,狠狠地训打了坠儿一顿:
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骂道:“要这爪子作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哭乱喊。
坠儿母亲虽百般求情,但晴雯坚执不依,果断将坠儿立马撵出家门。按历代家礼的规定,对奴仆偷盗都是不能容忍的,司马光《居家杂仪》谓“凡女仆,……屡为盗窃者,逐之。”坠儿被逐是自取其辱,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而夏花儿则在李桂姐、李娇儿的包庇下安然无事。两部小说虽同写偷金子,但两个丫鬟被谴责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
就仆妇的结局而言,《红楼梦》中的鲍二家的与《金瓶梅》中的宋惠莲是极为相似的,两人的身份、地位、需求、被骗过程、悲剧结局甚至在叙事方法上几乎完全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两部小说的密切关系。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借小丫头之口叙述贾琏以小恩小惠的手段勾引鲍二家的,“二爷(贾琏)就开了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根簪子,两匹缎子,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叫他进来。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聪明的凤姐一听就明白缘故,但她没有直接闯进去,而是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偷听他们二人的对话:
(3)Cu,Fe,ZnXXⅣ矿体。位于研究区西区南部,矿体赋存于印支期侵入岩花岗闪长岩与大理岩接触带形成的矽卡岩中,含矿岩石为透辉石、石榴子石矽卡岩,矿体呈近东西向展布,以铁为主的铁、锌、铜复合矿体。矿体呈长条状产出,矿体总长130 m,平均厚4.66 m。铁品位25.75×10-2~48×10-2,平均品位27.05×10-2;锌品位0.6×10-2~1.70×10-2;铜品位0.31×10-2~0.34×10-2,平均品位0.39×10-2。
往里听时,只听里头说笑。那妇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贾琏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呢?”那妇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贾琏道:“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
以凤姐的淫威与主子地位,她不会像潘金莲那样只是留下记号悄然离去,而是一脚踢开门,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厮打一顿,并百般的辱骂。而且,还要到贾母处讨个说法。作为仆妇,鲍二家的忍辱不过,上吊身亡。死后,其娘家的亲戚告状打官司,管家林之孝又是威吓,又是许钱,才压下去。而凤姐的态度却极为强横:既不给钱,也不劝慰,尽管让他们告去,“告不成倒问他个‘以尸讹诈’”。最后贾琏私许二百两银子,又求王子腾通融,又贿赂番役仵作才草草了事。而告状的人只得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了。两部小说写了同样的情节,也使用了几乎相同的叙事手法。
《红楼梦》较《金瓶梅》更引人深思的是,那些从小就小心伺候主子,心灵手巧,纯洁天真的女孩们,聚在一起嬉笑打闹,不过天性而已,并没有任何的邪心恶行,但何以被逐、被卖、配人、削发为尼,甚至被逼而亡?典型的如金钏、司棋、晴雯、入画、蕙香、芳官、蕊官、藕官等。贾宝玉就很不理解,不知她们犯了“何等滔天大罪”,竟遭如此荼毒?
站在封建家长的角度看,此事“事关风化”,用王夫人的话说就是“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我通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实际上,她们绝没有“勾引”宝玉,是主子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借故冤枉她们。
《金瓶梅》中的女仆,不管是愚笨、“不忠”的秋菊,还是聪慧却偷情违礼的春梅等,她们被逐被卖,多少与其本身在西门府沾染了诸多恶习有关,而《红楼梦》中那些“既才且美”、纯洁忠心的丫鬟们,她们被逐被卖死亡的悲剧结局,却让人难以理解。或许这正是《红楼梦》的深刻之处。女性的美——身体的美、心灵的美,都被封建家长彻底摧毁。也难怪人们称《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三、叙事层次、立场与态度
古代的通俗小说,如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明显受到民间说唱艺术的影响,其叙述者较为单一、固定,大多会虚拟一位说书艺人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说书艺人身兼作者和讲述者两种身份,所以,传统的白话小说基本上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客观叙事。而说书艺人面对广大的听众,并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蔽起来,相反,他常常以“看官听说”这样的套语中断故事的叙述,毫不掩饰地向听众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或对故事情节加以说明、阐释,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或道德说教,以此表现作者的意识。
就《金瓶梅》《红楼梦》两部小说的叙述者而言,《金瓶梅》相对固定单一,没有设置更多的叙事层次。从这个角度说,《金瓶梅》的叙述者“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代言者,叙述者与作者的爱憎褒贬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但《红楼梦》却不同,其与以往的章回小说,如《金瓶梅》《西游记》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设置了多层叙事,有多位叙述者,如作者曹雪芹、说书人、石头,这方面学界多有探讨,兹不赘述。
“看官听说”在《金瓶梅》中使用频率很高,全书一百回有近四十回使用了“看官听说”。如第二十五回叙西门庆与宋惠莲私通之事被孙雪娥泄密来旺儿,来旺儿质问宋惠莲,又打又骂,宋惠莲编造各种理由坚决否定,骗过来旺儿: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养汉子的婆娘,饶他男子汉十八分精细,咬断铁的汉子,吃他几句左话儿右说的话,十个九个都着了他道儿。正是:东净里砖儿——又臭又硬。
这段议论,直接表明了叙事者亦即作者的立场。
第二十二、二十四回有两处“看官听说”的议论,都直接或间接谴责了宋惠莲。第七十八回的“看官听说”是谴责贲四老婆(叶五儿)的,她先是与玳安有奸,后又勾引西门庆,故作者评论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仆皆效尤而行。”由此可见,作者对宋惠莲、贲四老婆“水性杨花”、败坏家风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除“看官听说”外,作者也经常使用倾向性明显、感情色彩强烈的叙述语言,或使用诗词、格言等表明态度。如评价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第十回);宋惠莲“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斜倚门儿立,人来倒目随。托腮并咬指,无故整衣裳。坐立随摇腿,无人曲唱低。开窗推户牖,停针不语时。未言先欲笑,必定与人私。”(第二十二回);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第十回);王六儿“檀口轻开,勾引得蜂狂蝶乱;纤腰拘束,暗带着月意风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闻瑟卓文君。”(第三十七回)
《金瓶梅》作者对被侮辱的下层女性结局的态度是很冷漠的,甚至带有嘲讽的意味,没有基本的怜悯同情,更别说给以肯定赞美了。当宋惠莲惦念丈夫来旺儿而寻死觅活上吊被救时,贲四嫂带有嘲讽的口气说:“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来也是个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谁家媳妇儿有这个道理?”玉箫也讥刺她“贞节轮不到你头上”。对她的死亡,西门庆认为她是“拙妇”“没福”。而对秋菊、春梅、孙雪娥的被卖,无论是主子还是同为被侮辱的奴仆,大多都显得冷酷无情,甚至还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后快。
《红楼梦》则不同,在对待被侮辱的下层女性的叙述态度上虽借鉴了《金瓶梅》但又有所超越,并不一味的谴责,而是有谴责、有同情更有肯定赞美。
其一,《红楼梦》的多层叙事中虽也设置了叙述者“说书人”,也使用了“看官听说”这类套话,但相较于《金瓶梅》已大大减少,只出现有限的几次,重要的是,没有一次涉及到被侮辱的下层女性。上文所举与贾琏通奸的鲍二家的,其被勾引、死亡,与《金瓶梅》中的宋惠莲有很大的相似性,虽说“我们无法通过这个人物的描写来探知曹雪芹对这种类型的女人的态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叙述者并没有使用“看官听说”对其进行明显的谴责。
其二,《红楼梦》中贾府的主子们以维护礼教为名,对那些纯真无邪的丫鬟少女常冠以“狐狸精”之罪名,非打即骂,给以强烈的谴责,少女们或被迫出家为尼,或被随意配人,或被强行卖掉,甚至被逼死亡,结局极为悲惨。但叙述者采用反讽的手法,证明她们不是“狐狸精”,完全是无辜的,是天大的冤枉。
比如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但第三十四回金钏与宝玉“调笑”,被王夫人发现后顺手就打了一个嘴巴子,不管金钏如何苦苦哀求,最终还是被撵了出去。细究此事,主要责任在宝玉而不在金钏。把罪过完全归咎于金钏,是王夫人在歪曲事实真相。后金钏忍辱不过投井自杀,王夫人又撒谎掩饰自己的罪责,由此可见王夫人表面“慈善”,实际心狠手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对晴雯的态度。晴雯在王夫人看来是典型的“狐狸精”,为了宝玉走正道不被“勾引”,愣是把“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恹恹弱息”濒临死亡的晴雯撵了出去,连件好衣服都不准带走。晴雯至死都不明白她做错了什么:“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然晴雯虽自证清白,终不如别人的证明更为有力。故《红楼梦》又通过灯姑娘“他者”的视角,让其勾引宝玉并潜听宝玉与晴雯的对话,反证他们之间确实清白无私,“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进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
其三,《红楼梦》对下层女性尤其是对丫鬟少女们不仅有同情,更有肯定、歌颂、赞美。且不说宝玉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在生活上处处维护她们,从不以主子的身份欺凌侮辱她们,这样的描写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单就晴雯死后宝玉所撰《芙蓉女儿诔》对其美好品格高度的礼赞就足以说明问题:“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媖娴,妪媪咸仰惠德。”具有如此高洁的品格,反被诬蔑为“狐狸精”而被逐出大观园,真是天理不容。“虽诔晴雯,实诔黛玉”(庚辰本脂批),说明在曹公心中,晴雯直可与黛玉相媲美,显见作者对晴雯高洁傲然品格的深情赞誉。这一点,《金瓶梅》无法与《红楼梦》相比拟。
虽然说《红楼梦》在对待下层女性的态度上,借鉴了《金瓶梅》却又在整体上有所超越,但《金瓶梅》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则绝对不能抹杀,而且在对下层女性的叙事上,某些精彩之处恐《红楼梦》所不及。如上文所述宋惠莲在得知西门庆欺骗她之后终于痛快淋漓地骂了一顿:“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这样的慷慨陈词,较之鲍二家的“无声无息”,不管怎么说,多少带有点女性觉醒的意识。而来旺儿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较之鲍二,老婆被人奸耍了,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到“又有体面,又有银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贾琏”这样十足的奴性,似乎也更具“男子气概”。
① 参看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辑)。另外,笔者检索吴敢编著《金学索引》(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版)、李古月编《红楼梦学刊目录汇编》(香江出版社2021年版)等资料,发现单独研究《金瓶梅》或《红楼梦》中下层女性的文章较多,而将两者比较研究的文章数量很少。其中冯子礼《善恶殊途 美丑判然——〈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之比较》(《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董芳《女性自我的失落与蜕变——简析〈金瓶梅〉〈红楼梦〉的妇女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涉及到几个女奴形象,对本文有所启发。然从传统仪礼、家礼、叙事态度等角度探讨两书下层女性形象的论文,似不多见。
② 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46页。
③④⑤⑥⑦⑨[12][14][19]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90、901—902、1115—1116、579、795、277—278、580、314页。
⑧ 参看白维国编《金瓶梅词典》(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486页)。
⑩[11][15][16]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514、889—890、621、514页。
[13] 参看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待奴仆当宽恕”条,《钦定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14页。
[17] 王平《论〈红楼梦〉的叙述者》,《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辑。
[18] 参看孟昭连《〈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文学遗产》1988年第1期);王平《论〈红楼梦〉的叙述者》;苗怀明《论〈红楼梦〉的故事讲述者与叙事层次》(《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0] 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