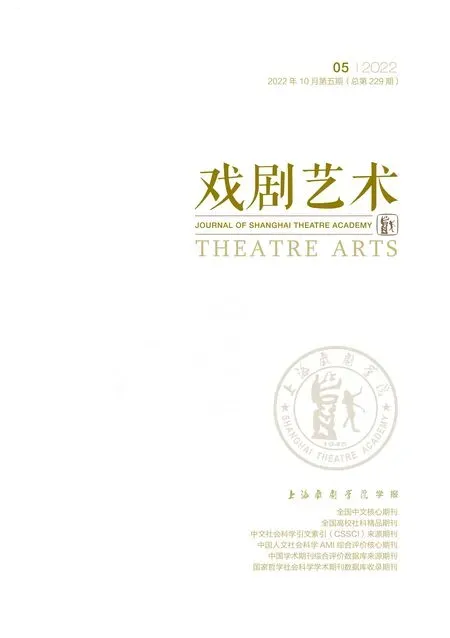具身感的临界与断裂
——“观演性”视域下戏剧演出与电子游戏“表演性”的比较研究
高 洋
“表演性”(performativity)是戏剧艺术在演出层面上最重要的本体论属性。作为一种“现场艺术”(live art),戏剧所具有的“活性”(liveness)的源泉无疑来自演员在剧场这个特定时空中的基于肉身的表演,亦即戏剧演出是一种“具身”(embodiment)化的艺术现象。不可否认的是,戏剧演出既然以活生生的人类演员的身体作为最基本的创作材料,那么具身感自然是戏剧“表演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戏剧的“表演性”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演员自己的具身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在剧场这个演出场域中,表演意义的生成不仅依赖于演员的具身在场,而且与剧场中的另一个重要群体——观众——以何种方式参与戏剧演出具身感的建构息息相关。可以说,在戏剧演出的整个过程中,演员与观众之间围绕着具身感的生成与认知建立了一套非常复杂而微妙的联系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在现象学层面上对演出事件的运行状态做出深刻规定的“观演性”才是探讨戏剧演出“表演性”特质的决定性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表演性”并不是戏剧演出独有的本体论问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般化的社会互动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表演。那么,相较于其他社会文化实践的“表演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形式的戏剧演出的“表演性”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在我们这个“数字化”(digitalization)现象正变得日益极端化的时代,特别是当“戏剧”这个概念的意涵已经从现实世界漫溢到基于计算机技术体制的数字空间,从而诞生了电子游戏这种全新的“赛博戏剧”(cyber-theatre)的时候,这个本来就不甚自明的问题的面貌似乎显得愈发暧昧不清起来。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戏剧演出和作为“赛博戏剧”的电子游戏各自在“观演性”层面上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具身感的建构与接受机制进行一番比较性的探究,因为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传统戏剧演出“表演性”的本质特征,也为阐明作为新兴数字“演出”活动的电子游戏的“表演性”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参照途径。
一、 “具身”与“非具身”的临界转换: 戏剧演出“表演性”中的“观演分离”
假如我们承认戏剧演出是一种“奇观”(spectacle)的话,那么奇观的本质“是视觉的统治,而视觉就是外部性”。视觉的“外部性”(exteriority)在戏剧演出的观演关系层面上表现为观众对演员的凝视,且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这种“看—被看”的关系就是一种“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关系。也就是说,观众看的是自我之外的、作为“他者”的演员,这是奇观化视觉的“外部性”作为一种“自我剥夺”(self-dispossession)的必然结果。观众与演员的“自我—他者”关系在传统的戏剧演出中造就了为人所熟知的“观演分离”的局面,亦即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观众端坐在观众席中欣赏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这种“观演分离”的现象在以镜框式舞台为中心结构的剧场演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观演之间的这种“自我—他者”关系并不是一种先验的、自然的存在,它的成立实际上要建立在另一重“自我—他者”关系的基础上。这另一重的“自我—他者”关系就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表象—被表象”关系。
按照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的理解,“分离乃奇观的主旨”,那么,戏剧性奇观所分离的乃“真实”(truth)与“幻觉”(illusion)。戏剧演出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是一种“幻觉”性事件。也就是说,戏剧,作为一种“艺术的虚假”(the false of art),其“最基本的表象技术是将‘此’(this)表现为‘非此’(not-this)”。这个“非此”,就是法国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所谓的“重影”(the double)。“重影”即为“假”,它不是真实本身,而是真实的“影子”“幻象”,这就是戏剧的假定性所在。虽然阿尔托极为无情与激烈地抨击了对现实世界进行幻觉式模仿的西方写实主义戏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无论何种戏剧形式(写实的还是非/反写实的),它的基础“总已经是一种‘非此’,一种否定,一种重影,由幻象所唤起”。
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表象—被表象”关系正是基于戏剧假定性所具有的这种“此—非此”关系性。也就是说,演员作为一个主体,他/她对某个角色的“扮演”(impersonation)并不“是”(be)那个角色本身,而是披上“人格面具”(persona)去“成为”(become)这个角色。在这种“扮演”过程中,演员的真实“自我”(“此”)总是隐藏在“面具”之下并通过“面具”的修饰去表象角色这个“他者”(“非此”)。从具身感的生产与感知方式来看,演员与角色之间的“此(表象)—非此(被表象)”扮演关系实际上使得“演员—角色”这个复合体始终处在一种微妙的“具身—非具身”的临界状态下: 一方面,作为“自我”的演员,他/她的有血有肉的身体作为演出创作的材料与手段在现实的剧场时空中是切实地、具身存在着的一种“现象身体”(phenomenal body);另一方面,作为“他者”的角色,不管其形式是经典戏剧文本中的具体人物形象还是先锋实验戏剧中抽象的概念与理念,本质上都是一种“符号身体”(semiotic body),亦即一种非具身的、再现(被表象)的指号。而演员对角色的“扮演”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具身的“现象身体”与非具身的“符号身体”之间不断发生的转换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处于“此(表象)—非此(被表象)”扮演关系中的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这种“具身—非具身”转换的维持还必须依赖这样一个基本前提: 与舞台上的表演相区隔的观众对演员“扮演”角色这一行为的外部化凝视。这是因为只有在作为“他者”的观众的主体性视域中,演员的现象身体才会“不可避免地要被非肉身化成这个现象身体的表达,被阅读、指认和框架化成指号”。
至此,我们可以看清戏剧演出的“表演性”是如何生成与展开的,那就是在“观演分离”这一层“自我—他者”关系的包裹下,演员与角色在另一重“自我—他者”关系中生发出现象主体(具身)到符号主体(非具身)的转换张力。由此看来,戏剧演出“表演性”的本体论基础就是观众在演出事件中的存在,且这种存在乃一种外部化的存在,亦即观众与舞台上的“演员—角色”是彼此分离的。在某种意义上,“观演分离”正是戏剧演出的“决定性的空间性格”。借用波兰戏剧导演塔德乌什·康托(Tadeusz Kantor, 1915-1990)的表述,观演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藩篱”。任何将观演之间的这种距离视为一种被动的“恶”、试图以激进的参与互动方式来赋予观众介入到表演行动中的自由的做法,实质上都是对戏剧演出“表演性”的本体论基础的破坏,在艺术性层面上也不会产生理想的美学效果。这一点已经被兴盛于西方1960年代、以理查·谢克纳为代表的环境戏剧运动的舞台实践遭遇的挫折所证实。
二、 “具身”与“非具身”的隔绝: 电子游戏“表演性”中的“观演融合”
到目前为止,计算机在“赛博戏剧”的演化进程中发挥了最为支柱性的作用。随着在软硬件层面上的快速迭代升级,计算机的角色早已从其诞生之初的单纯演算进化为全面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生活各个角落的基础设施性系统。如果说人类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由众多计算机互联而成的、涉及现代人一切重要社会文化行为的网络时空无疑是人类栖息其间的一座宏大的数字舞台。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计算机与戏剧在运作形式层面上可能具有的相似性,从而有了“作为戏剧的计算机”(computers as theatre)这样的隐喻化表达。进一步而言,计算机的硬件设备只是为数字剧场的建构提供了物质性保障,而运行于硬件平台之上的各种计算机软件和应用程序才是真正在这个赛博时空中展开的“演出”事件。在计算机的所有程序类别之中,电子游戏的运行样态是最富有“表演性”的。由玩家控制的“角色”在电子游戏这个赛博世界中经历的种种冒险故事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戏剧演员在现实世界的剧场中扮演角色从而推动多彩的戏剧情境的现象。然而,如果我们从“观演性”的视角对戏剧演出中的“演员—角色”关系与电子游戏中的“玩家—角色”关系加以细致的对比性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戏剧演出与电子游戏的“表演性”存在着本体性的差异。
正如前文所述,过度追求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以消除“观演分离”的诉求实际上逾越了戏剧演出的本体论界限,从而使戏剧演出退化成了“仪式”(ceremony)。仪式,作为一种“前戏剧”(pretheatre),是一个参与者不分彼此地在形式化的互动行为中建构的共同体。而游戏在这一点上恰恰是与仪式同构的,即游戏的本体论属性也是一种“互动性”(interactivity)。在即存的所有游戏样式中,基于复杂精细的人机交互界面的电子游戏无疑拥有最为丰富多元的互动机制,而这种强大的“互动性”让电子游戏的“观演性”呈现了与戏剧演出的“观演性”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果说在戏剧演出中希求完全消除“观众—演员”二元对立的所谓“观演员”(spect-actor)的诞生是一种违背戏剧本体性的一厢情愿的话,那么以人机交互为行为基础的游戏玩家无疑是电子游戏这个“赛博戏剧”中的“观演员”。电子游戏玩家在进行游戏时的存在状态确实是集“观”与“演”于一身的: 他/她透过与计算机系统的互动随时“观”看并操“演”着游戏中的角色。然而,不同于戏剧演出中观众对演员的观看是一种“自我”对“他者”的外部化凝视,电子游戏中玩家与角色之间的“看—被看”现象却并不具有一种“自我—他者”关系。这里就牵涉到戏剧演出中演员对角色的“扮演”与电子游戏中玩家对角色的“操演”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重大不同。
前文已经提及,戏剧中的“扮演”(impersonation)在演员与角色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此(表象)—非此(被表象)”的关系: 角色作为一种非具身的、观念世界中的“幻象”(真实世界的“重影”、“非此”),由现实时空中的演员(隐藏在“面具”下的“此”)具身地表象出来。与此相对,电子游戏中玩家对角色的“操演”,或者更准确地说——“操作”(operation),却体现不出这种关系,这是因为游戏中的角色在本体论意义上并不是“幻象”(illusion),而是一种“拟像”(simulacrum)。如果说“幻象”是与“真”(“此”)相对立的“假”(“非此”),那么“拟像”则脱离了这种真假对立范畴,因为它“是另一种状态的真实,而不是真实的反面”,是一种比真实更加“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幻象”虽然为“假”,但是它与真实还存在联系,它是现实世界的“影子”;而作为“超真实”的“拟像”则是一种“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是“影子的影子”。

这里我们就直面了戏剧演出中演员对角色的“扮演”与电子游戏中玩家对角色的“操演(作)”在“表演性”上的重大区别。“扮演”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分离,“自我”借助“面具”去“表象”这个“他者”,这就是演员与角色之间“此(表象)—非此(被表象)”关系的本质深度。而电子游戏“操演(作)”中的玩家与角色的关系却并没有这种深度。游戏角色不是玩家通过佩戴“人格面具”的扮演行为投射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像”,而是在计算机屏幕内的一个“绝对平的”世界中的“拟像”,它与真实并没有深度关联,是一种自在的“另一个原物”(another original)。这使得电子游戏这个数字“演出”时空丧失了传统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 一切都“是”(be)其所“是”,而不是通过“此”来表象“非此”。正因为丧失了这种“此(表象)—非此(被表象)”的关系,电子游戏中的角色对于玩家来说已不是“他者”,而是变成了玩家在游戏中的“代理”(agent),亦即玩家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电子游戏在“观演性”上所具有的“观演融合”特质的本体论基础正是玩家与角色之间的这种“自我—第二自我”的关系。作为游戏者的“我”所“操演(作)”的角色并不是被“我”所表象出的“他者”,而是“我”在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数字化身”(digital avatar)。所以“我”对其的观看也就不是对“他者”的外部化凝视,而是一种“自我凝视”(self-gazing)。归根结底,戏剧演出和电子游戏在“表演性”上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前者中的“表演”是一种“扮演”,而在后者中则是一种“操演(作)”。“扮演”因为在“观演性”上是处于一种“观演分离”的状态,所以其美学关注的焦点永远都是外在于“自我”(观众)的“他者”(演员—角色);而“操演(作)”则是一种自我美学投射,因为电子游戏玩家“是自己的表演的观众”,所以其“美学关注的焦点就变成了他们自己”,这可以被称为一种“自表演性”(self-performativity)。
此外,电子游戏与戏剧演出各自的“表演性”在具身感的生产与感知机制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前文已述,在戏剧演出中,演员与角色通过扮演行为在彼此之间搭建了从“具身(现象身体)”到“非具身(符号身体)”的转换回路,而这种临界转换在戏剧演出中还需要观众的外部化凝视来维持。不仅如此,观众与“演员—角色”之间的“看—被看”关系实际上也处在一种“具身”与“非具身”彼此交错共存的“临界”(liminality)状态中。也就是说,在戏剧演出中,观众在现实世界的剧场内具身地接受着同处于现实域的演员的具身表演的同时,也在观念域中与演员所表象的角色之间发生了非具身化的“情感认同”(identification)联系。与此相对,作为玩家在游戏世界里的“第二自我”,电子游戏中的角色仅仅在计算机的屏幕内以一种非具身的“数字身体”的形式自为地存在着,它只“是”它自己,与“第一自我”之间不存在“此(表象)—非此(被表象)”的扮演关系,所以与屏幕外玩家的肉身之间建立不起任何的“具身—非具身”转换通路,从而造成了两者之间具身感的彻底隔绝。换言之,对于游戏玩家来说,一方面,作为“操演(作)者”(operator),他/她的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在进行电子游戏的过程中确实有着极为频繁甚至高度精细复杂的具身化行为。然而,对于这些具身动作来说,其施加与接受反馈的对象实际上是透过人机界面与玩家进行互动的计算机系统在现实世界的外部接口,而并不会对非具身地存在于这个系统“内部”的角色产生任何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子游戏玩家对角色的凝视也很难会产生类似于戏剧演出中观众对角色的那种在观念层面上的“情感认同”。不可否认的是,玩家在进行游戏(特别是那些竞技性很强的游戏)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游戏中角色的一举一动。然而,多数情况下,这种专注却需要玩家将自己的意识封闭起来,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要求在玩家与角色之间建立有意识的非具身化情感联结,而在于玩家如何能够在一种下意识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无意识下,根据游戏所需的计算机设备(键盘、手柄等)的接口规格来技术性地调整自己的具身化操(演)行为,从而实现游戏效率的最大化。
结语
众所周知,笛卡尔的第一沉思主张一种身心对立的二元论式主体观。以胡塞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研究对这种认知进行了否定,揭示了主体乃是其“思”与其“身”紧密交缠在一起的“现象身体”式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现象身体”是“物理具身”(physical embodiment)的,也就是“思”依附于“肉”(物质性的“体”)之上。在传统的戏剧演出中,具身的演员与非具身的角色分列于两个不同的现象域,而演员与观众虽然同时物理具身地存在于现实的剧场中,但是由于主体作为“最小现象自我”(minimal phenomenal self)的制约,二者之间也有着能够明确区分彼我的具身独立性。这二重的“自我—他者”关系造就了戏剧演出“表演性”中的“观演分离”。然而,由于戏剧表演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一种基于“此(表象)—非此(被表象)”关系的“扮演”,所以恰恰是这种“观演分离”成就了不同现象域之间的“具身—非具身”的临界沟通。演员的“现象身体”假定性地“成为”了作为“符号身体”的角色在此世的“显像”,而作为这个“现象身体”的一个部分,演员的“思”也象征性地代替了角色的“思”(所谓的“进入角色”,也就是演员对角色的“移情”);另一方面,观众通过外部化的凝视对“演员—角色”扮演关系的具身接受中也包含着将自己的“思”向角色的“思”靠拢的非具身行为(观众对角色的“情感认同”,即某种意义上的“移情”)。
相较之下,电子游戏的“表演”在本质上乃一种“观演融合”的“操演(作)”,这使得游戏玩家获得了“观演员”的存在状态。然而,集观演于一体的玩家位于现实世界的身体却与数字世界中的游戏角色断绝了具身感的联系。游戏角色虽然是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第二自我”,但在本体论意义上乃一种“拟像”,也就是柏拉图式的、绝对理念化的“身体本身”。它就“是”它自己,反对被表象,也不需要“思”,而游戏玩家也不会代替它来“思”,这是因为游戏玩家自身在现实域中的“现象身体”也在与计算机的互动中遭遇了异化。玩家在进行游戏的过程中似乎展现了一种全神贯注的面貌,但是他/她的“思”实际上是处在被封闭的无意识状态(他/她对屏幕内“第二自我”的凝视是空洞无情的);而其生理性/物理性的肉体动作却被计算机的外部接口高度格式化了。在这种存在状态下,玩家的身体可以说已经变成了计算机设备的一部分,从而蜕变成了物质化的“体”。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电子游戏“表演性”实质的“操(演)”不仅在玩家与角色之间造成了具身感的断裂,而且也让玩家自身的“现象身体”遭遇了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
在朗西埃看来,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现代的一些先锋戏剧人,他们将传统戏剧演出的观演方式视为“知的反面”(the opposite of knowing)。由此阐发的观点是,知识要靠积极的“行动”(action)来获得,而传统戏剧演出中的演员与观众只是在舞台的上下被动消极地感受着“他者”(角色)的痛苦,这种行为仅是一种虚妄的“幻觉”,它不能为现实中的苦难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所以演员与观众都是不会行动的“无知者”(ignoramuses)。然而,行动意义的生产与传递最终离不开情感上的联结,而这种情感联结的最理想形式正应是“思”在主体间的碰撞与交流。以此观之,相较于作为“赛博戏剧”的电子游戏的“表演性”造成的无“思”状态,传统戏剧演出的“表演性”所具有的幻觉式“移情”效果尽管被人所诟病,但是它的实质正是“演员—角色”以及“观众—演员(角色)”间的“思”与“思”的融合(尽管这种融合仅仅发生在非具身的、观念性的层面上),它们触发了理解、同情等宝贵的情感,这恰恰是戏剧艺术能够唤起变革的潜能,也是它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与动力。
-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观演行动矫形术: 沉浸式剧场观演权利差异化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