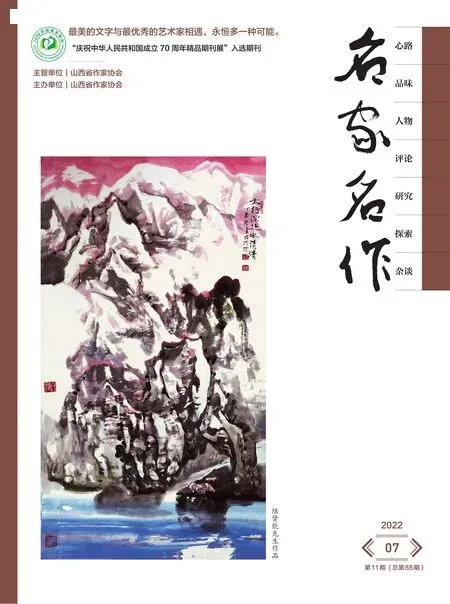我相信世界的什么而写作
樊健军
每次开始之前,我都会做这些事情,给自己洗个脸,泡一杯修水当地的茶,宁红或双井绿,有时也喝金丝皇菊,然后打开电脑,点支烟,放上一段音乐,最好是萨克斯,有时也播放一段乡村音乐。当然,这是在上午,大概从九点开始。我不希望这个时候接到电话,也不希望有人突然叫喊我的名字。我要在香烟、茶、音乐中静默好长一段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茶,香烟,音乐,都是清洗剂,慢慢地清洗我的内心。
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我必须这么干,否则没法开始。我要借助这种仪式进入一种状态,借助它驱逐一些滞留于内心的烦嚷和不洁。就像清理杂物间一样,我要将那些粗暴地进入内心的野蛮之物,无用之物,烦恼之物,滋生霉菌之物,妨碍思考之物,有碍观瞻之物……连根拔起,——从内心扫荡出去。我要清空自己,将那些同小说无关的、伤害小说的阴险之徒、无赖之徒,扫地出门。我要在短暂 的虚空和安静中进入被封闭的一重内心。香烟,茶,音乐,仿佛编织了一道隔离带,将我同俗世必经的烦琐暂时隔离开。
我要忽视、忽略一些东西。我的写作间在临街的二楼,街对面是一所医院,街道两边都是商铺,点钞机哗啦啦的响声不分白天和黑夜。我要将叫卖声、电动车喇叭声、汽车轮胎同水泥路面的摩擦声阻隔在书窗外。我不接纳讨价还价的争吵声,我要将它们隔离在我的耳朵之外,隔离在我的小说之外。它们都在考验我的意志和力量。它们是我创作时的敌人,是小说的敌人。好像在我和世界之间突然有了一条断裂带,这条断裂带依照我的意愿不断延伸、拉宽,它的深度也在不断增加,见不到底。我是故意的,偏执地在我和世界之间挖掘了这条鸿沟。
我好像对世界充满了疑虑。我怀疑它会伤害了我的小说,怀疑它的不真实,怀疑它的粗暴,怀疑它对我的统治欲望和对我的控制。怀疑它的琐碎就像水面浮萍一样虚假,没有扎根人类的本真。
在怀疑世界的同时,我也在怀疑自身。我几乎将自己当成了一个提线木偶,外部世界随便伸过来一只手,就会将我操控、把玩,依照外来之手的想象让我做出各种动作,取悦那些同样对自身充满疑虑的观众。
我就在被茶、香烟、音乐隔离出来的空间开始创作我的小说。我要在小说中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不同于外部的世界。它是内心真实的存在,是我培育的,从一颗胚芽开始,一把土、一杯水,像建造一个空中楼阁一样,它是我内心悬置的楼阁。事实上在我的小说和外部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隐秘通道,让我同世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内在世界的取材完全来自外部世界,我像精卫填海,一草一木,攫取所需。是的,对于世界我至少相信了其中的某些部分,那些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真实、最具可信度的部分。如果没有了这只鳞片羽的信任,那小说的内在世界就完全坍塌了。在疑虑丛生最为焦虑的时候,我就做个短暂的停顿,待疑虑消除之后再开始我的仪式,重新上路。
樊健军,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江南》等刊,著有长篇小说《诛金记》《桃花痒》,小说集《穿白衬衫的抹香鲸》《空房子》《行善记》《有花出售》《水门世相》等,曾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第二十九届梁斌小说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青岛文学》第一届海鸥文学奖,首届《星火》优秀小说奖。小说作品入选加拿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