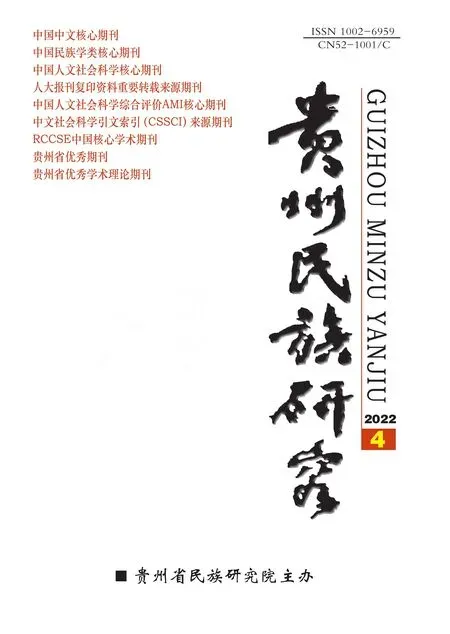论农村妇女的非正式组织与公共参与
——黔中屯堡修福民俗的质性研究
杨 兰 杨琼艳
(1.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2.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黔中屯堡是明代以来调北征南、调北填南遗留下的军屯、商屯及民屯,集中于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地,涉及300多个自然村(寨),至今仍保持相对完整文化的有九溪村、本寨村、云山 村、天龙村等。“回观屯堡文化研究轨辙,地戏傩戏之辩、屯堡族属之辩及屯堡社会形态之辩引领的民族志书写、人类学考察、社会学调查、历史学考证、文化学追根及民俗学实践的多学科研究已然由资料学意义上的搜集整理转向跨学科研究,由描写研究转向理论研究,由‘回望过去’转向‘朝向当下’”。值得注意的是,屯堡文化研究始于对女性的关注,正如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所说:“处于偏僻之地,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依然保留明代江南的民俗,原原本本的头饰发型,这对于后来人口众多的汉族移民,则感到异常稀奇”。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屯堡女性奇异的头饰服饰,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又忽视女性,由于“学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壁垒亟待洞穿,还原民俗书写的主体及书写主体的多元是民俗学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所以这些研究多以他者视域关注外显的文化符号,较少从女性本身探讨,导致完整的女性视域长久以来难以被完整纳入学术讨论。
修福是黔中屯堡女性的重要生命礼仪。屯堡女性至40岁时,就开始这一项事关家庭美满、亲人幸福、自身安宁的民俗活动。在调研过程中,传承人罗某英对修福歌作了诵唱:
管你修福不修福,各人修来各人得。一修儿女成双对,二修夫妻到白头;三修金银多得用,四修谷米在仓头;五修槽头有猪喂,六修房前有良田;七修八忏得清吉,九九地狱转回首;是行是忏修得有,免得二世转来愁。
屯堡修福是女性自我心灵救赎的礼仪,也是祈福性质的公共参与活动。不同于以往研究中使用“修佛”的表述,论文使用“修福”的表述是因为修佛的最高境界是达到智慧与道德的圆满,摆脱世间的悲苦,觉悟出万物皆空的佛性智慧,从而断除烦恼,清除妄念,超越生死轮回的世俗世界;而屯堡修福将传统佛教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造,转化为屯堡地域内的整套认知体系和生活态度,强调的是修福的实用性。同时,这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造就了独特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又在赓续绵延中不断产生新的意义,并实现屯堡文化的价值更新。如此,包括修福等民俗活动在内的屯堡文化记忆不仅包含了历史的承继性,也包含了被阐释的意义性,呈现出“书写女性”的叙事策略与“女性书写”的生存策略,成为屯堡人建构认同的主要方式,也成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 年7月至8月、2020年7月至8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屯堡文化综合数据库建设》课题组、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黔中屯堡民俗文化调查研究》课题组两次赴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区开展田野调查。调查发现,屯堡妇女朝山走会的修福民俗,是屯堡妇女在完成家庭生育职责后的一种心灵追求。屯堡妇女围绕修福民俗形成了若干非正式组织,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已成为普遍现象,她们用朴实的语言讲述醇厚的文化记忆,她们用一致的行动践行高度的文化自信,她们用擅长的方式表达积极的生活态度,她们的生活实践也因此从家庭走向社会,并借此参与到村庄公共生活中。
二、非正式组织:黔中屯堡妇女公共参与的解释框架
切斯特·巴纳德最早创造了非正式组织的概念,却因定义过于宽泛,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此后乔治·埃尔顿·梅奥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工厂进行了霍桑实验,发现工人们除了工作交往以外,会建立起一定的日常交往关系,并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组织。这种非正规群体,有着特殊的感情、规范和态度倾向,对成员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对团队的归属感也有效促进了生产。基于此,梅奥重新界定了非正式组织,即“人们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以感情、喜好等情绪为基础的、松散的、没有正式规定的群体”。他甚至认为“那种希望获得他人认同的意愿,即所谓与人协作的本能,远远胜过仅仅关注个人利益和只进行逻辑思考的意愿,而后者正是当今不少虚拟管理理论的基础。”人们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工作和接触,形成了以情感、爱好等为基础的群体,他们没有正式组织的限制,也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只是自发地形成一些关系结构,并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出现一些领头人,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
当前,学界对于非正式组织的界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框定在梅奥的界定之中,将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作为一组对立关系置于正式组织的结构框架之中,认为“非正式组织是组织内部某一特定群体为了寻求心理归属及同类依附与利益追求而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一种有共同价值取向(特定情况下也有共同而清晰的目标)、有心理的或权威的或精神的领袖却无固定组织结构无明文组织纪律的非公开化亚组织。”由于正式组织在权力安排、社会交往以及成就感等方面的不完全性,以至于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需由一些非正式的制度来连接。“正式组织是以效率的逻辑为重要标准,而非正式组织则强调情感的逻辑”。另一类则不再囿于梅奥所给出的界定,认为非正式组织可独立于正式组织之外,活动开展人数规模为3 人以上,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枢纽,也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网络,并广泛存在于任何一种群体之中。在农村,以共同情感和爱好形成的广场舞爱好群体、扭秧歌爱好群体等,正是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典型代表。
作为农村非正式组织的主要成员,针对妇女的研究“要将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和社会文化中所确立的地位区分开来”。加拿大学者劳雷尔·博森认为“妇女对财产和住房的含糊权利,在限制妇女的流动性和使许多妇女‘嫁给农田’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学者杰华则重点关注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流动者,主要观测她们在流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以及这些经历对她们的女性认同意识、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产生的影响。现代女性通过提升经济实力改变家庭地位,同时婆婆的权威也随着父权的式微而下降。随着耕种的机械化,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增多,闲暇时间已成为影响她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如何利用好闲暇时间成为了当代农村女性发展的重要问题。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婚姻、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历来广受关注,但是农村妇女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公共参与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因个体力量的局限性,农村妇女难以与其他群体进行力量的博弈,出于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她们常组建超越个体力量的组织群体,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因一些特殊原因,多在私人和非正式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因而较少参与公共事务。非正式组织的主要功用在于提供社会满足感,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们对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基于此种诉求形成的一些组织亦逐渐增多。黔中屯堡的妇女们会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妇女组织,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以改变在村庄公共活动中的边缘地位,这事实上也是她们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行为。修福群体是屯堡妇女们在日常民俗生活中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她们亦借此参与到村中的公共事务中。
三、修福与民俗:黔中屯堡妇女公共参与的媒介
女性民俗作为一个概念和术语出现是在20世纪70 年代西方女性民俗学科建立以后,女性民俗被界定为由女性口头表演、物质创造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所共同形成的文化文本。后随研究的拓展,将女性民俗的范围从女性本身延展到了女性之外。女性通过自身的创造和传达,或者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均属文化范畴,由此女性民俗的范围亦可涵括女性之外的其他人的民俗。女性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亦是文化问题,“在诸多文化模式中,女性发展的社会条件也许不足,但其文化资源充分,女性照样能得到个人与社会皆相得的发展”。
修福作为屯堡社区女性进行公共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其意义与传统佛教修福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自古家族体系严密,女性在家庭中上奉父母、下育子女,承担着血缘纽带意义的女性如果专事修福,必然造成家庭结构关系的断层,但是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女性亦有修福的权利,佛经中女子出家最终成佛的故事不断呼吁着女性参与其中。洪武六年(1373) 明太祖朱元璋规定:“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屯堡妇女延续此规定,至四十岁方可修福,且修福的目的已然发生改变。在屯堡社区,无论祠堂里供奉的是何种神祇,均是屯堡妇女们心灵寄托的对象,每逢会口和朝山都会对这些神祇展开供奉活动。
调查显示,屯堡妇女修福强调实用性,旨在为自己修功德,希望在亡故后,能获得庇佑避免遭受磨难。如果不修福积善亡故后会历经灾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可以随意修福,修福程序亦有筛选机制,只有多行善事,多种善果,才能获得跟随佛头进行修福的机会。屯堡修福的实用性还在于所参拜的神祇多元,结合了民众需求与儒、释、道于一体的一种全神参拜的世俗化的修福行为。在屯堡妇女的福歌中,就有广成子、赤精子、黄龙真人、惧留孙、太乙真人等,甚至灶神、汪公、五显亦被纳入供奉对象的范围。屯堡神祇系统的发达,主要是因为过去屯堡男性常年在外征战,留守家中的妇女只能寄希望于神祇,祈求神祇护佑父亲和丈夫平安归来,在强烈的担忧情绪中,妇女们不论何种神祇都一并祭拜,在不断传承中形成了屯堡多神祭拜的现象。
从传统的修福语境来看,妇女修福更多的是为征战沙场的男性家庭成员祈福,而后成俗沿袭。《太宗永乐实录》载:“成之湘潭人,祖父操舟为业,往来江淮之间,遂居江都……破贵州洞蛮,克普定西堡,升昭勇将军贵州都指挥同知。初,大军征云南,成镇普定,搤其后路,蛮人无敢叛走者,升骠骑将军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大将军印镇贵州”,彼时贵州战事频繁,屯堡男性戍守关卡、浴血奋战,女子则居家养老、抚幼、耕种,将对丈夫或者父兄的担忧寄托在各种神祇身上,以获心灵的慰藉。
从现代修福的语境来看,修福是屯堡女性为满足自己完成家庭角色所承担的责任之后的社会参与感,这种参与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参与行为,是指“社会成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社会各种活动或事务管理的行动,是社会成员对公共管理中各种决策及其贯彻执行的参与,是对社会的民主管理”。也有人将公共参与定义为“通过利益相关群体的民主协商,通过群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和专家的辅助作用,使利益相关群体中的普通群众真正地拥有自我发展的选择权、参与决策权和受益权。”在屯堡,妇女们虽然也有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但都是一些零散、分散的个体,她们即使有意无意地通过日常生活,建构有利于家庭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也并未超脱出家庭或者是家族的范围,相反还依靠家庭或家族的资源去发挥其影响力。屯堡地域中男性主外经商贸易,女性主内耕种编织,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着侍奉老人、抚养子女、保证家庭生活正常运行的作用,而当家中老人和子女脱离家庭后,女性的生活则陷入无序状态,她们忧心于丈夫和子女,希望通过修福的行为能让家人健康平安。同时修福将她们置于除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有利于建构人际交往和增强女性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其修福的目的自然与佛教修福不同,呈现出“既没有忽视世俗生活的实在意义,也没有排斥神圣实在的超越性”。
作为修福组织的领头人——佛头,是屯堡社区中热心公共事务而不求回报的人,她们主要服务于村中的大小事务,在生老病死的各环节开展民俗仪式,协助处理村中祭祀祈福等礼仪,对增强屯堡社区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屯堡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的关键人物。佛头可与仪式先生在葬礼上为亡人祈福,正是这些祭祀活动的严肃性与神圣性,要求修福的妇女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修福活动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修福形式多元,有村寨内常设的会口,亦有外出赴寺庙朝山,正如修福妇女们所说,“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要摆上路符,我也修福,去坐忏、过河,一般逢会口就去”。修福手册中,亦明确了屯堡妇女修福的时间囊括了所有的节庆活动,呈现出月月修福的状态:“正月初九迎春会,正月十五是上元;二月初二龙抬头,二月十九佛法兴;三月里来三月三,三月又到清明节;四月里来四月八;五月端午值仲夏,五月有个单刀会;六月初六在乡村,六月二十四日正;七月月半河灯节,七月十五是中元,七月作会供财神;八月里来是中秋;九月本是重阳月;十月初一供牛王,十月下元做圆满;冬月十九进庙堂;腊月有个二十三,腊月除夕了一年。”
屯堡妇女修福过程十分漫长,仅是跟随老佛头学习念诵福歌都要长达10多年的时间,且必须在完成子女抚育责任后方可学习。天龙屯堡佛头罗某英学习念福就花费了16年时间,其间跟随老佛头在周边寺庙朝山拜佛,也时常受寨邻的邀请在葬礼上为亡人念诵佛经,唱诵孝歌。屯堡妇女修福的比重大,修福原因多样,罗某英因时常与丈夫拌嘴,老佛头了解情况后主动劝导其参与修福,既可缓解家庭矛盾,又可丰富罗某英的闲暇时间。参与修福后罗某英时常跟随老佛头去丧葬仪式上为亡人祈福念经,在丧葬仪式上念诵的经文与闲时唱的福歌不同,葬礼上为度亡经文,闲时唱诵的福歌则多以娱乐为主。福歌的唱诵并没有纸质文本作为依据,屯堡女性识字不多,修福过程中多是跟随老一辈佛头口传心授获得福歌内容,福歌涉及内容广泛,屯堡妇女依靠自己的兴趣和毅力将这些内容烂熟于心,从福歌中了解历史,求得真谛,获得内心的安宁。亦可说修福是屯堡妇女在课堂之外的知识积累过程,是屯堡妇女对知识渴求的一种潜隐体现。
受传统性别观念和生理因素的影响,屯堡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在农村公共活动中处于边缘位置,修福积善、互助和组织活动的规律有序,满足了屯堡妇女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她们通过修福行为,参加修福活动以及对修福制度的遵守,加强了彼此间交往,相互熟悉,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了亲密关系,这种内聚力使她们彼此信任,社会资本形成了增量。屯堡女性在修福过程中获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同时修福通过建构公共性给她们提供组织归属感,满足农村女性自我认同的需要,亦通过修福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协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四、修福与婚姻:黔中屯堡妇女自我价值的实现
传统语境下,屯堡社区主张“妇无公事”“六二为女,女居阴位,九五为男,男居阳位,象征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妇女的活动范围多限于家庭,较少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生存和生活依靠天气与人力,男性从生理上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家庭与社会的支柱,女性的价值自然被遮蔽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分工里。“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的有权支配年少的”,男女关系为主从关系,妇女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她们只存在于由男性所建立的、符合男性标准的关系之中,这实质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布迪厄也讨论了“妇女被排除出严肃的事情、公共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的空间”,性别是生物性的,社会性别是文化性的,因此性别的意义由社会所赋予,尽管社会各界在较长时间内主动更新既有观念,但如同威廉·奥斯本所认为的“文化滞后”一般,社会系统各部分的变迁并不同步,而是物质文化在前,非物质文化在后。要想重新梳理新的性别观念和话语系统,必须依赖于漫长而又复杂的改变。
屯堡福歌将屯堡妇女的行为规束在其规定范围之内,也规定着屯堡妇女的道德伦理。屯堡民间故事中,亦有对女性宣扬忠孝道德观念的内容,故事中的女性徐娴洁力挺丈夫杀敌报国,独自赡养公婆,其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以及对公婆的孝顺,是屯堡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映射,也在流传过程中对屯堡妇女产生着道德教化的作用。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别在于,强调“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并非静态概念,而是伴随社会诸要素的变化而不断解构和重构,当然,社会性别势必是诸要素的核心。社会性别认可社会分工的重要影响,强调文化传统的积淀,否认社会分工源于生理性别,具体来说,文化不同,性别观念亦不相同。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是隐匿的,主体性所体现的人对自我的认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性别主体和社会主体”成为了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性别主体是基于男女关系中,女性主体的确立,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需要肯定自己能力,脱离他者眼光正视自己。而作为社会人,女性的社会主体性,则表现为对社会的参与能力,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是女性价值的体现。女性的社会主体性和性别主体性是相互支撑的,性别主体的确立是女性主体确立的最基本的条件,社会主体的确立则是在性别主体确立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体确立的一种现实保障。
屯堡婚姻以“屯对屯、堡对堡、民屯对民屯、商屯对商屯”为主要的婚姻模式,村寨中姑表、舅表、姨表开亲现象普遍,这种亲对亲、戚对戚或世家通婚的婚姻关系,在屯堡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互助互动的人际关系网,将固有的信仰、民俗、习尚等文化具象相互影响相互聚合而保存下来。青年男女结婚前不可见面,也无交流,全由父母做主,无自由恋爱之说亦无选择之自由。屯堡男女的不平等性,亦可从屯堡女性的成长叙述中体现:
我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女子不准读书,也不能穿好衣服,多吃一碗饭都不行。由于我比较懂事,嘴巴甜,还得读了两年的书,日子好过一点。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不同意的,因为我老伴家当时兄弟姊妹多,有5个弟兄,房子少,条件很差,但是我的父亲同意了,因为家里是父亲做主,父亲同意了就必须要嫁了。结婚时我的丈夫穿的都是旧衣服,没有房子,现在住的房子是后面一点一点慢慢修建起来的。
女子不能读书,女子不能多食,女子不能穿好衣,这些都是胡某娥奶奶对孙辈女子的潜在规定。父亲拥有决定子女婚姻的大权,即便胡某娥的母亲在其婚姻中曾极力反对,试图反抗家庭父亲的权力,希望女儿能婚姻自主,但是这种反抗并未成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规定,将男女婚姻置于集体惩戒机制之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传统家庭组建模式的样板。家庭中的女性长辈在男女间的权力抗争中,站在了女性的对立面,这也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婆媳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奶奶这种极端的行为模式,是受传统观念的浸润所致,世代相传的习俗和道德束缚将奶奶形塑成为男性权力的拥护者和依附者。另一方面,血缘关系是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站队男性权力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女性长辈形成了既追求自己权力又处处压制媳妇的自相损害和作茧自缚的矛盾心理行为。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基于女性与子女的生育关系,教养孩子的责任大多都由母亲承担。在屯堡婚俗中,女子出嫁前母亲会赠予一句唱词,内容为“说话言词要谨慎,做事处事要细精。义方教子勤读书,孟母三迁是典型”,这是母亲教导女儿到夫家之后,行为处事要再三思量,教育子女是为己任,“家庭是最基本的教育组织,个人人格特质、价值观念与生活习惯大都在家庭中习得,父母是孩子的主要教育者和学习对象,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重要、最基本的学习场所。”屯堡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将子女的教育责任归属到女性身上,正如屯堡女性的意识里面,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是她们前半生的重要职责,她们须在老人身故和子女成人后,才能考虑自己的志趣,所以屯堡妇女修福多在40岁之后。随着新思想的进入以及胡某娥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对男性权威的挑战意识,她坚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希望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社会性别的规范在家庭关系中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从家庭角色的分工和角色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观测到社会性别规范的痕迹。如果我们局限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框架,就难以发现生活中的不平等,并将这些认为是合乎规范的现象。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去研究妇女问题,就要跳出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站在平等的角度去看问题。胡某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丈夫支持,改变了自己在家庭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也通过参与到村的公共事务中,争取了屯堡女性在社区自我价值的实现。男女平权的思想逐渐融进了传统家庭,正如她所言:“我和老伴相互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理解,才有了现在的生活”。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对女性的约束多于男性,且强调女性的“忠”与“孝”。家庭建立在血缘与婚姻的基础之上,以爱与亲情作为纽带维系家庭成员的关系,并非权力和利益,但是却源于血缘关系,建立起了长幼秩序,将成员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尊亲,以长为尊,以夫为尊,如《鲍氏家谱》有载,妇人以节为重,一与之齐,终身不改。
当然,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的观念必然会带来婚姻的不平衡问题,而男女相互协调、相互支持才是维护婚姻稳定的关键要素。传统家庭中,两两相互间的依从关系不断弱化和瓦解,亲子或顺父母的轴心关系转变成为夫妻轴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提高,甚至在家庭中拥有了决策的权力。如《汪氏家训》 所载:“(重夫妇) 夫妇,伦常之始也。以为续嗣计,古人重之。近世不明此义,以色为爱憎,以财为重轻,以妻家盛衰为进退,名教之坏,莫此为甚。吾族子弟,娶妇三日后,谒庙告祖宗拜父母,请族中尊长辈至厅堂谒见以后,一唱一随,不得视为燕昵事。妻非有可出之条,毋许斥逐。”
五、小结
在黔中屯堡社区,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女性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女性对公共参与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公平、正义、平等的期待越来越凸显。妇女们在修福过程中思想观念“不断地与活跃的记忆产生新的结合并被其掌握。随着在自由辨别的环境下对这一内容的吸收,个体除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之外,也获得了文化认同。”妇女修福伴随着文化记忆与文化自信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受到强化,前者为后者提供支撑,后者为前者提供动力。屯堡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已成为普遍现象,女性追求的权利已由想象变成具体。她们用语言在讲述着屯堡的民俗文化,用行动在践行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她们用擅长的方式表达着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一轮明月照纱窗,二树梅花满院香;党是红花千万朵,朵朵开来喷鼻香;秋风吹动人清爽,桂花开来满树黄;劳动人民一双手,创造人间幸福长;丰足衣食全靠党,科学文化谷满仓;党是红星天空照,跟着党走永不忘。
屯堡女性常在午后聚会时,以这种或七言或九言的押韵唱词作为交流的主要方式,讲述着她们对生活、对家庭、对国家的情感和希望,郑某莲的这段唱词是在采访过程中,临时创编的,她说我们不仅唱过去,还要唱现在,更要唱未来,要将我们女性心中的话唱给大家听,要将我们屯堡的故事传递出去。屯堡女性在过去的生活中坚韧忠诚,在现在的生活中自信昂扬,屯堡女性叙事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潜藏在日常细微之处,所显露的是屯堡人民对当下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