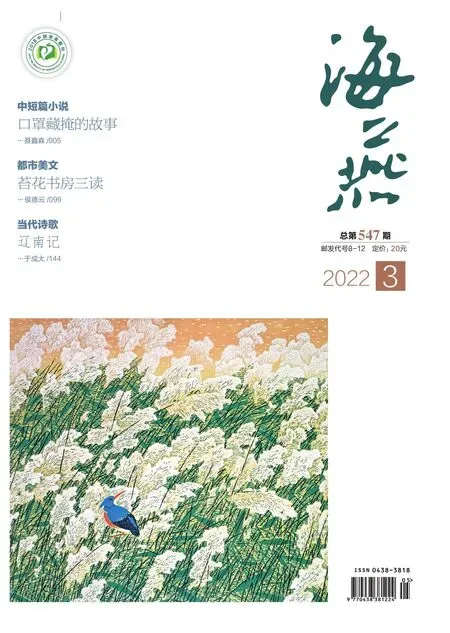引河街簿记
文 苏 宁
一
路和街是我生活中比较早就认识的两种事物。乡里人家,总是称门前可以行人、走车马的土地为“街”。而“路”,则是要比“街”更长、更通达。它存在的地方,可以没人家,没有热闹,但是,它就是那么鲜明地给予预示:可以让我们通过它走过去,走远。它有力,也更稳定。我居住这一带的人的概念,有“街”的地方,就是要有人、有房子和市场。而“路”所在的地方,可以什么都没有。路是有性别的,男性气质,可以是荒郊野外,可以无边无际。所以,它才可以被引义为方向、途径,和有轨迹、规则、律定之义的“道”连合使用。
而“街”是怕孤独的事物,喜欢有人、有物陪着。没那么博大,也不喜欢负载那么多精神和主义。它只是为某些热闹、繁华提供的一个场地,中间走车马行人,两边只陈列物质,要有建筑。
我有10年时间,周末除外,每天都从这条我要写的街上,走过至少四次:每天上午上下班,下午再上下班。
这条街,早就是水泥和沥青铺就的。又常有人修补,一直结实,耐走。可以用于步行,骑自行车,汽车也可以进出。在货车也可以进城的时代,它代表着城市的独特气质——无论下雨、下雪,这街都不会泥泞。不会让自行车滞陷骑不动,也不会让汽车的轮胎陷入泥水,要动用外力来推动它出泥潭。
我手中有一张这座城市30年前的地图。是几年前,在旧货摊上无意中发现的,一块钱买来。这张旧地图上,城比现在小几圈。街和路有很多,泾渭分明,很好认。连通东西者皆为路,某某路,名字标识清晰;贯通南北者,则称之为街,某某街,名字一目了然。
在这张旧年的地图上,我一眼认出我所住的街。这是一条可以通行人、车马的狭长地。关于这条街,我最早知道的名字是前街——这个“街”字,此地人读为gai。再早些的命名,是为丰登街。在这张地图上,它的标注名是繁荣街。它比丰登街晚一个时代。
在这座城市没有扩张之前,此地一些老人向我描述过这条街。它所在地带,50多年前,还属于城边角,全是平房。家家门口皆有小块菜地。还有在家门口种一畦小麦的。
此城在平原,乡民食物谱系中亦多爱小麦制品。多年后,我曾在一位很年长的女邻居的阳台上,看到几个花盆,这花盆中并无花草,种的都是小麦。这小麦种在花盆里,每年也结不出穗子,但她就是把好好的花盆种了小麦。
她说,她只是受不了一年到头都看不到小麦那种“青”——她比划了一下,“那种。”好像颜色可以通过手势演绎出。所以,她年年要种几盆小麦。只是为了看它在花盆也会萌绿,绿得和长在田里的小麦没有区别。
有几年光景,这街旁边修过一条小渠。据说想引古淮河和里运河的水进城。所以,为了吉庆和修渠引水工程的顺利,此街被更名“引河街”——过去年代想生一个男孩的人家,往往会给上面的女孩起名招弟,这街的更名也运用了这个民间理论。这使它因此有了民间与家常的意味。
只是后来,这渠不仅没有了水——水无论从古淮河还是里运河引来,都有太远的路,太消耗资重。兼之它渐渐被扩进城中心部位,“地皮”稀缺,渐渐又还水渠为马路。
越来越多的人住到这街边,街更热闹了。
我所写的就是这一条街,城市从此处开始生长。
二
几十年前,牵依围绕这条街的,只是城市近郊一个小村。当时名为“革命生产大队”。改革开放之后,城里四处贴上主题词为“繁荣经济”的标语。如何落实到行动?“革命村”更名为“繁荣村”曾是具体举措之一。
这个一直种着油菜、小麦,四处是稻草苫着房顶的小平房的地方,30年之后,渐渐上升为一个城市的中心部位。
先是泥草的平房变为尖顶的青瓦红砖房。上世纪80年代末,各家门口蔬菜和麦子都不许种了。划出土地,建起工厂,盖上楼房,升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工业街区。服装厂、机电厂,在这一带建起来了。但彼时巷陌间的平房仍依稀可见。
又过几年,很多人家翻旧屋为2层小楼。那时这个城市最高的楼房只是6层。又过10年,到了90年代中期,城市开始大规模拆改和动迁,那些新盖的也就十多年的2层、6层楼房,几乎一夜之间被齐齐拆掉。几乎连夜就打起地基,没多久,原地盖出了更高的房子。20世纪末那几年,20层的楼房在这条街两边一年就盖起了好几栋。
高楼省土地,那省出的土地,却也没有种回蔬菜和麦子,又渐渐地全盖成了房子。
街两边从前的人家,都搬到高楼里住了。有的也就此搬到其他街上。
街两边一齐开发出的房子,全是用于卖商品。
这些房子归谁所有?当初买下这些土地的人,他们负责卖房,有钱的人家皆可来买。那时,房子有了新身价、新命名,街边一色的新房子,被称为“商品门面房”。由于这条街已经是城中心街,两边的房子市值不同。第一二层,不作为住宅使用、出售,用于陈列商品、售卖商品的店铺,简称“商铺”。
这条街改造的初起之意,就直向“商品街”的定位而来。一座城市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商业呢?商业比之于其他,更指向城市的灵魂。
不知是谁的起意,更“引河街”为“女人街”,即女性商品一条街。新版地图在这些房子没盖好之前就已经印出来了,这条街在新地图上的名字为“女人街”。但这一城的人,并不认可这名字似的,仍呼它为“引河街”。
三
我决意搬离。第一个原因,是不满意开发商置换给我的新房间,在一栋有电梯的20层楼房里。我喜欢的房子,不是一个只是盛装肉身和肉身所需的场所,一个有界限的凌空的方块物体。
这个方块,不管是正方,或是长方,都不是问题。我的问题是:在它之上,不能总是另一个同样的物体叠压着,而我,也如此叠压着另一个方块。或者这样表达:我的房顶是另一个人家的地板;而我天天所踏的地板,是另一些人头顶的天棚。
我不在意一座房子的封闭感。虽然高层楼房有以我们肉身之力爬不出去的窗子,有坚固的护栏,绝对可以为生命和日常生息提供庇护,可以遮风挡雨,可以住得很安全。
我在乎的是,推开门,头上可以看到天空,这天空就在我头上,是我的;我脚下能踩踏到泥土,这泥土抓起来有可以春种秋收的踏实。我不止需要房子,还需要一小块天空和土地。
然而,在这个改造建设中,以前那种6层以下的房子已经不再有了,都是20层以上的房子。6层以下,被重新定义,叫多层;6层以上,定义为高层。
这是我半生以来亲历的大事之一:突然经历了一条街上所有门楣都被更改。
伴随这条街更改名字,它的功用也在发生变化。
这街面上的陈列,曾经只是物品,一些植物。作为一条街,它对任何一个从这街面走过的人都无情绪。它是日常生活的正面。它对人的故事没有好奇心,它知道每个人面对生活都会有不同。
它也不好奇每个平凡的人——如何度过在外人眼里不同的一天。它只是一条街。很多人曾在这街上游荡。
某个瞬间,是否来了一个人,想从这街面深入世面的褶皱?自从这条街忽然更名,我变得敏感多虑,每次经过这条街,心里就有无数的绒毛、触须长出来,这绒毛、触须伸到了街上……
四
这条街生长的第一阶段,是店铺们午夜时分也不歇业。每间店都希望能因为开业时间长而多卖出一碗粥、一件商品。更多、更闪耀的路灯,直直地排下去,一起亮向又一个天明。
一个曾经小而安静、过了午夜就半城漆黑的城,忽然有了“不夜”的标签。
没有车辆往来,没有灯光闪耀的店铺,没有那么高的楼,只是平常人的生活场地,日出而作、夜来关灯睡觉——这样的街,被我们丢弃在身后。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城市,在一些国家,一些异域,看到了更多式样的街。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对于一条街的状态的意愿,只是一个符合世俗生活所需的定居之地。但城市需要的第一要素是结实丰富的物质。成为一个更大城市的首要特质,是物质,是不熄灯火与汨汨地来投奔它的人。
这条街在百年之前,在它还叫村的时候,这儿全是平房。彼时水泥珍贵。为了让泥结实,往泥里掺的是上好的糯米熬的浆。房子是石头、泥、木草盖出来的;房梁、门窗、桌椅,是木头的。彼时家家种树,一为盖房,二为做箱做柜,所以,没有哪家房前屋后不种树的。后来它被纳入城市中,我住到这街上时,正是这街处于城中心区向商业区进发之时。这城里,再无以“村”称唤之处,开始以某小区、大院称之。
五
每个城市,都有过这样一条街吧。稳稳当当,在城中心部位。根深蒂固,让年轻的人也能继续踏实笃定地住下去,比图书馆、博物馆更深入人心。
这条街上,五六十年前种的梧桐树处处可见,一年年长大,很多树就是一户人家的门口,这门口是许多小孩子的记忆。那时这条街,只是普通人家的住地,也没有那么多做生意开店的。
这条街,也有旁系,两旁边曲曲弯弯伸出一些小巷,卖菜的,理发的,卖小物品的,夹在其间,只要有钱,采买日用所需,也只是开门就可以办到的小事儿。
住这街上的人,二三十年的住下来,自己从没觉得这住的房子有多金贵,只是一天天地积攒出生活的便利和从容。当这条街被开发商和政府重新开发——那时,房产开发商是一个新出现没多久的词,也是一个新行业。三百六十行之外的新业。四处变旧房子为新房子、四处盖房子的行业。
那售卖房屋的广告册页,房子还没拆完就开始发了。在这条街上的人还没醒神或更新认识时,这条街,街边重新翻盖的房子,街上的商铺,一夜之间售罄,这是十几年前的真实事件,地产业辉煌闪耀的时代。
这条街的改建,是这个行业在这座城市最轰动的一次亮相。
这个胜利,激发了更多阶层向房地产业进军的信心,更多人加入进来。那几年所见到的局面,一是这些商人更加努力地买地、盖房,和政府、土地持有者、银行亲密对接;二是这城市中原有一些街区都在被重新规划,大面积拆迁,并向空中拓展空间,使有限的土地展现更多价值。为使土地增值,把教育、学校也联系起来。最先贵起来的房子,全是优质教育资源所在地。儿童入学政策里,是按常居住地的房产证报名上学的。
为了让孩子读到一个好的幼稚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而不惜在好的学区重金购买房子,这种选择逐渐多了起来。
土地资源从来不是无限的。土地从来不是某个群体、某个类别可以向它任意索取价值的。它所能循环无尽地给予的,只是春种秋收。只是年年的对于养育生命之物的呈现,而不是其他。这个城市,在第一波大规模拆迁改建的浪潮之后,开始分批地甚至是悄悄地将一些优质幼儿园、小学、中学搬家,或建立分支机构、分园、分校。没有条件建新的,就将一些原来所有的幼儿园、学校名字去掉,改为某某分园、某某分校。以此为策,一波波新的土地,得以快速进入有活力的增值范畴。
因而,这样一个僻静地、只是在每天的日升月落中过着小日子的四线小城,被这样的经济发展思潮裹挟着,一圈圈向外围伸展。
10年前,在地图上,看它和比邻的南京城的距离,还是240公里。10年后,在一张新地图上,只有170公里的距离了。
20年前,这城里普通住房的价格,每平方米大约三五千块钱,商铺大约是10000元左右。彼时猪肉价每斤四五块钱。
30年中本城发生的大事并不多,第一件大事就是这城里,大多数房子有了电梯。总高五六层的楼房,早已成为稀缺资源。至于那平房更是见不到了。低层住宅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六
因为我的旧房子被拆——那旧房子,是一栋5层楼房的5楼东首,8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晴天早上,太阳直直地从玻璃窗透进来,地板都晒暖了。雨天,雨水落在窗檐上,落了多年,那窗檐也没损坏。
那些年,我从没有再去买一个房子的想法。有了住处,不就是会住一辈子,一直住到老吗?我父母那一代对房子就是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他们没有对我说出过。可我,就是有了一间屋一世就已安顿下的理念。我也偶尔存钱,分类存:旅行、给长辈、教育经费。我能存下的钱,一直分这三类功用。
我的房子,是住一百年也不会有问题的。记得我刚住进这房子时,因为看到房子的墙壁不是那么厚——这座城市处在秦岭淮河一线,气候亦南亦北的结果是冬天全城所有房子都不供暖,夏天却比北方晒。这个厚度,远没有北方房子的墙壁厚,所以我不确定它是否夏天隔热、冬天隔寒。
家人也看出了这墙壁要比北方房子薄一些,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钉锤,敲了敲墙壁,说:“再怎么,从现在开始,住一百年没问题。”
我算了算,那时我已二十几了,再一百年——那一定够我住了。至于我的子孙,他们长大自然要分家出去自己过。他们长大的时候,也还不够一百年。这一百年,够他们长大再出去了。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喜欢起这个房子。
可是,我才住了10年。既没把它住坏,它也没有在风水上隐现不吉。我很爱惜,不停地装扮它,擦洗它。虽然它没有特色,甚至千万屋一面:我理智地看到了这城中的房子,几乎每一栋都是一张图纸所出,一室、两室、三室。在任何地段、小区,都是一样的风格,好像这城中只有一位建筑设计师。
后来我去一些其他城市,也特意去看建筑,感觉很多城市好像都用了同一位设计师的图纸。
在这种“同一”或者是“抄袭”和“模仿”中,在某些航班上,我会从舷窗上细看经过的一座座城市,一簇又一簇雷同建筑的组合,一片又一片灯火闪亮的街区的交错与相融,确实都是一样的。
所有城市,都在高空之下、远距离中模糊了特质——如果存在特质,我指的是一座城市应由有丰富个人气息的各色物质与精神集合。有鲜明的地域面貌,有被不同历史文化折射出的光影,并由“人为”把这些独特一代代地保存下去,而不是越来越趋同。
是城市居住建筑追求实用甚于追求美吧。在早已放弃了传统建筑材料时,也放弃了那种对细节的修饰——在建设的潮流中,我熟悉的成屋过程中的各种仪式,也不见了。
某一天在街上,我忽然觉得这城市真的是缺了一些自然气息时,我找到了真正的源头:这城市中所有建筑,不再是用有气息的草木、泥土、沙石建构。只是钢筋,只是水泥。坚硬和板结之物在日积月累、触目惊心的堆积。很多东西囤压其中,难以被肉身唤醒。
城市建设中,首先牺牲的——就是个人对于一座自己向往的房屋格局的设想吧。诗意与美好栖居的实现,要跨越的事情越来越多:规范、法律。无法通过和实现的审批。
虽有种种不好,亦全无个体风格,但也总是我住久了的、住进来就没有想离开的一个房子。才住了10年,被告知,它要拆掉。
前面提过,开发商说可以换给我的新房子,我并不喜欢。它在十几层——那么高,虽然即使天塌下,上面还有房子,即使地陷落,下面也还有人家和房子,可在我,总是不喜欢。从前的5楼,已经是我对高度的接受极限了。我总是到了高层住房,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就来了。没有安全感,失去屏障和依靠。不敢从窗子向外和向下看。不敢去阳台上走动,更别说每日去阳台上行晾晒之举了。
我的家人并不赞同我的想法:你以前的房子,也是多层,你住了10年的5楼,你就是上挨着天,下挨着地了吗?
后来是,我固执地不惜反抗家人集体意见,草草收了开发商的补偿金,四处去找新房。
七
彼时,这城中还有不少在卖的新楼。有一次,售楼的姑娘在我两次看房却没有说买时,有点生气,婉转问我,是不是资金有问题?
我直言:“这房子有缺陷。”
这姑娘却继续说:“可以贷款,还可以打折利率……”
然后,她取出一张省钱表。
这边却看也没看:“不要。”
那一段,心气确实不平,现在平复了,我也仍如此回复那几个我没买的房子的卖家:房子有缺陷。
我住的那种6层内的房子,都早已经被拆得不剩几所。想在城中心重置一个楼层不太高、不需要用电梯的房子,一是房源稀缺,二是即使找到也不会是新房,又旧又潦草,说不定买下又要被动迁。而高层中6层以下的,楼层看似符合我的想法,可我仍无法接受好好的房子被植入一部电梯。
电梯于我,也是没安全感的存在。
现在的楼房,最显著的设施,是有一部电梯。没有电梯,每日如何数次便捷地回到自己的家?
这是一个费体力和时间的问题。一部有电梯的房子,一格格地隔出一户户人家,通往外部世界的,除了被钢筋铁网罩个严实的窗子,就是门和一部电梯。
时间成本的消耗也恼人,再也不看了,直奔郊区去买平房,四家一排的两层楼房。然后,才开始计算路程。第二天,骑自行车从新房子到单位,单程50分钟左右,完全可以接受。然后,又开车一试,不堵只需20多分钟。
彼时,这栋房子几乎是在这个城的最外围。
我买房时,在城中心区域,所有的老式平房都拆净了。之所以有这样的低层,因为这块地在当时几乎被认为是乡下,被一开发商买下,建了这样一个低层楼园区。
前面说的不喜高楼的各种原因之外,直接的潜意识是:想离“地面”近些。
这城中,没有一寸土地的功能属于种植,在土里种一棵树或者一株花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我潜意识里可能就是想,只要离地面近些,就已足够好。趁我有这个想法时,尽量实现它。
我的小孩,或者将来的其他人的孩子,他们即使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某一天,回忆中,要有这样一个关于上一代人生活场景的印象。再下一代的人,能像我一样,经历居住房屋的三个时代是不易的事件——从砖石草木的平房,到多层楼房,再到三四十层高的高楼。
很多孩子出生时就住在十几层高的房屋中,对于泥草砖石的瓦屋,也许只是某次旅行时的一次遇见。
生活中怎么可能不经历这样一个场景:一张床直直正正地放在大地之上,那样稳妥笃定。下了床,最好是一夜醒来下了这张床,推开门,哦,外面满眼是直接的大地。大地上的一切直视可见,草木、花朵。关了门,再回到房中,那些屋外的事物,和自己也是没有一点隔膜的平视即见的距离。下一代人,是否没机会经历这样的生活了?
这样和自然相见的场景,平凡、安定、家常,在城市所急需的发展中慢慢被放弃。当所有的院落被简化,所有的绿化也一致,再无门前的一小块田地。前面说的那种平房,有一个门口和一小块田地——散漫地想种点什么就种点什么,想不种什么就可以那么凭空搁置。任杂草丛生,露水、清霜下来,不管它是落在了好花好叶上,还是杂芜上。
在新城市人看来,也许那些新楼显得更好看、私密、实用,不像之前那样一开门,谁从自己门前经过就可以望清门里所有的局面。也许人类至今对自己的每一份了解里,都放进了期待改变和进化。城市孜孜不倦地扩展、改变,总是没有能和这种心灵困境与难局有过正面交锋。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种种件件都在被发掘出前所未有的价值,被赋予从来没有想象到它可以有的意义。
它和自然的关系,因为渗进这些千丝万缕的隔绊——这一点小小的隔绊,或可说成是对城市功能认识的不同。或许,也可说是各层之间产生了认知差距。这种结果,就像新摘好的菜——摘下了,只是多在太阳地里放了那么一会儿,然而那最终呈现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八
前几天,我开车过引河街。看到一辆运菜的车子,后面小小的字:金圩村。
这种运菜的车子以前常见,居然没被杜绝,也算是稀缺的惊喜了。“金圩”是郊区的蔬菜种植村,名字还没被改掉,我也觉得是奇迹。
街口坐下。一个小孩正在那儿剥花生吃。可能是某个店家的孩子。
“告诉阿姨,花生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超市。”
“宝宝中午吃的菜哪里来的?”
“超市。”
“宝宝吃的饭呢?就是米。”
“超市。”
“那宝宝知道超市里的花生从哪里来吗?”
“花生妈妈生的。”
“花生妈妈在哪儿生的它?”
“树上。”
“……”这孩子的话让我笑起来。我抱起她。“你怎么知道这些?”
他并不回我,也不认生,继续把一个花生放进小嘴里。
“绿的东西都是树上生的,果实也是树上生的。”他说,有点害羞,但也很笃定。
“树在哪里?”
“在街上,还有我奶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