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胜业,不欲暂废
周明全

2022 年7 月23 日早晨8 点,睡梦里接到快递电话,懵懂着下楼,快递小哥将一个暗红色的包裹递给我,上面“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几个黄色大字在晨光里显得格外耀眼。虽然几日前,我已在招生网上看过通知书的版样,但当实实在在的通知书递到手上,内心还是欢喜异常。
不久前,一位非常爱惜我的长者知道我准备考博时,对我说:“你混得还不错,完全没必要去折腾了。一个学位,对你不是雪中送炭,甚至连锦上添花都不是。浪费时间去读书,会影响你进步的。”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告诉他:“我今年42 岁,老大不小了,不想再在安逸的生活里、在所谓的成功中迷失和放弃自己。读书和写作之于我,是我生命的真爱。”
一
我出生在云南曲靖一个叫色格的小山村,祖祖辈辈和土地以命相搏,是土里刨食的农人。在我的父亲4 岁时,祖父在井边饮水,意外溺亡。三年后,祖母病故。自此,成为孤儿的父亲被大伯家收养。父亲一生胆小怕事、沉默少言,这都是幼年失怙给他内心留下的伤痛所致。我的母亲却是见过世面的,很小去到县城里帮兄长领娃。等孩子大了,又返回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最终下嫁给我的父亲。一个见过世面却不得不返乡的女子,其内心的不甘也许无人能懂。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虽自小调皮,却最能懂得母亲。三兄妹中,我和母亲的感情最深。母亲苦难、辛酸却坚韧的一生,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多年后,我读到一句诗“一棵树浑身长满翅膀却不能飞”,心一下就被刺痛了。我觉得,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浑身长满翅膀却不能飞”,只能扎根在泥土里的苦命女子。
从文的人,或许都深受过自己父母的影响吧。在这里诉说我的家事,是想说,我的性格像父亲,一切事都拼尽全力去做好它,且要今日事今日毕——作为孤儿,只有将事做好,才能立足。不过我似乎更多地还是继承了母亲的遗传。母亲从小就给我讲述城市的生活,对一个山野间的孩子,它是有着巨大吸引力的。因此,母亲对我的学习也要求苛刻,她希望我们兄妹都能走出大山,摆脱土地对我们的束缚。我1980 年出生,当时已开始计划生育,我属于超生,家里被罚款,后来土地承包,也没能分到田。老家人叫超生的孩子为“黑人”。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断地告诫我:“你可是没有一分田,不读书你没法活啊!”
就这样,读书进城似乎成为我唯一的出路。我知道,这其实也包含了母亲自己对城市的向往。她无疑是对的。人本质的追寻,是让生命愉快。农人的苦楚,我是有体会的。那种一厢情愿地将农民描写成打死都不愿脱离土地、固执地热爱土地的作品,其间似乎有些幼稚和浅薄。做文学研究后,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想法——人,不能做土地的奴隶。那种对农民固守土地以力相搏的生存的歌颂,不能让人体验到生命真实的美感和高贵。
勉强考上高中之后,我来到了县城。一时间眼花缭乱,鬼迷心窍地突然对绘画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情,在县一中追随绘画老师学基础素描两年,但专业统考却考砸了,羞愧中干脆放弃了文化高考。在母亲的苦劝下,我又狼狈地进了高考补习班。天意弄人又随人,结果当年高考专业分、文化课分远远超出本科线的我,却未被第一志愿录取,莫名其妙地去到本省的一所州市院校。巨大的失落让我沮丧,意却难甘。
挫败感伴我多年,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的性格。大学几年,我荒废度日。不过竟也是失之桑榆,居然爱上了文学,疯狂地写下了大量诗歌和小说。今天回看当初写下的诗行,那种对现实的迷茫、对寻找出路左冲右撞的匪气,仍然让我久久难以释怀。曾经和我的一个朋友讲起这段不堪的生活,我说当时若有引导,也许我真的就成了诗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受困于生活。在无处可逃的2006 年夏天,无意中在书店看到老村的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老村讲述了家族史、个人艰难的成长史、自己的小说美学观,以及长篇小说《骚土》被忽视、被埋没的痛苦。那种底层的色彩与其时我内心的失败感高度重合,从此我将老村引为知己。失败者通常只有在失败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抚慰。
后来,我又读到陈思和先生的著作,也有幸结识了先生。先生对我,有若精神上的长辈,让我犹如沐浴在春风中的童子,为人为文,似乎找到了家园。然而最初的文学启蒙,还是从阅读《吾命如此》及《骚土》开始的。老村给了我一个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有情绪、有对抗、有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执着和探寻,有在命运无情戏弄下生命的坚韧和坚守。
回想30 岁前后的那几年,总感觉个人的渺小与卑微。正是那段混沌不安的时期,在与老村相遇后,我终于在阅读里安顿了自己。也就是说,年少时,母亲给我的身体指明了出路;30 岁后,我为自己的心找到了出路。我明白了,人生所有的血汗之苦、血泪之疼,只能用生命去体味和消化、抗拒和吸取,别无他法。每个生命,只有自己走过所有的欢快与苦难,才能够称得上是生命的自身。而读书,无疑是生命从无知到有知的最好陪伴。否则,真的是白活了一生。
二
2010 年10 月,时任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大伟先生大约是看到我爱读书的缘故,将我从报社调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也是在这一年,我的宝贝女儿出生,初为人父,欢喜异常。自此工作身心,似乎皆得安顿。
这些年,也总是在关键处,得到刘先生这样的兄长们无私的提携,才使我有了更好的读写环境与机会。刘先生早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后从军八载,转业至云南省委宣传部,后又辗转到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云南出版集团,最后落脚出版社。他时刻手不离书,信奉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做人中正坦荡,一心谋事做事,了无私欲。我在他身边工作六年,耳濡目染,深受影响。现在,对很多事、很多人,都能包容了,这都和刘先生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染有关。近年,他沉浸在老子研究中,颇有新见。我一直鼓励他将自己的研究写下来,但他却迟迟未动笔。后来读到陈思和先生谈傅雷时说,傅雷的“德行”胜过了“言行”。知识分子与他所处时代之关系,不能仅仅以“言”的多少来论定其价值。我释然了,似乎也懂得了刘先生为何在经历了世事苍苍之后,如此用功地研究老子,或许他是借对老子的研究,来探寻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如何与时代相处之道吧。
我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最直接的缘由大概是2011 年冬单位派我到清华大学参加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班上,我结识了一位名叫刘涛的青年批评家。他广博的阅读、深邃的见解,以及说话时慢悠悠的样子,让我欣悦。我想,如果自己搞文学批评,或许也不错。几天后,我去到老村位于北京郊区的家。老村为人朴实,见面即熟,其热情的接待让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颇为感动。激动之下,我居然张口说要写一篇关于《骚土》的评论。从北京回来后,我边阅读边思考,心想自己说出的话,总要兑现才好。然而写评论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从没有过的经历。过去那些所谓的诗歌写作,海阔天空地胡乱发挥便能凑合过去。评论就不那么简单了。评论要说理。我怎么才能说明白一个道理呢?我想到的是老村和《骚土》的命运,顺着这个思路,写了下去。写了删,删了写。终于在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可以无视,不会淹没》。在时任《名作欣赏》副主编古红卫的举荐下,稿子在《名作欣赏》2012 年第12 期上刊发。
我对“中国小说”的理解和阐释,基本上来自老村《骚土》为我提供的美学经验。可以说,是通过对老村创作实践的理解研究,构成了我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兴趣,甚至也构成了我今天的小说评论方式。坦率地说,作家老村,按当下的文学名望来排序,前三百人里也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他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骚土》既平静又朴拙的叙述、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之美,直接影响和启发了我对传统小说美学的研究。现在的一线作家,无论写什么,身后总有一堆批评家发声,热闹非凡。大概我也是地处偏远,又喜欢安静,所以更愿意去关注那些边缘或边远地区的,或是只愿沉浸在自己艺术世界里的作家。几年前,我读到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主人公在垃圾场工作,每天开着巨大的机器,将成吨的纸质垃圾推去焚烧。他从这些垃圾里翻检读书,有着非同寻常的发现与喜悦。我想,这似乎也是我向往的境界。是的,现在的图书是太多了些,而那些像金子一样会闪光的文学,却深埋在沙土里。
在《骚土》的研读经验里,我开始专注于中国古典小说。这让我感受到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些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让我穿越时代的尘埃,仿佛进入到历史的写作现场。在那一个个和当下相隔久远的写作现场里,我看到当时的一位位写作者在各自的作坊里,就像汉语的工匠,对自己的“手艺”无比用心、孜孜矻矻地斟酌每个字、每句话,孤独而卓绝地精心制作着自己的语言工艺品,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开拓着一门后来叫作“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看着他们流传下来的“手艺”,我感到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如此高级、细致、优雅、微妙和完美。用学术的说法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在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审美风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和西方源自史诗的小说传统判然有别。晚清年间,西学东渐的潮流加速,小说艺术亦如此。“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百年间,中国小说的写作者们大都以向西方小说学习模仿为要务,对西方小说技艺尤其是对西方小说现代性的学习,灌注了巨大激情。这种学习的激情,如今依旧延续在当下中国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中。而在这种学习借鉴中,中国古典小说自身的叙述传统、美学特质,这门如此精致、高级甚或伟大的“手艺”,却被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了,它的高贵传统只能在极少数的优秀写作中得以存续。
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中,我切身感受到,昔时的中国小说家从不玩弄那种故作深沉、让人看不懂的东西,而是从看似简明的叙述里隐藏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得之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早熟,让我们古老的小说先辈形成了深具东方特色的、对世界和人生独特的领悟方式和表达特点,而这也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特质。这种特质,在我看来直指人心,简单而博大,也是我所理解的小说美学的极高境界。
这种美学境界,我把它理解为一种深邃的混沌之美,它含而不露地描写世界和人生的状态,包含有最深沉的智慧和最美好的情感。这种独具东方和中国特质的混沌之美,画家黄宾虹先生将其称之为“内美”。在我的阅读感受中,从《山海经》到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四大名著,等等,几乎都呈现出这种名之为“内美”的美学大气象。我想,在当下的中国小说写作中,这种“内美”不能缺席。一部文学作品,假如能将这种“内美”和当代小说美学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理当期待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作为一位批评家,我也愿为这样的作家和作品鼓舞与欢呼,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根据多年对传统小说的阅读,和对老村,以及此后的格非、金宇澄等当代作家的阅读,我个人认为,应对“中国小说”进行重新命名。只有对“中国小说”的叙述系统作出精要的阐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所以,我在《“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一文里写道:“‘中国小说’来自历代文人的叙述实践,自成体系。不对‘中国小说’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评介当代中国小说的地位,不能认识‘中国小说’之于世界文学的独特性,也会让中国小说的写作者在膜拜西方的道路上迷失自我。”当然,我不是说对西方小说的学习和对现代性的追寻就该放弃,这两者并不矛盾。随着近年小说写作中出现的部分作家对腐朽价值观的歌颂频频发生的现实,我觉得,对西方现代派小说进行客观的把握和辨析,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文学在晚清至20 世纪30年代,虽经历了时局动荡、“五四”的否定传统,但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又都浸泡在传统文化中多年,他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传统的血脉,又加之他们大都远涉欧美、日本,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中西两种优秀文化的养护下,自然能自成一体。但此后,这股清新之风因战乱等缘故中断。80 年代,国门再开,魔幻现实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干扰了现实主义的方向。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一度使得中国作家们几乎全军迷失其麾下,逃避现实、逃避焦点,竟成为一时的写作风尚。作家们再也没有热情去接触现实,对普通人的生活不感兴趣,百姓的柴米油盐的日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见不到了。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品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红楼梦》也概莫能外。没有俗世的悲欢离合、渔樵闲话,没有普通人的跌宕自喜,哪还有什么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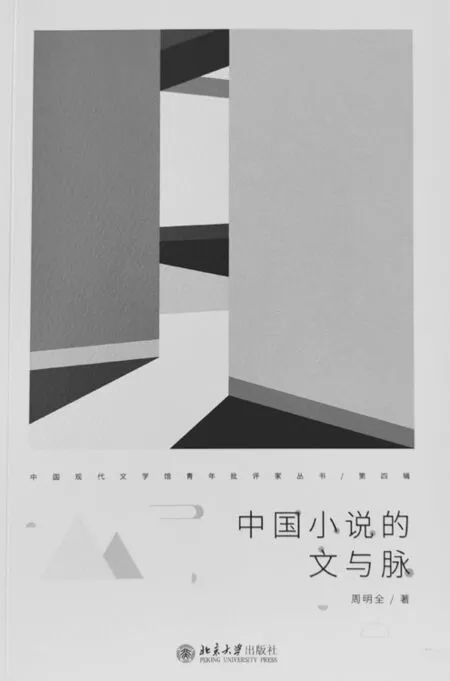
周明全:《中国小说的文与脉》
夸张、变形、寓言化的描写,严重地阻碍了现实主义的发展。文学对生活的关注力度和深度开始下滑。我想,魔幻现实主义并不坏,但它不该成为主流的审美状态。它不是增强了文学的批判力量,而是极大地削弱了它。像30 年代那一批能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魔幻现实主义给了不少中国作家编织想象的武器,却解除了他们对现实思考的武装。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讲新文学时有个很精辟的比喻,他说:“有意思的是喝过新文学之酒而成醉翁的许多人,只喝一种酒,而且酒后脾气很大,说别的酒都是坏酒,新文学酒店只许一家,所谓宗派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由此生出的先锋文学,使得许多中国作家沉醉其间,完全忘记了我们传统的这坛老酒,刚喝了几口洋酒便自鸣得意,以为自己真的懂酒了似的。
自2012 年4 月始,我先后撰写了《可以无视,不会淹没》《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等文章。2018 年开始,受《小说评论》时任主编李国平兄之邀,在《小说评论》上开设专栏。当时国平兄征求我专栏名称时,我说就叫“中国小说”吧,这使得我有机会系统思考中国传统小说。虽然很多想法还不成熟,写出来的文章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将努力去阅读那些被遗忘的古典,认真地去思考它们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
2019 年5 月,我的第一批对古典小说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小说的文与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荣获了在业内知名度、影响力较大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20年更名为南方文学盛典),授奖词写道:“周明全的文学批评,感情充沛,潇洒不羁,放胆为文,直白其心,而他又有格物穷理、小心求证的执着与耐心。2019 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的文与脉》,在古今、中西的对照中,重申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辨析当代文学的优长与不足,也探寻写作多维度的价值与意义。他的论辩,貌似复古,实为开新,始终保持锋芒。如何实现传统、学问与生命的相互照明,往深邃阔大处前行,周明全有其独特的取径。”这个授奖词出自著名批评家谢有顺之手,写得才华横溢。我把它理解为是有顺兄对我的勉励。虽目前能力不及,但心向往之。
如今,老村从喧嚣的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陕西澄城,在山水之间探寻中国绘画的神韵,由小说转向绘画,亦是在追寻传统在当下的意义和价值。只是这几年受困于疫情,见面交流的机会很少了。我也因为各种忙乱,暂时从古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中抽身。幸好2022 年7 月,百花文艺出版社接手了《微型小说月报》,负责人徐福伟兄找到我,让我根据自己对古典小说的阅读,选择优秀的文言小说并作解读,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创意,遂欣然领命。昆明的夏天,今年出奇地热。我独坐在书房里,翻阅那些先人留下的作品,内心清凉无比。我满足,但也时而苦笑,感受读书在幽深僻境里那种独享的愉悦。
我的学术起点低,后天营养也不良。这些年来,虽然始终在努力,每天坚持阅读,按自己对生活和时代的理解,尽量去做事,但还是觉得知识结构有问题,遂在2019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招生的作家班,跟随著名批评家、诗人张清华读硕士。这三年,在清华师无微不至的教导下,虽愚钝,但仍学到不少知识。

本文作者与张清华先生合影
清华师身上有一股酣畅淋漓的才情,具有丰沛情感、敏锐洞见,以及深邃哲思的气质,文章少有学究气,而且敢于对自己欣赏的作家、作品下判断,这在学界是非常难得的品质。同时,清华师是一个诗人,鲜活的诗歌语言中蕴藏着对人世丰沛的情感和敏锐的洞见,能将两者拔升至文化层面的哲思。这些尚属知识层面,更彰显他人文情怀的是一次在课堂上,清华师讲到一位诗人的作品和际遇时,忽然声音哽咽,转身掩面而泣。这一“泣”,让我百感交集;这一“泣”,也让清华师那种高尚的人格永远屹立在我和北师大诸多学子的心中。在北师大期间,能得到清华师的指导,实属人生一大幸事。在论文写作时,清华师多次致电,和我沟通论文的写作,让我受益匪浅。人生的路还很漫长,在今后的道路上,我将时刻谨记清华师的教导,认真读书,认真做学问。
三
相对于古典的研读,我近些年也对当代批评家的批评状态发生兴趣。这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批评家作为文学研究者,反而在文学史书写中、在常态化的研究中被忽视。我看过很多版本的文学史,只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批评家开设专章展开论述,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对现代文学批评有所涉及,其他的即使有,也只是作为文学运动或思潮的附带物,论述也很单薄,偏重知识介绍;二是我始终认为,只研究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和文学制度,对整个文学发展的研究,还显得不足,至少不完整;三是我更喜欢作“人”的研究。与那些优秀的批评家、学者面对面交流,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之所以作批评家研究,亦是机缘所致。2013 年3 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奖。当时有与会专家说到“‘80后’批评家的缺席”,此论经媒体争相报道讨论渐成热门话题。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题的生长点,若能出版一套反映“80 后”批评家的文丛,不仅能回应质疑,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80 后”批评家的成长。随即在刘涛的帮助下,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和组稿,“‘80 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八本在当年年底正式出版,推出了金理、杨庆祥、黄平、何同彬、刘涛等八位的批评文集。文丛基本代表了当时已经出道且有一定影响力的“80 后”批评家的研究水平,同时也是“80 后”批评家首次集中亮相。随后,青年批评家张元珂在《“80 后”批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一文中对文丛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他看来,“80 后”批评家群的形成,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北馆)的客座研究员机制,另一个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南社)推出的“‘80 后’批评家文丛”。“北馆南社”分别在北方和南方联手培养、推出“80 后”批评家,形成了南北互动态势,使得几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80 后”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当下文学现场的前沿。
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在选编“‘80 后’批评家文丛”时,我集中阅读了第一批入选者的文章,我觉得这一代年轻批评家的视野、理论功底均很深厚,于是自2013 年6 月开始,着手作“80 后”批评家研究。我当时的想法,一是通过对同代且是同行人的研究,来解答我自身在成长中的迷茫;二是借此回应媒体鼓噪的“80 后”难出批评家的起哄,同时也为继续策划“‘80 后’批评家文丛”作前期准备;三是践行自己作“人的批评”的理念。在著名散文家闫文盛兄的邀请下,在他当时供职的《都市》杂志以“同步成长”为题开设专栏。2015 年2 月,在陆梅主编的邀请下,在《文学报》开设“枪和玫瑰·聚焦80 后批评家”专栏。
2015 年,我的“80 后”批评家研究第一批研究成果结集为《“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7 月3 日,杨庆祥兄在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文学课堂”召开关于本书的研讨会,引起不小的关注后,有一位“70 后”批评家朋友开玩笑地说,因为你自己是“80后”,所以就只关注你的小伙伴,也不关注一下我们“70 后”。朋友的话自然只是玩笑,但却触动了我。正在此时,受《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现已停刊)之邀,我开始主持“青年批评家”栏目,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70 后”批评家的成长、研究方向以及对高校文科教育的理解和反思等,试图厘清这代人的思想来源、今后的发展潜力等。专栏选取了张莉、霍俊明、李云雷、刘志荣、刘大先、张元珂等十余位“70 后”批评家进行对话。这个对话,我故意将部分问题设计成相似的,这样不仅能掌握他们的生活、学习、研究,还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异同,也能为研究界提供第一手鲜活的研究素材。2015 年年底,我再次和陈思和先生合作,策划主编“‘70 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收录谢有顺、霍俊明、张莉、梁鸿、李丹梦、刘志荣、李云雷的评论文集。这套书没用单本的书名,而是以作者名字命名,这是陈思和先生的建议,他认为,这代学者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慢慢地定位了。
延续对“80 后”“70 后”批评家研究的路子,2016 年,受时任《名作欣赏》主编傅书华先生之邀,我在《名作欣赏》开设“未来批评家”专栏,展开对“未来批评家”的探讨。“未来批评家”的意思,它不限定年龄,唯才情、学识为第一标准,选取和推介批评者。当然,也暗含我个人对代际的看法——脱“代”成“个”是一个批评者走向成熟的必然。遗憾的是,2016 年年底,我从云南人民出版社调任《大家》杂志社,导致此项工作没有按预期开展。
正是对青年批评家们的介入,我才有幸结识了陈思和先生。那是2013 年9 月,我因第一辑“‘80 后’批评家文丛”到北京拜访作者,在刘涛的带领下,第一次见到先生。巧合的是,去北京时,我正在阅读《思和文存》第三卷,遂请先生在书上题字。先生对我们邀请他担任“‘80后’批评家文丛”的主编欣然接受,并为丛书撰写了序言。2015 年4 月,我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因为“‘70 后’批评家文丛”的人选和编辑体例需与先生沟通,便去了一趟上海。那次,在先生家旁边的咖啡馆,与先生聊了一下午。最后,说起我的低学历,先生就鼓励我报考博士。因各种外在的原因,七年后的今天,才得偿所愿。
自认识陈思和先生以来,其实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先生对我的关爱却始终如一。一次,先生看到我一篇写莫言的文章,因笔误将日本汉学家吉田富夫写成了“吉田宫夫”,马上给我电话,并给我介绍了吉田富夫的一些研究情况。另一次,我写一篇批评史的文章,在谈胡适称周作人《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时,因觉得这个评价我很熟悉,就懒得去翻《胡适文集》,顺手用一个选本作了注释。先生看到文章后,特意将此处标红,并注明让我去查原文。身为学界大佬,又被各种事务缠身,却能抽时间看我浅薄的文章,并能在我疏忽大意的地方指出我的问题。先生让我懂得了作学问必须严谨,写论文一定要去阅读最初的文献资料。这几年,我逐渐对各种说法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涉及史料时一定要恭勤恭谨,不厌其烦地去查找原始的出处。
在选编《陈思和研究资料》时,我阅读了几篇对先生“民间”理论、文学史著作批评的文章,就致电先生,问能不能收录,先生说:“没关系啊!要啊!”所以,我将李新宇教授的《走出民间的沼泽》、李扬教授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收录到了书里。我觉得,这是批评界、读者更全面了解先生理论的有益补充。这和有些学者,一见对自己的批评就大动肝火形成了鲜明对比。先生说:“我作文学批评,不怕被批评。”这不仅仅是一个姿态,而且贯穿在先生的整个学术研究之中。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思和先生说:“只有传道授业、出版和学术研究三位一体,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这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期许之言,对我影响甚大。多年来,虽不能至,但努力践行之。2013 年年底,延续着先生编辑“火凤凰文库”的理念,与先生共同策划、主编“‘80 后’批评家文丛”;2015 年,再度和先生共同主编“‘70后’批评家文丛”;2022 年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也是在先生的支持下策划编辑的。做这些工作,无非想再次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在承传、接续、播撒精神传统方面,做一点自己的工作。对我而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学,既能亲炙前辈们的风范,同时也算是努力朝着先生所言的“理想岗位”靠近了一步吧。离先生之理想,尚差距万千,但在精神的血脉上,我渴望与先生随行。

本文作者与陈思和先生合影
当然,让我感到开心的是,这些工作不仅得到先生的支持,他对此也有极高的评价。我准备去读书,他写了推荐语:“周明全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他不仅撰写了大量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文章,同时还显示出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策划能力,他身居云南边远地区,却着眼全国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连续推出了不同形式的搜集、保存、宣传各个年龄层批评家的资料文献,如对‘40 后’‘50 后’的学者编辑出版资料专集的形式,对‘70 后’‘80 后’批评家出版批评文选、个人专集的形式,对‘未来’即‘90 后’青年批评家推出专号、专辑的形式,来全面研究中国当代评论家的事业和贡献,把云南的一家杂志、一个出版社搞得有声有色。我觉得全国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以一人的努力做这么多工作。这个人不缺少聪明才智,也不缺少理想和能力,唯独缺少的是在一流名校接受学院的系统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提升,如能达到这一点,一定会是前途无量。”
我终于没有辜负先生的期待,2022 年硕士毕业后顺利考上博士,成为先生的学生。记得很多年前,我到上海旅游,跑到复旦大学光华楼前拍照留念,同行的朋友很不屑地嘲讽我。我告诉朋友,对我来说,复旦大学有陈思和先生,它就是我一生追寻的理想。还好,天意这次没有捉弄我,让我夸下的海口没有成为笑话。
这些年,我在出版系统工作,始终立足于自己的岗位,力所能及地做事。当然,我亦始终没有放弃阅读,放弃一个知识人的思考。谢有顺在《成为一个创造者——我所理解的陈思和老师》一文中说:“在陈思和身上,洋溢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极为可贵的担当精神、岗位意识。由他,我经常想,中国不缺思想者、写作者,最缺的恰恰是如何把思想转化成实践,如何把纸上的构想变成现实的人。空想容易,行动却难……一切思想,不能返回到现实,不能转化成实践,它的意义都是有限的。”读之令我感慨。我辈虽然无法如陈思和先生那样承担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但结合自己的岗位和阅读思考,力所能及地做事,却是我一直坚持并将始终如一的。
四
近年我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20 世纪80 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五代批评家的整体崛起方式和2012 年后出道的“70 后”“80 后”批评家的整体崛起方式很相似。譬如1986 年5 月在海南举办的“青年文艺批评家会议”,几乎全国的青年批评家都到会了。会后由漓江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一本《我的批评观》,收录了23 位青年批评家的自述文章,以及陈骏涛、周介人等5 位前辈对青年批评家评介的文章。《当代文艺思潮》1986 年第3 期还专门推出了“第五代批评家专号”,这在当时属于非常前卫的举动。一代青年批评家就这样被推上了潮头,很多前辈对第五代批评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介人在《新潮汐——对新评论群体的初描》中连用了四个“新”——“新群体、新态势、新节奏、新向度”。谢昌余在《第五代批评家》中评价第五代批评家有“宏阔的历史眼光、顽强的探索精神、现代的理性自觉、深刻的自由意识”。陈骏涛在《翱翔吧!“第五代批评家”》中说第五代批评家“思想敏锐、长于和善于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作家王蒙在《读评论文章偶记》中,也对第五代批评家进行了点评,并给予高度赞扬。
2012 年以后,“70 后”“80 后”批评家的出道,也是以整体崛起的方式,尤其是“80 后”批评家。2012年,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80后”批评家在《南方文坛》开设了“三人谈”专栏,从选择以文学为“志业”的自我经验谈起,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审美的嬗变,辩驳文学在各色语境中的纠葛和挣扎。2013 年5 月13 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理论批评委员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 后’批评家研讨会”,这是首次高级别的“80 后”批评家的研讨会。2013 年,“‘80 后’批评家文丛”出版,亦是国内第一次从出版上对新生的批评力量的推介。
当我和陈思和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先生说,这也许是新一代批评队伍形成的几个发力点,但是要从更加广泛的学术传承背景上去讨论,从价值取向的变化中找出这一代批评家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的状况、学院体制对他们的批评事业的干扰,以及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等等。先生所言甚是。学术是讲传承的。只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譬如从贾植芳、章培恒到陈思和,往下到郜元宝、张新颖、金理,等等,都是在这鲁迅开创的现实批判的精神脉络里。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使用的批评方法可能不一样,研究的重心可能也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文学专业的研究与对现实批判的介入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个传统衔接的正是“五四”传统。这就是学术传承的迷人之处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批评家成长的外部推力。对年轻一代批评家而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开设于1998 年),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自己也是这两个培养机制的受益者。
2015 年4 月,我入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这是我进入批评界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南方文坛》2016 年第6 期“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了我的专辑。“今日批评家”是批评家成长的重要平台,当下最活跃的一批批评家都是从“今日批评家”走上批评道路的。我能进入这个谱系,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我今天开展批评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以上的机遇。所以,在对批评家展开研究时,我也特别留意以上两个机制对其他批评家成长的助推。
从2012 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启动、《南方文坛》“三人谈”专栏设立开始到2022 年,正好十年。2021 年年底,我和《名作欣赏》张玲玲主编沟通,准备对这十年来青年一代的批评家的成长作一个回望。在讨论专栏名称时,我提出了用“第七代批评家”这个概念。当然,以第几代来论述批评家,非我独创,最早使用代际来归纳批评家的是《当代文艺思潮》杂志。早在1986 年第3 期,该刊就推出了“第五代批评家专号”。之所以打破简单的年龄划分,以更大的“代”的概念来讨论,是我觉得虽然每个批评家因阅读、学校教育,甚至是跟随的导师的思想资源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但在个体差异之下,仍不难看出每个代际的批评家的共性。而这个共性和时代的大主题与个人之间,亦存在着对话或矫正的关系。今年,重新回望第七代批评家(含“70 后”“80 后”两个年龄段的批评家)成长之路,亦是对此前访谈的一个深化和拓展。多年前的访谈和今年的访谈,形成了一个张力场。在这两个对话形成的张力之间,也似能窥见这代批评家的成长和进步。
除了对青年一代批评家展开研究外,近几年我也逐渐对第五代批评家展开了研究。除了断断续续地作口述史外,主要工作是出了第五代批评家的研究资料丛书。此一工作,对我更深入地了解第五代批评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020 年疫情期间,我窝在家里重读《陈思和文集》。对先生的著述,我自信是熟悉的,就想看看他的同代学者、后辈学者,包括他的学生,是如何评价他的文学研究。因此查到了不少杂志,并在知网检索、下载了数百篇评论陈思和的文章一一拜读。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在文章上写写画画,就顺手在那些评论文章上作了不少批注,并把我觉得评价得非常好的文章分门别类地作了归纳整理。等我把整理好的文章打印出来后,发现竟然有50 多万字,整整一大本。我当时想,若有人要研究陈思和,除了看他本人的著作外,我手上这本研究资料,肯定会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参考文本。正好那段时间,我对第五代批评家作了不少研究,就想编辑一套第五代批评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研究资料集,为当下以及后来研究这代批评家提供一些参考。我的想法得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赵石定的支持。赵社长是一个有文化情怀的出版人,他是80 年代初的大学生,身上散发着80 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光芒。当年在云大中文系毕业后,作为优秀毕业生,他本可以选择去政府、社科院等更好的单位工作,但因喜书爱书,才选择到出版社工作的。这些年他主导了很多有学术价值的出版项目。我的学术研究,甚至生活琐事,他都给予了很多帮助。其实,最初我是为自己方便找资料而后萌生编辑这套书的想法。为自己方能为别人,渡人渡己。

本文作者(中)在2020 年南方文学盛典上领奖
对批评家的研究,虽然已快十年,但于我,这项工作也才是一个预热,在未来的时间,我将倾注更多的热情,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作更广意义上的批评家和批评史研究。
五
今年7 月底,因左脚脚踝处腱鞘囊肿,我到医院做了一个手术。本以为三五天就可以下地,但半个月依旧只能借助拐杖,行动极为不便。遂在家里重读了周作人的几本书。周作人的一个转变,源自1921 年的一场大病。这场病改变了他后来对人生和学问的理解。周作人在《胜业》中说:“偶看《菩萨戒本经》,见他说凡受菩萨戒的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忧恼,都犯染污起。只有几条例外不犯,其一是自修胜业,不欲暂废。我看了很有感触,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这也让我深受触动。
我一直认为,名和利太易得,人也太容易受时代的左右而温水煮青蛙一般迷失自我。对于读书人,最难得的就是安静地坐在书斋,读点书,认真思考些有价值的问题。我虽小疾,但同样,这场小疾也因《传记文学》“学人自传”栏目的约稿,让我反观自己数年来的读书与文学之路,得之失之,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接下来,又该冷静地去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