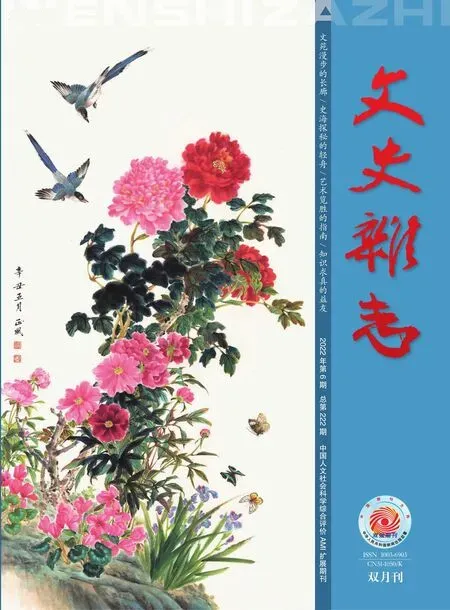试论宋代的“依文彦博故事”
云南 汤明琪
“依文彦博故事”,又称“依文彦博例”,主要指宋人以北宋名臣文彦博的生前经历作为依据,将这些过往之事用于处置朝政事务、或为当世重臣提供礼遇及官位。在宋代历史上,“文彦博故事”曾多次为宋廷所用,将之作为高官权臣升官进爵、提供优遇的参照,也曾被朝臣当做自身行事的依据。此种不成文之制的存在,对于宋代政局演进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目前的学术界,已经出现许多关于文彦博的研究论著,极大丰富了学术界以及公众对于文彦博的认识;但对宋朝存在的“依文彦博故事”现象的关注,则仍然有所不足。本文计划将“文彦博故事”作为考证的重点,试图揭示“依文彦博故事”对宋代政局的影响,并对此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宋代政治转向进行浅析。
一、史料所见的“依文彦博故事”
对于宋代朝廷及君臣比照“文彦博故事”行事之举,见于史册者如下。
“依文彦博故事”行事的首次出现,是在政和二年(1112年)。这年三月,已经致仕的蔡京前往皇宫朝见宋徽宗。徽宗诏命,令其“二十五日朝见,引对,拜数特依元丰中文彦博例,仍择日垂拱殿赐宴,许依旧服玉带佩金鱼”。在此之前,宋哲宗曾于绍圣三年(1096年)“诏文彦博三十七人为元祐党人”。崇宁年间(1102—1106年),宋徽宗与蔡京炮制元祐党人碑,又将文彦博名列其中。但至政和(1111—1118年)时期,徽宗却下诏为文彦博正名,并“特命出籍(元祐党籍),追复太师(政和四年),谥曰忠烈(政和八年)”,以皇命将文彦博排斥在旧党人士之外。因此,蔡京在觐见徽宗时,徽宗以文彦博在元丰年间面见神宗并接受赐宴之事为依据用于招待蔡京,表明了徽宗朝对文彦博正面形象的肯定,以及蔡京等新党人士对文彦博的接纳;同时,此举也是宋廷为文彦博平反的先声,对于展现朝廷的宽容、弥合党争带来的严重分歧,亦具有一定的作用。
靖康之难的突然发生,将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在乱局中,宋高宗凭借着张邦昌“还政赵氏”之举以及元祐皇后的扶持得以登基称帝。在张邦昌归还政权之后,宋高宗也曾比照文彦博晚年受过的殊荣给予张邦昌礼遇。在《中兴两朝圣政》的记载中,此事被描述为:
例,一月两赴都堂(尚书都省)。先是,御史中丞颜岐言:“邦昌,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会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
通过此段史料的记述可以看出,高宗以文彦博所获礼遇优待张邦昌,是对张邦昌在朝野主战派压力下被迫“累章求退”之举的折中处理。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主和派颜岐提升张邦昌地位以讨好金人的请求,试图在金人面前表现出对前伪楚皇帝张邦昌的尊崇,意在尽可能消弭金国兴兵南下的借口,为高宗重建宋廷、巩固自身的权势与合法地位争取时间。
宋孝宗时期,重臣史浩(史弥远之父)也有将神宗皇帝与文彦博的互动当成自身行事凭据的经历。史浩在朝期间,孝宗曾想赐宴于他以示宠信。对于帝王的恩宠,史浩则选择了谦让,在给皇帝的表文中,他认为自己“资望比之彦博霄壤不同,发肤之外,皆陛下所赐”,因此请求孝宗不必效法元丰七年(1084年)文彦博入朝故事赐宴款待,而应“特降处分,并免见日赐宴”。除此之外,史浩晚年也曾在“朝辞归乡”之时再次以元丰七年的文彦博入朝觐见为例,称彦博“以二月五日入谢、三月二日出京,首尾曾不及月”,要求在这月的二十三日辞职回乡(朝辞还乡);若如此行事,则距离其上月二十三日入朝觐见刚好为一个月。根据这些材料不难看出,“文彦博故事”可被朝臣们当做日常行事的依据以及让朝廷批准所请的理由,系“依文彦博例”在朝臣上疏言事时被当做范例运用的体现。此外,宋孝宗自己亦曾在次子魏王赵恺出镇地方(宁国府)前夕“依文彦博故事”,在玉津园内为儿设宴践行。赵恺本为孝宗所喜爱。在孝宗长子庄文太子赵愭早逝之后,“恺次当立,帝意未决”。最终,孝宗以小儿子恭王赵惇“英武类己”为由,将其立为储君;对于落选储君之位的次子,则以其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进封魏王,判宁国府。妻华国夫人韦氏,特封韩、魏两国夫人,以示优礼”。在次子出任地方职务前,孝宗于乾道七年(1171年)二月二十二日,“诏魏王恺出镇,可依元祐五年(1090年)文彦博例宴饯于玉津园”。对于父亲依前朝重臣故事设下的宴请,赵恺自认德才皆不配位,于是选择了推辞。孝宗遂命周必大起草诏书“命不允”,强调自己设宴为儿饯行在于“敦天性,示慈惠也”。此宴的设立,既符合朝廷的礼数,也显示了孝宗对儿子的重视与抚慰。

文彦博(1006—1097)画像(苏文绘)
至南宋中后期,“依文彦博故事”行事则被宋廷及权臣党羽赋予了加官晋爵的新“使命”。权相韩侂胄把持朝政期间,韩党成员们曾多次将“文彦博故事”搬出,用于提升韩侂胄的地位与权力。嘉泰元年(1201年),监太平惠民局夏允中首次请求宁宗“依文彦博故事”,为韩侂胄加平章军国重事衔。对于夏允中的提议,韩侂胄则“上疏请致仕”。此议遂因韩侂胄的退缩而暂告一段落。但至嘉泰四年,受到韩侂胄恩惠得以入朝为相的陈自强(韩侂胄的启蒙老师)为报“韩师王”的提携之恩,遂联合三名朝臣向宁宗提议,希望“援国朝故事(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之事),乞命侂胄兼领平章事”。至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面对陈自强的再度请示,韩侂胄方才接受平章军国重事一职,并去官名中的“重”字,仅称“平章军国事”。在上朝时,则“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至此,韩侂胄在名义上达到了权势的顶峰,正式成为继秦桧之后南宋的第二个权相。理宗朝后期,贾似道于前线拜相,并于鄂州城下重创忽必烈所部。为表达朝廷对有功之臣的重视,理宗遂命朝廷百官来到临安府郊外“如文彦博故事”列班迎接凯旋的贾似道。郊迎及面圣结束之后,则由理宗出面赐宴为贾相洗尘。对于理宗的诏命,贾似道并未全盘接受(《通鉴续编》记为“似道辞,乃止”)。至度宗朝,贾似道则于咸淳三年(1267年)二月被委任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获得了文彦博晚年的官衔。同时,朝廷还赐予其“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的特权。靠着权术及朝廷授予的权势,在朝堂上,度宗皇帝与百官则对贾似道毕恭毕敬,尊称他为“周公”“师臣”。咸淳十年度宗驾崩后,宋廷则更进一步,允许贾似道“依文彦博故事,独班起居”。与张邦昌、韩侂胄之流相比,在贾似道身上发生的“依文彦博故事”之事显得更为频繁。这类举动的频频发生,既表明了朝廷对贾似道功绩与权力的充分肯定,也说明贾相此时在朝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势。贾似道由此登临权势之巅。而在贾似道倒台之后,宋廷则于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令老臣王爚接替他掌管朝政,允许“如文彦博故事,自朝参起居外(即独班起居)并免拜”。六月,王爚升任平章军国重事,并“一月两赴经筵,五日一朝”。但至同年八月,王爚即在元军兵锋及朝廷政争的夹击之下选择致仕逃跑,终在德祐元年十二月辞世。对于王爚在国家危难之际的表现,时人刘一清指出,王爚任平章军国重事期间“在朝无所建明,不顾君父之颠危,退为保身存家之计”,乃是一介自私无能、贪生怕死之辈。王爚终究名节尽毁,成了宋季遗民嘲讽谴责的对象。
综上所述,除蔡京曾“依文彦博例”朝拜徽宗、并接受徽宗赐宴外,“依文彦博故事”行事基本属于南宋朝堂现象。在文彦博逝世之后的上百年里,他对宋朝政坛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他的经历多次被宋廷当做优待朝臣、宗室的参照,也作为朝臣向皇帝提出请求的依据。至南宋中后期,“依文彦博故事”行事又被赋予了加封权相、给予元老重臣以高位的“使命”,并为权相及其党羽所操纵,成为权臣巩固地位与权势的工具。

宋孝宗(1127—1194年在位)画像(清殿藏本,藏国家博物馆)
二、“文彦博故事”之原事
(一)官爵与朝堂之礼
在南宋时期“依文彦博故事”的案例当中,文彦博曾担任的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之职常常被用于替权相(或重臣)加官进爵。文彦博被授予平章军国重事一职的时间为元祐元年(1086年)。此时的宋廷正处在“元祐更化”初期,朝政则由高太皇太后(英宗宣仁皇后)把持。在高太后的主持下,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重新得势,并在短时间内罢黜新党,尽废新法。为了巩固权势、拉拢旧臣元老,司马光将目光对准了曾经批评过新法的文彦博,并在上书中称赞文彦博“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效显著,天下之所共知也”。在司马光的提携下,本已经致仕的四朝元老文彦博再度出山,被旧党赋予了“置之百僚之首,以镇安四海”的使命。元祐更化旋起旋灭,短短数载即随着司马光、高太后的相继去世而落下了帷幕;亲政的哲宗借谏议大夫杨畏之提议,以“神宗更制立法,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为由,宣布实行“绍圣绍述”,新党成员章惇、曾布等陆续得势并位居中枢;曾受司马光推举的文彦博亦遭新党弹劾,被褫夺太师头衔,“降为太子太保”。
“独班起居”“一月两赴”,是哲宗朝时文彦博在朝堂之上所享有的特权。据《宋史·礼志》记载,元祐元年五月,朝廷诏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所谓“独班起居”,与“序位在宰臣之上”相对应,表明文彦博在朝中的地位要高于当朝的其他宰辅,享有独自为一班的权利,无需同其他朝臣一样被置于垂拱殿常朝的“一十八班起居”之中。“一月两赴”,指的则是朝廷允许文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与辅臣共议”;据此记载可知,文彦博所享受的待遇,乃是每月赴经筵两次,唯有遇到朝政大事,方才去都堂与执政们共同商议。因而,高宗“依文彦博故事”授予张邦昌“每月两赴都堂”的特权,乃是参照文彦博所受礼遇,并非是对文彦博晚年经历的简单模仿。
文彦博受“百官郊迎”的故事,则源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仁宗诏令“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至文彦博、富弼入朝担任宰辅之时,则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彦博、富弼”。南宋末年,朝廷依此案例,命人迎接从前线归来的贾似道。此举既是朝廷对贾似道所获军功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仁宗盛世的追忆,表明了时人对于太平再临、赵宋中兴的渴望。
(二)宴饮之事
有宋一代,朝廷设宴款待朝士乃是常事。除在帝王生辰、节日期间举行宴饮活动,与群臣共度良辰之外,诸如射宴、赐宴等临时宴饮活动亦层出不穷。这些宴会大多带有政治目的,也是君王“笼络臣心、宣示皇恩、广布教化的一种政治手段”。作为朝廷重臣,文彦博曾多次接受神宗、哲宗皇帝的赐宴,并在宴会上与君王进行互动。他的经历,成为后世皇帝赐宴于大臣的样板及参照案例。
元丰年间,神宗曾两次赐宴于文彦博。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神宗“赐彦博御筵”,并亲自“为诗赐之”。元丰七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文彦博入朝拜见皇帝,在君臣即将告别之时,神宗“宴文彦博于琼林苑,赐御制诗”。哲宗幼年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借助旧党势力大行更化之举措。在元祐更化期间,文彦博以四朝元老的身份成为旧党的座上宾,哲宗亦赐宴于彦博以示优礼。史载“元祐五年二月甲子,诏即玉津园宴饯太师文彦博”。此类赐宴活动,成为哲宗以后宋代帝王为臣子、皇子赐宴的参照案例。其借文彦博在宋代政坛的“四朝元老”“功勋卓著”的地位,宣示皇恩浩荡以及对被赐宴者的器重。
通过观察“文彦博故事”的来由可以看出,这些被用作行事参照的案例涉及了官爵制度、礼待重臣、宫廷宴饮。这些事迹时间跨度较长,所含内涵亦较为广泛,遂给予哲宗以后的宋廷可供活用的行事凭据。加上彦博乃是“四朝元老”,朝廷用他的“故事”作为参照行事,也可借用他的名望抬高受恩泽者的影响力与地位,从而彰显朝廷对接受恩泽之人的重视与肯定。
三、“依文彦博故事”与宋代政治转向
从表面上看,“文彦博故事”只是朝廷或朝臣在日常行事时用于参照的案例,且多用以尊崇朝臣。但从宋代政治理念变迁的角度出发进行观察,即可发现“依文彦博故事”与两宋之际新旧两党在政坛上的兴亡有着紧密联系。这亦是南宋统治者尊崇旧党、贬斥新党思想的展现之一。
宋代清算王安石及新党,平反司马光及旧党,起于宋钦宗靖康年间。蔡京倒台之后,杨时等朝臣以“(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为由,要求朝廷对已死的王安石施加“追夺王爵,明诏中外,以毁去配享之像”的惩处。对于杨时等人的请求,朝廷予以采纳,“疏上,诏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高宗朝时,高宗曾公开表示“朕最爱元祐”,将元祐之政视为自身执政及朝廷修史的正面参照,并表达新朝追溯仁宗之政、秉持“祖宗之法”旗帜的意愿。赵鼎等人亦将王安石当做抨击的对象,认定“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国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而朝廷如今面临的困局则“始于安石,成于蔡京”;因此必须取消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以达到清算蔡京一党弊政的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借着反蔡京之名反对王安石本人及其新法的情绪,终究变成了对王安石本人的全盘否定,并近乎贯穿了整个南宋。宋宁宗在绍熙五年(1194年)通过绍熙内禅登基,之后以明年为庆元元年,在改元诏书中宁宗认为:
亲君子,选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税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以纪元,其以明年为庆元元年。

王安石(1021—1086)画像(清殿藏本,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该诏书将旨在清算新党的元祐之政与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相提并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同时也将宁宗朝对王安石变法及新党的否定态度表露无遗。至理宗朝,理宗依照礼部尚书兼侍讲李埴所奏,以“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为由,将“子思并与升祀,列在十哲之间”,使得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士的地位抬高至与孔子嫡孙孔伋并列。与之相对的,则是王安石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年)下诏称王安石系“万世罪人,不宜从祀孔子庙庭”,从而将王安石彻底赶出了孔庙。由此,旧党反对新法的“功绩”得以被朝廷所承认,成为宋朝官方对新旧党争的定论。在清算王安石及新党的过程中,平日里与旧党成员有着密切往来、暮年受到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提携而出任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也在身故之后得以受益,作为“元祐之政”的重要参与者。文彦博由此成了宋人心目中的“正人君子”、为国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他的生前事迹也因此多次被宋廷及朝臣当做行事与论事的依据,化作有宋一代“前朝故事”的构成部分之一。
结语
自哲宗朝之后,伴随着徽宗为文彦博平反正名,“文彦博故事”开始被朝廷当做行事的依据,“依文彦博故事”行事也由此在朝堂上频频上演。在“依文彦博例”行事的过程中,皇帝、重臣们皆能从中找寻适合自己、适合国家的案例,并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发挥使用。与此同时,“依文彦博故事”还夹杂了权相政治的因素,与宋人对王安石及新法的看法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在运用“文彦博故事”行事的过程中,哲宗之后的宋代君臣也将文彦博个人生前的政治影响力加以发挥,使之成为展现皇恩、巩固权势地位的重要依托。文彦博遗留下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宋季,与南宋相伴始终。

[1]近年涉及文彦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申利:《论文彦博的道教诗和道趣诗创作》,《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北宋名相文彦博的为政风范研究》,《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年第1期;向有强:《“熙丰洛阳名臣诗人群体”交游核心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孔子君:《北宋河南府知府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2](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3页。
[3](宋)释志盘:《佛祖统纪》,《续修四库全书》第12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
[4][10][11][12][20][22][23][24][25][26][33][34](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3页,8733页,8733页,8733页,13781页,897页,897页,921页,929页,931页,2785页,2757页。
[5](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2页。
[6][7][8][9](宋)史浩:《峰真隐漫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3页,773页,774页,774页。
[13][42](宋)礼部太常寺撰修,(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15页。
[14][15](宋)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2页,142页。
[16][18][19][50][52][53](元)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489页,2504页,2504页,2423页,2696页,2696页。
[17](宋)佚名:《庆元党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页。

[27](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全宋笔记》第8编第6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244页。
[28][29][36][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54页,8854页,4356页,4357页。
[30][31](宋)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页,48页。
[32](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1—622页。
[35](宋)洪迈:《容斋四笔》,《全宋笔记》第5编第6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38]尹高林:《北宋宴饮活动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1页。
[39][40][41](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页,590页,590页。
[43][44][45][48][49](明)王锡爵:《历代名臣奏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612页,612页,617页,617页。
[46](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87页。
[47]参见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关于高宗“最爱元祐”的其他含义,可参见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1]虞云国:《南宋行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
[54](清)嵇璜:《钦定续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