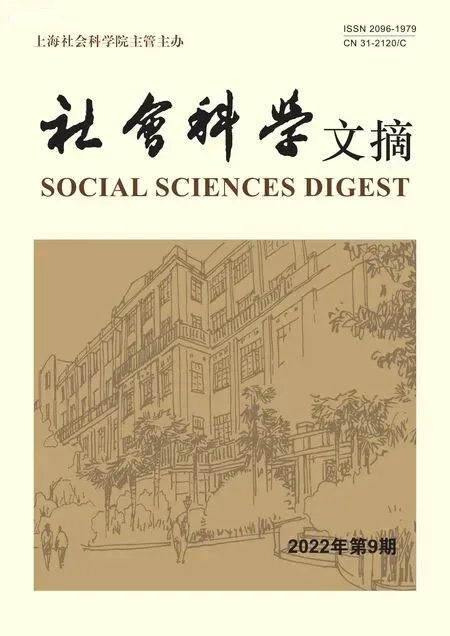走向“特定性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化
文/郗戈
传统的哲学史解释模式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思想阶段,甚至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哲学革命及其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和“验证”。这种解释模式可能会遮蔽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互生成的总体性关系,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视作单纯的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并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去哲学化”诠释路向,并且为各种形式的“哲学空场论”或“哲学补充论”留下了余地。对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不是完成于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一次性事件,而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持续深化发展的思想历程,甚至是在马克思身后仍未完成的一种思想趋势。而这一持续深化的哲学革命的内在推动力,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显然已经不能被传统哲学理论形态或学科概念所囊括,已经越出了传统哲学视界而内在地“切中现实”。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学科分化视域来看,政治经济学日益呈现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非哲学学科”,与“哲学”学科并无从属关系。然而,马克思本人却主要不是在“哲学学科”内部,而恰恰是在“非哲学学科”的特定社会科学内部开展了哲学思想活动。要理解这一悖谬之处,关键在于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同于“哲学”学科形态,也不等于政治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学科形态,而是内化在特定的社会科学中的否定性、超越性的思想维度,它在切入“现代的特定现实”的根基处越出了整个传统哲学的视界,开启了“历史特定性”这一新型哲学思维的可能性空间。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作用,使得马克思能够在特定社会科学形式中构建一种切中“现实”的“新哲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特定化”逻辑
政治经济学批判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两次“范式转换”。从思想史上看,正是这两次范式转换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内核。不同于传统理解,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包含两次“范式转换”,因而表现为两个思想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自我意识”范式转到“实践”范式,理论形态上从唯心主义、市民社会唯物主义转到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第二阶段从“实践一般”范式深化为“特定实践体系即资本生产体系”范式,理论形态上从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化为特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其中,实践一般范式及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最高最终成果,而仅仅是哲学革命的中介环节和阶段性成果。并且,促进上述两次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力,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深化作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革命的推动作用,在思想的内在演进逻辑上主要是“特定化”进程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对于哲学革命的思维逻辑,必须摆脱传统哲学史解释模式的“推广论”或“应用论”。“推广论”将“自我意识”向“实践”的范式转换理解为从一般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广”。而“应用论”将“实践一般”向“资本生产”的范式转换理解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应用”“验证”或“丰富”。上述传统解释模式在根本上都是一种从既成的一般性原理向特殊对象的“演绎”思维。然而,深入的思想史阐释和文本研究表明,哲学革命或两次范式转换的内在理路,不能理解为普遍原理向特殊理论的“演绎”推理:既不能从一般唯物主义推广或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推导出或应用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说,哲学革命或两次范式转换的逻辑应理解为一种广义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过程。这种“综合”是一般性概念即抽象范畴通过特殊化而上升到特定概念体系总体即思想具体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特定形态建构
从“自我意识”到“实践”的范式转换的理论成果是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而从“实践一般”到“资本生产”的范式转换的理论成果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暂且称之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或“具体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及手稿中,政治经济批判通过将哲学思维“特定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对象上,从而塑造出了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的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形态。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形成后,《资本论》自身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新哲学形态。这种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表现为一个作为综合结果的具体理论总体,而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则表现为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抽象侧面或抽象环节。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到《资本论》及手稿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从普遍到特殊的“推广”和“应用”式的演绎推理,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从一般范畴特定化为范畴体系总体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与飞跃。由此,作为思维成果的“理论总体”是受特定性规定的,而初始的普遍性范畴则成为这一“特定总体”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按照范畴的发展逻辑,从“实践一般”经历“特殊化”“个别化”而发展为特定实践体系的“具体总体”,即以资本生产为轴心来运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总体。进而,一旦“实践一般”范畴发展为“特殊的实践总体”,“实践一般”本身就从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特殊实践总体”这一新理论体系的一个侧面、局部和环节。从《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总体“从后思索”地反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基本原理就“下降”为一些不能独立自存、不能单独抽象出来的环节和侧面。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特定生成论”的哲学深蕴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提出并研究现代社会的特定“本质”与特定“现象”的特定存在论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了《资本论》的哲学形态。从哲学层面上看,《资本论》逻辑也相应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资本逻辑的展开,即社会存在论的本质层面的生成过程,集中表现在剩余价值生成和转化的过程。二是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物象化逻辑的展开,即从社会存在的内在本质向外部表象进而向社会意识的颠倒表现过程:物象化以剩余价值的生成转化为基础,实质上是特定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的主客复合效应。要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可以理解为,社会存在论层次上从特定社会存在的内部联系、本质内核逐渐生产再生产出其特定的外部联系、表象形式的历史生成论过程。
进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本质向表象的生成,是一种特定性的、交互生成、再生产式的关系。《资本论》一至三卷对于资本逻辑的再现,不仅是线性顺序的演进,更是一种“再生产”式的循环演历:本质(剩余价值生产)转化生成出现象(物象),而现象(物象)又反过来参与到本质(剩余价值生产)的再生产之中,不断循环、扩大、上升。由此,对《资本论》的阅读也要打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直线性思维,而遵循《资本论》本身的再生产逻辑,采取首尾交互、循环往复的阅读方式,从中真正读出一种交互生成性的哲学思维。
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够总体再现本质与现象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进程,因而是一种特定性社会存在论,并且内含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身的抽象维度。这种特定社会存在论聚焦于诸种“社会定在”何以历史先验地可能的具体存在论问题,并蕴含“社会存在一般”何以历史先验地可能的一般存在论问题作为抽象环节,因而仍然属于哲学思想范畴。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马克思哲学,不是“去哲学化”“部门哲学化”或“实证科学化”,而是超越现代学科分工藩篱,更为内在地把握《资本论》的新型哲学理论总体。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历史特定性维度
马克思哲学革命所遵循的历史性原则和“特定化”逻辑,所建构的“特定理论形态”和“特定生成论”,最终都指向了内在切中“现实”的“历史特定性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抓住了哲学形态自身流变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变迁的历史性维度。只要“现实”仍然被把握为“现实一般”,“现实”概念所再现的就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对现实一般共性的抽象。“作为现实的现实”只能是“特定现实”,而不是在传统“意识”范式中表象出来的“现实一般”。如果要真正切入规定着现代社会的“特定现实”,就必须走出传统哲学的“现实一般”概念,通过历史地理解社会科学中呈现的“特定现实”才能批判传统哲学的历史前提与先验根基,从而真正打开新的哲学视野,推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哲学革命的历史性原则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化为“历史特定性”概念,才使得马克思哲学革命能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哲学范畴的“新”哲学维度。
历史性原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维度。然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第一次范式转换只达到了“实践一般”范式和“历史性一般”视域,与后黑格尔的现代欧陆哲学基本上处于同一思想地平线上。实际上,只有哲学革命的第二次范式转换才真正实现了历史性原则,通过“资本生产”或“资本批判”范式达到了“历史特定性”或“历史性定在”。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一般范畴作为环节从属于特定范畴体系总体的思维方式,体现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性深蕴。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恰恰实现了哲学存在论的思想视域、理论主题和提问方式等的根本转换:扬弃抽象的“存在(者)一般”的形而上学探究,直接追问“特定存在物的特定存在方式”的历史性问题。不仅将历史性,更进一步将“历史特定性”置于哲学存在论的核心,这是对整个存在论的普遍性执着以及认识论的确定性执着的扬弃。《资本论》已经不属于传统存在论的“纯存在”“存在一般”的范畴,也不属于传统认识论的“表象论”“主客二元”的范畴,甚至不同于现代生存论传统对于“此在一般性演历”的执着。
切中现实根本地说是切中特定现实的本质与现象的特定的历史性关联,“新哲学”之所以能够切中现实,在于其以历史性进而特定性为原则,穿透了超历史性的普遍性原则,探究特定现实何以历史的可能。现实的特殊性定在,孕育着普遍性的规律;普遍性的规律和趋势正是扎根于特定性的实存。对于科学来说,任何现实对象首先都是“特定现实”,进而才能被合理抽象为“普遍现实”。不预设特殊性的普遍性或宣称超离于特定现实的普遍法则,都具有僭越现实界限而导向思辨形而上学的危险。
特定现实的自身扬弃趋势,保持着对普遍化趋势以及新生成的特定现实的历史开放性。由资本逻辑批判引导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内生出历史开放性的新哲学理论。所谓资本逻辑,并不是黑格尔置于体系顶端的自我复归的绝对理念,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我划界的理论理性,而是一个始终蕴含无意识的自身否定性的过渡性范畴。《资本论》的旨趣不在于描绘资本逻辑,而在于超越资本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新体系,而在于扬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这种理论体系的自我批判性、自身否定性,恰恰意味着哲学革命一直在路上。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种历史特定性定向,使得其在整个哲学史上都卓尔不群。传统的哲学变迁大多是以新的普遍概念来拒斥或取代旧的普遍概念,而马克思走向特定性的新哲学却破天荒地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社会存在论来改造和扬弃黑格尔的普遍概念辩证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来发展和扬弃一般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历史特定性和开放性维度,真正基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差异,把握住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历史性辩证法,从而将自身凸显为一种能够内在切中“特定现实”的新哲学。
结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动下,马克思哲学革命展现出一种向着多种学科和多元现实开放的未来向度。今天,我们要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当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精神形式为中介,切入诸种社会科学形式中呈现出来的自在的、实证化的“特定现实”,开启“特定现实”的内在历史性、辩证性与开放性,继承和深化哲学革命的精神内核,在当代真正开启哲学维度。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切中“现代现实”而非“现实一般”的根本优势,既不在于纯粹思辨也不在于经验实证,而是在于扬弃了“思辨”与“实证”二元对峙的“超学科”的总体性思维。而这种超学科思维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历史特定性”视野中达到了高峰。继续推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进程,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通过内在批判社会科学而切入“当代的特定现实”,将会在现时代极大激发哲学的生命力与创新潜能。
在历史特定性的新哲学视域下,所谓“当代现实”就是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诸种条件制约的“特定现实”。切中这一“当代现实”的任务,要求我们继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开放性建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和问题性思索中持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