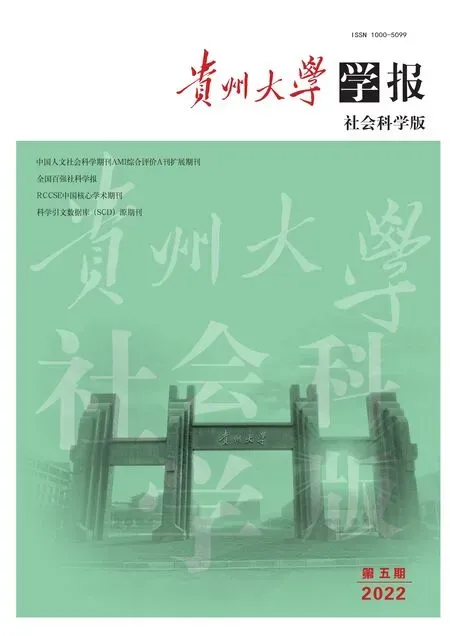《庄子》的无为思想与引导性政治
陈 赟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 200241)
一、引导性政治与支配性政治
《庄子·应帝王》将明王的立身基础托付给“立乎不测”与“游于无有”,这一基础关联着“天下藏于天下”的秩序追求。这一追求拒绝对世界与人性的透明化与确定性的过分渴望,后者包含了简化、驯服、支配世界与人性的强力要求——这种要求也是一切有为性机制的归宿。“三代以下”的“明王”虽然不再有“三代以上”的神圣光环,但仍在道之指引下运作,从而展开为一种引导性的政治,而非支配性(以对人民的操纵与掌控而达成的统治)的政治;引导性的政治在于引导人们自觉地开发性命之情并守护性命之情在其中展开的生活世界,而支配性政治则恰恰相反,击穿、虚无化人民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将人们导入另一焦点性的统治空间。
如果将“为”理解为一种由施为者承担的活动,那么通常所谓的“有为”和“无为”,就是“为”的不同活动形式,二者并非施为者及其活动的缺席,而是“为”的不同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无为”只是“无为之为”;与此相应,“有为”也并不能占有“为”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有为之为”。“有为之为”与“无为之为”区分的核心在于对自然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方式,由此而与上述两种秩序类型相应。一旦“有为之为”主导了统治活动,被导向的往往是支配性的统治;而“无为之为”则意味着引导性的秩序,它引导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回归本真的性命之情(1)以本真自我作为理想人格追求,是《庄子》思想的独特之点。《齐物论》将道称为“真君”“真宰”,《大宗师》《刻意》《田子方》《徐无鬼》将理想人格称为“真人”;《大宗师》将生存真理称为“真知”;《马蹄》有所谓“真性”;《天运》将逍遥游称为“采真之游”;《渔父》提出“法天贵真”的说法;《天下篇》将至人理解为“不离于真”。宋俞文豹在《吹剑四录》中说:“六经、《语》《孟》无‘真’字,凡经义皆不用‘真’字。”[1]顾炎武说:“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说文》曰:‘真,僊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八其所乘也。’(人老则近于死,故老字从匕;既死则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2]王船山的《说文广义》也有类似看法[3]。。支配性政治秩序总是走向这样一种方式,即不仅贬低而且解构人们的自然本性,其极端形式则是将自然本性完全虚无化,而后通过名相的体制化等方式,建构一种焦点性政治化空间,将本性业已虚无化了的人们组织到这一空间中去,以便达成对人的征用与动员。无论这个空间采取民族、国家的名义,还是冠以美善的华饰,其目的皆在诱导人们在此空间中展开自我确证。就西方现代文明来看,通过名相秩序(譬如18世纪以来西方的“地上天国”的“政治神话”与种种价值化了的“意识形态”等)达成的动员,可以弥漫在生活世界的每一角落,从而使得权力的毛细血管伸展到生命的所有领地,以至于出现将人口、卫生等,或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纳入统治领地的“生命政治”现象。操纵性统治发展到极致,则是建构内卷化机制,形成“非动员的动员”“非组织的组织”,统治不再直接邀请人们到名相空间中成为被组织、被动员、被征召的对象,但却通过体制化的力量让人们自发地甚至自觉地朝向这一人为建构的秩序空间。
体制性事实及其过程具有某种反噬性,它不仅褫夺、敉平了被统治者的自然本性,转而也会导致统治者本身对于体制性事实的适应,即体制性事实也将改变统治者,最终无论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都被体制化现实打造成适应那种虽然由人构想但却有了自身存在的政治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被整合到巨型的机械系统中,它的存在及其自我延续的强力本身超出了设计构建它的人类主体,并最终将这种主体卷入系统本身的自我持存和延续中去。一旦人的性命之情被空心化、虚无化,那么支配性政治秩序及其系统最终会以自我延续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目的”,它的存在就是自我增强与自我延续,而它们的最佳方式就是将生活在这种系统中的人的性命之情不断虚无化,让其成为承载这种系统的容器,或者成为系统自身自我增强的工具。这样,本质上无人(不论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能居于其上,而是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体制性系统之中,试图通过体制性秩序操纵另一部分人的支配者也终将无法摆脱被支配的结局。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会发现,支配性秩序的逻辑是消解生活主体而将之转化为政治主体的过程,政治空间成为人的自我确证的唯一场所,“政治生活”成了人的生活之全部;或者反过来说,弥散性的生活世界被蜕变为焦点性的政治空间。这就是隐藏在一切支配性政治秩序中的机制,它实质上是以贬抑生活主体为前提而创造脱离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政治主体的过程。《庄子》所谓的“无为”,虽然有其时代的语境,但也承接了上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主流脉络,这就是“大禹治水”这一符号所象征的对秩序之引导本性的意识。
消解支配性与操纵性并不是最终目的,正当的政治生活是引导性的。引导性是“道”这一颇具有隐喻性质的概念之本质,它既体现在“大禹治水”的具有原型意味的典范叙事中——因顺“水之就下”的本性疏导而不封堵洪水,从而成就治水之功,又体现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的“封建之道”(“民族区域自治”可以视为其现代变形)中;引导性的政治以其对人之天性的信念及其守卫,从而潜在地抵御一切形式的人为操纵,而将政治生活定义为引导人们各正性命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天下人走上政治的前台,而统治者则退藏在舞台的背景里,其核心是把天下还交给天下人,“藏天下于天下”(《大宗师》)。这样,政治生活就不再是打造或发明适应政治秩序及其体制性现实的新政治主体的过程,也不是驯服生活主体的过程,而是消解与体制性事实关联着的“政治主体”想象,激唤生活主体的负载与自我担当。引导性政治不是将人们引导到脱离生活世界的政治空间,而是让政治空间成为回归生活世界与性命之情的桥梁与通道。政治空间的政治性只有在政治共同体面对其他政治共同体的挑战与压迫,在保护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并最终又超出了它本身的教养与文明时,才以积极的方式自我彰显,但这已是政治共同体的非常状况;在政治共同体内部,正常状态是政治性当让位于生活秩序。《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记载:“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在正常的生活世界中,人们赶马拉粪去耕种土地;但当这些马匹作为战马出现在战场时,很大程度上,人们已经身处天下无道的状况;与此相呼应的另一个表述来自《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当天下有道之时,道就殉失在人们的身体中,显现在生命和生活的自我享用过程中,而不是去寻求生活与生命之外的名之为道的终极实在;反之,当人们以殉失身体的方式去追寻道时,恰恰是天下无道的表现(2)通常的理解,将孟子此言与《论语·泰伯》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视为同义,天下无道时,以身存道;天下有道时,道随身出,达于家国天下。这一解释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层面[4],它凸显的是个人即便在天下无道的状况下也要“守死善道”。譬如张栻在《南轩先生孟子说》中说:“天下有道,则身达而道行,所谓以道殉身也。天下无道,则身退而守道,所谓以身殉道。道之于己不可离也,故非道殉身,即身殉道。”[5]上述个人修身视角的解释并未注意到“徇”(又作“殉”)揭示的道与身在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时的张力,更未注意到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的表述自身就设置了政治语境。一般对徇(殉)的解释有二:一是“殉,从也”;二是“亡身从物谓之殉”或“杀身从之曰殉”[6]。 “殉”的后一种意义,更加突出了有道与无道时道与身的张力。天下无道的状况,表现在以道的名义征召动员,反而使得道不是润身成身,而是榨取与抽空业已被资源化的“身体”;天下有道的状况下,道本身就徇失在身体中,身体不是朝向所谓的“道”体的,而是即在道之滋润之中,实享道之实而忘道之名。王艮《心斋语录》道出了天下有道时,道与身之间的关系:“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7]。
二、作为引导性机制的“无为”
在壶子“四示”的寓言性叙事之后,《应帝王》试图以“庄语”形式揭示引导性政治的本性,这一章的“庄语”可以视为对全篇主旨的概括,张默生把它作为全篇的总论,以为即便将之移到篇首,也未尝不可[8]。该章文本如下: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9]279
这里的四个“无为”意在透显“无为”的本质。“无为”并不是“为”的缺席,而是“为”的方式的转变(3)《文子·自然》:“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镸尗,泥用輴,山用樏,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非吾所为也。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故常虚而无为,抱素见朴,不与物杂。”这里可以看出“无为”只是“为”的方式不同于“有为之为”而已。,因而更准确地刻画应该是“为无为”(4)《道德经》第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以及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或者“无为之为”(5)“无为”之“为”,即是采用了“无为”这一形式的“作为”。《庚桑楚》记载:“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矣。”“出为”意味着给出了“作为”,但这种“作为”的方式却是“无为”,这就是出于“无为”的“为”,或者“无为之为”。。我们必须注意,在政治生活中,统治者的活动方式始终关联着被统治者相应的回应方式,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共构性:如果统治者采取了“无为之为”的方式,那么被统治者的“有为之为”则可能被激发,从隐暗背景走向开放前台;相反,如果统治者采用“有为之为”的方式,那么被统治者则会以消极方式加以回应。这里面所包含着的是不同政治主体性之间的辩证张力。明王的正当统治方式不是创发性的“有为之为”,而是引导性的“无为之为”,这是一种削弱统治者的政治主体性而调动被统治者的政治主体性的方式。
在《应帝王》的语境中,四个“无为”的主语是明王,即统治者,而不是泛指一切人,统治者的“无为”是其施为于被统治者的正当机制,它意味着一种引导性的机制。正确地理解“无为”,不能忽略施为者与受为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语境。郭象的解释始终注意这一语境:“因物则物各自当其名也,使物各自谋也,付物使各自任,无心则物各自主其知也。”[9]279-280这一理解的核心是,统治者的“无为”(无为“名尸”“谋府”“事任”“知主”),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自我约束,而是意在引出物之自为,即物之“各自当其名”“各自谋”“各自任”“各自主其知”(6)《淮南子·修务训》:“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也。”《淮南子·原道训》:“所谓无为者,不先为也;所谓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也就是说,郭象的理解充分呈现了其中的政治语境,即统治者当以何种方式实施正当的统治,也就是其行动当以何种方式作用于被统治者?一旦祛除了这一政治语境,变成个人修身或养气的身体技术时,施为者与受为者在结构上的相关性脉络就消失了,四个“无为”就会蜕变成施为者主体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基于受为者的本性而展开的在施者与受者之间的政治行动。
“无为名尸”的字面意思是,不要做名声的承受者,不做“有名者”,其实质含义则是统治者不要自居为名声的主体;事情成功了,统治者不居其名,而将名声还给当事的执行者——臣下与百姓。“无为名尸”中的“名尸”本是隐喻,“名尸”指名的承受者,古人祭祀时祖先的孙子坐于神位,以代表祖先神灵受祭,此即为“尸”;“尸”有“主”之意,《仪礼·士虞礼》郑玄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10]927《礼记·曲礼》:“孙可以为王父尸。”故《仪礼·特牲馈食礼》注:“尸,所祭者之孙也。祖之尸,则主人乃宗子。祢之尸,则主人乃父道。”[10]990(7)值得注意的是,李华在《卜论》中说:“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变。战国荡古法,祭无尸。”(《全唐文》卷三百一十七)由此,战国时代,已经不再用尸来祭。祭祀时充当尸主的孙既非孙之实,也非祖之实,在祭祀时刻只是祖先的符号化象征、一个无实的名位;“名尸”为名所主,因而受到名的机制化之支配。《逍遥游》:“圣人无名。”对于居于天子之位者来说,天子只是天之子,天下乃是天之天下或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是天子之天下,天子并非天下的所有者,而只是临时性的代天治理天下者,或受天下人之委托而治理天下者,任何事功或治功的成就,都是当事的参与者,即臣下与百姓参与治理的结果;而王者在其中扮演的不过是引导者、调节者的角色,因而如果王者居其名,则与实不副。“无为名尸”,在最终意义上意味着有天下而己不与,将天下还归天下人,而不是让天下受到名的役使,丧失其本真之实。换言之,“圣人无名”的潜台词是“名归天下人”(8)阮毓崧说:“名者实之宾,去实为宾,圣人谢之。况名乃天下所争趋,而我或独享之,如尸主然,则群相倾轧矣。”[11]236陆西星将“无为名尸”与壶子章“名实不入”联系起来:“无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实之宾,实者名之主;不为名主,则不特无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实者亦遣而无有,此便是‘名实不入’之意。”[12],所谓“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山木》)。“名”一旦还归百姓,而不在王者,则王者无名,天下也就“莫之能名”[13]165。从体道论的视角来看,《淮南子·诠言训》:“名与道不两明,人受名则道不用,道胜人则名息矣。”《则阳》:“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意味着,有为名尸,去道必远;“无名为尸”,方可与于道。
“无为谋府”的字面意思是不要作智谋、谋略的府库,其言说的对象同样是统治者,统治者不要将自己当作谋略的府库,仿佛自己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谋略智慧,一切皆可从己而出,甚至经式义度也可以一并从自己这里发出去要求天下人。相反,与统治者相应的品质是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的局限性,尽可能地做到绝圣弃智、废黜聪明——这是统治者对统治者自身的要求,这一要求关联着另一预设:在天下,智慧谋略的府库在天下人那里,而不在特定个人那里,特定个人的智慧谋略总是有限的;统治者不把自己作为谋府,而让天下人自谋天下事,也就是让物各自为谋,引导并激发天下人的智慧与创造力,这样的谋略与智慧则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吕惠卿深明此中关窍:“谋者作之聪,而稽之众者也。府我所有也,谋而为之府,则其出不博,而聪有所不尽也。无为谋府则我不谋,而天下为之谋矣。”[13]165天下人谋天下事,在古往今来视域中,天下人本来无穷,其智慧也是无尽的;统治者的大智,在于不自恃其一人之小智,而能运用与调节众谋,让天下人谋天下事。阮毓崧清晰地揭示了此中道理:“以一人为天下谋,不若听天下之自为谋。倘好施心计,欲天下皆受制于我一人,则阴险所趋,即为丛怨之府矣。”[11]236-237本句针对的是以逞其聪明、计其谋略去统治的方式,这种方式没有注意到无论统治者自身多么聪明能干,在天下人整体这里也只是极为有限的,所以抑制自己的用智用谋,其实也就是为调动天下人各谋其事提供条件。统治者的不自用其智、不自用其谋,是为天下人运用天下之智、天下之谋处理天下之事预留空间。
无为事任,即不以事自任。“任”有自觉地承担、主持、负责之意。“无为事任”,意味着就统治者自身而言,“顺事而应,若非己出者也”[14],憨山的这一解释着眼的还只是个人自修。从政治语境来看,“无为事任”意味着统治者通过避免以事自任的专断独行,引导天下人各任其事,统治者在此的无为,关联着引导天下人自任其事。统治者不是具体的做事者,而是做事者的管理者、引导者、调节者;他必须限制自己不去从事具体的事务,而是让任事者(被统治者)自任其事。吕惠卿认为:“事者,下之所以事上,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事而任之则为天下用,而非所以用天下也。无为事任则我无为而任事者责矣。”[13]165如前所云,事与技的主体,都是具体的当事人或从技者,他们面对的不是人事,而是物事。统治者面对的则是人事,物事的核心是人对事务的关系(这里事务或者是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所从事的技术,或者是事情所关联着的物),而人事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统治者如果不能从具体的事务中退却,则是与民争事,与民竞技、竞智,就会对事情依照其自身逻辑的展开构成最大的困扰。统治者从具体事务中抽身而退,只是前提,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则在于让天下人各任其事、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有攸归。“天下之事,任天下自为之,未有不胜其任者。若擅事而总任之,则丛脞纠纷,无非性分之累矣。”[11]237统治者的职分在于,引导从事具体事务的天下人,各从其序,进而各正性命;一旦统治者去亲自处理具体的事务,反而鸠占鹊巢,僭越了自己的合理领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各有职分,不得相僭,这本身就是政治社会有序化的方式。“无为事任”不仅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有序化安置,而且既保证了统治活动自身的无为性质,也保证了统治活动的最大化收益,即“无不为”:“‘无为事任’,非不任事也,以事任之天下,天下各尽其职,而王者要其成,所以无不为也。”[15]179
同样,“无为知主”是让统治者不要成为聪明智慧的汇集者,不以一人之智盖天下,而是调动天下人,各尽其智,各称其能。吕惠卿的理解很到位:“智虽落天地不自虑也,智而主之则自虑矣,无为智主则我无虑而天下为之虑矣。”[13]165即便某个统治者的确聪明,相对于其他个人在才智上可谓出类拔萃,但也要放弃依恃自己的智慧,以让人们的智慧得以充分施展和发挥,这就是去一己之智的“大智”。王叔岷指出:“案《淮南子·诠言篇》《文子·符言篇》知并作智。此谓不执着己智也。《吕氏春秋·任数篇》载申子对韩昭侯曰:‘至智去智。’”[16]无为知主,并不是对智慧的完全否定,只是对统治者自恃一己之智的否定。《人间世》业已发现:“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常人任知,其害小;统治者任知,其害大。故而,这里的“不为知主”,不仅是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同时也导向被统治者的约束。阮毓崧说:“智也者,争之器也。《庚桑楚》曰‘任智则民相盗’,以必争归于利耳。故惟忘心去虑,不运智以宰物,而使物各自主其知,则率土皆真,群相安于浑穆矣。”[11]237阮毓崧道出了统治者不自用智的目的,乃在于引出天下人的各主其智,只有以此方式,统治者才能达到“大智”的状态。大智者若愚,最能虚心听取天下人的意见,让天下人竭尽聪明才智——这也是《礼记·中庸》称舜何以是真正有大智者的原因(9)《中庸》谓:“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之注说得最清楚:“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17]对此的详尽分析,参见陈赟的《中庸的思想》[18]。。
显然,“无为知主”有其政治语境,一旦这一语境被褫夺,它就变成了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去语境化的结果就会导致对《庄子》乃至《道德经》的反智主义的理解。《道德经》第十九章记载:“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庄子·胠箧》接续了《道德经》的思路,提出:“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庄子·在宥》强调“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在这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等的主语是统治者: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古典文明的语境中,很难看到以民有可绝之“圣”“智”。《说文》:“民,众萌也。言萌而无识也。”“民”是不显身于“群”而淹没于“众”中的人,而“众”之所以为“众”,《孟子·尽心上》有经典的概括:“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仁义圣智,即便一切人本性所固有,但也只有待之君子,方能充分显其德。其次,“绝圣弃智”与“民利百倍”的对举,关联着两种不同的主语,即君和民,当《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时,“民”与“君”对言;当《诗经·假乐》说“宜民宜人”时,“民”与在位对言,人谓臣,民谓众庶。在上述语境中,“无为知主”可以视为针对统治者(王者或君主)的教育,而与之相关的“民”则是隐藏在背景中。《应帝王》四个“无为”,皆是针对统治者而发,对之做了去语境化的理解之后,反过来就要其(不仅是庄子而且还有老子)为其反智主义负责——这并非《道德经》《庄子》自身的问题,而是今人犯了“语境的误置”的错误,即:将《道德经》与《庄子》针对统治者所讲的东西,反而误置到普通的常人那里去了(10)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中将道家思想定位为“超越的反智论”,以为老子反智论聚焦于政治思想,而庄子的则聚焦于人生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以道家反智的代表性看法[19]。。在古典语境中,“无为知主”关联着的不仅不是反智主义;而恰恰相反,体现的是统治者的“大智”:“非不用知也,以知止于不知,知效其用,而不知操其棅,所以为大知也。”[15]179这里内蕴着一个深刻的生存论真理,不论是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个人修身的层面都是成立的,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伴随着认识到自己之无知的,并不是将自己托付给某种智慧者的象征——“神”,或者终身以朝向这种“神”展开自己的生活,而是不再“以一人之知盖天下”[20],向同样无知的众人开放自己,通过向普通而平凡的人们——他们日用大道而不自知——开放自己,这本身就是圣智者自身那没有身位的身位(11)章学诚如下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21]。
综合以上的讨论,《应帝王》之“无为”思想包含四项表现:其一,统治者不做名尸的承担主体,而将之还给被统治者;其二,统治者不做谋略的府库,而将此府库向天下人开放;其三,统治者不自己任事而让被统治者各任其事;其四,统治者不以一人之知盖天下,而以调动激发天下人之知以治理天下。在“无为”思想的以上四种表现中,始终可见无为思想的两个维度,即统治者的无为与被统治者的有为,二者具有共构关系。统治者唯有以自身的“无为”,才能激发被统治者的积极“有为”;唯有基于被统治者的积极“有为”,统治者的“无为”才能获得“无不为”的功效——既是一种“无功之功”,但同时也是功效的最大化[22]。但就被统治者而言,哪怕是积极的活动,只要是出于或合于其性命之情的,也是“无为”;然而,这种“无为”只是相对于统治者的“无为”而言,才可以视为一种被“无为”引发并受到引导的“有为”。
三、“为无为”:治教分殊下的明王之治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可谓“为无为”的具体化,它所要达到的是抑制统治者的有意识、有意志、有欲望的“造作”,而让自己主动地处于一种无“作”无“为”的“被动”状态,唯独以此方式,才能承受天下人的有为和万物的并作,并进一步对后者加以引导。当天下人在统治者的调节、引导下,有序地自作、自为而并行不悖、互不相伤时,统治者的“无为”反而取得了“无不为”的功效:
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至乐》)
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知北游》)
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庚桑楚》)
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则阳》)
“无为而无不为”必须在统治结构的层面加以理解:无为是一种统治活动,其实施主体是统治者;“无不为”的功效则无法脱离作为被统治者的“天下人”来理解,虽然它未必意味着天下事无不得到合理的处理,但应当包含着天下人皆能得到有序化安顿;对于天下这个开放性的政治场域而言,其秩序绝非王者一人之事,而是天下人的共同责任。“无为之为”是这样一种活动的机制,它虽然由统治者实施,但却引发被统治者的积极参与。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的矛盾在社会层面以社会化方式加以化解,社会是人民的社会,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因而“无为之为”意味着,将社会还给社会,将天下还给天下人。“无为”的主语必须被限定在统治者那里;而在一般常人那里,“无为”只是其个人的自修,并不能达到引发天下人自为进而达到“无不为”的功效;如果将“无为”的主语转换为教统的圣人,那么它只能表明教化的方式必须采取启发性、引导性的方式,这是最高的教化方式,但是对于有德而无位的圣人而言,其无为本身不必也未必能保证“无不为”的功效。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告别了三代以上“治出于一”的秩序格局,精神于权力分离的结果是“治出于二”架构的形成,即圣贤为担纲主体的教统与君主为担纲主体的治统的分化。在这一语境中,圣人与明王的角色有着本质的不同。圣人作为确立人极的典范,它可以是一切卓越智慧与伟大品质的集大成者,甚至被符号化为“神—人”(God-man)。譬如:基督教中的耶稣基督,被构思为全知全能、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知晓一切、会聚一切优美良善品质的伟大位格,即人即神,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又如,孔子作为教统的圣者,被符号化为中华文明人格化身。但这种人格,在“治出于二”的语境中,只是在教统内部才有可能。对于治统的君主而言,绝无可能,因为王者不再是“治出于一”的神王(God-king),它们只是“人王”,“明”而非“神”,才是其合理的品质;在“治出于二”的语境中,任何将王者神圣化的方式都将失去正当性,被视为僭越天道的表现。作为政治社会的“一位”或“一爵”的王者,其核心品质即是明白自身的限制,即便是王者个人在德、能、力上达到相当程度,自恃其本人的智德和能力的方式,也达不到统治的正当化[23]。自三代以上的宇宙论帝国秩序解体之后,人性论或心性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业已替代神圣宇宙论,成为天道、天命的新的承载或新的通道,而这时的人性或人心并不能被限于统治者,而是面向天下人,每个人皆可以自尽其心、自知其性的方式沟通天道,这种沟通天道对于天下人而言,就是自正性命的活动。王者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便在于为天下人的沟通天道、自正性命提供秩序的担保,但它本人却不能构成天下人自正性命的典范与榜样,承担典范与榜样的主体已经是教统内的圣人,而不是王者。王者与生者之于天道,因而有不同的上达方式。
在古典思想中,圣人的品质被构想为与天道相似的生生之“明德”,而王者的品质被理解为与天道相通的“玄德”,玄德之所以为玄,乃是因为:一方面,它隐身于天下人以“明德”为榜样而自正性命的背景视域之中;另一方面,它是“无为”的方式抵达“无不为”的功效。“明德”与“玄德”与其被理解为儒家与道家两个学派的差异(12)很大程度上,《道德经》所谓的圣人仍然是指在位的统治者,而不是作为人伦典范、百世之师的圣者,或者作为体现生存真理、智慧、生存美学意义上的真人。而战国时代的《庄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中已经有明显的圣王分殊的意识,尽管这一点或许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毋宁当被置放于同一个真理的两种不同层面来理解;我们尤其不能简单地以为“明德”与“玄德”二者之间,非此即彼,此是彼非,彼非此是,以至于只能在其中选择其一。在规范性的意义上,教统的圣人与治统的王者分别继承天德的生生维度与无为维度(13)《道德经》虽然提及“圣人”与“王”,但在很大程度上,“圣人”在其语境中仍然是“有位者”。如第二章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显然并不能理解为治教分离下的圣人,而是“有位”。第三章的“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更能看出“圣人”在《道德经》中作为有位者的特点。。宇宙之运化整体及其过程,本是无尽的气化,本无所谓终极决定者,或终极因,其中有偶然与演化的要素,也有必然之理与不得不然之势,之所以将宇宙的运化委之于“天”,正在于这种运化过程及其整体在最终意义上超出了人的知能畛域,非人所可逆转,非人所可主宰,而“天”在这里不过是宇宙整体运化之“自然”的虚拟表达。一切决定论、完全透明化以及(排除混沌的)彻底规则化的构思,都只是从人的视点加诸宇宙的结果。如同众多有其生存周期的物种一样,人类生存在宇宙的无尽运化过程中,只是宇宙过程中带有瞬间性与偶然性的插曲。这是从宇宙整体演化进程及其现象性层面可以看到的事实。但人本身却不会这样看待宇宙,人并不会如其所是的接纳偶然、变易与自然。人在宇宙的运化中体悟天道(即:《荀子》所谓“天行”、《庄子》所谓“天运”),在天行、天运中领会天德。其实宇宙本无所谓天德,所谓天德只是人在观察天运、天行过程中看到的某些稳定性的品质,天德之为天德,离不开人类的“看作”。船山在解释《在宥》云将、鸿蒙一章时说:“无形无体,无明无冥,含物而忘物,与物同而不同乎物,此天地之本体,而于人为心。”[24]这里刻画的天地与物的关系——“天之含物而忘物、与物同而不同乎物”,同样也适用于人(尤其是人心)与物的关系。天德主要显现在天与物的关系上,而人心所理解的天德同样在人与万有的关系上。
在天德的理解上,有“生生”与“无为”两种模型或取向。《周易·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又《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礼记·中庸》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以《系辞》与《中庸》为代表的儒家式理解,是以圣统消化帝王之统为前提的[25],其意义在于为教统畛域的圣道张本,为教化提供依据:“生生”作为天地之大德,与圣人作为人伦之至、百世之师的形象是相通的,圣之所以为圣,在于他是体现人性高度与深度的典范,他被构想为人性的最高可能性——完美地体现了天地之德。儒家以仁统人道,而以生生不息为仁之实,正见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接续并推进生生之天德,对于一切个人而言,生生便是实有的内在品质,是自立、自得、自成的根据。圣人之道在于将在天之乾德(健)与在地之坤德(顺)合一于圣人自身。是故孔颖达解“天地之大德曰生”时说:“明圣人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常生万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26]619[27]生而不有生,不生而物自生,即将生之所有归于万物,天之生物实即万物之自生,这是生生与无为的连接处(14)韩康伯注“天地之大德曰生”时说:“施生而不为,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28][26]349孔颖达解《易》之“复”卦时说:“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天地之心也。”[26]132即以无为解释天地之心,而所谓天地之心,实即天地之德。朱熹即便仍然坚持天的主宰义,但还是强调万物的自生与自然:“天只是一气流行,万物自生自长,自形自色,岂是逐一妆点得如此!圣人只是一个大本大原里发出,视自然明,听自然聪,色自然温,貌自然恭,在父子则为仁,在君臣则为义。从大本中流出,便成许多道理。只是这个一,便贯将去。”[29]。事实上,在《易传》中,“生生”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传》)的意思相通,《尚书·盘庚》四次言及“生生”,而所谓“生生”即“易”,意思就是改变、迁徙、变通(15)焦循《尚书补疏》卷下:“《盘庚》凡四言‘生生’,《传》皆以‘进进’解之,意殊不豁。余谓,《易传》云:‘生生之谓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为‘易’字训释,‘易’者,改变之义,可与此经互明。此经‘生生’指迁徙言,谓变通也。”[30]。“生生”是面对无尽变易过程,通过不断地随时变通、协调而达成的在时间中的恒久性持续。《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的恒久就在于生而不有,而所谓的生也并非天地的自生,而是让万物自生。不自生而让物自生,就是天道(天地之道)的无为品质。
先秦道家更强调天道的无为品质,无为的主体内容是不盲目干预、不强硬介入,而意在让天下自为、自治,这是安天下即是与天下自安的方式。“无为”并不指向一切个人的德性,不是每个人性命之情的固有内在内容,因而它不是天下人的自修之道;而只是一个人对于他人性命之情的承认、尊重、不干预。在伦理生活上,它并非共同成就的积极伦理,而是彼此不干预、彼此不强力介入的消极伦理;在政治层面上,它则指向对统治者的活动的限制,即:不是去积极介入、参与、改造天下人的性命之情,而是让天下人的性命之情以其自身的机制运作。因此,对于明王而言,无为的目的不在于明王个人之自修,而是意在尊重天下人性命之情的前提下引导天下人之自治。
但无论是教统的生生,还是治统的无为,都与天地之德相通。天地不能理解为万物之上的主宰者与支配者,主宰与支配的想象乃是将社会性法律创制所依托的所有权想象投射到自然秩序中的结果。我们要注意的是,天地并不能被指认为万物之上的实体,天地只是无心的气化过程的整体及其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呈现出来的作为人道(圣道、王道)效法根据的“天地”,它既不是天地之形体,也不是天地之气化,也不能在直接意义上就是天地之道,而是天地运作过程中对人彰显出来而又被人效法的品质——天地之大德。我们历史地看,作为天地之德的“生生”往往被视为治和教的共同根据(16)譬如曾丰《缘督集》卷十四《六经论》记载:“‘生生之谓易。’夫生生者,子丑寅之气也,而圣人托焉,有以哉。断曰:易,东北之运气也,天地于焉生物,羲农于焉生治,孔子于焉生教。”[31];而《庄子》则将天地之德视为圣道、帝道的共同根据,只不过其所谓的天地之德的内容更多地被理解为“无为”(17)《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钟泰指出:“言帝道,圣道而先以天道者,帝道、圣道皆本乎天也。”[15]284。在规范性的意义上,“生生”与“无为”是对人显现的天德;人之所以视之为天德,乃是基于生存论的取向,尤其是政治社会中需要以统治的方式达成秩序、文明社会中需要以教化的方式达成生存的意义,这两者分别是王者与圣人的使命。王者之所以效法天德的无为向度,乃是因为统治虽是王者实施的行动,但其所指向的目的却是政治共同体的所有人的各正性命,而各正性命必须由每一个人自己承担,不可能由他者替代,王者及其统治的意义便在于激发并引导人们的各正性命,为之提供秩序的担保。圣者在文明社会中达成教化的方式,是将自身确立为人极,将个人的生命树立为意义饱满的榜样,以体现人性的最高可能性,这是必须由圣者通过对自身生命和生活的雕刻来完成的,故而圣者必须重视天道的生生品质。天道的品质,无论是生生,还是无为,对于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甚至对于天运自身,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只是人看待天道并以此继承天道的方式。
我们之所以说王者与圣者各以自身方式继承了天道,乃是因为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圣人为人性立极,教化天下人,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最大化地充实人性,使得人生在深度、广度、高度上达到极致,自然充实而有光辉,引发进取上达者,指示路标,不管这些人与圣人是否共处同一时地。王者只是一个政治社会或文明系统中的王者,只能在位时承担其职责,唯有以他自身的无为(具体而言,就是“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才能激唤起政治社会内部人们敞开性命之情的自为。因此,这是一种最少成本而功效最大化的统治智慧。正因为王者“外不为名尸、事任,内不为谋府、智主”,统治者本身才以虚化自己的方式(“我固无己”),而达到“名尸”“事任”“谋府”“智主”的最大化,这其中的逻辑就是,让天下人而不是王者成为“名尸”“事任”“谋府”“智主”的真正主体。以这样的方式,王者就可以做到“体尽无穷,而游无朕”[13]165。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四个“无为”所刻画的明王之所以为明王的品质,正与阳子居的“明王”——“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相反,阳子居所理解的明王其实是智慧、德性、能力集于一人之身的大成者,是一切卓越品质在其一人那里的荟萃者。这样的理解,其实是把教统畛域中的圣人错置为治统之内的明王。阳子居那里并没有王与圣及其职分的分殊化的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引导性机制的“无为”,关联着作为功效最大化的“无不为”,一旦脱离了天下人政治主体性的回归,脱离天下人本真性命之情的回归,就会下降为一种谋略,即通过对天下人的利用以达到统治权力的巩固。事实上,黄老学派与法家都意识到“无为”关联着的统治功效的最大化。譬如,如下的论述似乎与《庄子》极为相似:
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管子·形势解》)
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故其计失;与之举事,故其事败。夫计失而事败,此与不可之罪。故曰:“毋与不可。”(《管子·形势解》)
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韩非子·喻老》)
显然,《韩非子》与《管子》都以不同方式强调唯有基于无为的统治才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而无为之治在二者那里的核心则是尽最大限度动员、组织天下人,以实现有限统治的目标(18)清儒陈澧提出:“申不害之术,于此可见其略矣。其所谓无为者,本于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专自秘,臣下莫得窥其旨。”[32]。但问题是,它们缺乏《庄子》对政治社会的开放性理解,即将天下藏于天下人而不是藏于王者一人那里,缺乏对天下人性命之情的敬畏与引导。这就使得“无为”变成了“无不为”的技艺与谋略,而“无不为”仍然被限定在统治者设定的维护与巩固自身统治的目标上,政治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还给天下人;与此相反,《庄子》恰恰要最大程度地虚化统治者的政治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