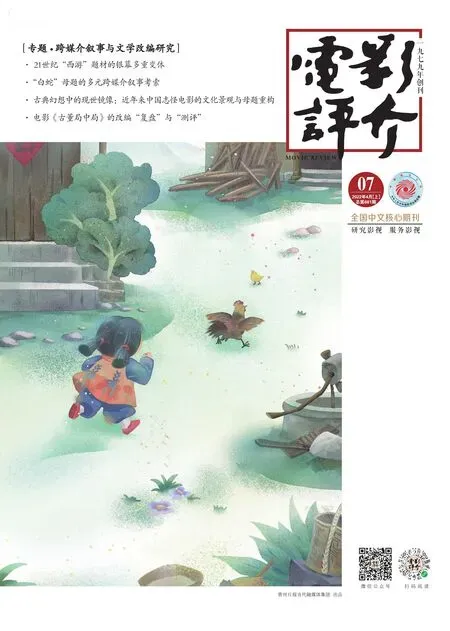21世纪“西游”题材的银幕多重变体
张 燕 赵 媛
《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包涵了众多精妙绝伦的故事,广为大众熟知。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灵感与素材来源于民间,汇集了自唐末至宋元时期关于玄奘西天取经的神异故事,兼具文学性与趣味性。鲁迅曾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评价:“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西游记》的版本、作者、内容曾被多次考证,不过接受度与流传度最广的依然是吴承恩的版本,影视剧也多以此版本为基础进行改编创作。
最早的“西游记”电影出现于1906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出品的京剧电影《金钱豹》首次将唐僧与孙悟空的故事搬上银幕。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史中,曾多次出现了改编《西游记》的热潮,在致敬经典的同时,融合了时代精神。“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盘丝洞”等故事被不断地解构重演,“孙悟空”“玄奘”“猪八戒”等人物不断变换姿态,这些影片在戏谑狂欢中展现了不同时期大众的情感诉求与审美文化。此外,《西游记》改编电影也成为建构东方魔幻主义的炫技乐园,通过视觉奇观将现代性与中国神话相结合。
一、《西游记》的经典改编
《西游记》曾多次被搬上银幕,通俗化、娱乐化的改编赢得了观众的持续性喜爱。杨洁执导的1986年版电视剧,更是令《西游记》的故事与人物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多次出现《西游记》的改编热潮,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武侠神怪片、60年代邵氏改编、90年代“大话西游”以及21世纪以来的西游系列电影等。《西游记》的长盛不衰,既离不开原著的经典与丰富,也与改编者锐意创新、不断注入新的时代精神有关。
(一)原著的经久不衰
《西游记》的创作来源于“玄奘取经”的真实历史,从现实出发,走向了神佛妖魔故事,在虚构故事中,融入对宗教的感悟与对现实的思索。玄奘取经的经历曾被其弟子记录为《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卷更侧重于记录沿路风土的地理风俗,不过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或许曾为小说提供了材料,如卷十一记载的西女国;之后,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加入了部分神仙志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出现了孙悟空的雏形“猴行者”,开始从历史小说转向神魔小说;此外,戏剧方面如《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等多种形式,都为后来的《西游记》积累了素材。
胡适评价《西游记》“以诙谐滑稽为宗旨”,称它“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戏言寓诸幻笔”,将谐谑与奇幻结合,以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描摹神魔鬼怪,作者吸收民间文化,并从宗教文化、志怪小说中汲取营养,将现实与想象融合,突破传统的桎梏,在西游世界中展现世间百态。“《西游记》的嘲谑则含蓄与夸张兼备。含蓄时,旨微语婉,令人会心莞尔;夸张时,锋芒毕露,使人捧腹喷饭。”故事中既有俗世的烦恼与诱惑,如八戒经历的多次情欲考验;又有佛性的超脱与顿悟,如第24回唐僧问“你说得几时方可到?”悟空答“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西游记》也有不少续篇,最为出挑的当属董说的《西游补》。《西游补》与《西游记》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包括作者在内承认《西游补》为《西游记》的补缺;另一种则认为《西游补》是独立性的创作,与《西游记》原著的情节主题大相径庭。林佩芬认为《西游补》自《西游记》第61回补起,“中途演化出另一个体系、另一种局面中多彩多姿、奇幻绝妙的故事来”,它“是创作,而非吴承恩《西游记》的续作”。这种争议同样适用于《西游记》的改编电影,创作者从西游的背景和人物设定出发,讲述全新的故事,是否已经完全地脱离原著,变成了不相关的独立体。然而,正如德里达所认为的整个文本世界是一个差异系统,每一次阅读都会制造出一种“起源”或“在场”的幻影,幻影的不确定性将差异性推及至文本脉络与集合中。“续书、补入、改写,作为一种‘修正的阅读’,自有其发生的因缘,有情志补憾的功能,也有作者个人的偏见。”因此,《西游记》本身的内容丰富性与主旨多元性,为之后的延展创作提供了灵感,改写、改编反作用于这本经典著作,不断扩充着“西游”的文本宇宙,令其经久不衰。
(二)电影化历程:持续的改编热潮
《西游记》的第一次改编热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西游题材的“武侠神怪片”兴盛,根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记录,仅1926—1930年间出品的《西游记》改编影片就有二十多部。这些电影往往迎合了20年代古装片的潮流,从传统文学与民间故事中获取素材,集武侠打斗、神怪与艳情为一体。上海影戏公司充分认识到“《西游记》为中国著名说部,寓有哲理,欧美各国无不迻译,早成全世界传诵之作”,故“将全书分编摄制成影片,分十集,每集自十本至十二本”。杜宇的《盘丝洞》(1927)便是典型的改编作品,《申报·剧场消息》称“《盘丝洞》一片,轰动全沪,其情节之热闹动人,早经脍炙人口,无烦赘述。”可见该片在当时叫好又卖座。
第二次改编热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地出品了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0)与动画电影《大闹天宫》(1961),后者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借鉴了京剧、脸谱、版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充分发挥了民族审美的优势,达成了艺术性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此外,在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邵氏公司著名导演何梦华执导了《西游记》(1966)、《铁扇公主》(1966)、《盘丝洞》(1967)、《女儿国》(1968)等系列电影,将传统的动作片融合特效技术。第三次改编热潮出现在90年代,当时的文学改编电影迎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过程亦悄然地完成了由8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向90年代经济奇迹和物质、经济拯救的现实与话语的转换。完成了由精英文化的(指点江山)朝向大众文化引导,重构社会的转换”。在此语境下,刘镇伟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1995)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大胆地解构古典文学,利用戏拟的手法消解改写原作的人物关系与时空设定,拼贴、戏谑化的语言曾在当时掀起一阵“大话西游热”,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也成为了众多观众的青春记忆。
21世纪以来,《西游记》改编电影大部分延续了90年代“大话西游”的娱乐解构,刘镇伟的《情癫大圣》(2005)突出爱情主题,《大话西游3》(2016)以无厘头风格重述孙悟空与紫霞仙子的爱情故事;周星驰执导的《西游·降魔篇》(2013)和徐克执导的《西游·伏妖篇》(2017)沿袭了港片一贯的恶搞喜剧风格,颠覆人物形象,并充分利用技术构建奇观化场景;郑保瑞的系列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2016)《西游记之女儿国》(2018)借用原著里的人物,讲述现代性的新西游故事。这些由香港导演执导的电影,多选择在春节档上映,并用当红明星与老戏骨演员进行搭配,“西游记”这一老少皆宜的题材与合家欢的气氛非常契合节日氛围,因此往往能够获得高票房,这也成为“西游记”这一经典IP不断重拍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也出现了以西游人物成长为主线的衍生故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和《悟空传》(2017),“孙悟空”的个人形象被全新演绎与解读。
二、21世纪改编特点:《西游记》的现代重构
《西游记》作为一部内韵丰富的神怪小说,文本涉及宗教、地理、历史、诗词等多种文化。21世纪以来的创作者从“西游”出发,依托个人对原著的理解,在考虑观众接受度与市场消费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了“超文性”改编,派生出全新的故事。吉拉尔·热耐特曾对“互文性”与“超文性”进行定义,一方面,他将一篇文本在另一篇中切实地出现(即“再现”)称为“互文性”;另一方面,他又将一篇文本从另一篇文本中被“派生”出来的关系命名为“超文性”。他所称的超文是“通过简单转换或间接转换把一篇文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西游记》的超文性改编,对原有的故事、主题、人物、结构多方面进行现代性的重构,延展了西游的原有文本。
(一)人物形象重塑
后现代的大众文化是“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将文字语言转换为图像符号,派生构建出新的影视形象,投射出与时代精神与审美接受相关的新诉求。《西游记》从文字转向影像,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唐僧等人的影视化形象最为深入人心,然而它同样包含了创作者特定的倾向性。21世纪以来,《西游记》中的人物更是被不断地解构重塑,在部分保持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更具现代性的特质。
首先,外在形象上,原著中对孙悟空的外貌描写为“七高八低孤拐脸,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电影常常弱化他的妖魔性,强调其人的特质和“美猴王”的形象,六小龄童演绎的孙悟空最为典型。郑保瑞系列电影中孙悟空的外在形象相对保守还原,周星驰和徐克的“西游篇”则在视觉形象上进行了全新的改造。《西游·降魔篇》中的孙悟空有三个造型:秃头奸诈的大叔、贴合戏曲的精巧猴王扮相和战斗力爆满的巨猩,《西游·伏妖篇》的悟空也多以人相而非猴相出现。这两部电影改动最大的当属猪八戒的外形,除了猪的本体形象外,他多以油面书生出场,纯白脸谱搭配红色大烟熏妆,浮夸又滑稽。这些形象的变动创新,令西游记展现出了全新的风貌,带来颠覆的新鲜感与惊奇感。
其次,人物的行为模式与内在心理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一直以来,孙悟空的反叛形象深入人心,1961年的经典动画《大闹天宫》更是配合时代背景,放大了悟空“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战斗者姿态。原著前七回描述了孙悟空的出生、学艺、称圣、大闹天宫等经历,他的初始状态尚未开化,带着天真的野蛮。中国台湾学者罗龙治认为孙悟空在未皈依佛教以前与其他从天界逃出或散居地上的妖魔无异,都是没有是非观念的非道德动物,无限制地追求满足。孙悟空在之前的影视化中多以正面积极的形象示人,然而在21世纪的改编作品中,开始展现他妖魔化的一面,如《西游·降魔篇》中的绝对利己主义,他为逃脱五指山设局,杀害众人。在《西游·伏妖篇》中,孙悟空甚至几次产生杀害唐僧的心思。孙悟空不同以往的邪恶形象颠覆了观众的常态认知,虽有争议,但某种程度上却与原著中的初始心性相通,既是创新,也是回归。
在原著小说中孙悟空是一个“无性”之人,生于仙石,与情欲隔绝。第23回“四圣试禅心”,寡妇招赘,唐僧说“悟空,你也在这里罢。”悟空答:“我从小儿不晓得干那般事,教八戒在这里罢。”原著中的孙悟空没有情关,曾有后人续写行者的情难。董说的《西游补》以“情”贯穿全文,将文人的精神世界投射于悟空的心境遭遇之中,借“西游”喻史,感叹时局。电影化的孙悟空也是如此,他不再是无性无情的灵猴,而是在遭遇情关后获得成长:“大话西游”中他与紫霞仙子上演时空穿越之爱;《悟空传》中与阿紫相识相知;《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中与白狐狸相依相伴。另外,最为清心寡欲的三藏同样陷入了在“大爱与小爱”的取舍之中。《西游·降魔篇》与《西游·伏妖篇》中唐僧与段小姐、小善都有感情戏份,对段小姐的情感更是成为他彻悟的重要原因,《一生所爱》的旋律成为他降妖和取经路上的法宝与寄托。《西游记之女儿国》更是直接将“法性西来逢女国”的故事重构扩展,出现了“我舍我的王权富贵,你守你的戒律清规”。爱情元素的加入,加强了故事的通俗娱乐性。
此外,人物关系也进行了更为现代化与平等化的处理,如唐僧与孙悟空之间的师徒关系。《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五行山下沉寂了五百年的孙悟空被童年唐僧江流儿误打误撞地解除封印,两人相伴,踏上冒险旅途,在这个过程中江流儿感化并激励悟空,使他重新找回初心。《西游·伏妖篇》中孙悟空对于唐僧在公众面前惩罚自己,令自己受辱的行为感到不满,唐僧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道歉,两人勾肩搭背,比起师徒,更像兄弟。
(二)故事选材与“超文性”创作
《西游记》的影视化改编在选择故事上趋向雷同,在进行二次创作后,派生出不一样的新内容。胡适曾将《西游记》按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齐天大圣的传(第一回至第七回);第二部分为取经的因缘与取经的人(第八回至十二回);第三部分为八十一难的经历(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第一部分为悟空个人的成长史,对照改编多突出“反天宫诸神捉怪”,郑保瑞的系列电影第一部便是“大闹天宫”。《悟空传》虽为衍生小说改编,但其剧情重点仍集中在悟空与天庭的矛盾争斗上。这些电影中的悟空“与天斗”的行为动机要更为明确,也更为世俗化。《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中牛魔王从中作梗,挑拨悟空与天庭的关系;《悟空传》里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有被动无力的一面,然而却依然决心与命运抗争。
原著的第二部分以玄奘为主,对照影视改编变动更多,杂糅了众多其他的故事元素,并将多个人物汇聚到同一场域中。玄奘取经的故事来自于真实的历史,从史实出发的电影作品《大唐玄奘》(2016)与《西游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1986年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对这一部分做了相对完整的表现,交代了唐太宗与三藏的关系,却删减了第十回的“唐太宗地府还魂”。第十回在影视改编中极少出现,李珞的《唐皇游地府》(2012)是对《西游记》的精妙改编,他将西游故事搬演到21世纪的当下现实,唐太宗变成企业老总,龙王是夜总会老板,阎王为黑社会老大,他们操着武汉方言,在城市里交际游荡。创作者在新说西游中,戏谑地展现了社会现实,充分继承了《西游记》揶揄百态的精神。《西游·降魔篇》虽以玄奘为主角,但是已与原著全然不同,更侧重于以爱情为主线,同时串联起徒弟三人的出场与身世。
第三部分的八十一难中,影视改编偏好“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法性西来逢女国”“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盘丝洞七情迷本”等回目,白骨精、蜘蛛精、铁扇公主、牛魔王、红孩儿等人物被多次塑造演绎。这些篇章美艳女妖的魅惑性强,增强了视觉观感;涉及情爱纠葛,改编空间大,受众更广。《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的白骨精形象贴近西方魔幻电影中的女巫形象,故事并无太多的新意,创新多体现在视觉建构方面。《西游·伏妖篇》的白骨精化为纯良无害的少女小善,并对唐僧产生了爱恋之情。此外,这部电影中也出现了蜘蛛精、红孩儿等经典人物。《西游记之女儿国》从唐僧与女儿国国王的相遇,便是经典的爱情片设定,一眼倾心。
(三)主题背后的文化演变
《西游记》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不受拘束的想象力与跌宕起伏的故事,还在于它历久弥新、鞭策时代的精神内核。电影改编作品也在继承其精神的同时,融入了当下的人文反思与现实批判。
首先是对于“驯伏”的多元化解读,由强调集体意识转为突出个体的独立性。“《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西游记》以孙悟空的出生反抗为开篇,未开化的石猴被佛祖收于五行山下,后与唐僧踏上取经之路,逐渐参悟佛道。这一过程既是心性的培养,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驯化。在《西游记之大闹天空》中,孙悟空答菩萨:“我看到自己,却也看不到自己。”而“‘空’的消极面,是指殊相的消失,个体的不存。”郑保瑞电影中悟空自身的反叛性较弱,更偏重于“空”,在争斗过后,与固有的意识形态达成和解,是一种甘愿“招安”状态。他的后两部电影中悟空已完全是坚定的意识形态工程的维护者,在《西游记之女儿国》中,他对于取经的执念比唐僧还要深刻。不过,周星驰、徐克的“西游篇”则保留了原著中更初始的悟空状态,甚至加重了“恶”的一面。《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悟空传》更强调反叛精神与斗争精神,是对原著“驯伏”的现代颠覆。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改编者对于悟空的“皈依”有着不同的理解,郑保瑞侧重于维护集体和谐,强调心性修行;其它电影则更注重真实的人性,并放大了悟空的叛逆姿态,打破清规戒律,传达对自由的向往。
其次,加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注重平等化。《西游记》改编电影不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价值,那些符号化的妖魔开始由扁平走向丰富。《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白骨夫人并不是十足的恶人,她也是被村民抛弃、被他人嫁祸、执念无法散去的可怜人。唐僧不忍悟空伤人,即使面对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白骨精,依然不惜牺牲自我来度她轮回,将“善”无限地放大。原著第17回中,观音道:“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唐僧也曾说过“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神与妖只是在一念之间,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别。《西游记》的改编电影逐渐以更平等化的现代视角看待人、神、妖之间的关系,取经之路是为众生,然而路途中相遇之妖也是众生的一部分。
最后,完成了从英雄主义向平民视角的转化,更贴合现实,传达出奋斗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孙悟空不再是毫无畏惧的齐天大圣,他也有颓丧软弱的一面,在沉沦中被善意与鼓励唤醒;玄奘也不再是不被世间红尘叨扰的圣人形象,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和伪装,也会面临情关考验。这些改编使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更容易获得共鸣。
三、消费主义视域下的古典文学改编
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艺术,在从文字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随着电影消费市场的繁荣与IP盛行,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成为了创作者挖掘素材进行二次创作的重要资源。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严格地说,物品的本质或意义不再具有对形象的优先权了。”《西游记》的电影改编迎合了观众的审美与消费需求,在发挥经典魅力的同时,不断进行娱乐解构,并试图打造东方魔幻主义,呈现奇观化的视觉狂欢。
(一)东方魔幻主义建构
近几年民间故事与古典文学不断地被搬上银幕,被人熟知的内容通过超文本性创作与视觉奇观建构,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单是“白蛇传”就被先后改编为《白蛇传说》(2011)、《白蛇:缘起》(2019)、《白蛇2:青蛇劫起》(2021),与“封神榜”相关的也出现了《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等作品。同《西游记》的改编电影一样,这些电影都对人物与故事进行了重新演绎与解读,并借助数字技术,融合传统的中国神话与西方魔幻元素,构建奇观景观。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服妆、场景设计非常西化,白骨精的造型与中国神话中的女鬼形象相差甚远,身着白色或黑色斗篷,更像是迪士尼中的经典女巫形象。蛇妖、箭猪妖、蝙蝠妖的形象设计突出身体曲线、手臂纹路与耳朵异形等特点,这些妖怪的设计融合了《山海经》与西方怪物的元素。场景方面,设计团队想要表现出让人信服又有陌生感的效果,因此加入了很多中东异域元素,如阿富汗、斯里兰卡等,西行过程中的戈壁滩借鉴了曾经辉煌的古格王朝等历史遗迹。此外,在云海西国中也将东方主义油画融入其中。这些景观搭建与设计巧思,打破了观众对于西游的视觉想象,带来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奇感。《西游·伏妖篇》同样突出了特效技术的使用,电影设计了三场大型打斗戏,将武术与技术结合。红孩儿的形象设计是最具代表性的融合实验品,戏剧脸谱化的恶童脸搭配机械化的身体,充满新旧混合的怪异浮夸之感。
然而,在构建视觉奇观夺人眼球的同时,也常常陷入过分依赖技术的危机,视效投入远大于剧本精化,造成故事混乱与叙事脱节。此外,将西方视觉搬运到东方神话中,打着构建东方魔幻主义的旗号,实际常会陷入水土不服的“四不像”中,甚至在观看“西游”电影时产生了在看“哈利波特”的错觉。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地讲好中国神话,在创新的同时,保持本土的特色,充分表达东方的想象力,依然需要创作者进一步思考与实践。
(二)娱乐解构古典文学
《西游记》作为古典文学广为流传,其内在的想象力与游戏化的故事情节深入人心。它来源于民间,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它文本的传奇性、自带的通俗性与亲切感才是被不断电影化的重要原因。然而,《西游记》的改编始终面临着争议,1927年的《盘丝洞》在赢得票房的同时,也曾因尺度问题被批评“艺术之堕落,至是亦堪称观止”。如今的改编,面对的批驳大多集中在远离原著、娱乐无底线、叙事混乱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末,刘镇伟开启“大话西游”,自此拉开了对于西游的后现代解构的帷幕。这些无厘头的戏谑背后裹挟的狂欢精神,打破了时空与文化阶层的限制,更贴近于大众。语言变得碎片、杂糅与拼贴,颠覆性地阐释传统文本,英雄人物转为平民主义,在嬉笑怒骂中,充满了现代社会的玩味性嘲讽。表演性的人格也延续到了21世纪的“西游”电影中,《西游·降魔篇》群众演员的生硬演技将这种浮夸的虚假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过分强调喜剧性与商业性,一味迎合市场,追求突破创新,也造成了部分影片在叙事上不符合逻辑。他们只是借用《西游记》的设定,其内容与精神完全脱离了原著。《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将最大反派设定为牛魔王,对于天庭权力的渴望,致使他策划了一场骗局,误导悟空与天庭斗争。电影中的玉帝反而是正派形象,甚至带着与世无争的飘逸随和气质,时不时与悟空悠闲地对话。这与原著的态度迥然不同,小说在对待悟空与天庭斗争时秉持着相对客观的中间派立场,斗争双方没有明确意义上的对与错。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并非儒和佛,或道和佛,或儒道释和白莲教,但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初始状态的悟空以自我为中心,其与天庭的对抗,是为自我欲求的满足,带着人性中的童心,因出发点的直接性与单纯性,在庞大的意识形态面前,反而彰显出难能可贵的自发性与反叛性。而郑保瑞电影中的孙悟空却沦为了工具性人物,被双方利用,缺乏独立性。
(三)奇观下的改编反思
21世纪以来,《西游记》的改编往往以系列电影的形式开展,这种方式,一方面能够不断拓展IP内容,保证创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能收获一批固定的观众,形成粉丝效应。前篇的成功往往能够带动下一部影片的创作,并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如《白蛇:缘起》的成功令观众更加期待同系列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此外,近几年由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姜子牙》《风语咒》等国产动画电影的热映,掀起了一股国漫热,也促使众多影人投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IP的开发工作之中。
将古典文学与民间故事改编为电影,既能为电影注入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把时代精神融入古典文学中,达成文本的交互与超越。然而,在改编创作中也需要把握好尺度,解构与创新不能完全脱离原著;在利用技术制造视觉奇观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民族的审美文化,不能一味地仿制西方;在消费主义视域下,既要考虑受众,也不能过分低估观众的审美水平,一味标新求异。颠覆认知带来的不一定是新奇和喝彩,也可能会令观众感到智商受到了侮辱。
结语
《西游记》以其文本经典性、故事丰富性及受众广泛性的特点,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古典文学IP。通过对照原著与电影文本,基于后续银幕创作与改编的超文性,使得“西游”宇宙被不断拓展。21世纪以来,《西游记》改编电影在沿袭经典的同时,还进行了现代重构,故事在忠于原著的同时加入了全新的想象,人物形象持续由英雄主义向平民主义转化,主题突出了人文性、独立性并更贴合现实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展现出当下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