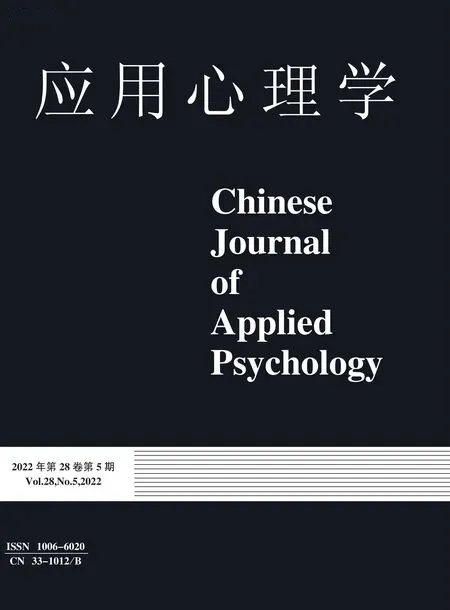不同认知资源下情绪调节策略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范 宁 张 晨 靖淑针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保定 071002)
1 引 言
个体在道德两难决策中,往往会伴随强烈的情绪体验和认知冲突。道义论决策指无论损失多大都不会做出伤害行为,功利论决策则反映了人们为避免更大损失而伤害他人的倾向(Greene,2009)。道义论决策由情绪驱动,功利论决策则由认知推理驱动,情绪和认知推理会针对道德决策中的矛盾冲突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个体的道德决策(Han,2017)。
情绪在道德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Zhang,Kong,& Li,2017)。消极情绪如厌恶、愤怒、悲伤等会增强道德两难问题中的道义判断(Szekely & Miu,2015),而积极情绪则会增加功利判断(Valdesolo &DeSteno,2006)。有关情绪脑区受损病人(Moll et al.,2018) 和高精神病性特征者(Pletti,Lotto,Buodo,& Sarlo,2017) 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发现。另外,两难情境带来的情绪体验的强烈程度也会影响道德决策。若两难情境满足:对目标对象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伤害指向某一特定个体或人群、伤害是由于转移现有威胁造成的,则被称为“个人”情境,否则称为“非个人”情境(Greene,2009)。个人情境相较于非个人情境,会引发更多的情绪反应,从而促使个体做出道义判断(Moore,Lee,Clark,& Conway,2011)。
有效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改变道德决策的倾向。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前者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早期,通过改变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观点态度,降低情绪反应;而后者则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通过控制外显表情来压抑情绪,减少情绪体验(Gross & John,2003)。有研究要求被试判断无害但会引起厌恶情绪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错误,发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被试在道德判断中所需时间更长,对直觉反应的依赖程度更弱,厌恶感下降,同时降低了对行为选择的不道德评价 程 度(Feinberg,Willer,Antonenko,&John,2012)。Szekely 和Miu(2015)让被试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是否接受”的行为选择,发现与自我相关的情绪在道德决策中占主导地位,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功利判断,而表达抑制则没有影响。然而,Lee 和Gino(2015)的一系列研究却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无论是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是否判断”还是“怎样做”的决策,表达抑制都能使被试做出更多的功利判断,相比于视频材料,认知重评只在困境以听觉方式呈现时增加了功利判断。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实验所用视频材料导致个体的卷入程度过高,情绪唤醒度过强,从而难以进行认知重评。
然而,认知重评的失败也可能是由于视频刺激的加工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Recarte&Nunes,2003)。认知资源对道德决策有着显著影响,当被试处于高时间压力(Rosas&Aguilar-Pardo,2020)或高认知负荷(De Neys&Bialek,2017)时,道德决策过程更多依赖于快速的直觉系统,从而产生更多的道义判断。这说明功利判断需要的认知资源相较于道义判断更多。根据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Gross,1998),认知重评是通过改变情绪的前因来调节情绪,需要的认知资源可能较多;而表达抑制则是直接改变情绪的反应,需要的认知资源可能较少。两种调节策略对道德决策的不同影响可能受到认知资源的调节。
综上所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尚无统一结论。本研究从认知资源角度探讨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明确情绪调节在道德决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认知机制上的差异,进而为情绪调节手段在道德决策中的应用提供证据,并为道德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的实证依据。实验一采用时间压力范式,控制被试可用的认知资源,即时地影响调节策略的使用和道德决策过程,以探讨不同调节方式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及其对认知资源的依赖程度。实验二使用Stroop 范式,在道德决策任务之前操纵被试的认知资源损耗水平,对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究。本研究假设,在认知资源不受限时,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都能增加被试的功利判断;而在认知资源受限时,与认知重评相比,表达抑制会增加被试的功利判断。
2 实验一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117 名(男性56 名),平均年龄22.10±2.59 岁。被试无身体疾病和精神障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2.2 实验设计
2(时间压力:有、无)×3(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无)×2(困境类型:个人困境、非个人困境)的三因素混合设计,被试间变量为时间压力和情绪调节策略,被试内变量为困境类型,因变量为功利决策百分比和决策的不道德评价分数。
2.3 实验材料与程序
首先填写修订的情绪自评量表(Gross,1998),其中消极情绪包括:恐惧、悲伤、同情、内疚、愤怒、厌恶、后悔,Cronbach’s α=0.660;积极情绪包括:愉快、自豪、热情,Cronbach’s α=0.654(采用Likert7 点计分:1=完全没有,7=非常强烈)。分别将两类情绪的均值作为测量指标。
之后向被试介绍指导语,情绪调节策略指导语参考已有研究进行改编(黄敏儿,郭德俊,2001),其中,认知重评组要求“尽可能从多个视角去审视问题,全面地进行思考”;表达抑制组要求“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不让任何情绪表露出来,不让别人感受到你的任何体验”;无调节组则无特殊指导语。采用情绪调节检验表(李静,卢家媚,2007)对54 名大学生(未参与正式实验)的情绪调节策略执行度进行检验,发现两种调节策略均起到显著作用,ps<0.001。
对Lotto 等(2014)使用的30 条道德两难困境进行翻译改编,由心理学专业的6名研究生对项目叙述的清晰性与明确性进行评定,最终保留10 条,其中个人困境和非个人困境各5 则。为避免困境材料唤起过高的情绪反应,有利于情绪调节策略在被试的道德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Lee &Gino,2015),所有故事材料中不包含明确的情绪描述内容。被试在计算机上以随机顺序阅读10 个困境,每个困境前有1000ms 的“+”注视点,阅读完成后,先对困境中需要做出的伤害行为进行是否接受的判断,“接受”代表功利论决策,“不接受”代表道义论决策。其中,有时间压力组要求在8 秒内判断(Suter&Hertwig,2011);无时间压力组要求仔细思考后判断。然后对该行为的不道德程度进行7 级评分:1=极其道德,7=极其不道德。
最后,再次填写情绪自评量表,以考察情绪调节策略是否通过削弱个体对道德两难困境的情绪反应强度来影响道德决策。
2.4 结果
2.4.1 情绪自评分数
将情绪自评后测评分减去前测评分来衡量被试在道德决策中的情绪状态。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消极情绪中,情绪调节策略和时间压力主效应显著,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s(2,111)≥10.10,ps<0.001,η≥0.15,BF≥1043.24。简单效应检验发现,无时间压力时,无调节组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ps≤0.001;有时间压力时,认知重评组和无调节组显著高于表达抑制组,p≤0.003。
积极情绪的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2.4.2 功利论决策百分比
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1)结果表明,困境类型、情绪调节策略和时间压力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s ≥11.52,ps ≤0.001,η≥0.09,BF≥727.21。三个因素两两之间 的 交 互 作 用 均 显 著,Fs ≥5.94,ps ≤0.013,η≥0.05,BF≥87.23。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 (2,111)=5.02,p=0.008,η=0.08,BF=147.52。简单简单效应的事后多重比较显示,无时间压力时,个人困境中,认知重评组与表达抑制组显著高于无调节组,ps<0.001,非个人困境中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s>0.05;有时间压力时,个人困境中,表达抑制组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组和无调节组,ps<0.001,非个人困境中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s>0.05。

表1 不同时间压力下各组的平均功利论决策比例和不道德评分(M±SD)
2.4.3 不道德评价分数
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主效应显著,Fs≥15.734,ps<0.001,η≥0.13,BF≥1819.58。情绪调节策略与时间压力交互作用显著,F(2,111)=33.56,p<0.001,η=0.38,BF=4.50e+7。简单效应检验表明,无时间压力时,无调节组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组与表达抑制组,ps<0.001;有时间压力时,无调节组和认知重评组显著高于表达抑制组,ps<0.001。其余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无时间压力条件下均能有效降低消极情绪,使被试在个人困境决策中更功利化,并对功利决策的评价更积极。但在8 秒的时间压力下,认知重评无法有效地调节情绪,也没有影响道德决策结果。而表达抑制对消极情绪和道德决策的影响则不受时间压力的影响。
3 实验二
3.1 被试
在校大学生102 名(男性38 名),平均年龄21.47±2.53 岁。被试无身体疾病和精神障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3.2 实验设计
2(认知资源损耗:高、低)×3(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无)×2(困境类型:个人困境、非个人困境)的三因素混合设计。
3.3 实验材料与程序
情绪自评量表、情绪调节策略指导语和道德决策问题同实验一。
首先,被试填写情绪自评量表。之后完成Stroop 任务以操纵认知资源损耗程度,其中高损耗组完成不一致色词任务,如黄色的“蓝”字,蓝色的“黄”字,低损耗组完成一致色词任务,如黄色的“黄”字,蓝色的“蓝”字。共120 个试次,试次间间隔1000ms,每个刺激前呈现200ms 的白色“+”注视点,屏幕背景为黑色,被试需在2s内进行按键反应。任务完成后要求被试回答:“你感到这一任务给你带来的疲劳程度如何?”(1=一点也不疲劳,7=十分疲劳)。
之后开始道德判断实验,流程同实验一。最后再次填写情绪自评量表。
3.4 结果
3.4.1 操作性检验
独立样本t 检验显示,Stroop 任务有效地操纵了被试的认知资源损耗水平,高损耗 组 的 疲 劳 程 度 更 高,t(100)=16.297,p<0.001,Cohen’s d=3.22,BF=2.41e+26。
3.4.2 情绪自评分数
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消极情绪中,情绪调节策略主效应显著,F(2,96)=12.37,p<0.001,η=0.21,BF=947.27,无调节组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组(p=0.016)和表达抑制组(p<0.001);认知负荷主效应显著,F(1,96)=4.29,p=0.041,η=0.043,BF= 1.84,高损耗组显著高于低损耗组。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2,96)=2.86,p=0.062。
积极情绪的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3.4.3 功利论决策百分比
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见表2),各 主 效 应 显 著,Fs ≥5.39,p ≤0.022,η≥0.05,BF≥56.17。困境类型与情绪调节策略交互作用显著,F(2,96)=28.40,p<0.001,η=0.37,BF=2.30e+9,简单效应检验显示,个人困境中,表达抑制组显著高于无调节组和认知重评组,ps<0.001;非个人困境中,认知重评组显著高于无调节组,p=0.017。困境类型与认知资源损耗交互作用显著,F(1,96)=5.94,p=0.017,η=0.06,BF=8.07。情绪调节策略与认知资源损耗交 互 作 用 显 著,F(2,96)=7.40,p=0.001,η=0.13,BF=46.90,低损耗下,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显著高于无调节组,ps<0.001;高损耗下,表达抑制组显著高于无调节组和认知重评组,ps≤0.005。三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p=0.622。

表2 不同认知资源损耗下各组的平均功利论决策比例和不道德评分(M±SD)
3.4.4 不道德评价分数
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各主效应显著,Fs≥11.86,p≤0.001,η≥0.11,BF≥2.24e+4。困境类型与认知资源损耗交互作用显著,F(1,96)=18.94,p<0.001,η=0.17,BF=3949.87。情绪调节策略与认知 资 源 损 耗 交 互 作 用 显 著,F(2,96)=37.23,p< 0.001,η=0.44,BF=2.10e+9,低损耗下,无调节组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组与表达抑制组,ps<0.001;高损耗下,认知重评组和无调节组显著高于表达抑制组,ps<0.001,认知重评组显著高于无调节组,p=0.010。其余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实验二的结果与实验一类似,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低认知资源损耗下均能有效降低消极情绪,使被试在个人困境中的道德决策更功利化,并对功利决策的评价更道德。但Stroop 任务所带来的高认知资源损耗同样使认知重评无法对消极情绪进行有效调节。而表达抑制对消极情绪和道德决策的影响同样不受认知资源损耗的影响。
4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认知资源条件下情绪调节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与前人研究一致,本研究证实了情绪调节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Lee & Gino,2015;Feinberg et al.,2012)。两实验均发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可以调节负性情绪,导致更多的功利论决策,同时对功利决策的评价更道德。Szekely和Miu(2015)的研究并未发现表达抑制的作用,原因可能是该研究探讨的是个体长期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倾向,而本研究使用的是实验室条件下的短时情绪调节。Lee和Gino(2015)使用的音视频刺激材料可能导致情绪唤起程度出现了差异,但也混淆了认知加工负荷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资源是否充足是影响情绪调节策略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时间紧迫或疲劳导致的个体认知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表达抑制能够更加有效地调节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对道德推理决策的影响。
道德两难困境能够诱发被试的消极情绪,使其更多地倾向于道义论决策。而且个人困境中牺牲者被有目的地作为工具使用,被试的卷入程度更高,情绪唤起更加强烈,而在非个人困境中,决策者并没有故意利用某人来拯救多人,牺牲者只是助人行动的附带损失(褚华东等,2019)。因此相较于非个人困境,个人困境中情绪对道德决策的影响更大。两实验均发现,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个人困境的道德决策中,在个人困境中,道德判断主要受到负性情绪的主导(Lotto et al.,2014)。当个体能够有效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时,负性情绪的主导作用受到了调节控制,控制了情绪的个体会较少地体验到对受害者的同情,从而更倾向于功利论决策(Lee&Gino,2015)。而非个人困境中被试卷入程度相对较低,情绪唤起程度较低,认知推理在与情绪的竞争中更容易胜出,更容易做出功利论决策,因此情绪调节策略对其影响较小。虽然在道德判断阶段情绪对个人困境的影响更大,但是个体在对非个人困境中的功利决策进行道德程度评价时,难免会产生后悔、自责等负面情绪,此时有效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能够使被试直面自己的选择,使其对决策结果的评价更为积极。因此,在不道德评分上,情绪调节策略在两种困境中产生了相同的结果趋势。
两个实验分别采用时间压力范式和Stroop 任务操纵了被试的认知资源,结果发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果是不同的。认知重评会受到认知资源的影响,在高时间压力和高认知损耗下,认知重评策略不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似乎表明,两种调节策略的内部机制是不同的。当个体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时,道德推理所需的资源被占用,认知重评的能力也受到限制,从而无法给予功利论决策足够的支持,情绪主导的道义论决策更占优势。而表达抑制则不同,面部反馈假说认为,表情模式与情绪感受存在先天的、遗传而来的连接(McIntosh,1996),对表情的抑制可以减弱情绪的主观感受。因此,表达抑制占用的认知资源更少,为个体的道德推理加工留下了更大空间。时间压力范式在不改变总可用资源的情况下,使被试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对困境进行反复思考,只能将认知资源投入到决策判断而非情绪调节上,导致不同策略的作用效果出现差异。Stroop 任务使被试在开始道德决策前消耗了一部分认知资源,虽然判断过程中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有限的认知资源使其无法有效地进行情绪调节。因此,结合两个实验结果说明,两种限制认知资源的方法均能有效减少可用的认知资源,认知重评受到了认知资源限制和损耗的显著影响,而表达抑制则对认知资源的需求较少,对情绪的调节更直接。
本研究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启示,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教师要积极关注并加以引导,培养学生的情绪自知能力与情绪调节能力,提高学生对于道德事件的理解与判断,以期帮助其在道德决策中变得更加理性和公正。
5 结 论
(1)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都能显著降低负性情绪,导致更多的功利论决策。
(2)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对认知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只有在认知资源充足时才能有效地调节情绪并影响道德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