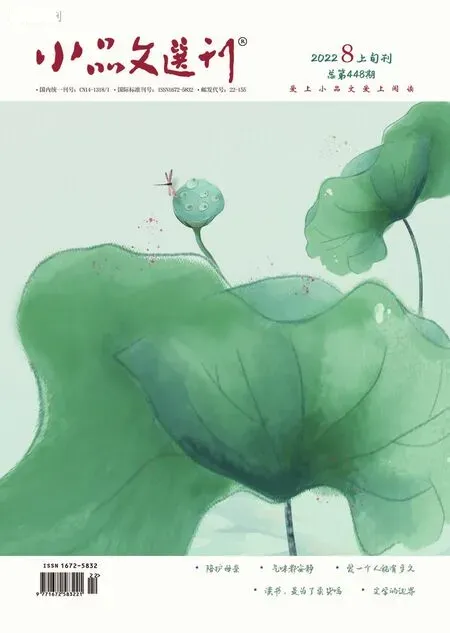父亲走后
□陈宇菁
父亲的离去给我的人生留下一道沟壑,我此前的人生变得如梦般缥缈。我不知往后的日子该如何生活,开始陷入漫长而深不见底的昏睡。那段时间,我过得昼夜不分,有时醒来也不记得上一顿饭是哪天吃的。不得不挣扎起身去学校的时候,我精神涣散,回过神来才注意到手机的未读信息,错过了母亲的越洋电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向她汇报我的状况,也不敢去关心她的生活。日复一日,在昏睡和焦虑间,时间就在混沌中蹉跎开去。
母亲在2014年12月中旬来到纽约,在学期结束后,我们启程去了加州。这是母亲第一次来美,整趟旅程却一切从简。父亲的离世让我们无暇顾及旅途的具体安排,只是有意避开了游人众多的区域。我和母亲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沙滩或密林里伫立、行走,默不作声。我尝试透过相机取景器去默默地关照她,一前一后,走走停停,不时用眼神和微笑确认彼此,互相搀扶。
两周后,我送走母亲,各自回到需要独自面对的生活。又一个学期开始,胶卷陆续被冲洗出来,父亲烟火弥漫的葬礼和与母亲的加州旅行在我脑海中被重新翻开。我意识到自己这些照片已经与父亲的离世变得密不可分。它为这些图像染上死亡的底色,是这些照片的动机,更成为这些照片所要抵抗的事情。
父亲的死是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影,它不仅在我们心中留下空洞,彻底掀翻了我们的日常,也让未来变得模糊,摇摇欲坠。而当我将一卷卷胶片作为可被触摸的记忆握在手中时,父亲存在过的痕迹却变得有迹可循。这似乎让我摸索出了与“父亲会永远缺席我的后半生”这一事实共处的可能。
2015年夏天,我结束了大学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回到家,也回到了父亲的墓前。再一次踏入大河村时我意识到,这只是我与它漫长纠葛的起点。大河村曾与我完全无关,若非父亲的离去,我可能永远不会了解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去接触素昧平生的乡亲们;若非父亲的离去,我似乎从未对他从哪儿来有过好奇。大河村成了我了解父亲过去的唯一途径。在可见的未来里,它将会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坐标系,来这里扫墓,从这儿离开,再回到这里,再从这儿离开……
一年又一年的往返让我对曾经陌生的乡土一点点熟悉。如今我已能在村巷中自如穿梭,理清了复杂的乡亲网络。我逐渐明白这里不仅是父亲生命的终点,也保留着他完整的青春岁月。父亲一直惦念着这方故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还同爷爷和叔叔翻修了宅基地,预备着退休后回乡养老。父亲在这里长大,从这里走出,目睹了他的乡亲们不曾见过的风景,最终又魂归于此。
如今距离2014年的夏天已过去了七年。
在这过去的七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回到父亲的墓前,用镜头去关照依然在身边的家人。父亲的死在我身上依旧残留着痕迹,照片中的爷爷也已离开人世,留下的胶片则成了我用来反抗遗忘的武器——它被定格在那里,接受时间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