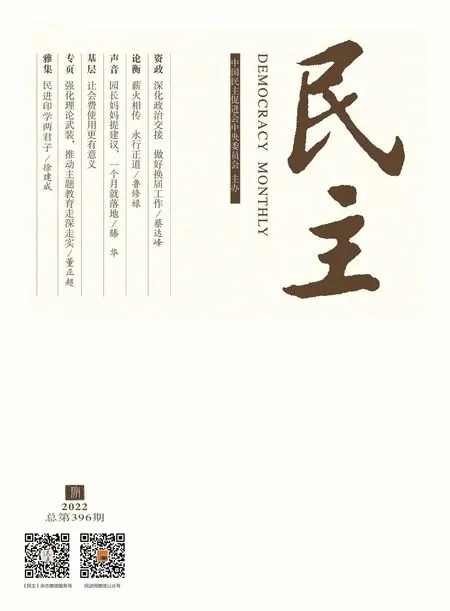读 走 写
——我这一辈子在干些啥
□邓伟志
老汉我今年八十有五,已成风中之烛。在行将就木时,免不了要回忆过去,想来想去我这一辈子轻如鸿毛,似乎就干了三个字:读,走,写。
诗词是我童年的精神食粮
我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家庭。曾祖父行医,他脾气很怪,穷人请他看病,不分昼夜奔去,如果路途遥远他会骑着小毛驴去给穷人医治;达官贵人请他看病,如果不来轿子、马车接他,他不走。有次给邻县的县太爷看病,县太爷死了。官府咬定是他有意害的。在清末那年代,文人跟官员打官司是打不赢的。曾祖父被判“穿红绣鞋”,即是走在烧红的烙铁上。曾祖冤死后,祖父也气死了,从此家境衰落。十多岁的伯父只好放弃读书,耕田种地,维持生活。父亲和叔父在亲戚支助下读书。父亲读完师范,1925年18岁到上海大学读书,1926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又被党组织派到由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昌农讲所学习,从此很少回家。
解放战争时间,我家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京沪和陇海两条铁路都经过萧县。我们在萧宿永一带住过一二十个小村庄,好在母亲读过师范,不管住哪里,她都要教我们背诗词,白天没时间教,晚上睡在床上教。《木兰词》、岳飞的《满江红》,背一遍再背一遍,字不识,照样背,错一个字重新背。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滚瓜烂熟。在“跑反”时,六七岁的我跑不动,母亲就叫我背“乞丐诗”:“赋性生来本野流,手提竹杖过通州。饭篮向晓迎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两脚踢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如今不受嗟来粟,村犬何须吠不休。”在黑暗的旧社会,背这首诗时,浑身是力量。幼小的我萌生了踢翻旧社会的念头,在跑不动时,更想踢翻尘世路。母亲鼓励我:“要有‘一肩担尽古今愁’的抱负。”
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诗人,他也在被窝里教我诗词。有一次,敌人扫荡,我们不得不离开外祖家,逃向河南省。临别时外祖写了首诗给我们姊弟三个送行:“三个小儿童,今将有远行。前程期广大,一路祝安平。学与年同进,身随日俱增。待当归来日,四海望澄清。”一路上,母亲叫我们反复背外祖的诗,鼓励我们向前,向前。
诗词是我童年时的精神食粮。背诗的时候,吃野菜、窝窝头也不觉苦。诗词伴随我成长。
读
1960年,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本科毕业后,留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学习室。
经过一年多,我在导师精心培养下养成了读书的追求和方法。“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吃穿简单点,头脑复杂点”成了我的座右铭。在吃不饱的困难时期,我从筷子底省出钱来买书。我到好多大学图书馆借过书,向名人家属借过书。孤本、善本不可出馆,我就在南京路上海图书馆吃住了一个多月,读孤本、善本。我在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和古医史专家刘书农指导下读过马王堆出土的竹简。我还在北大考古学家指导下,手捧甲骨文读周朝人的日记。我还出乎人们意料地卖过书。“文化大革命”前,每周四上午干部都要劳动。经领导批准,我到福州路新华书店、徐家汇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书店以及淮海路华亭路书店卖书。我认为卖书也是读书,利用卖书了解读者的真正爱好和评论。我每次出国讲学,都要去他们的图书馆,前前后后,去了捷克、英国、爱尔兰、美国等几十个外国的图书馆。在奥地利图书馆背过他们的木质背斗借书。奥地利学人见我这位“老外”背得不熟练,先微笑而后帮我纠正背书斗的姿势。
走
在名片时髦的日子里,我名片上写的是“读书人邓伟志”。读书人诚然要读书,但是如果不了解社会,很难读懂书;如果脱离实际,书房会变成空中楼阁、象牙之塔。在学习室时,几位导师教导我们“要眼睛向下”“沉到底”。因此,我两条腿不停地到处走。
上海纺织、冶金、机电、仪表、轻工等工业系统的工厂,我去过120多家,边劳动,边调查。我当过上钢三厂二转炉的炉前工;我到过臭气薰天的皮鞋厂、污水横流的造纸厂劳动过;我在造铀造镭的工厂里见过镭;我在上港五区、七区背着200斤重的棉布包过“天桥”,上外轮;我在刘志丹的侄子刘从军工程师的带领下,抱过尚未安装的导弹壳。我还与聋哑人一起织过五彩斑斓的被单。我在精神病院与各类精神病患者一起生活了好几天。林林总总,豁目开襟。
读书是为了强国。为了国强必须了解国情。写文章要从国情出发。为了熟悉国情,我北从黑河,南到睦南关,东从长白山,西到嘉峪关,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春雨不攀高墩”。出门走红地毯方便,爬山间小路困难。为了熟悉国情,我爬过几十米高的悬崖,越过激流险滩,穿过树上有蚂蝗的密林和荆棘,在金沙江、澜沧江、图门江里洗过澡。我访问过住在沙漠上、因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脸的可爱的农民。“自古圣贤多贫贱”。就是这个没穿过一件衣的民族兄弟的老氏族长,为保存火种弯腰用胸口挡雨,胸部烧得伤疤连伤疤,伤疤叠伤疤,他真是以身作则的“优秀领导干部”。我前后写过《论乞丐》等几十篇呼吁共同富裕的文章。
我走访过60多个国家,接触过150多个国家的百姓。在马克思调查玻璃厂的旧厂房前,我哼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古罗马遗址,看到奴隶主住的高大建筑只剩下几根断了的柱子,而奴隶住的矮小地下室仍完好存在,让我想起穷且益坚。走进过世世代代发诺贝尔奖的那既小而又建筑出错的礼堂,我很自然地背出“室雅何须大”“庙小乾坤大”。走进因思想自由而出过40多名诺贝尔奖的慕尼里大学,看到他们百年前的“学生监狱”遗址,让我强烈地感到改革之重要,改革是解放人才。坐在南美以“错误的港湾”命名的港湾旁,想起“错误是正确的先导”。
写
使命和癖好决定我不管看到什么社会现象,总要想一下能从中引出什么观点,能不能进入笔下。上海有位笔杆子写文章,赞我与他一起参观采矿展览也拿出笔记本记录。我说,那是因为我想变无知为有知。参加集体活动,有的自己有兴趣,有的自己没有兴趣,既然去了,就要学会变没兴趣为有兴趣,尽量进入笔下。没兴趣往往是不懂门道,没进入角色,但是不能一味地看热闹,要学会进入角色,看门道。
看书,看报,我爱拿笔摘两句,或者做个记号,做最重要记号,做次重要记号,对不赞成的打叉,有疑点的打问号。问号像把钥匙,在我眼里是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形形色色的符号集零为整,积少成多,不知哪一天“读”和“走”接上头,就会升华为比较系统的想法,试着提笔写点什么。有了理论冲动,不吃饭也得写,不睡觉也得写,不看病也得写,写,写,写成了“写瘾”。读加走化合成写,是我人生的公式。
从1956年进大学至今66年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强大威力,逼着我“拼多多”,出版了全集25卷,发表了一千多万字(还有几百万字日记未发表),有长有短,有深有浅,良莠不齐,有被人认为对的,有被人认为错的。面对形形色色的议论我冷静思考,择其正确者而从之,对未必正确的我不从,不从也不埋怨,不生气,压力变动力,有坑就填坑,填不了就纵身跳过去,跳不过去即使掉进坑里也无所谓。我是中国共产党把我从死的边缘救出来的。1948年我10足岁,在淮海战役中遭飞机轰炸,父亲请王文书送我转移,走在濉溪镇的桥上,敌机炸弹落在距离我俩一米远,结果是哑弹,未炸;走出濉溪东关刚到场地上,飞机又来了,王文书把我搂在怀里,抓起一把又一把沙土当烟幕弹,炸弹没能落我俩头上;走到麦田边的车道上,敌机又来了,没有了沙土。王文书见飞机从东来,拉我躺在路边坟墓的西边。飞机疯狂地扫了我俩几梭子,有的扫在坟东边,有的扫在我俩脚的西边,就是没扫在我俩身上,再一次让我与他死里逃生。飞机飞跑后,王文书得意地说:“我料他们角度算不准!”小时候不怕死,到中青年时还会怕离死有十万八千里的墨笔官司吗?
几十年来,我文章受到批评和商榷的有十来篇。
1980年,富有欺骗性的“耳朵认字”在报刊上、电视上猖獗。我毫不买账,既写文章又出书揭穿“耳朵认字”作假。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文汇报》上接连发表了《家庭的淡化问题》《淡化当官心理》《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被人称作“邓氏三论”。每一论都受到很多批判文章。《文汇报》公开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文汇报》办的内参《理论讨论》也发了几篇。
1982年,我提出“妇女学”。有妇女理论专家批评说:“妇女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我立即写文章讲明妇女学既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东方的。
1986年,我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办了《邓伟志信箱》,就听众所提理论问题作些回答,全国广播电视会议予以赞扬,1987年获奖。有人上告《邓伟志信箱》是自由化:“在社会主义舆论阵地上节目以个人命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奖大会不让我参加,不登台,会后把奖状、奖品送到我家中。
1999年,我写了篇《不创新毋宁死》,后来发表在一家杂志上,紧接着又陆续写了十几篇倡导创新的文章,于2006年用《不创新毋宁死》为书名,出了本小集子。

几十年来,我读过多少有关学者的小传,记不得了,写学者传记的大书家里大约有一二百本。我在写作中遇到的这些麻烦,说实在的,较之老一辈只能算鸡毛蒜皮。我坚信“双百”方针。我认为“商榷→商榷的商榷”是新思想的催生婆。都用“酸甜苦辣”形容人生,我觉得用在我身上不尽然,面对曲曲折折,我说人生有八味:酸甜苦辣、咸痒涩麻。我尝的多是咸痒涩麻。面对起起伏伏,我无怨无悔,起不俏,伏不倒,拦不住,甩不掉。云卷云舒是气象的研究对象。花开花落是植物的生长规律。挫折是历练。在我眼里是褒是贬不关情。行藏用舍是任何人都脱不开的经历。千变万变,追求真理的志向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和放松。声如钟,站如松,是文化人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