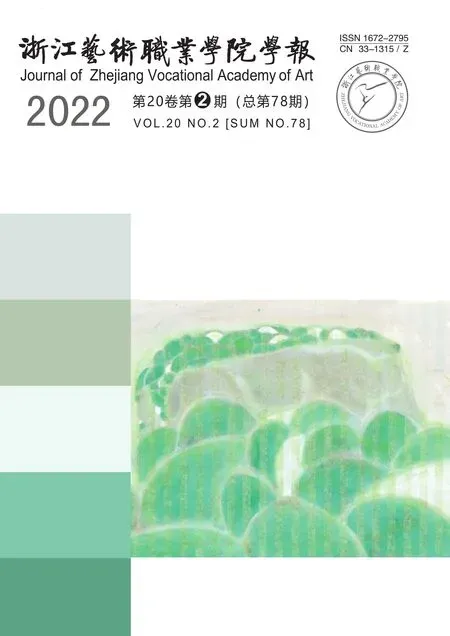“取韵”类新音乐混生样态与族性的美学分析*
——以《牧童短笛》为例
宋 瑾
笔者另文探讨了作为现代中国混生音乐典型的“新音乐”(含“新潮音乐”)对传统音乐的移植(改编)、主题化、引用和拼贴,接下来要探讨“取韵”或“神似”的类型。在这种类型的混生音乐中找不到具体的传统音乐素材来源,但又能明显感受到传统音乐的神韵。如钢琴曲《牧童短笛》 没有直接采用具体的中国传统音乐素材,却公认具有中国传统音乐韵味。又如“京歌”找不到具体从哪个京剧曲牌唱段获取素材,却能感受到浓郁的京腔京韵。以往此类问题都归在“风格”范畴;在本文的语境中,它涉及混生音乐的族性归属。20年前在若干学术会议上香港大学的刘靖之提出的问题是:“人们都说《牧童短笛》 是中国作品,为什么不能说它是中国风格的西方作品?”他指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 除了五声曲调是中国的之外,乐器、和声、复调、曲式等等都是西方的。实际上他想说的是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的族性归属问题——既然是中西结合,就不能只归中国一方。在刘靖之看来,《牧童短笛》 对西方音乐的隶属度更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因此,本文将以此为例进行取韵类型的混生音乐族性分析。
一、《牧童短笛》 的混生样态“取韵” 类型
1934年5月,齐尔品从北京致信萧友梅,委托他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活动。《音乐杂志》 第三期很快就登载了启事,要求投稿者为中国人。当时31 岁的贺绿汀正在上海国立音专师从黄自学习作曲,虽缺乏获奖信心,还是决定尝试。笔者关注的是贺绿汀是否采用具体的传统音乐素材。据作曲家自己透露并非如此。
作品写出来以后, 我才想到要给它取个名, 根据音乐的情趣, 我用了一个英文标题, 译成《牧童之笛》, 后来总觉得曲名有点文绉绉, 才根据一首民谣—— “小牧童, 骑牛背, 短笛无腔信口吹” 的词意, 改成《牧童短笛》, ……[1]
贺绿汀“根据音乐的情趣”用英文起名为“Buffalo boy's flute”,再翻译成中文“牧童之笛”,[2]这种做法很普遍。许多作曲家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都说到作品完成在先起名在后的情形。以上作曲家的自白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牧童短笛》 是先写完再起名的;其二,起名根据的是民谣而不是民歌。也就是说,《牧童短笛》 没有取用既有传统音乐具体素材,但又符合“中国之风味”的要求,并获得一等奖。事后由于齐尔品等人的推崇,得以迅速在国内外各地传播。联想起后人对《牧童短笛》 的解释,有很多“牧童”形象或意象的解读,应该属于标题引起的理解和赋意。这里的“牧童”限定为“buffalo boy”( “buffalo”是水牛),而不是“shepherd boy”(牧羊少年)、“cowboy”(牛仔/牧童)、“cowherd”(牧牛者)等(“cow”指奶牛、母牛),提供了“骑在水牛背上吹笛的牧童”的形象,因此该曲调风格最可能的归属地域是多见水牛的南方。这个“牧童”形象最早出现在齐尔品于193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音乐出版社“龙吟社”出版的“齐尔品收集品”系列的封面上,该册第一篇乐谱即《牧童短笛》。

图1 龙吟社“齐尔品收集品”封面图案
有人根据《牧童短笛》 带有中国传统音乐“句句双”的旋法特点,认为它取材于同样具有“句句双”特点的民间小调《小放牛》。但是贺绿汀强调该曲调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戴鹏海相信他的说法,“因为他历来反对创作时采用某首现成的民歌作素材,理由是限制太大,容易把人‘框住’ (改编当然例外);他主张平时要多方面地接触民间音乐,消化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到创作时再让它自然而然地 ‘流出来’ ”[3]。
总之,《牧童短笛》 作为新音乐作品,具有中西结合的混生样态,属于“取韵”类型,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
二、混生样态分析
作曲家明确指出自己学了西方复调、对位手法,所以才用对位体创作了第一、三乐段。一方面“完全是用对位体写的”,另一方面“还是完全的中国风格”。这里的两个“完全”,道出了混生音乐的特征。
当时我已经学了复调、对位。 所以《牧童短笛》 的首、尾段落完全是用对位体写的。 如果你没有学过复调, 怎么能写? 所以, 有人当时反对学外国的东西, 说是学了外国东西就变成外国人了, 都是洋的了。《牧童短笛》 不是吧? 还是完全的中国风格, 但还是用了外国的复调手法。[4]
显然,完全的西方对位体,完全的中国风格,后一个“完全”,是作曲家的意愿,也是齐尔品征集作品的要求。但从混生音乐的角度看,“中国风格”的“中国”,是新文化新音乐的“中国”,是千年传统之“局”变为现代之“局”的“中国”。
谱例1:《牧童短笛》 1—3 小节

除了复调、对位,《牧童短笛》 还采用了西方的和声,但不再是“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所提供的经验,为后来不断被探索的“和声民族化”或“民族和声”提供了有益参考。贺绿汀在学习西方和声的过程中就进行了和声民族化的探索。例如,他在黄自的引导下为古典诗词配四声部合唱,就用了“不是完全传统的和声”。这里的“传统”指欧洲古典音乐的和声传统。
黄自曾要我自己找些古典诗词来配合唱, 我又写了一首《归国谣》: “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 芦花千里霜月白。 伤行色, 明朝便是关山隔。” 我写了四部合唱, 用的不是完全传统的和声, 比如Ⅱ—Ⅰ, 我也用了, 这在传统和声里是犯禁的。 我记得黄自把这个曲子给俄国钢琴家阿可萨柯夫看, 他很欣赏。 我还写过好几首, 都是作和声习题时写的。[4]
1932年前后,贺绿汀翻译了普劳特的《和声学》,加上国立音专的正规学习,“传统和声”应该掌握得很好。之所以要用Ⅱ—Ⅰ,就是想寻找民族化途径。
《牧童短笛》 中段的和声设计很巧妙,在持续低音g 音的上面是级进下行的三度和声音程,功能上完全符合“传统”。G:T-D-Ⅵ-Ⅲ-S-D。这个模式不断在其他调上重复(模进)。
谱例2:《牧童短笛》 中段片段

和声民族化主要体现在终止式。按照西方功能和声体系惯例,终止须采用属和弦到主和弦D-T 的进行。《牧童短笛》 采取A-B-A′的三段体结构,因此有3 个终止式,都作了民族化处理;虽然调性不同,但它们都采用Ⅵ-T 终止式。此外,除了G 宫B 段的主和弦保持三度叠置结构g-b-d (Do-Mi-Sol)之外,A段和A′段的结束主和弦也作了变化——G 徵调主和弦左手采用了五声化和弦结构g-d-e-g (Sol-Re-Mi-Sol)。如下所示。
谱例3:《牧童短笛》 三段和声终止式

以上是根据作曲家的自述阐发的内容。在一次学术活动中,笔者听到伍国栋谈论《牧童短笛》,特别关注他关联民间音乐的分析。事后又查阅他正式发表的论文,追寻其分析的具体细节,得到以下信息。
2015年11月2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上,伍国栋的发言以《牧童短笛》 为例,阐明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要有主位立场的观点。他尝试采用中国传统音乐3 种“代表性构曲法则”来分析《牧童短笛》 的音乐形态(曲调形态),理由是“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作为精通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贺绿汀,他在《牧童短笛》 创作构思中,至少比较明显地采用了有别于西方音乐创作的中国传统音乐三种代表性构曲法则,在与西方音乐作曲手法的交融之中,为我们留下了难能可贵的音乐形态分析的民族音乐语境空间”[5]。
这3 种构曲法则即:“句句双”与“对句”;“犯调”与“死曲(腔)活调”;“加花”与“死板活腔”。
“句句双”指核心乐句成双成对出现的句式。《牧童短笛》 A 段首句和次句相同,就是典型的句句双结构。“死曲活调”指一个曲调在不同调上出现的样态。B 段通过转调(旋宫),将一个动感十足的上下乐句构成的曲调在不同调上重复,G 宫—D 宫—A 宫—G 宫—D 宫—A 宫—G 宫,其中还暗含“鱼咬尾”的旋法。这就是板式不变而宫音位置改变的“犯调”。第三段A′呼应首段,即重复式“合头”,但采用了民间音乐“加花”手法,使再现有新情趣,此即“死板活腔”。
采用民间音乐话语来阐述《牧童短笛》 的曲调特点,确实具有“主位”身份。笔者问伍国栋是否从贺绿汀那里得到确认,他说没有。笔者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贺绿汀确实“精通中国传统音乐”,在创作中自然而然采用了传统音乐构曲方法。何况他本来就是要参加“中国之风味”钢琴作品的征集活动。不过,如果分析西方音乐作品,也能发现类似的“构曲法则”。不论。
如此看来,《牧童短笛》 曲调的“中国之风味”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都可以确认,乐器、复调、和声等属于“洋为中用”也没有疑问;曲调没有具体出处(母本),作曲家说是自己想的,理论家也没有提供可靠的母本信息,因此如前所述,该作品属于“取韵”类型的混生音乐。当然,钢琴弹奏的五声风格曲调没有润腔,是因为它只能出现“颗粒性”音高。
三、族性分析
(一)新局内观的确立
无论从作品分析和感受看,还是从作曲家的言论看,都可以确认贺绿汀为代表的“新音乐”人-事具有新局内观,那就是走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道路的观念。
贺绿汀的新音乐局内观可以概括出几个具体内涵。
其一,学习“民族乐派”,借鉴有价值的西方音乐。
“在音乐方面,所谓‘民族派’ 音乐,在西洋音乐史上占有极大的篇幅,成功的作者如俄国的巴拉基也夫,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等的五人团,挪威的格里格,波兰的肖邦,波西米亚的德沃夏克等等,他们不仅是本国不朽的作曲家而且也是世界不朽的作曲家。”[6]17贺绿汀呼吁中国作曲家学习西方的民族乐派,掌握系统的作曲技法,创作出有民族风格的作品。这一音乐创作理念逐渐成为中国音乐工作者的集体意识,并贯穿在整个20 世纪的中国音乐界,成为一条创作“律令”。在贺绿汀看来,西洋音乐理论有借鉴价值,而且西洋乐器“极其精巧”,可以为我所用。他一再强调中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跟世界关联在一起。因此对中国传统音乐,“要用新的方法和技巧,新的意识,发展到它最高形式,而成为世界上极其有价值的民族音乐之一”[6]12。
其二,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现状,改造传统音乐。
“中国在文化方面落后,政治经济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因此“我们应该鼓起勇气来建设崭新的中国音乐”。一方面要反对国粹主义,一方面要挖掘传统音乐文化宝藏。贺绿汀说:“我们须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及分析中国一切过去的音乐,给它们算一个总账。”[6]2-3这里的“科学方法”显然是借鉴西方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而得的方法。他概括了“丰富的活的音乐遗产”包括山歌小调、曲艺、戏曲等,其中提到“牧童的山歌”[6]6。也许这种“牧童的山歌”储存在作曲家的记忆深处,为他创作《牧童短笛》 提供了“取韵”对象,可惜作曲家没有提供具体母本信息。比起西方“极其精巧”的乐器,贺绿汀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很粗糙,因此要利用西方乐器。
中国乐器大都是高音乐器, 音域短, 管乐由于制造简陋, 声音不准, 因之十支笛子几乎是十个不同的音高, 再加上唢呐、管子、笙就更加困难, 往往费了很大功夫配备一套D 调的乐器, 奏F 调乐曲时, 胡琴、三弦之类必须重新调弦, 管、笛、笙、箫之类必须重新全部换过。 至于一首乐曲欲从一个调转入另一调时, 那就更加困难重重了。[6]32
他从童斐章的《中乐寻源》 中了解到胡琴、琵琶、唢呐等,都来自外国,但跟现代西方乐器相比却是差距甚大。“这些外国的乐器比起我们祖先遗下来的(从前的外国乐器),不知进步多少倍,不用它,对我们自己是个大损失。”贺绿汀认为“乐器愈进步,表现的力量就愈强”,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民族乐器,“但这些乐器都退到了次要的地位,音乐上最主要的作品还是用进步的西洋乐器演奏”。而民族乐器可以当作色彩性音色使用。[6]31-32除了乐器,还有记谱法等进步的音乐理论需要我们学习,用来整理传统音乐。因为“中国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停留在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有系统的科学化的研究,所以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单音音乐的阶段,没有向前走出一步”。从今天的学术眼光看,这是“单线进化论”的论调。但是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从政治实用功能的角度看,从“新音乐”的价值取向看,是可以理解的。
其三,反对低级趣味的“新”音乐。
贺绿汀指出低级趣味的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外来的,如爵士乐和填词歌,一种是民歌改编的。他认为爵士乐本来是黑人音乐,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它已被投机的流行音乐创作者所利用。它已成为一种酒醉灯迷的音乐了。……假如中国人采取它作为大众化音乐的基础,无异教中国人学下流”[6]11。“有些投机的人利用一些民间俗调配上一些淫荡的辞句,广为传播,结果有一部分人接受了。……其作用恰似一服麻醉剂,是变相的鸦片。这种东西不惟不能鼓舞人民上进,反而引导人民堕落。”[6]2从这里可以看出,贺绿汀对“新音乐”的发展方向是有严格取舍的,那就是借鉴西方科学的音乐理论,整理、发掘民族传统音乐。除了创作健康、革命的大众歌曲,还要使用西方精致的乐器,“创作出比较高深些的大型作品如交响曲、管弦乐曲、歌剧等等,以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6]19。按今天的话说,贺绿汀反对低俗音乐,提倡高雅音乐。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种“高雅”与政治功用或新文化新音乐运动密切相关。
其四,强调作曲技术的重要性,维护“学院派”的价值,认为普及与提高不可偏废。
在“新音乐”运动期间,出现了很多革命歌曲。但是在贺绿汀看来,其中有不少歌曲缺乏艺术价值,“作曲的技术水平过低”是一种“最普遍的现象”[6]14。因此他一再强调学习作曲技术的重要性。具体做法是“埋头去研究那些进步的西洋音乐理论技术,去研究和分析那些古典派、近代派各家的作品,以提高我们的技巧”,“达到世界的一般国家中作家的水准”,以此开采传统音乐宝藏,“创造新中国的和声、中国的对位、中国的曲体”,“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族音乐”。[6]18据此,他对当时反对“学院派”的观点持否定意见,指出应该反对的是低级趣味的流行音乐,而不应该拒绝专业音乐的学习和实践。与此相关的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贺绿汀指出“提高”不等于“脱离群众”,反之,“在提高方面,我认为提高音乐工作干部的水平最为迫切”,具体做法就是让他们集中一年或半年到音乐院校去作专门的业务学习。[6]30
其五,坚持按艺术规律创作的立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
贺绿汀发表在《文汇增刊》 1980年第6 期上的文章《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第一个二级标题就是“音乐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是领导外行”。他指出外行的领导由于不懂音乐文化,只能闻风使舵,给我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带来极大损失。例如1963年刮的风,文艺界一方面要反对“鬼戏”,一方面要反对资本主义的文艺,很多外行领导跟风,结果很多地方取消了外国乐队,学校取消了外国乐器专业;1980年又刮风,依然有人反对外国音乐,提出除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以外,其他院校都必须以传统音乐为主进行教学。在1954年11月5日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举行的戏曲音乐专题报告会上,贺绿汀作了题为《我对戏曲音乐改革工作的意见》 的发言,他也指出直接领导不懂音乐,又自以为是,在工作中发号施令,将重点放在剧本上,自然没有好结果。[6]36这种坚持按艺术规律创作的态度,不畏权贵敢于批评的精神,贯穿贺绿汀的艺术和教学生涯,因此他被誉为音乐界的“硬骨头”。
(二)新局内感的形成
新的局内感也就是新音乐的乐感,是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的乐感。这在20 世纪上叶的中国,是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从学堂乐歌开始,国人就对新音乐非常感兴趣。从美学上说,是因为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具有新鲜感,而且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的心理需求。当然,这也是时代的选择。就像贺绿汀所言,胡琴、笛子之类固然承载了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但是它们毕竟是原始的,没有西洋乐器那样精致。从时代需要振奋人心的声音看,西洋军乐队和管弦乐队显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性效果。铜管乐比民族吹奏乐有气势,而管弦乐的丰富性也使之更有表现力。如上提及的发言,从贺绿汀对20 世纪50年代的戏曲改革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他的新局内感具有明确的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追求。(以下引文均出自《我对戏曲音乐改革工作的意见》 一文,不再标明出处。)
其一,中国传统音乐别具一格,却有两个弊端,一是内容有糟粕,二是形式比较粗糙。
正如同我国的其他文化遗产一样, 我国戏曲音乐也是别具一格的。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拥有像我们的地方戏曲这样丰富并各具特色的戏曲音乐。 但是, 也必须承认: 我国戏曲音乐的极大部分, 都还比较粗糙, 必须剔除其糟粕, 保留其精华, 并积极加以发展, 绝不能满足于现状而不求进步。
以上文论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需要特别关注,那就是音乐的标准——涉及优劣评价和“发展/进步”取向。“丰富”和“各具特色”的评价体现了作曲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了解。“粗糙”和“糟粕”,前者似以西方的“精致”为参照,而后者则以普遍性伦理道德和革命理想为尺度。“发展”和“进步”也以“科学”的西方音乐文化和新中国建设对新文化新音乐的要求为参照。这些合起来体现了新局内感的价值取向,也即混生音乐的乐感取向。
其二,创造新音乐,要向自己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的古典传统学习。
以创造新歌剧为例,一方面要学习传统戏曲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古典歌剧的经验。
有些原来的地方戏曲, 道白与唱本来还能统一, 编剧、导演来一个“戏改”, 反而改成了个“话剧加唱”, 没有唱时就说话, 说上一阵忽而又唱起来, 教人听了很不自然。……
要创造新歌剧, 我们就应该深刻钻研自己民族歌剧的传统, 同时也要向古典的外国歌剧传统学习。
这里需要关注两点,一个是为什么要创造“新歌剧”,一个是怎样创造“新歌剧”。关于前者,显然跟建设新中国有关,也就是要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音乐。关于后者,再次体现了走中西结合混生道路的新音乐价值与审美取向。
其三,音乐修养很重要,对乐队音乐写作具有重大意义。
贺绿汀具体谈到要学习中西音乐理论和技术,尤其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论和技术。特别是多声部音乐写作,还有对打击乐器的合理应用。
有的乐队编制虽很大, 但是全是大齐奏, 没有发挥音乐的性能, ……
许多国家, 民族的音乐在发展过程中, 曾逐渐扬弃一些打击乐器, 而用有音高的管弦乐去代替它, 这对于我们也是完全合适的。 我国京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剧种, 各方面都有它一定成就, 但我觉得唯独它的锣鼓是不值得完全去学习的, ……过去所有的戏曲一般都是在广场上演出的, 锣鼓点不会妨碍演员的歌声。 到了室内, 就应该尽量设法不使锣鼓声掩盖了演员的歌声, ……
关于京剧锣鼓“不值得完全去学习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各地的戏曲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趋合于京剧;一是现在的戏曲主要在室内演出,锣鼓声容易掩盖演员的歌声。事实上传统戏曲也多在室内表演,锣鼓和歌唱往往不同时发声。贺绿汀讲的应该是新创作的歌剧问题。为此他希望戏改工作者向西洋音乐(歌剧)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音乐的业务水平,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自己的和其他的剧种的艺术。从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贺绿汀的乐感显然受到西方歌剧和传统戏曲的双重影响,但是倾向于用西方音乐理论来成就新音乐、新歌剧创造。
其四,表演者和创作者一样,也要学习中西进步的方法,让新音乐走向现代化。
艺人们起码应能认识简谱、五线谱, 渐渐地, 甚至文艺理论、西洋音乐理论、声乐技术等都应该列入到学习的课程中去。 试想, 我们的工业在加速地现代化起来, 音乐方面怎能保持原样不动呢?
要知道学习正确地运用嗓子、保护嗓子的方法。……我们只有把中外进步的发声方法学下来, 才能使艺术得到全面的发展。
欧洲率先走向工业化,西方古典音乐也在18 世纪成熟。因此贺绿汀将二者放在一起,指出要走向现代化,就要向西方学习。其中提到“中外进步的发声方法”,一个是美声唱法,一个是戏曲唱法。后者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显然是使用汉语歌唱所必须的。后来形成的“民族唱法”,依循的正是这样的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方式。
其五,从传统音乐走向新音乐,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必须肯定从地方戏发展成新歌剧是可能的, 是一条行得通的道路。
我们的地方戏曲既是别具风格的, 但不否认也是较为原始的东西,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发展它,如何加紧学习, 去促使地方戏曲走进新歌剧的领域。
这里的进化逻辑是:由于传统音乐是原始、粗糙的,必须发展;发展的方向是促使它走向新音乐,也就是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显然,当时的革命音乐家们已经形成了新音乐的乐感,也即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的乐感。这种乐感一直影响到现在。笔者在各地演讲的时候,播放西方音乐、传统音乐和新音乐,发现后者引起的共鸣最为显著。这就印证了20 世纪以来局内感的变化,从千年传统的局内感变为百年新传统的局内感。
(三)新局内情的表达
新音乐表达出来的情感,具有多重性,可以概括为民族情感、革命情感、对西方的复杂情感,以及追求混生音乐的综合情感(民族、革命、审美、借鉴等)。(为了避免脚注的重复,以下引文均出自贺绿汀论文选集,仅注明文集中的文章名称。)
其一,民族情感。此时的“民族”,指“中华儿女”,也即新一代中华民族。艺术家应该作为这个民族的代言人。
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有理性的伟大中华民族的儿女, 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 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全体动员起来, 把音乐变成武器, 去武装千万个同胞, 动员千万个同胞, 为了驱逐日本强盗而英勇抗战。( 《抗战中的音乐家》 )
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是由他个人创造出来的, 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个时代的代言人, 或新时代的预言家; ……他不单是民众的喉舌, 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 《音乐艺术的时代性》 )
显然,艺术家应该把自己融入整个民族之中,音乐应该表现“大我”的感情,而不是“小我”的情调。
其二,革命情感。或者作为时代精神的感情。这种情感跟新民族情感是一体的。艺术家应该用艺术反映时代,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鸣。
时代提出的问题、矛盾给人们以很深刻的影响, 使人们的内心燃烧着极强烈的感情, 艺术家抓住了这强烈的感情, 把它具体地表现出来, 无论这表现的工具是用诗歌、音乐、戏剧、绘画或小说, 只要他所代表的感情是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真实, 就一定可以得到普遍的同情与共鸣。(《音乐艺术的时代性》 )
民族感情、时代精神、革命激情,这些都统一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境遇中。
其三,对西方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日本鬼子欺凌中国民众,引起中华民族强烈的愤怒与拼死抵抗的情感;另一方面,国人反省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得出弱者受欺、应该自强的共识。而要实现国富民强,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先进者学习。当时的先进者主要是西方,因此要向西方学习。这样,向打我们的人学习,体现了复杂情感,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也学习日本的简谱、乐歌创作等。
我们虽然用不着刻板地模仿西洋音乐, 但是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西洋音乐理论我们必须采取, 作为建设新中国音乐的借鉴。 我们的音乐虽然可以发挥东方民族的精神, 但决不为狭义的民族意识所束缚。( 《音乐艺术的时代性》 )
其四,追求混生音乐。
在美学上,当时新音乐工作者显然持有他律论立场,强调音乐表现思想情感。也就是说,把思想情感当作内容。作为内容的思想情感,当然是反映上述民族感情、时代精神和革命激情的,而作为形式,则应该是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形式。这样的内容和形式才是匹配的。
任何一种艺术必须有一个适宜于表达它的内容的形式, 形式就是表现内容的一种手段; 没有高度的艺术性的形式就不可能充分地表现充实的内容。……文艺工作者强调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 向工农兵学习这是万分必要的。 但近年来有许多的音乐工作者, 在业务学习与技术训练方面除了学习一些民歌民谣之外, 别的方面几乎等于没有。 并且由于缺乏指导性的理论书籍和技术教师, 以及无原则地反对外国音乐理论与技术, 甚至乐器, 把音乐工作者陷入一个极其狭隘的圈子里不能进步。(《音乐艺术中现存问题的商榷》 )
在1980年的《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 一文中,贺绿汀再次强调要走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道路。他引用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谈话》 中的语录:“应该学习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以此为指导思想,强调要和“鼠目寸光的国粹主义、民族排外主义的落后思想作斗争”。
事实上, 中国民族音乐也由于近代的科学文化发展而随着发展。 我们不可能仍旧用落后的工尺谱、简谱, 必须改用外来的五线谱。……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他们各自的民族音乐, 但也没有一个民族用排斥外来音乐文化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 外来音乐文化只能使自己民族音乐增加新的因素, 不可能淹没自己民族音乐的特色。
从以上贺绿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各种言论中,可以看到一以贯之的“新音乐”理念,即采用中西结合的音乐形式,表现时代精神的民族思想感情。
回过头来看《牧童短笛》。
本来笔者也觉得《牧童短笛》 这种没有抽取具体传统音乐素材的混生音乐需要探讨族性归属,刘靖之关于“中国风格的西方音乐”的说法有道理,但是通过本项目的研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观念:如今族群/国族的名称没有变化,但是具体成员已经自然更替,尤其是心性有很大变化;也就是说族群或国族已经名存实异。“中华民族”以及56 个族群已经名存实异。从史实看,经过新文化新音乐运动洗礼的新兴中华民族已经拥有了新传统,具有了新族性。这个新传统新族性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它与中西千年传统文化都相关,但已经跟二者不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质。骡与驴马相关而不相同,已经是新物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新音乐都属于新兴中华民族,具有新族性。可以类比的是漫瀚人和它的蒙汉调,还有爵士人(美国黑人)和爵士乐,它们都已经是独立的族群及其归属的混生音乐。
总之,20 世纪30年代创作的《牧童短笛》,是新音乐作曲家的一次成功的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实践。该作品符合“中国之风格”的要求;没有明显的革命激情,是因为创作目的在于参赛。但是,作为“取韵”类型的混生音乐,它还是鲜明地体现了新的中华民族的局内观、局内感和局内情,也即体现了新的中华民族的族性。当然,其他类型的新音乐,也同样体现了这样的新族体的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