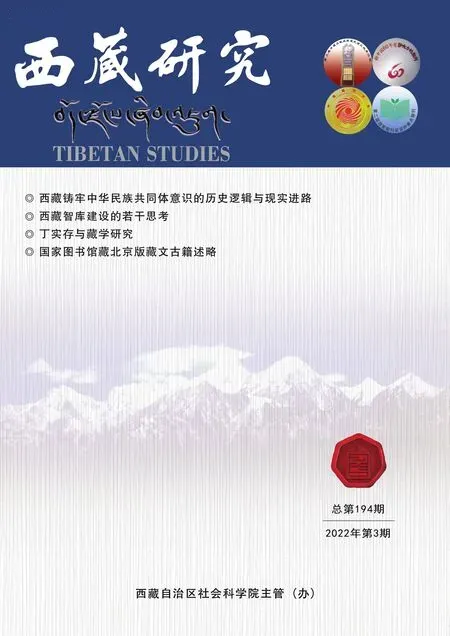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的“鄂托克”与“兀鲁思”考
董晓荣 忠布它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格萨尔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30)
一、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的“鄂托克”与“兀鲁思”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蒙古文,共7章,梵夹装长条书,纸张规格为14厘米×46.5厘米,共178叶,每叶分正面页与背面页。该书是蒙古史诗《格斯尔》各种抄本的底本,蒙古地区其他《格斯尔》史诗抄本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异本,目前发现的蒙古族史诗《格斯尔》木刻版也只有这一种。从史诗末尾记有“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孟春吉日完成”字样可判断史诗于1716年刻印完成。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处出现“鄂托克”与“兀鲁思”一词:
那时候有多萨、东萨尔、岭三个鄂托克,多萨的首领是僧伦,东萨尔的首领是叉尔根,岭的首领是晁通[1]8。
格斯尔把自己的一个化身幻化成陌生人,从远处喊道:“听说阿珠·莫日根杀死了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格斯尔的哥哥嘉萨·席克尔听到后,召集了三个鄂托克的百姓,找阿珠·莫日根问罪来了。”[1]73
格斯尔把锡莱河三可汗的子孙斩尽杀绝了,还掳获了他们的妻女和百姓,并收回了如意宝、无裂纹的黑炭宝、金粉抄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三百名先锋和三十个勇士的尸骨,以及三大鄂托克的百姓和十三金刚寺[1]231。
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虽然不在家,难道他亲爱的哥哥嘉萨和三十个勇士,以及我们三个鄂托克的兀鲁思都不在家吗?就让他们打来吧!
去吧,把三十个勇士和三个鄂托克的兀鲁思,还有吐伯特、唐兀特的兵马都叫来!骑着马的骑兵和没有骑马的步兵,把他们统统叫来[1]141。
他们到了一个名叫萨布的兀鲁思,把他们的一群马赶回来了。萨布兀鲁思有一个名叫戎萨的人[1]185。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得知,当时格斯尔的故乡有多萨、东萨尔、岭三个鄂托克,多萨的首领是僧伦,东萨尔的首领是叉尔根(叉根),岭的首领是晁通。僧伦是格斯尔的父亲,叉尔根和晁通是格斯尔的叔父。后来格斯尔成为三个鄂托克兀鲁思的统领。
蒙古族史诗《格斯尔》虽是以口头形式传播的民间作品,但其内容中也出现了诸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类名物词汇,留下了时代烙印。外蒙古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伦先生在其《格萨尔的历史源流》一书的引言中说:“格萨尔史诗中所提到的几十个亚洲的王国人名,其中多数已被历史证实,提到的王国、皇帝和英雄的名字,多数也属著名的历史人物。叙事诗中保存着几百个人名,几百个地名。而且,还有不少的历史事件、日期,也被历史所证实。史诗的版本很多,都可以作为研究基础,可以帮助我们从虚构的外皮下找出历史的内核。”[2]本文拟对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的“鄂托克”“兀鲁思”等词汇进行分析,以推断藏族史诗《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年代。
二、“鄂托克”一词的来源和出现于蒙古史料的年代
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鄂托克”一词来源于中亚细亚语群,是从粟特语演化而来的,原指国家和疆域,后来出现在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的各种方言中,表示它与场所、地域等的关系,蒙古地区的“鄂托克”正是以地域单位为基础的。在一定地域内游牧并使用其牧场的数量不等的阿寅勒集团组成了鄂托克。在军事方面,蒙古地区的鄂托克同样表示一定的单位,由鄂托克的兵丁组成的独特军队叫作“和锡衮”。同时,他还认为,鄂托克是蒙古汗国时代的“千户”[3]207-208。
蒙古汗国时期的军事制度中特色最为突出的是怯薛制度,《成吉思汗法典》载:“‘怯薛’,蒙古语,汉译多作‘宿卫’,直译为‘轮流值宿守卫’,简译为‘护卫军’。怯薛人员又称怯薛歹、怯薛丹……怯薛军是成吉思汗在征伐乃蛮部前夕为取得军事胜利而组建的。1204年,为迎击乃蛮部太阳汗的部队,成吉思汗将军队集合于哈拉哈河的客勒帖该合答颁布扎撒,以千、百、十人为单位组编军队,任命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和扯儿必(军官的职衔)……从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和平民子弟中选取强壮的、有技能的人建立了一支怯薛军队。”[4]这说明蒙古汗国时期怯薛军是在“千户”和“百户”及“十户”中产生的。
明朝时期,诸多蒙古史料中出现了“鄂托克”一词,如《蒙古源流》中载:“其人去后,齐齐克妃子将察哈尔、呼拉巴特营(鄂托克,1452)之鄂推媪之女来,置于摇车内诣其曾祖母萨木尔公主诉其故。”[5]334从这一时期(1500)开始诸多蒙文史料中出现了“鄂托克”一词,如《蒙古黄金史纲》中载:“以七部(鄂托克)喀喇沁中最大的永谢布,归入我们七部(鄂托克)科尔沁吧!八部(鄂托克)鄂尔多斯是主体,归入八部(鄂托克)察哈尔吧!以十二土默特,归入十二喀尔喀吧!”[6]115,224《蒙古源流》中载:“阿木达喇辛卯年(1531)生,据右翼卫古尔沁四鄂托克;乌克拉罕癸巳年(1533)生,据右翼阿玛海三鄂托克矣。”[7]在1600年的相关史料中还记载有:“格哷森扎据外七部(鄂托克)喀勒喀之地;瓦齐尔·博罗特据察哈尔八营(鄂托克)克什克腾之地。”[5]271由此可见,16世纪以后的蒙古史料中经常出现“鄂托克”一词。明清时期的诸多汉文史料,如《明史》《全边略记》《明实录》《清实录》等中“鄂托克”一词以“营”或“部”出现[8]27,因而当时的许多蒙古文史料译成汉文时多将“鄂托克”译为“营”或“部”。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也认为:“从十五世纪开始,我们在蒙古人那里看到了一种新的联合体,即鄂托克,它代替了前述古氏族——克兰,代替了世界帝国时代的‘千户’。”[3]206这说明“鄂托克”一词是15世纪后出现于蒙古语中的。
三、“鄂托克”与“千户”“兀鲁思”的关系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的“兀鲁思”与蒙元时期的“万户”等同,且是在鄂托克之上的一种政治联盟,包括若干个鄂托克组织。下面从“鄂托克”与“兀鲁思”之关系以及“鄂托克”与“千户”之关系看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三个鄂托克”的含义。
(一)“鄂托克”与“千户”的关系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元朝以后,这种区分仍旧保留下来,那就是在元朝崩溃以前存在的四十万户中,存下来的还有六万户,其中三万户属于左翼,三万户属于右翼。”[3]211他还认为,鄂托克下为爱马克,“中世纪的蒙古,游牧于同一地区的同族阿寅勒集团被称为爱马克。”[3]213这说明中世纪的蒙古社会组织为爱马克、鄂托克(指千户)和土绵(指万户)。达力扎布先生认为,“爱马克,元、明汉文史籍中一般音译为‘爱马’,或意译为‘投下’和‘部落’等……但在不同场合下投下(爱马)又具体指所谓千户军事游牧集团、王公贵族封地封民等。”[9]103-104这说明爱马克和鄂托克(千户)也是同一等级的社会组织。“蒙三汗国及元朝时期的千户,本身就是封授给某一诸王或功臣的封地、封民,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称作爱马……爱马是由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并不是血缘组织。”[9]104所以,鄂托克这一社会组织也与爱马克(爱马)一样由分属于社会阶层不同、血缘关系不同的人们组成。
(二)“鄂托克”与“兀鲁思”的关系
“兀鲁思”是突厥语词,它原来的形式为“兀鲁昔”,8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变成了后来的形式“兀鲁思”,语义也发生了一定变化;13—14世纪蒙古汗国的建立及其强大影响,使“兀鲁思”又被借回到突厥语中,并保留了其在蒙古语中的语音形式和主要义项,如“国家”“人民”“部落”等含义,但其在蒙古语中的“氏族”“家族”等含义由于受突厥语中相应词汇的影响却没有保留下来[10]。
早期的蒙古文文献中就出现了“兀鲁思”一词,《蒙古秘史》第1卷载:“巴兀鲁思亦儿坚兀禄帖蔑彻惕(俺不与人争国土百姓)。”[11]其中的“兀鲁思亦儿坚”是指“国与百姓”。蒙古国史学家乌兰先生认为:兀鲁思的蒙古语本意为“人众”“百姓”,引申为“国家”[12]。“兀鲁思”也称作“土绵”,汉译为“万户”,“土绵是一个同姓贵族家族及其属民构成的大集团,包括这个家族各台吉的鄂托克、爱马克、还包括附牧于该部的其他源于不同祖先的台吉们的爱马克等,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松散的联盟。”[9]120符拉基米尔佐夫先生说:“大部落集团组成为土绵,即‘万户、万人军团’并以其名为名。例如:乌梁海土绵,即‘乌梁海万户’或兀鲁思之意。由于土绵大小不一,而且其中又有一些难于分割的基本单位——鄂托克,因此,兀鲁思—土绵的范围是不稳定的,他们有分有合;旧的消灭之后,新的又代之而起。”[3]211由此可知,万户(土绵、兀鲁思)是由若干鄂托克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9]120。所以,兀鲁思与万户等同,且是在鄂托克之上的一种政治联盟。一个兀鲁思包括若干个鄂托克组织。
四、“鄂托克”与“兀鲁思”的含义及藏族《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时间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处出现“三个鄂托克兀鲁思”。“兀鲁思”包括若干个“鄂托克”组织,应该是由三个鄂托克组成的“兀鲁思”,即“万户”。下面从“鄂托克”与“爱马克”的关系来探讨““三个鄂托克兀鲁思”的含义及藏族史诗《格萨尔》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时间。
(一)“三个鄂托克兀鲁思”的含义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安冲对茹格牡一高娃说:“派人去通知三十勇士、三百个先锋;派人去通知三个鄂托克的人民,让他们全都备上盛宴,准备迎接圣主……”[1]92这说明格斯尔统辖“三个鄂托克”。
从前文的讨论中可知,史诗中所说“三个鄂托克”就是三个爱马克,也就是三个千户的规模,是由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政治联盟。
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载:“(敌人)变成黑花纹的毒蛇来了慌什么,我们变成大鹏金翅鸟将其擒拿;敌人变成咆哮的老虎来了惊什么,(我们)化作青铜鬃狮子把他战胜!好吧!那有什么呢?去吧,把三十个勇士和三个鄂托克的兀鲁思,还有吐伯特、唐兀特的兵马都叫来!骑着马的骑兵和没有骑马的步兵,把他们统统叫来。大部队在澈澈尔格纳河集结!到红草滩上格斯尔可汗的家里来!”[1]141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处出现“兀鲁思”一词。兀鲁思(指万户,蒙古为“土绵”)是由若干鄂托克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处出现的“三个鄂托克兀鲁思”应指以三个鄂托克组成的万户,即土绵(兀鲁思)。
(二)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流传于蒙古地区的大致时间
明朝时期的诸多蒙古文史料中,蒙古人自称为四十万蒙古,如《蒙古源流》载:“四十万蒙古中,得脱者惟六万,其三十四万皆被围而陷矣。遂聚前后脱出之六万人,至克鲁伦河之界,筑巴尔斯城而居”。[5]223《黄金史纲》中载:“士兵摆开阵势,几乎快要包围可汗的金殿的时刻,可汗才发觉了。于是抛弃了三十万蒙古,从先前见到的洞里,携同后妃、皇子,带着其余十万蒙古出走了。”[6]47这说明蒙古族退出漠北时,只剩下十万户,其中蒙古六万户和卫拉特四万户。
“清太祖自兴京地方崛起,打败其西北部的同族和东蒙古各部的联盟合军之后,岭东的蒙古各部相继降附清朝……到了太宗崇德初年,内蒙古几乎全部归属于清朝了。”[8]58-59之后清朝开始在蒙古地区设旗,旗下层组织是牛录,“万历四十二三年前后(1614—1615),八旗的三百零八个牛录中,蒙古牛录有七十六个。这说明蒙古人从清初以来,就作为满洲人的协助者扮演了重要角色[8]60。“盟旗是在蒙古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的基础上,参照满洲八旗制度而建立的,旗是满语‘固山’的汉译,蒙古语为‘和硕’。”[13]
达延汗时期(1)孛儿只斤·巴图孟克(1474—1517),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明史称之为小王子。自瓦剌也先死后,直到孛儿只斤·巴图孟克时草原才重新出现霸主,因其功绩被后人誉为达延汗,乃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六万户之一的喀尔喀万户格哷森札札赉尔珲台吉的外喀尔喀由七鄂托克组成,与内喀尔喀五鄂托克相对应[8]73。内喀尔喀各部,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年间(1606)投降清朝,约在清太宗天聪年间(1636年之后)设旗。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任命当时外喀尔喀代表人物八人为札萨克。原由七鄂托克形成的外喀尔喀,在太祖、世祖时代变成了七固山或七族、七和硕等[8]75。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颁赐哈密头目额贝都勒拉以札萨克印绶,并赐给红纛;第二年即编为旗队。”[8]80自此,四万卫拉特归属清朝并创建旗制。
从上文可以看出,到17世纪末期,内外蒙古六万户和卫拉特四万户均改编旗制,15世纪以后出现的“万户”之下的“鄂托克”这一社会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从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多处出现“鄂托克”一词来推测,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传入蒙古地区的大致时间段可能是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蒙古族《格斯尔》史诗源自藏族《格萨尔》史诗。从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出现的“鄂托克”“兀鲁思”等词汇来看,藏族《格萨尔》史诗传入蒙古地区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既有藏族文化原色、又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史诗——《格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