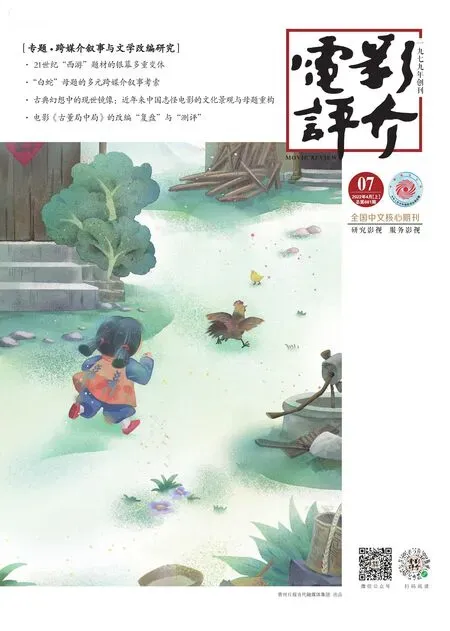《如果·爱》:一场视听语言符号构筑的“悬置式”诗意对话
徐丽沙 张楠楠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意传统,指围绕诗歌抒情性而形成的语言美感。如今,诗意已成为中国文艺的一种显性风格,形成了中国当代电影艺术突破商业和文艺两大传统的又一特定范式。当电影语言不再等同于镜头工具,可以独立刻画人物心理,实现对片段化、画面化审美经验的整合,电影作品便具有了独特的诗意美感。
上映于2005年的国产影片《如果·爱》在电影语言的诗意性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该片由陈可辛执导,上映即获得《时代》周刊好评,被誉为当年最具观赏性的华语电影。
一、电影语言诗意性的来源
将电影看作是一种语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影响下的文艺理论“语言学转向”。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在将电影语言与诗学研究方法相联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该流派主要成员的论文集《电影诗学》是学界公认的首部从理论角度阐发电影语言特征的论著。电影语言分为两部分:一是单个镜头在摄影机有目的的处理下转化为电影语言的过程;二是多个镜头可以通过拼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序列,这是电影实现复杂叙事功能的基础,也是蒙太奇作用下的电影语义生成过程。这两个部分是电影语言的理论基础,亦为电影语言诗意性来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电影语言的特点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所认为,其生成来自摄影机对物象素材的处理。这使得电影语言的诗意性实现不能仅依赖物象影像本身,而主要依赖镜头拼接促使单个影像本身的现实所指弱化,将片段串联成连贯故事的蒙太奇语义即电影的叙事功能。于是,研究者可以发掘电影语言诗意性的来源。首先,电影语言的核心目的是叙事。具体来说,就是利用镜头语言构造假定的、虚构的空间,再利用空间拼接及视听混合展开故事的时间序列。借用德勒兹的表述,即“镜头不再是一个空间范畴,而变为时间范畴”,也就是连贯、流畅的空间拼接构成的时间流动的叙事体验。其次,在电影叙事过程中,镜头语言下的时间、空间都脱离了现实生活中日常所见的时空体验,而引导观众走进一个电影语言塑造出的虚构的故事时空中。这就是电影语言的诗意性及其接受。
影片《如果·爱》讲述了一个超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正如片名“如果”一样,这是一次在电影语言打造的错位时空中完成的虚构。
二、电影语言诗意性的表现
(一)时空悬置的诗意
如上所述,电影语言的诗意性来源于电影叙事,是一个将现实的时空体验悬置而重新构建的虚构世界。正如法国哲学家利科所说:“对现实指称的悬置乃是接近虚构性指称的条件……建立另一个世界——符合最本己的可能性的世界,这难道不是诗歌的功能吗?”叙事艺术的诗意表现需要“悬置”现实中既定的组合意义,即在新的虚构时空中构建新的指涉意义的可能,引导观众跟随虚构的故事展开想象和联想,体会超越现实时空的人生真谛。这是电影语言诗意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电影《如果·爱》的叙事游离于不同层次的时间、空间中,引导观众在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穿越转换,从而实现时空悬置背后的诗意传达。片中的时间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维度。叙事时间是影片放映的时间,也是观众观影的总时长——约100分钟。故事时间是影片所讲述的故事的发生时间——这是一个跨越10年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于10年前的北京,影片叙事开始于两人分手10年后在上海因合作拍戏而再度重逢的场景,从而引发了回忆、感慨和未知的结局。关于两人的关系、当年分手的原因、重逢后的心境等系列问题,影片都将其打碎在观影的100分钟内,片段式抛给观众。如此促使观众紧紧跟随叙事节奏,在脑海中整理线索碎片段、透析人物心理。片中穿插运用多元叙事技巧,为了防止“时空错乱”而用到了诸多时间标记作为提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原声录音”。例如,当男女主人公10年后从上海赶回北京,重新来到当年“蜗居”的地下室时,镜头对准了桌上的录音机,孙纳打开录音机,便听到了当年林见东痛失爱人后多次来此等她未果而留下的录音:“1995年12月9日,你没有回来……”“1996年11月……”。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用这种方式记录着他次次期盼又次次失望的心碎感、无力感。而此时银幕前的观众也透过这些时间标记,体会这段往事带给人物的伤痛。
片中的另一个维度即时间指涉维度,是指涉时间和被指涉时间的维度。指涉时间即故事发生的时间;被指涉时间最终形成于观众的脑海中,即看完整个故事后引发观众联想的总时长。在《如果·爱》中,前者等同于故事时间——10年;后者则取决于每位观众在还原了故事中所有的片段、细节后,引发的对时代背景、人生经历、成长体验的联想和回忆。这里,影片用到了一处明显的时间标记来强化这种效果:画外音反复穿插着歌手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带有时代烙印的流行歌曲提示着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的时代背景;而其中的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每次出现都暗示着主人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心境。这些时间标记足够提示二人分手的原因,也足够唤起有着相似生活、情感经历的观众联想,从而让电影的被指涉时间更长,让故事内容更具穿透力。
电影中的空间“是人为组合的假定空间的构成形式”,由被摄影机限定在有限空间内的视觉呈现构成,通过蒙太奇的拼接,在影片的叙事中能够引起观众的无限联想。电影《如果·爱》中的空间包含故事中的现实空间和回忆空间。
现实空间即故事发生的地点、场景,地点是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场景包括10年后二人重逢的上海片场、记者发布会现场、放映厅、宾馆、游泳池、餐馆等,还包括10年后二人故地重游到北京所到的公园、街道等。回忆空间主要指故事主人公回忆里的空间场景,比如,宿舍、地下室、结冰后的护城河、公交车等。影片配合“闪回”的叙事技巧,每每在主人公陷入回忆的视角下呈现出清晰、丰富、生动的回忆空间,与千篇一律、高楼耸立、街景重复的现实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按人们正常的感知心理,现实空间因为与现实的时间距离更近,应该更加清晰和生动,而回忆空间因为记忆远去,应该模糊和单一。但影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将生锈的自行车、凌乱的生活用品等大量细节填充到回忆空间。这些独特的电影语言使回忆里的画面鲜活、饱满地呈现在人物和观众面前;而这无疑暗示着回忆的鲜活,暗示着这段回忆在主人公人生中的重要性,观众亦被这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深深打动。
(二)复杂叙事中的情感诗意
诗意的内核是抒情。作为叙事艺术的电影,是将人物情感穿插至复杂叙事中,从而实现诗意表达。“在电影试图用它的语言表现诗意的时候,不得不尽可能减少叙事中的信息含量,以使情绪能够凸显出来,这是电影语言走向诗意表现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下,电影语言在提供大量信息讲述完整故事和利用叙事技巧表现人物情感之间,选择了后者,由此表现出诗意性特征。
电影《如果·爱》是一个将复杂叙事发挥到极致的范例。在有限的叙事时长内,它讲述了三段彼此交织的故事:一是10年前在北京,男女主人公相恋的故事;二是时隔10年后,二人在上海合作拍戏的故事;三是合作拍戏的剧本中班主、小雨和张扬的故事。三段故事可以分别简称为: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故事、剧中的故事。
影片开篇,俯视镜头拍摄一辆穿行在雪天城市里的公交车。当公交车缓缓驶出镜头,记者从车上走下来,将视点带到了上海的片场——10年后的现在的故事现场,紧接着又是一场全景歌舞剧场面,提示观众故事发生的背景及主要人物身份。此处系列镜头一气呵成,标记了现实和虚构故事之间的界限。而其中的线索人物——记者,在此过程中讲出了一段内心独白:“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这段“人生如戏式”的独白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是电影片场,故事的内容是艺术家们剧中剧外的人生经历,故事的情绪底色是黯淡的、悲伤的。这一底色和热闹的片场、发布会现场构成了鲜明对比。接下来故事展开的过程,正是叙事者带领观众去解开疑问的过程。女主人公孙纳出现在发布会化妆间,拒绝了记者为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建议,说道“别人哪能理解我吃过的苦”——此处以记者之眼见证人物内心的苦涩。此时,蒙太奇将视点切到了正在乘车赶来的男主人公林见东,镜头用随行经纪人的视点追问林见东接片的原因:“你不要告诉我,你爱上了女主角,不可能的,你没有利用价值,她只跟导演。”这既是对故事前因后果的交代,也是对男女主人公10年前爱情故事的旁观式解读。看到此处,观众似乎已对故事结局有了预判,但还是与主人公一样,对遗憾无法释怀,于是主动跟随镜头深入到故事中随人物感知。这即是影片开篇的电影语言,也是电影诗意的起点。
内聚焦视点是故事中人物的视点。这类视点聚焦在故事中的人物内心,用电影语言尽可能还原人物所想、所感。电影《如果·爱》在开场由叙事者视点引入后,用多人物视点间的拼接、跳跃,推动叙事继续展开。过去的故事,在男女主人公交叉的回忆视点中交替讲述;现在的故事,在包括导演聂文在内的当事人的视点中讲述;而剧中的故事则由分饰各角色的人物视点讲述。
如此讲述,自然而然地将观众带到一处处故事现场,感人物之所感。尤其是人物视点在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间拼接转化、交替“闪回”,将两个时空的精神感知传递给观众,引发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矛盾感和无力感的深刻共鸣。例如,片中多次出现男女主人公分别在游泳池里潜到水底,引发回忆的情节,皆是由水底画面交替拼接二人相识、相知、相恋的片段画面。这些零散的回忆在人物视点的带领下为观众一一还原,也使故事的情感张力得到了充分释放。这是推动电影叙事的情感力量,也是电影诗意的主要来源。
三、电影语言诗意性的意蕴
电影语言的诗意性使得影片具有丰富的意蕴空间。“电影即是充满间隙的连续性画面,其本质在于看不见的抽象空间,这是在镜头碰撞中产生出的想象性空间。”当虚构的故事在情感寓意、人生哲思方面,唤起了观众对现实人生的新的思考,那么一个全新的“想象性空间”就达成了。这是电影语言诗意性引发的意蕴阐释。
电影《如果·爱》的意蕴空间集中在电影语言讲述的现实与虚拟故事之间的同构和象征隐喻。影片用复杂的叙事语言讲述了三段故事——过去的、现在的、剧中的。三段故事又构成了一个“套叠”结构。显然,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故事中,主人公及时空关系在影片叙事下是现实的人物关系,这是一个现实的跨越10年的爱情故事。而剧中的故事,是由现实故事的主人公在拍戏这一工作中演绎出来的,是在现实故事框架下套叠讲述出来的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
剧中故事的开端由导演聂文的一句话引出“张扬并非真的爱小雨,班长和小雨间也谈不上爱情”——镜头追踪聂文讲戏的画面,蒙太奇语义介绍了聂文的身份——导演,也就是女主人公孙纳现在“依靠”的人,她现在的情人,而林见东是她过去的情人。这样的语义暗示了这是一个现实三角恋的故事,套叠讲述了一个剧中小雨、班长、张扬三人三角恋的故事,而且现实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正好是剧中三个角色的饰演者。这两个三角恋故事构成了明显的同构关系。在电影的蒙太奇语义下,现实与虚构开始了互相指涉的语义游戏,将电影语言的诗意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将意蕴空间进行了充分释放。
这种双层次的互相指涉在片中比比皆是。例如,林见东在拍戏过程中借台词质问孙纳“告诉我,怎样才能像你一样快乐?”。这是剧中人物张扬对小雨的质问,同时也是林见东对孙纳时隔10年后的质问,传达着他被孙纳抛弃后的心酸、痛楚、恨意。再如,聂文在发现孙纳和林见东的旧情后,曾几次修改剧本;而全剧的高潮也是整部影片的高潮,即拍摄最后一场戏时,聂文即兴改了剧本,并借歌舞抒怀,对孙纳说出了心底的那句话——“让我成为你的回忆”。这是剧中人物做出的选择——放弃,也是现实中聂文与孙纳的结局。
影片中还出现了三层次的互相指涉。例如,当观众沉浸在林见东的痴情和孙纳的绝情中,为男主人公愤愤不平时,镜头对准了坐在放映厅里的二人。这时放映厅里放映着剧中小雨、张扬的画面,而坐在放映厅里的孙、林二人在画面的触发下共同回忆起10年前二人在冰上相拥的场景。剧中、现在、过去,三段故事在系列蒙太奇中共同呈现,也完成了现实与虚构的互相指涉。孙、林二人最终相拥在放映厅中。此刻,观众已被深深打动,感慨这份感情的珍贵,而忘却了方才的遗憾。但紧接着跟随拍摄进度,剧中人物走向了无言的结局,观众也似乎被拉回了“现实”——这份充满矛盾、彷徨,结果未知又让人无法自拔的情感体验,就是《如果·爱》电影语言寓意言说的意蕴——真爱何为?
此外,在影片中,除了蒙太奇语义外,音乐、歌舞的象征性拼接也构成了这种意蕴的诗意性呈现:有浅层次象征,例如前文提到的歌曲《外面的世界》,寓意着现实的无奈;还有深层次象征,例如在过去的故事中,孙纳决定离开林见东,影片在这一部分用了歌舞剧和故事画面交替出现的叙事手法,实现了互相指涉的象征意蕴。孙纳出卖身体“跟了”导演,遭遇背叛的林见东久久不能释怀。影片此处的画面处理沿用了歌舞剧里的音乐和歌曲,同时用晃动的镜头,模糊现实和回忆的界限,让观众体会到林见东长期被爱折磨、精神恍惚的状态。另外,影片中多次出现在拍摄现场,孙纳彷徨在十字路口的人流中,在“狂欢”般喧闹的街头加入群舞演出。这些都象征着主人公在爱情面前的矛盾心境。
结语
《如果·爱》这个片名提示了一种假设和虚构。影片正是用电影语言“悬置”了对“爱”的现实指涉,旨在在虚构的时空中给予“爱”一份诗意的表达。引人追问“如果爱了,会怎样?”——对于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是对过去和现在、现实和理想的共同拷问,故事最终“如果式”的结局,也给予这个问题一个开放式的回答。而留给观众的是现实的共鸣抑或是理想的寄托——正如影片开篇处那段“人生如戏”的独白所述,这是一场时空、真实与虚构的诗意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