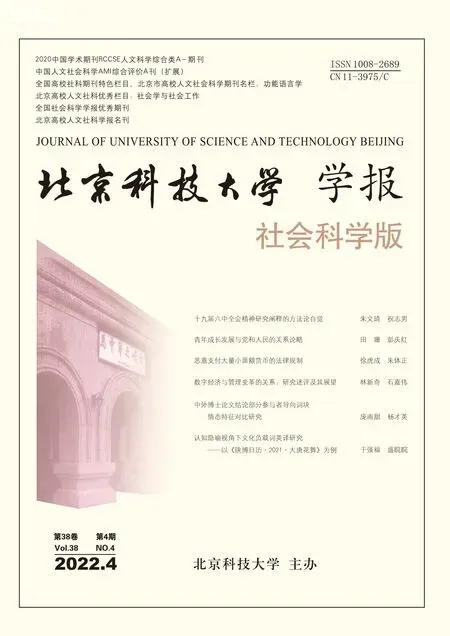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阐释的方法论自觉
朱文琦 祝志男
〔摘要〕 坚持方法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也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哲学依据。文章认为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要着重把握三对对立统一关系。一是坚持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科学分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历史成就,从整体上揭示党的百年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内在统一性。二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全面展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世界意义,坚定党和人民走好中国道路的信心。三是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掌握历史主动,在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中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方法论;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2689(2022)04 0359 0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集中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议》的说明中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1]79。这一原则要求,是贯穿《决议》起草和形成过程的哲学依据。在马克思主义话语谱系中,“方法论属于主观辩证法的范畴”[2]598,方法论自觉则强调的是主体在看待、研究客体时应秉持正确的思维方法,从而对关涉对象的“一些基本立场、方法、路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3]。强调方法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正如恩格斯[4]437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就研究阐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方法论自觉而言,主要包括坚持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三个方面。
一、坚持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二者共同呈现着事物变化发展的整体概貌。一方面,阶段性与连续性相互区别。阶段性反映的是某一时间段内事物变化发展的凭依条件、任务要求及系统特征,连续性体现的是事物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以及不同阶段之间演进变化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阶段性与连续性彼此依存。阶段性是相对于连续性而言的,反之亦然。阶段性内在地规定着连续性的要素构成及变化规律,尽管它具有某些程度上的整体性特征,但毕竟不是整体。连续性表征的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能较为清晰明了地展现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基于阶段性、以阶段性为前提的一种属性,连续性与阶段性二者互为存在条件。
应当看到,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把握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内在逻辑等方面,社会上仍然存在误解、误读,甚至歪曲、丑化党的历史的倾向。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提上,有观点认为,中国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革命预想不相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有的人看到了改革开放前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变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改早了”“搞糟了”。其依据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消灭了中国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导向,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在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上,有的人过分夸大两个时期在内外政策、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实际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差别,认为二者是各自独立的,甚至别有用心的人以前者否定后者或是以后者否定前者,等等。以上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如何看待党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展开的。这不仅影响民心民意、弱化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而且事关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党的执政基础,对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精神也提出了现实要求。
为此,我们必须分析把握好百年党史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可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这四个时期既相对独立、各有特点,又前后继起、有机关联,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就阶段性特征来说,一是四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不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决议》在分时段系统阐发百年党史的奋斗历程时,首先明确指出的就是党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使国家复兴”[5]1469,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尽管付出艰辛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决议》用两个“迫切需要”[1]4的凝练表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也印证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指導思想之间的良性互动。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航程。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从革命、建设、改革等实际出发,善于分析和研判每一阶段的时代形势,在此基础上明确重点任务,并持之以恒不懈奋斗。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开天辟地”“改天换地”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6],中国共产党在回应时代要求、解决时代任务的过程中成长壮大,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中推进事业发展。二是四个时期的历史成就不同。从逻辑关系上看,主要任务与历史成就直接相关,“主要任务”体现的是问题导向,“历史成就”彰显的是目标导向。党对于时代提出的要求、实践赋予的使命、人民向往的生活回应越主动、越富有成效,就表明主要任务完成得越好,也就意味着党越能顺应时代发展、契合实践需要、赢得人民拥护爱戴。《决议》对四个时期历史成就的回顾总结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系统全面的。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1]3到“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从“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15到为民族复兴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61,党领导人民砥砺拼搏、迎难而上,不断创造着新的人间奇迹。具体到每一时期的历史成就,《决议》大致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次序展开,这既诠释了“一”与“多”及“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联,又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体现了阶段性框架内党的历史的整体性特征。
在注重研究阐发阶段性特征的同时,我们也要分析把握好百年党史的连续性特征。诚如前述,四个时期相对区别又相互关联。当然,这种紧密的统一性不是人为赋予的,也不是靠主观想象推演得出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统一性,不仅全维度、全过程展示着党领导人民历经百年沧桑创造的丰功伟绩,而且全景式再现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就连续性特征来说,一是四个时期坚持党的领导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百年奋斗史。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封的,而是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最终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贯通百年党史的主线,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所在。二是四个时期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一以贯之。《决议》强调:“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1]66。百年来,党依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各项事业,千方百计带领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从列强凌辱、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深受三座大山奴役压迫,到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书写新时代新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三是四个时期党的奋斗主题一以贯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经过百年艰苦探索、不懈努力,这一主题得以持续深化,民族复兴前景更加光明。
此外,我们还要从整体上研究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论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固然有所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8]22。同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百年党史的梳理总结,也是从整体意义上阐发的。四个“伟大成就”,是党领导人民赓续奋斗的必然结果,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生动展示。十个方面宝贵经验分别在根本保证、价值追求、思想先导、基本立场、历史抉择、世界格局、不竭动力、立身之基、致胜法宝、强大支撑等方面各有侧重,同时又密切衔接、相互配合,是党和人民的重要精神财富。四个“伟大成就”和十个方面宝贵经验都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共同创造和积累的,这一整体性视域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逻辑前提。
总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原理启示我们,只讲阶段性而忽视连续性,就割裂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联系,容易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甚至偏离中心关键,而对事物未来发展缺乏系统预见和长远规划。相反,如果只讲连续性而忽视阶段性,则会看不到每一阶段的具体实际、突出矛盾和发展要求,容易催生急躁冒进情绪而影响事业发展。强调坚持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就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时,自觉做到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要注意系统综合,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二、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其中,矛盾普遍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事物之所以存在发展的共性所在。矛盾特殊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某一事物或事物某一方面、某一环节、某一阶段等所呈现出的特征。正是有赖于特殊性的存在,从而将不同事物区分开来。普遍性与特殊性既不等同也不能完全分开,当具备了一定条件时,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列宁[9]558指出:“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10]320在《矛盾论》中也对二者关系作出深刻阐释:“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决议》[1]68总结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强调:“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每个国家都有从实际出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道路选择不同,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及最终确定,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交织作用的结果。道路选择只有切合本国实际及人民利益需要,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反之,则可能走入歧途,使国家和人民事业遭遇被动局面。习近平总书记[8]21深刻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融贯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项事业之中,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大革命失败后,党客观分析敌我力量,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向农村进军的正确抉择。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经济、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不失时机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党和人民事业由此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迈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在中国道路上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发展理念、实践成就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道路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决议》[1]67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在科学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的基础上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壮大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道路可以形成、赖以发展的精神指引,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冰冷的教条和僵化的教义,其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5。脱离中国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情况,而仅将目光局限于“本本”“教条”或外来经验,不仅不利于中国道路的深化拓展,而且容易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百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决议》对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也作出了系统总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62。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等日益为世人所关注,这其中“具有本源意义”[12]的就是中国道路。对于人类进步事业来说,党的百年奋斗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整体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依托制度优势,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不仅避免了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现代性之殇,而且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現代性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从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价值指向等多个方面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概括地说,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及生成发展集中体现了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的辩证法,而中国道路的示范作用及世界意义则充分彰显了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辩证法。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贯通、辩证统一的典范,标志着“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13]。矢志不渝沿着这条道路奋力前进,是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不断走向未来的根本保证。深入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维度看清楚过去百年来党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不是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也有助于我们从现实的、未来的维度弄明白党如何才能继续成功,而不是在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面前停滞不前。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阐释中国道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及实践要求时,我们尤其要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片面夸大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不愿承认或否认其他国家和民族探寻自身发展道路的有益尝试、宝贵经验和独特智慧,看不到中国道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制度架构、文化文明的共通之点及互补之处,甚至将中国道路与其他道路模式完全对立起来;一种是过分突出中国道路的一般性,基于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因而认为中国道路为其他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模板”,而忽视了中国实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传统、国内环境、制度基础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主动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理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探索推进中国道路的新征程中不断创造出更大成就。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议》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1]67。中国道路扎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固的实践支撑和广泛的民意基础,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通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成立百年来团结带领人民开创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铸就的光明前景,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走好这条发展道路,才能掌握自己命运、赢得历史主动。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积极借鉴其他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在新时代不断创造新辉煌。中国道路有其特殊性,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是作茧自缚、封闭僵化的。人类文明具有丰富性、多样性,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要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借鉴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潮中坚持好、拓展好中国道路。
总之,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统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条道路全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内在联结,也为我们在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供了基本切入点。
三、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
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前进性揭示的是事物发展总的前进方向和总的发展趋势,曲折性反映的是事物前进和发展过程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辨证统一,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生动体现,这一“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4]148,同样贯穿于、体现在百年来党和人民事业的开创、发展、壮大过程中。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作为过程而产生、存在和发展,形而上学的“不变论”“激变论”都是错误的。恩格斯[14]270强调,在“辩证哲学”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泽东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15]29。他还警醒全党,“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16]220
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深刻论断,不仅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远大前途及发展行进的曲折历程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两个必然”[11]43的重要论断。之后,结合革命实践及对形势任务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强调了“两个绝不会”[11]592。“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是内在贯通、具有高度逻辑自洽性的统一整体,这既为共产党人从长远着眼应对复杂革命形势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同时为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列宁[17]263在论述1914 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曾分析说:“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当时国内弥漫着的“速胜论”“亡国论”,毛泽东[18]215一方面严厉指出“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客观分析问题,指出“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此外,毛泽东还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总体进程及最终结局,即经由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最终取得抗战胜利,这对于廓清部分群众的认知迷雾、万众一心打败日本法西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实践中,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新的实践阶段,这標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同时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经验借鉴。毋庸讳言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革命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并非易事。列宁[19]343在十月革命后曾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列宁的反思是实事求是的,中国革命同样面临这样的现实挑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革命初期,年轻的共产党人将工作中心放在城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党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决议》指出,“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5经过28年浴血奋战,党和人民付出巨大牺牲,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发展新纪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实现了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一时期尽管遇到了挫折,但成就是主要的,期间取得的发展成果、发生的深刻变革、总体的前进态势不容否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峻考验。邓小平[20]383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作为思想、运动与制度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同样遵循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矛盾关系原理,不断实现着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丰富拓展。
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等诸多领域存在的结构性、深层次、历史性矛盾,及外部环境新的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调动和汇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力量,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此,《决议》从13个方面分领域作出全面总结。这些成就之所以取得、变革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得益于“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1]26。在看到历史性发展成就和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21]。前进的道路上,无论是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还是西方长期奉行的敌视政策,无论是基本国情的长期不变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局性变化,都对新时代坚持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更高要求。那種对客观形势缺乏系统性、客观性思考,看不到前进中的风险挑战,一厢情愿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而过于夸大困难挫折,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同样是错误的。
越是在特定历史关头,越是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刻,越要保持政治清醒。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务必”。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5]1438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22]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申了“两个务必”,并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他又作出“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23]的重大论断,为我们深刻把握“时”与“势”、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了方法依据。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24]226为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脚踏实地,不超越阶段,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聚精会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总之,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既是我们研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方法遵循,也是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决议》[1]69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面向未来,我们要精准研判“危”与“机”,善于从百年党史的伟大征程中汲取自信自强、攻坚克难的奋进力量,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将党和人民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 ]肖前, 黄楠森, 陈晏清.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 3 ]丰子仪.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17-27.
[ 4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曲青山.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N]. 光明日报, 2021-02-03(11).
[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02).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9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列宁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2]韩庆祥. 作为一种学术分析框架的“中国道路”[J]. 江海学刊,2020(2):37-42.
[13]陈曙光. 现代性建构的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J]. 哲学研究,2019(11):22-28, 126.
[14]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6]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7]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9]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0]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1]习近平. 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光明日报, 2022-04-22(02).
[22]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12-19(02).
[23]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N]. 光明日报, 2022-03-07(01).
[24]習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to Study and Interpret the Spiri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U Wen-qi1, ZHU Zhi-nan2
(1.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2. College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Adhering to method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 is a consistent proposition of Marxism, and it is also a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summarizing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 To study and interpret the spirit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 must focus on grasping the unity of three pairs of opposites. The partys century-long history, major achievements and the inherent unit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second is to adhere to the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fully demonstrat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follow the Chinese road well. The third is to adhere to the unity of progressiveness and tortuousness, maintai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grasp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advance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world development.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ral Committee;methodology;new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