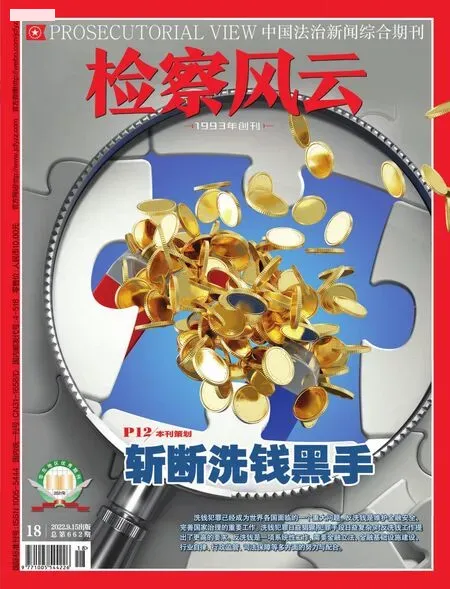船舶碰撞事故处理如何适用交通肇事罪
文/颜乔浠 梁春程

船舶碰撞事故法律问题值得研究
船舶碰撞侵权的管辖问题
我国《刑法》第6条规定,犯罪行为或者结果之一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属于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应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发生在海域的船舶事故,1952年《统一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中刑事管辖权方面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第1条规定:“在海运船舶发生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并涉及船长或船上任何其他工作人员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刑事或纪律案件,仅能向发生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时船舶所悬旗帜国家的司法或行政机关提出。”
因此,只要事故发生在我国领海或者碰撞船舶其中之一的船旗国为我国,我国的主管机关就享有管辖权,采取调查取证、公诉以及审判等措施追究犯罪。
船舶特点
第一,船舶人员的特点。船舶的驾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由船长或大副是无法完成的,需要不同职责的人员进行分工配合。一般而言,船长掌控船上所有的人员和设备,以及指挥船舶驾驶,不参与船上具体事务,但有总体管理监督职责。按船上人员岗位性质,可分为三个部门:甲板部、轮机部、事务部,与船舶驾驶相关的是甲板部和轮机部。甲板部是指负责船舶安全航行、停泊、与外界联系以及本船船员日常生活的部门,甲板部通常由大副负责,下面还有二副、三副、水手长、一水、二水等人员组成。轮机部负责船舶动力装置的管理,由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电机员、机工长、机工等人员组成。船舶的驾驶需要分工协作,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会危及船舶的行驶安全。当船舶发生碰撞事故时,很难归咎某一个固定的个体。在现有的交通肇事判例中,往往是肇事时的驾驶员被追究刑责。
第二,船舶行驶特点。一是惯性大,机动车虽然速度快,但驾驶易操作,而船舶(大型)的船速虽然很慢,但是其在水面上的惯性也很大,其操纵性不如机动车,并且没有迅速有效的制动措施;二是船吸现象,当两船并行时,因两船间水的流速加快,压力降低,外舷的流速慢,水压力相对较高,左右舷形成压力差,推动船舶互相靠拢。另外,航行船舶的首尾高压区及船中部的低压区,也会引起并行船舶的靠拢和偏转。如果在船吸现象产生前未能察觉或很好避让,可能无法避免碰撞。
船舶碰撞事故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特点
第一,定性标准依交通肇事罪相关标准。船舶因其造价高、吨位大、搭载人员多、搭载货物价值高,肇事后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大于道路交通肇事的损失,比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万元,在交通肇事罪规定中已经属于“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可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2015年新版《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中,造成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属于一般事故,低于100万元的仅为小事故。显然我国《刑法》所指的重大责任与《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所指的重大责任不是同一概念。但在实践中,这一区别有时不会被考虑。以〔2015〕佛三法刑初字第472号判决书为例,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区分陆地或者水上交通肇事,应按照该司法解释对水上交通肇事案件进行定性、裁判。
第二,从轻、减轻情节效果明显。水上交通肇事虽然造成的损害结果较道路交通肇事严重,且标准仍沿用道路交通肇事的损害标准,但其在量刑上,从轻、减轻情节的效果明显。如同是造成两人死亡、负全部责任的事故,按照交通肇事罪的标准应当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水上交通肇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如果有自首、立功、赔偿、获得谅解等情节,在量刑上都可以获得较大幅度的从宽。以〔2014〕沅刑初字第109号判决书为例,该案死亡人数达到12人、肇事船负主要责任,因具有自首、立功、积极救援、当庭认罪等情节,法院最终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第三,肇事船舶公司进行赔偿等同于被告人赔偿。在水上交通肇事中,赔偿与被害人谅解是量刑的重要考虑的因素。但如果肇事船舶公司赔偿了受害人家属,被告人没有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法院会如何认定?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会将肇事船舶公司的赔偿认定为法定的从轻情节,但处理上却是将船舶公司赔偿视同被告人(员工)赔偿,与被告人全赔是一样的效果。以〔2017〕粤2071刑初2627号判决书为例,该案死亡人数两人、肇事船负主要责任,肇事船舶的公司已赔偿,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法院最终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第四,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判断。交通肇事罪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是法定升格刑,这在道路交通肇事中较易判定。在一般情况下,驾驶机动车撞到他人是很容易令驾驶员察觉的一件事情,但在水上船舶航行则不同,如大型船舶的船身特别大,并且坚硬,如果碰到了别的小船甚至没感觉,船员没有察觉有碰撞,继续驾驶船往前开,后来通知说其实相撞了,又把船开回来。这种情况下,较难判定船舶是否逃逸,实践中如无法证明主观明知肇事后驾船驶离,则不认定为逃逸。
第五,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判断。同样的,逃逸致人死亡在道路交通肇事中较易判定,在水上就难以认定了。因在水域中援助无法像陆地上一般及时,尤其在初春、冬季和秋末等寒冷季节,落水的船员很容易因为水温低而冻死。在水上肇事后逃逸的情形下,往往难以认定受害人的死亡究竟是碰撞肇事还是因为无法得到及时救助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一般定性为逃逸,但有确切证据可证明肇事时如被告人施以援救就能挽救被害人生命的除外。在〔2017〕沪0110刑初966号判决书中,法院审理查明,船舶碰撞后,黄某等人在“金虹18”轮甲板上呼救,并使用手电筒向“宁高鹏666”轮驾驶台照射求救,被告人孔某、孙某见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不向主管机关报告,选择驾船逃逸,约9分钟后“金虹18”轮因碰撞进水沉没,黄某等3人均溺水而亡。法院认为,孔某、孙某明知肇事后有义务留在现场、对方情况紧急且有施救条件,仍驾船逃离,致使“金虹18”轮因碰撞进水沉没,遇险3名船员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落水而溺水死亡,故本案中因逃逸而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应予认定。
第六,避免可能性问题。在过失犯罪中,要求行为人遵守注意义务,是确信可借此回避法益的损害后果,也即是过失犯的客观归责以结果避免可能性为中心。但由于船舶自身特性,如惯性、操作缓慢等,有些事故即便早两分钟进行规避都无法避免,此时船舶碰撞中的过错认定应当如何?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大多以危害结果为判定,即认定被告人驾驶船舶操作不当引起交通事故发生为定性标准。以〔2013〕连刑初字第333号判决书为例,律师提出,根据发报记录、水手证言、当班轮机员证言等证据均能说明陈某某当时已履行了相应的职责。按照两船当时的航行情况,满载吃水的恒晖轮单独有效避让时长超过10分钟,根本不可能让船长在进驾驶台不足3分钟内避让成功,碰撞已不可避免。而法院认为,根据海事部门的事故调查报告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在案证据,被告人陈某某进入驾驶室后存在指挥驾船操作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系导致该起重大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