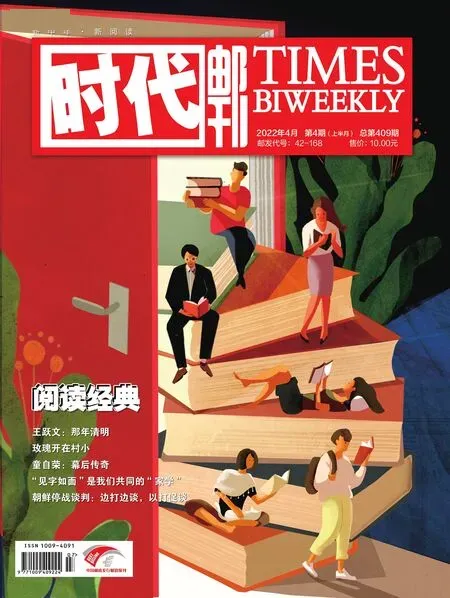那年清明
王跃文

2017年清明,我照例回乡挂青。那些埋在黄土里的先人,我只见过奶奶。我自小是奶奶带的,直到她老人家去世。1975年,我十三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从学校回家,听村里的人说:你奶奶死了。我喉咙立马干了,在田埂上飞跑。田野虫蛾狂舞,打在脸上生痛。回到家里,空中弥漫着鞭炮和纸钱的烟尘,奶奶已躺在棺木里,棺材盖还没有合上。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凉凉的。
乡下的丧礼要图热闹,当时唱老戏是禁止的,村里安排了文艺演出。一个小节目,故事是一个叫“地老鼠”的地主,偷生产队的粮食,被女红小兵抓住了。红小兵端着木头削的梭镖不停地刺向地主,反复唱着一句唱词:地老鼠,大坏蛋!我听着很生气,因为我爷爷的诨名就叫“老鼠”。乡下人都有诨名,平辈间通常不喊大名,多以诨名相称。乡下人不能容忍别人喊自己长辈的名讳,而让人喊自己长辈的诨名简直就是侮辱了。母亲和亲戚们都在哭丧,帮忙的乡亲们只是看热闹,没谁在意正在地场坪演出的小节目。
奶奶去世时,爹在四川放蜂。通信不便,无法告知爹回来奔丧。夏天将尽,爹带着蜂群回乡。爹先安顿好蜂场,才领着运蜂的卡车司机回到家里。妈妈客气地招呼卡车司机,请他入座吃晚饭。临坐下,爹问:老母亲呢?爹望望妈妈的眼神,忙站起来,去了奶奶房间。我也跟了进去。依乡俗,奶奶床上的被子、床垫草、竹簟,统统都烧掉了。奶奶的床上,只有空空的床板。爹站在奶奶床前,卷了喇叭筒烟,火柴却怎么也刮不燃。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时常会想起那个荒诞的葬礼,也时常想起爹站在奶奶的空床前刮不燃火柴的样子。
我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我都没见过。爷爷五兄弟都穷得精光,只有我亲爷爷娶妻成家,养了一个独子,我的父亲。爷爷的兄弟们都是我父亲养老送终,他们的坟也都在村庄对面的太平垴上。清明上坟那天,我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满眼皆是挂了白的黄土堆。我想起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都白”,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他在外教书,也写文章。他想过自己手头做的事,同那些故去的先人,同那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到底有多少关系?
我脑子里关于乡村的故事,有自己亲眼看见的,但大多都是听来的。我知道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有两位爷爷辈的,一位大名王禹夫,一位大名王悠然。我自小听说,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我家还欠着王禹夫家三升米。很多人家欠财主的账都不想再还,我奶奶却在夜里偷偷跑去把米还了。奶奶说,欠的就是欠的,借账是要还的。多年后,这件事常被人说起,有人笑话我奶奶胆小怕事。那些乡亲,有对王禹夫他们拳脚相加的,也有对他们暗自同情的,更多却是围着看热闹的。如今,喧嚣的历史已经尘埃落定,乡亲们谈起王禹夫、王悠然,都说他们是大善人。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