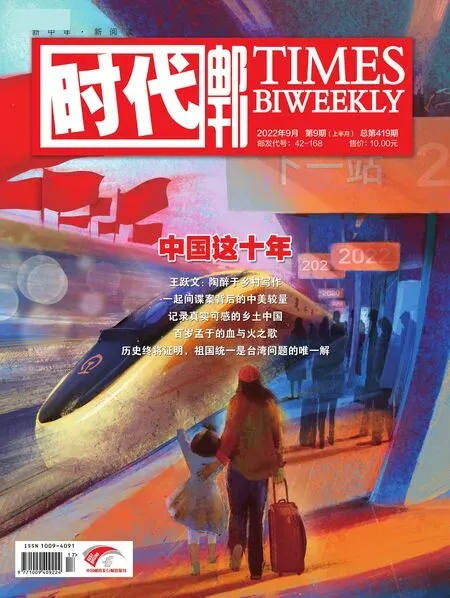陶醉于乡村写作
王跃文

我之所以喜欢创作乡土小说,除了喜欢作品中展示的自然散淡的生活状态,以及乡村人物身上的质朴人生,写作本身的过程也是令人陶醉的。
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置身于家乡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笔下人物的习性和形象,尽是我熟识的,他们都是家乡的风俗风情和山水阳光陶冶出来的。乡村人物语言是那么有意味,他们有自己的语汇,有自己的修辞,有自己的幽默。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些很土的乡村方言也可以在标准汉语里找到读音和意思吻合的字。我并不认为严格地使用方言才是好的乡村小说,方言文学化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种,不少经典作家给我们提供了好经验。比如周立波对东北方言和湖南方言的处理都到了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地步。我使用民间语言写作,学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还有家乡人物的神态、腔调,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我写不同题材的小说,语言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小说语言,构成不同的文学世界。
乡村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读书人倘不熟悉,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他们的处世方式、世界观,也是作家无法虚构的。我在《漫水》里写到乡下老人对待生死的通达,均是古风。村上有人老了,村里人不会讲什么节哀之类的套话,只会实实在在地安慰丧家:“莫难过,人都有一回的!”乡村人对待生死,如同对待四季,如同对待花开花落,多持一种平和心态。他们谈到别人的死,言语和表情都是非常平淡的,有时甚至会把死亡当成笑谈。乡村人进入暮年,会早早地预备好自己的后事。我从记事时候开始,就知道堂屋角落里放着一副棺材,那是奶奶年纪轻轻就为自己备下的。隔一段时间,奶奶就要把盖在棺材上的破蓑衣拿开,像对待宝贝样地抹一遍。我常听奶奶同人谈论自己的死,就像谈论与己无关的事情。乡下人对待死亡的豁达,就是乡村人与生俱来的生死观,世代相因,无须教化。乡村的人死了,没有人会考虑丧事的规格,尽管有的人家奢华,有的人家简朴,但一律庄严肃穆。古人讲的“死生亦大”,乡下人都明白。
我写完《漫水》,通宵没有合眼。小说结尾写到慧娘娘的灵棺被火红的飞龙架着抬上太平垴,慢慢地就像升到天上去。写到这里,我眼里充满泪水。一个乡村农妇的一生,让我生出许多难以言说的感慨。余公公、慧娘娘,他们是极其普通的乡村人,活得真实、自适、仁爱。他们终生匍匐大地辛勤劳作,而回到大地时却是那么庄严。他们都是我熟悉、热爱的乡亲,我小时候见到过的乡亲就是这样的人。我奶奶,我妈妈,她们身上都有传统乡村妇女的智慧和贤惠。我父亲,我叔伯,他们身上都有传统乡村男人的善良、勤劳和聪明。乡村人呼吸着乡野气息,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杆秤,只认天底下堂堂正正的大道理。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