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利手性”及其礼法境遇
——兼与西方传统比较
方 潇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曾从解剖学角度指出了“手”的重大功能和意义:“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事实,决定于他有一双会用工具的手。”(1)[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然而,双手却呈现出典型的灵巧不平衡性,此即为“利手性”现象。所谓利手性,即指一个人用手去做某种不定事项时,是习惯性地用左手还是右手;惯用右手,则为右利手,否则即为左利手。人们通常将左利手称为“左撇子”,后为对称计,将右利手称为“右撇子”。从人口比例看,右利手显然占绝对多数,而左撇子则较为稀少。(2)粗略估计左撇子占全世界人口的10%左右,参见马溥编著:《左撇子的神奇世界》,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右手便利”主导的世界,一切工具、设施和规则几乎只考虑右撇子的特点,而左撇子则似乎被遗忘,甚至被赋予邪恶因素而被排斥。左撇子因之生活在“右手霸权主义”的社会环境中。
随着近代以来人权观念的渐趋兴盛,左撇子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尊重,所占人口比例也有提高之势。但是,由于生理及传统的因素使然,右手便利依然是主流和主导。如果回到传统中国语境中,中国人典型的“右利手”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和展现的?传统中国人的利手性有无受到相关礼法的规训?在右手主宰的传统社会,“左撇子”又有着怎样的礼法境遇?与西方传统有无差异?而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利手性又遭遇怎样的礼制变迁?这些问题不仅饶有趣味,而且从传统角度可更深入认知左、右利手与礼法的关联,进一步理解人类生理的社会属性,进而去实践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那句经典铭言——“认识你自己”。
一、“左”“右”字源及古人左右观概析
(一)源于身体双手的“左”“右”汉字

可见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左右手的功能差异,右手便利赛过左手,后来还创造出“佐”和“佑”来表达引申义。这种认识,也为右手便利或优越说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古人的左右观
左右又是方位观念的基础。已有研究表明,至商代中国人就已经有较丰富的方位观念体系了。(3)参见朱彦民:《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页。因古人观察世界,如《周易·系辞》所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己身推及其他,故左右方位的观念实源于左右手的相对定位,在左手边的即为“左”,在右手边的即为“右”。此判定法在孙武为吴王训练宫女时就有着生动表现(4)《史记》:“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史记》卷65《孙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1页。,至抗倭名将戚继光操练士兵时仍在使用。(5)《纪效新书》:“凡面所向谓之前……凡面所背谓之后……凡左手所指谓之左……凡右手所指谓之右……凡脚下所立谓之中央。”戚继光著、马明达点校:《纪效新书》卷2,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古人普遍的左右观渐渐脱离“手”的因素,最终落在“方位”的意义上。而这个方位上的左右,又被注入了情感和礼仪因素,竟有了孰尊孰卑的价值判断。
这种价值判断,大体有“尊右卑左”和“尊左卑右”两个系统。“尊右卑左”主要体现在权力及道义场域,实从“右便”发源而来。因为右手的便利使用,从而成为崇拜对象并有所引申。(6)需说明的是,这种情况主要针对秦汉及以前而论。汉代以后的情况复杂,魏晋可谓过渡时期,至唐宋如左右丞相、左右仆射等均以左为尊,元代改为尚右,明代又改为尊左,而清代承袭明制。笔者认为,汉代以后官制上的左右尊卑变迁,实是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阴阳五行说虽在西汉中期由董仲舒全面建构,但真正对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当开始于魏晋时期,至唐宋全面展开。该说强调阳尊阴卑、左尊右卑,故唐宋官制以左为尊。元代蒙古族政权尚武,故以右便之右尊为制。明代朱元璋拨乱反正,遂回归唐宋之左尊。而与此相对的“左”则意义相反。南宋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提及:“手足便右,以左为僻,故凡幽猥皆曰僻左。”此“右便左僻”说基本构成了尊右卑左的理论基础。(7)参见常林炎:《尊右、尊左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而“尊左卑右”则建立在古人阴阳观的基础上。我国先民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很早就有太阳崇拜情结和“阳尊阴卑”的认识。特别是我国的地理位置大多地处北半球,尤其是都城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太阳始终在南方天空,故“坐北朝南”不仅成了居室的朝向方位,还成为帝王临朝的身体方位。“尊左卑右”实是阴阳观在“崇阳”前提下“尊君”的结果,与帝王的身体朝向与双手定位密切相关。(8)与“尊君”密切相关的是“尊亲”(长辈),也有南面位的尊敬礼节。随着阴阳观不断融入统治思想,“尊左卑右”遂成一个系统。
二、右手优越的礼制规训及其缘由
许多人会想当然认为右手便利是源于遗传天性,然而后天的社会规训则对右利手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比遗传更为重要。诚如学者所说:“人成为右手便利者可能不是因为功能的必然性——尽管我们不能排除机体影响的竞争假设——而是服从一种强加于人的规则。”(9)[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在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特别是饮食礼制,对右利手性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规训作用和意义。
(一)“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的礼制
中国古人普遍性的右手便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的食礼规定。《礼记·内则》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五十命为大夫……七十致事。”这些有关人生礼仪的教育可分为两部分,十岁之后主要针对男性的成长模式,十岁之前男女共说。而在十岁前的教育中,虽然从“能言”开始即有了性别分工,但开端则是不论性别,就开始强调当孩子能自己吃饭之时,就要教育他用“右手”进食,这是最基本的食礼教育要求。以此为开端,展开了人一生的礼制教育模式。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从接受右手取食的礼制规训开始的。
如果说“子能食食,教以右手”是从孩子饮食的某种自主性出发,那么当其还是新生婴儿蒙昧状态之时,右手取食的象征性礼制教育就已经开始了。就在上引《内则》此段话之前句,即有规定:“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适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这是说,自受爵位以上的士以及大夫的孩子在出生后十天即行见父礼。若是嫡长子,父在未与嫡妻行共餐礼之前优先见,必握着孩子的右手;若是一般嫡子或庶子,父就在与嫡妻行共餐礼后再见,必以手抚摸孩子的头。虽然由于诸子身份不同,见父礼有不同的礼制,但却均在饮食事项上有所体现。嫡长子的见父礼在餐前进行,并要求父亲握其右手,体现出饮食对于家庭未来传承者的重要性,以及用右手取食的象征性礼仪教育。刚生下才十天的婴儿虽然客观上无法认知“右手被执”的意义,但在“礼制通神”的语境中,此种象征性教育又是必须的。此外,当孩子出生三个月而行取名礼时也要如此。《礼记·内则》:“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是日也,妻以子见于父……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遂适寝……夫入,食如养礼。”此谓孩子三个月大时,家长选择吉日为其剪发并取名的礼节。需注意的是,取名礼依然在孩子父母共餐前发生,且须父亲握住孩子的右手完成。可见,右手取食的礼制,再次被强调。父亲在特定礼仪中一而再的“执子右手”,无疑体现出对蒙昧婴孩进行“右手取食”的身体前训。而至“子能食食”时,“教以右手”就成为日常性的礼制教育了。
可以说,“教以右手”的食礼,自《礼记》以来,就一直成为后世童蒙教育的首要内容。虽然幼儿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以宋代为界发生了从道德训练到识字读书的转变(10)参见熊秉真:《童年忆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但“右手进食”的礼教则始终被强调。如司马光的《家范》卷三可见,其完全照录《礼记·内则》,强调“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在司马光常为后世援引的幼教模式《居家杂仪》中,则稍变通为“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在清人罗泽南所撰的《小学韵语》中,依然重复强调“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的礼教训辞。可见,后世的幼儿教育均坚定贯彻了《礼记》关于“右手进食”的规定。再加上饮食本乃日常生存之事,“右手进食”的礼教自然推动了右手便利习惯的养成。(11)当然,由于儿童自小就被礼教规训用右手持筷吃饭,不排除某些原本惯用左手者被强制纠正,他们虽养成了右手便利习惯,却是隐性的左撇子。
(二)“教以右手”礼制背后的成因
《礼记》之所以有“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的规定,当是古人祭祀鬼神核心礼仪的需要。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与成肃公作为周天子代表参加晋国主导的诸侯伐秦,成肃公因 “受脤于社,不敬”,而遭到刘康公批评,并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之说。今人普遍将“祀”与“戎”解释为祭祀与战争,但从当时语境看,其实应是指祀礼和军礼,都与祭祀有关。(12)参见王学军、贺威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可见“国之大事”的要旨均在祭祀,只不过“祀”为平时祭祖,在宗庙进行,而“戎”为出征祭社,在社庙举行。不仅祭祀如此重要,祭祀中祭品的奉献及享用也很重要。“祀有执膰,戎有受脤”,膰与脤均为祭祀所用之祭肉,既表达了祭祀的对象为鬼神,更体现了鬼神对人们执膰与受脤行为的偏爱。食物被当作祭品献神,根源于人们认为神与人有相似的食欲,只有让神得到满足,才可能降福回报于人。《诗经·小雅·楚茨》所谓“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就是此意。因祈福需要,古人往往将最美味的食物敬献,故神灵食谱一般以肉食为主,辅以粮食、果疏和饮料。当然,鬼神嗜好肉食并非仅满足于己,其伟大之处还在将食物分享给祭者,因此就有了“执膰”与“受脤”之礼。那祭者如何去“执”和“受”呢?用左手还是右手?抑或随意?


三、左手便利现象及其礼法境遇
在礼制强化右手进食的传统中国,右手优越自然会更多地展现于世。(16)比如在正史记载的“割股疗亲”现象中,几乎全是所谓“刲左臂”之类,其右手便利显见。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人游离于右手的礼制规训之外,而呈现出左手便利。那么在贯彻“右手主义”的传统中国,“左撇子”又会面临怎样的礼法境遇呢?
(一)礼制视野下左手便利的类型化分析
左利手按其来源可分为自然性左利手和逆转性左利手两类。所谓自然性左利手,是指那些可能源于遗传或出生的左手便利者。此处“自然性”,乃主要基于古代语境,而非现代科学观念。如出生时大脑受到挤压,或早期婴幼儿因照护不周、医疗技术不足等外因所致左脑受损,现代均将其归入后天(17)现代医学证明,相当部分的左利手当源于出生时左脑被挤压,或婴幼儿时左脑受损所致。,而古人则往往将之归入自然性而视为先天。
既然礼制自幼强调右手规训,为何还有自然性左利手的出现?此可分为“反抗礼制”和“游离礼制”两种情况。前者是指虽有家长反复的右手规训,但终因左手便利的天性或习性使然,拒绝服从右手规矩。后者是指自小缺失或并不严格强调右手规训,从而游离于礼制之外,相对“任性”而成左利手。此两种大都发生于寻常百姓之家,因其往往缺少礼制的强力规训。传统中国的主流礼制,更多是为官贵等有身份者设立,所谓“礼不下庶人”,孔子编订的《礼记》,规范对象也主要是贵族。虽然庶人也会受到礼的普及性教育,但无法和贵族相提并论。
不过此类左利手毕竟另类,而史料少见,也难以确定其种属。如北宋名僧释惠洪在其笔记小说《冷斋夜话》中载:“予与李德修、游公义过一新贵人,贵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举箸,贵人曰:‘公等皆左转也。’予遂应声曰:‘我辈自应须左转,知君岂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喷饭满案。”(18)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惠洪自幼家贫,十四岁父母双亡,或因忙于生计而难以顾及右手教育,而李、游二人则不排除反抗右手规训的可能。又如:“赵广……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掳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实用左手。”(19)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李伯时作为官宦人家,礼教自当严格,然书童赵广却是左利手,可推知其幼时右手家教可能不严或者缺失;而将自己儿子输送人家做书童者,也往往是寻常或贫寒家庭。(20)将子孙输送成为士兵或刽子手也可能如此。如明清易代之际,多铎下令将礼部主事黄端伯处死:“刑者左手刃,忽自颤;右之,亦然。端伯曰:‘吾心不死耳,曷刺吾心!’乃死。”此刽子手当为左利手。参见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台湾大通书局1957年版,第488页。可见右手礼制与家庭境况的关联,并对自然性左利手有着重要影响。
所谓逆转性左利手,是指本为右利手,但因受伤或疾病使得右手无法使用,从而不得不训练左手而成。可以说,此类原本就是右手礼制规训的优良成效者,只不过因伤病障碍而逆转左利手。
因古代医疗资源相对落后,一些伤病往往导致患者终身残疾,如右臂或右体不遂。不过残疾并没有让他们沉沦消迷,而是将左手的潜能激发。如元代书法家郑元祐,“儿时以乳媪失手,伤右臂。比长,能左手作楷书,规矩备至,自号尚左生。”(21)何绍忞:《新元史》卷238《郑元祐传》,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920页。再如“枣强宋中郎,康熙丁未进士,工诸体书,后知获嘉县,忽遘风疾,遂以左手把笔,其工不减于旧。”(22)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2页。最令人瞩目者为清代书画家高凤翰:“久寓江淮间,病偏痺,遂以左手作书画,纵逸有奇气。”(23)《清史稿》卷504《高凤翰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14页。高凤翰于55岁那年右手病残,以坚强毅力训练左手书画,终取得巨大成功(24)高凤翰的左手书法,被人誉为明清数百年间最以左手擅长书法者;其艺术造诣十分精湛,被人归于“扬州八怪”或“画中十哲”。,并自号“尚左生”。
上述事例,虽只突出左手握笔问题,但却是左利手的成功转型。逆转性左利手,虽表面上与右手的礼制规训相违,但因右手残疾的客观不能,更因其毅力换来成功,反而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赞赏。从某种意义上看,此种左利手,实为右手礼制在右手残疾下转移至左手的杰出表现。像郑元祐与高凤翰之所以敢自号“尚左生”,就是建立在右手客观病残而非主观不能之上。也就是说,逆转性左利手的背后,反映的依然是右手规训的礼制。
(二)左利手的传统礼法境遇
1.游离于礼法与现实之间
传统社会的左利手,作为右手规训的叛逆者或漏网者,会受到礼法的惩罚吗?可用“游离于礼法与现实之间”来概括,并有如下表现:其一,传统社会一方面强调用右手食食,另一方面却又相对尊重现实中的左利手。从有关左利手的史料中,我们似看不出人们有意的排斥左利手,反而对“逆转性”的左利手,更多的是肯定乃至赞佩。虽然人们会觉得左撇子有某种怪异,但考虑更多的是其便利问题,并未上升到道德评价而进行歧视。当然偏见也有一定的表现。如皇太极反对儒臣建议效仿汉人服饰时,就曾设一比喻讽刺了左利手:“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25)《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当然,皇太极对左利手的排斥有其政治背景,而非一般性的道德评价。可以说,古人虽有左右方位上的尊卑观念,但对左右利手性,似并无明显的尊卑意识。
其二,左利手虽然背离了右手礼制,但并未受到法律的调整或处罚。传统中国强调“出礼则入刑”,但并未发现哪条法律涉及调整左利手,也未见有史料反映出对左利手予以惩罚。可见,右手规训主要在“礼制”而非“法制”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当然,左利手未能进入法律调整,并不说明其就不受礼制约束和制裁,实际上在祭祀中广泛禁用左利手,日常生活中,家长也会对孩子惯用左手进行喝斥甚至体罚。传统家训及童蒙大都赞成严教和体罚,对右手食食,往往就像训练小狗需“扑挞”一样运作。(26)二程就将严教体罚事与训狗相比拟:“至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尔,况人乎?”参见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页。
其三,右手礼制主要源于饮食,而非针对所有行为。《礼记》之“教以右手”,主要针对的是“子能食食”。因为从小就被规训用右手进食,长大后自然地就成为了右手便利。可见从发生学看,右手礼制实只对食礼所承载的特定行为负责。其深层主因,则是祭祀中的右手持肉,此可谓中国古人普遍右手优越的社会性本源。因此,右手便利虽具有社会性而有着伦理因素,但也主要体现在神与人的饮食礼中,而非必须施于所有的礼仪或行为。正因为如此,除祭祀与饮食受到右手规训外,社会对左利手行为有着普遍的宽容,即使有异辞,也不至于通过法律途径来规训。
2.利用左利手特征解决司法疑案
左利手在传统社会的法律境遇,最有特色者当为司法官员从案件所留痕迹判断左利手罪犯或排除左利手嫌疑,从而解决司法难题;当然也不排除以左利手特征错审者。例如:
其一,宋代钱惟济断盗案。钱惟济“知绛州”时,“民有条桑者,盗夺桑不能得,乃自创其臂,诬桑主欲杀人,久系不能辨。惟济取盗与之食,视之,盗以左手举匕箸,惟济曰:‘以右手创人者上重下轻,今汝创特下重,正用左手伤右臂,非尔自为之邪?’辞遂服。”(27)《宋史》卷480《钱惟济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913页。此案即钱惟济观察到疑犯的左撇子特征而断案。无独有偶,宋欧阳晔治鄂州时,“桂阳民有争舟而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公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饮食之,食讫,悉劳而还于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视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手,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杀也,不敢以累他人。’”(28)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23页。此亦为通过观察左手用餐而锁定凶犯。南宋郑克在《折狱龟鉴》中对此两案均有记载,并都有按语以示郑重。(29)参见杨奉琨校释:《疑狱集 折狱龟鉴校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327页。
其二,元朝邓文原鞫得真凶案。延祐五年,邓文原“出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时,“吴兴民夜归,巡逻者执之,系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胁,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归,比死,其兄问杀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长身者也。’其兄愬于官,有司问直初更者曰张福儿,执之,使服焉。械系三年,文原录之曰:‘福儿身不满六尺,未见其长也;刃伤右胁,而福儿素用左手,伤宜在左,何右伤也?’鞫之,果得真杀人者,而释福儿。”(30)《元史》卷172《邓文原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23—4024页。此案中,录囚官根据伤情在右排除了左利手的犯罪,从而还冤狱者清白,并真正鞫得真凶。
其三,清代袁枚错审案。袁枚《子不语》记有一则他做沐阳县令时办错案件的故事:“有淮安吴秀才者,馆于洪氏……吴挈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馔先生并其子,妻独居于室。夜二更返,妻被杀死,刀掷墙外,即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验尸,见妇人颈上三创,粥流喉外,为之惨然。根究凶手,无可踪迹。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轻,遂刑讯之。初即承认,既而诉:‘为家主洪生某指使为奸师母不遂,故杀之。生即吴之学徒也。’及讯洪生,则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诬耳。狱未具,余调江宁。后任魏公廷会,竟坐洪安,以状上。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确,均释之,别缉正凶。十二年来,未得也。丙子六月,余从弟凤仪自沭阳来,道有洪某者,系武生员,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见梦于其妻曰:‘某年某月奸杀吴先生妇者我也。漏网十余载,今被冤魂诉于天,明午雷来击棺,可速为我迁棺避之。’其妻惊觉,方议引輴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为灰烬矣,其余草屋木器俱完好也。”(31)袁枚著、崔国光校点:《新齐谐:子不语》,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6页。此案中袁枚据死者伤情而刑讯左撇子洪安,从而为后任者定案提供前提,幸亏臬司英明而别缉正凶。虽然袁枚认识到自己错误,乃建立在十二年后的“怪力乱神”之上,但自负于左利手杀人的认知却是事实,故发出“余方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做吏之累”的愧疚和感叹。
以上司法官均利用左利手用手习惯对案件进行审断,反映出时人对左撇子特征的充分认识。宋慈《洗冤集录》卷五《验他物及手足伤死》云:“若是尸首左边损,即是凶身行右物致打,顺故也。若是右边损,即损处在近后,若在右前即非也。”又《自刑》:“若用左手,刃必起自右耳后,过喉一二寸;用右手,必起自左耳后……其痕起手重,收手轻。(假如用左手把刃而伤,则喉右边下手处深,左边收刃处浅,其中间不如右边。盖下刃大重,渐渐负痛缩手,因而轻浅,及左手须似握物是也。右手亦然。)”,“验自刑人,即先问原申人,其身死人……在生之日,使左手使右手?如是奴婢……更问有无亲戚及已死人使左手使右手?并须仔细看验痕迹去处”。此几处记载,反复强调利手性在凶杀和自杀中的不同表现,以及验尸时要问清死者生前的用手习惯,特别是以小注方式说明惯用左手者的自杀刀痕。可以说,以上经验是宋慈对现实案例的总结,对当时及后世审断左利手犯罪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与西方传统“利手性”礼法境遇之比较
(一)西方传统:绝对的左右利手对立观
法国学者贝尔特朗曾揭示“原始人倾向于以自己身体的方位来度量世界的地理位置”。(32)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5—6、22—24、25—26、31—35、80—91页。这既与中国古人的左右方位来源不谋而合,也反映了西方传统。然颇需注意的是,西方传统社会却赋予了左手和右手根本对立的意义,从而使得“左利手”和“右利手”更具有完全对立的意蕴。
文明建立在语言力量上,真理则寓于语言之中。拉丁语中有许多与右手联系在一起的词语表达出忠诚或吉利的意思:如形容词dexter表示“右边的”,同时也意为“幸运的”“吉利的”;dextra既表示“右手”,也转义为“帮助”“友谊”“礼物”。而在法语世界,虽然droite(右手)并不来自拉丁语的dexter,但直至16世纪,仍然用dextre或destre表示“在右边”,如人们起誓时说“par ma destre”(以我的右手)等。(33)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5—6、22—24、25—26、31—35、80—91页。而英语中的right更是明显,既表示“右边”“右边的”,同时也表示“正确”“正确的”。可见在西方传统语境中,右手表达的是吉善、忠诚、完美、灵巧、荣耀、正确等正能量含义。左手则始终伴随着罪恶、背叛、不幸、笨拙、耻辱、错误等负面意义。比如“左”在拉丁语中有三种叫法sinister、scoevus及loevus,其含义不是表示恶毒或不幸,就是表示敌意或愚笨。在中世纪的法语中,senestre(左边的)的意思为“倒霉的”;mettre à senestre不仅表示“放在左边”,还表示无能的“忽视”。(34)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5—6、22—24、25—26、31—35、80—91页。而现代法语gauche,不仅意为“左”“左手”“左边的”,还表达“笨拙的”“歪扭的”“粗鲁的”等意思。英语中的left同样如此,在“左边”“左边的”的意思之外,还有诸如“剩余的”“左派的”“激进的”等含义,均暗含多余、偏邪等贬义。(35)参见Elizabeth Svoboda撰、朱鋐雄译:《“左撇子”人群引出的思考》,《世界科学》2000年第11期。
因“左手/右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左/右”,在西方传统中被赋予了截然相反的含义,使得左右利手的礼法境遇有天壤之别。右利手获得了绝对的优越和尊重,在礼法待遇上则操纵特权,畅行无阻,而左利手则雪上加霜,被卑微地嘲讽、排斥和打击。惯用右手被标榜为“正手”,而左撇子则沦为“反手”,成为邪恶、叛逆和罪恶的象征。可以说这种对立观念,很早就融入礼法规则中。比如罗马法规定用右手宣誓,否则就是不能容忍的行为;西欧封建骑士制度的马上比武,左手仅限持盾牌,右手则持武器;公平的格斗中,只须右手持剑;中世纪普遍流行对严重犯罪者处死前切除右手,迫使其使用左手,以贬低其人格;源于罗马法的在犯人右肩打烙印也是如此,主要目的就是使其失去尊严。(36)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5—6、22—24、25—26、31—35、80—91页。
而特别注意的是,左撇子的阴暗形象在中世纪后更加恶化(37)虽然中世纪对左手和左撇子存在诸如祸害、邪恶等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其受到有组织的社会迫害、追捕和某种方式的惩罚。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129—131页。,还被塑造成“退化或种族低劣的一个标志”,面临着“造成犯罪的一个因素”甚至“等同于歹徒”的法律境遇。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左手便利是“退化的生理标志”的观念曾广为流传,不仅推动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犯罪理论上得以运用。当时著名的犯罪学创始人龙勃罗梭,即据此提出左撇子更具有犯罪倾向性的理论。这种犯罪理论因“迎合常识”而影响巨大,乃至于“左撇子等同于歹徒”的偏见也“进入了科学真理的行列”(38)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5—6、22—24、25—26、31—35、80—91页。,以致法医、法官、检察官、警察、学者以及民众在犯罪问题上对左撇子特别警惕。可以想见,在这种法律语境中,左撇子的冤假错案也就在所难免。直到今天,左撇子更具有灵魂阴暗面的偏见依然存在;左撇子与犯罪的所谓“正比例”关系问题,依然是西方社会津津乐道的研究课题。(39)参见[日]前原胜矢著、陆求实译:《左撇子,右撇子》,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21页。
(二)中国传统:相对的左右利手对等观
中国传统针对左右利手的礼法态度,则是展现出相对平和的对等观。中国传统虽然强调右手食食,乃至延伸出强调用右手做事,但并没有发展出右手至上的观念,更没有对左利手投以鄙视、警惕或怀疑的目光,也没有将其作为潜在的犯罪者予以监控或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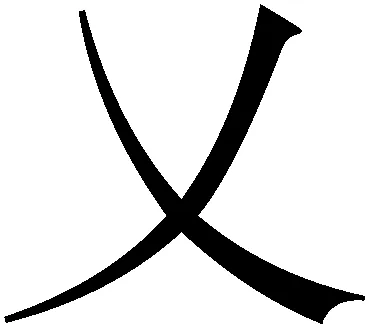
中国传统司法同样会利用左撇子的生理特征进行案件的审断。惟不同的是,西方传统做法是将左撇子的左手特征及凶残形象无限放大,乃至非左撇子的犯罪者也往往被塑造成邪恶的左撇子形象。(44)比如在著名左撇子罪犯清单中,19世纪末英国的开膛手杰克与美国的崽子比利均赫然其中。然而真相是,他们都不是左撇子。而在中国传统司法中,虽然会留意是否左撇子所为从而锁定罪犯,但主要展现的是司法官在疑难个案问题上的断案智慧,而非西方传统中左撇子倾向犯罪观念的运用。也就是说,左撇子并没有被视作潜在罪犯而先入为主地被怀疑和定性,虽然偶尔会出现像袁枚那样的误判,但也只是个案上的认知不足所致,而非指导性的观念问题。
(三)中西传统中“利手性”礼法境遇差异之原因
1.宗教与礼教的区别
中西方传统中左右利手的不同礼法境遇,首先当源于不同的强大社会气场,那就是西方的宗教和中国的礼教。也许没有任何一种精神力量可以超越基督教对西方传统的深刻影响。作为西方文化的原型,《圣经》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左手和右手的论述。如《传道书》(10:2):“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诗篇》(144:8、11):“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可见左手是被贬低的,右手是被肯定的。《圣经》还描写拉结难产去世前给儿子起名“便俄尼”(意为“我的痛苦之子”),而丈夫雅各却要起名“便雅悯”(意为“右手之子”)(45)参见《创世纪》35:16—18。,表示要受到特殊恩泽,是在右手庇护下出生的;书中还描述雅各交换他的左右手,坚持将右手按在约瑟次子以法莲头上的故事(46)参见《创世纪》48:8—20。,表示用右手祝福比用左手更具有荣誉。而最著名的或许是“最后的审判”中上帝之子将人类分别左右的情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7)参见《马太福音》25:31—41。基督的右手赐福“绵羊”,即那些温顺服从圣经戒律的信教者,而左手则惩罚“山羊”,即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不信者。右手边的就被赐福,左手边的就被诅咒,上帝就这样通过基督之手对左右手的优劣贵贱作了“神”的规定。因此,在神权长期凌驾王权的西方传统社会,基督徒和信教者必然对右利手持赞美和推崇、对左利手持贬低和压制的态度。
与此相反,虽然道教、佛教等在传统中国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真正统治社会和规训秩序的是儒家积极推动的礼教。所谓礼教,即是礼制的教化,其核心在礼。古人很早就对礼的功能高度评价(48)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语·晋语》:“夫礼,国之纪也。”,儒家更强调以礼修身治国。(49)如《荀子·修身》:“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至正统儒家成为官方思想,礼制更是被大力宣扬并渗透到法律中,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可以说,中国古人普遍的右利手性,除生物学意义外,更与“子能食食,教以右手”食礼规定有关。在“民以食为天”及重视以食物祭祀的传统语境中,右手食礼自小就主导教化着饮食用手模式,并由此延伸到其他用手习惯当中去,从而造就并推动了右手便利。
然而中国的右手礼教并没有导致对左手及左撇子的排斥或者迫害。首先当归因于“礼本乎情”,源于感性世俗的人情世态。礼虽起源于祭祀仪式,有其鬼神因素,但中国的鬼神从来都是交感于世俗社会的,其意志也充分尊重民情民意。(50)如作为鬼神最高存在的“天”,在西周“以德配天”思想推动下,一直有着“天意即民意”的思想传统。这可谓礼教难以走上西方超验式宗教的重要原因。从内容看,礼一方面为“圣人所以治人七情”(51)《礼记·礼运》。的“节文”,另一方面又“礼顺人情”(52)《后汉书》卷25《卓茂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0页。,“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53)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7《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0页。,强调真情实感的重要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言:“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可见儒家重“情感”而轻“事实”,重“善恶”而轻“是非”,认为价值上的善恶远胜于事实上的对错。“德性伦理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伦理的主流”(54)参见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礼教注重的是道德至上。因此,当人们用左手从事某种行为,乃至惯用左手成为左撇子,只要无违礼的禁忌,一般都能得到社会尊重乃至法律庇护。其次,礼教对等级差别的强调及国家“身体化”治理的宣示,也决定了左右手在政治隐喻上的相互地位。无论左手还是右手,充其量都只是大脑(古人认为是心)驱使的工具,虽有着功能分工,甚或轻重之别,但并无或少有道德高下之分。古代君主常将臣子称为自己的“左右手”或“左膀右臂”,可见在右手优越的世界里,礼教并没有冷落左手的政治地位。
2.二元对立与阴阳相成的区别
左右利手的不同礼法境遇,还根源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区别,即西方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观与中国传统中的阴阳相成观。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赫尔兹研究发现,在原始思维中,“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无处不在,成为“占据原始人精神世界的最基本的一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通过自然界中的诸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高与低、天空与大地等比喻形式来体现,而且还主导着男人女人、部落组织等社会性的对立划分。可以说,“宇宙的一极是力量、善和生命;而另一极却是无力、恶和死亡”。诚如赫尔兹所问,人的身体又怎么能够逃脱控制万物的两极性的法则呢?(55)参见[法]赫尔兹著、吴凤玲译:《死亡与右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8—102页。因此,右手和左手,自然成为了人类表达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的符号。
赫尔兹的研究虽无明确地域性,但主要着眼于西方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基督教中天堂与地狱、上帝与魔鬼,以及右手与左手的意义不对称,就是二元对立观的宗教反映。那为何偏偏右手代表神圣呢?按英国学者麦克马纳斯对赫尔兹的解读,因为右手更强壮,也更灵巧。但这并不仅仅与生物学相关。两手之间的差别虽然十分微小,但由于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系统,及其几乎对任何事物都采用的二元论观点,创造了使右手变为神圣而左手变成凡俗的动力和能量。即当微小的生物学上的差别与巨大的社会力量相耦合时,就转化为一种重大的影响。(56)参见[英]麦克马纳斯著、胡新和译:《右手,左手——大脑、身体、原子和文化中不对称性的起源》,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此种影响深远的二元对立观,不仅将左右手作了符号意义的对立划分,更是将左撇子打入深渊。
然而,传统中国很早就对宇宙世界的构成有“阴阳相成”的认识。阴和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认为任何事物内部及相关事物之间均可用阴阳来划分和解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古人认识宇宙世界的基本原理。阴阳学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是阴阳相成。阴和阳不仅是对立的,更是互根互用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国古人以一种包容依存的辩证智慧对待所谓的对立面,在左右手的礼法态度上即有深刻的表现。
左右方位虽然源于身体的左右手,但中国传统左右方位概念的运用已经远远脱离左右手的本源。此当缘自周代开始兴起的阴阳观念及学说。阴阳观念的出现,使得左右方位开始直接与太阳的向背发生联系,而不是与一般人的左右手相关。虽然左阳右阴说与君主朝政时的身体朝向在本源意义上有关,但由于阴阳学说的日益政治化和社会化,左右方位逐渐脱离帝王的特殊身体,而与阴阳形成了固化关系。因为这个脱离,周代以降虽然普遍为右利手性,但集体观念开始普遍尚左,因为左阳右阴,阳尊阴卑。不过,在阴阳相成观念下,中国古人认识事物并不绝对于固定视点,而常常随事物的变化而变换,能进能退,可此可彼。由于是动态的把握,左和右既可作为“尊”的观念显现而被肯定,又可作为“卑”的观念显现而被否定。(57)参见谭学纯:《“左、右/东、西”:尊卑意识及其文化蕴含》,《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因为尊卑随左右不同情形而转变,故《道德经》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礼记·少仪》也言“军尚左,卒尚右”。因为左右尊卑的变动性,导致以左右界定手的各自道德评价和区分无从建立;而左右方位上相对对等的尊尚态度,又不可避免对左右手的礼法境遇产生影响。此外,因阴阳相成观念的推动,中国古人谈论左右时,总习惯于左右相随,像前述之“左膀右臂”及“左右手”,说明对左手和右手的态度并无厚此薄彼之处。
余论:“利手性”的现代性与中国性
通过上述,可知中国传统的“利手性”主要是双手工具性功能的实现途径,除在祭食礼制以及某些刑罚(58)比如元明清时期的“刺臂刑”,就存在先左臂后右臂,还是先右臂后左臂的顺序问题。方面有其特别价值外,基本与道德评价无甚关联。此外,虽然右手优越乃人类普遍共性,但在中西方却遭遇截然不同的礼法境遇。中国传统对左撇子有着较多宽容,而西方传统则对其深有偏见,甚至视为潜在罪犯。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利手性礼法境遇,更多体现出一种“身体政治”,而非“身体宗教”,而西方恰恰与此相反。因为是身体政治,故注重双手的“实用性功能”;因为是身体宗教,故聚焦双手的“精神性区别”。
然而,随着中西方文化在近代的白热化交锋,中国礼法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其利手性的传统观念和境遇也受到一定影响,“握手礼”即是一个典型体现。中国传统见面礼主要是跪拜和作揖,近代以来象征人格平等的握手礼得以输入并被不断强化,传统见面礼终被弃用。(59)虽亦有“握手”一说,但要么表达亲近关系的牵手,要么指丧葬礼中用黑色带子系在死者手里的物品。不过因对左右手并没有厚此薄彼,握手礼传入中国之初难免出现一些尴尬情景。如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回描写一位意大利地质专家与中国官员初次见面的情形:“见面之后,矿师一只手摘掉帽子,柳知府是懂外国礼信的,连忙伸出一只右手,同他拉手。……末了方是首县,上来伸错了一只手,伸的是只左手,那矿师便不肯同他去拉,幸亏张师爷看了出来,赶紧把他的右手拉了出来,方算把礼行过。”显然,左手作为“邪恶之手”,依然是西方矿师心头的阴影;而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也学会了用右手握手,右手作为“正确之手”开始被接受。直到今天,连左利手也懂得用右手握手。虽然用右手握手在古罗马只是“握手言和”的一种习惯,是凯撒将其确立为礼法规定(60)参见马溥编著:《左撇子的神奇世界》,第22—23页。,但用右手握手在西方流行,却与宗教对“右手神圣”的推动有直接关联。
当然,西方传统对左撇子的礼法排斥并非铁板一块,随着近现代以来人权理念的“现代性”兴起,特别是身体权对传统消极利益构造的突破(61)参见刘召成:《身体权的现代变革及其法典化设计》,《当代法学》2020年第2期。,以及一战后大量失去右手军人的左手训练(62)比如法国就有许多军人在一战中丧失右手,为重新回归生活,政府帮助他们进行左手功能训练。从那时起,使用左手突然变成了公民美德的标志,和平世界的象征,使用左手第一次在全民范围内与人类尊严和社会秩序联在一起。参见[法]贝尔特朗著、姜志辉译:《左撇子的历史》,第157—160页。,人们对左撇子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左撇子数量的增加,还推动了左撇子用品的市场开发,以及左撇子协会或俱乐部等合法组织的出现。这种建立在西方“现代性”上的左撇子态势(63)当然对此不可过分乐观,因为西方传统对左撇子的歧视,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亦对现代中国左撇子的命运产生影响,今天的中国人可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宽容地对待左手便利者。
不过,因深受代代相传得用右手吃饭及写字等礼制的身体规训,中国的左撇子再怎样被善待和宽容,其人口比例也远远低于西方。(64)据“全国利手研究协作组”1981年对18593名男女正常人的调查,左利手率仅占0.23%;如将潜在左利手计算在内,也仅占1.84%。参见李心天:《中国人的左右利手分布》,《心理学报》1983年第3期。这说明中国传统礼制的社会渗透性,实比近代西方输入的人权魅力更为强大。可以说,在对待左手及左撇子的态度上,中国社会基本上秉承传统,相较西方的大起大落,显得较为稳定和淡定。像印度佛教虽然崇尚右手,贬低左手(65)印度人至今都深受其影响,如右手只做高贵圣洁的事,而左手只能做低贱污秽的事。,但其输入中国被中国化后,却并未在伦理上显现出对左右手的明显爱恶。为解读利手性,学界虽提出了诸多理论(66)如太阳崇拜说、保护心脏说、极性法则说、优势脑说、遗传说、人体重心说等。,但“右手进食”等“礼制教育说”,无疑是中国右利手最普遍的身体规训。可以说,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汇中,针对右利手特别是左撇子的地位,中国社会既有“现代性”的跟进,更有传统“中国性”的坚守。人们对利手性的理性态度,或可为其他领域的礼法问题提供启示或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