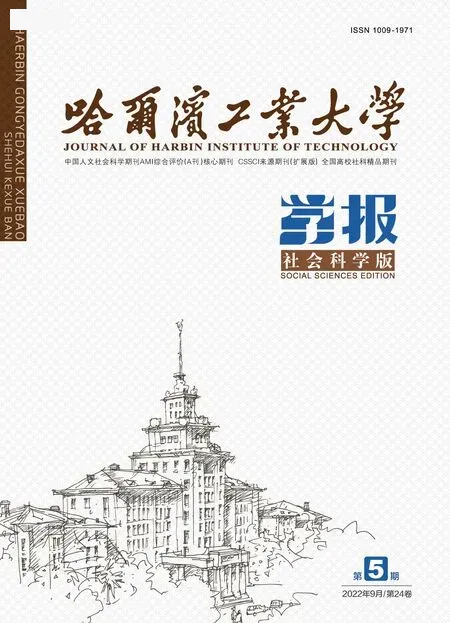《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对先唐文献的整理与改写
高思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71)
严可均是清代辑佚大家,《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早已为世人所知。他一生寒微,39岁冒籍宛平得以中举,经年飘摇寓居人下,61岁选授建德教谕。他广搜精善古籍、金石碑刻,旁及释道烈女、域外文献,发立宏志以成《全文》巨著,其志可嘉,而其法更为可观。
作为研究讨论先唐文学文本面貌的对象,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严可均编纂《全文》的校辑之法,觉察到严可均《全文》是以编纂总集的形式对先唐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一个典型范式。颇为遗憾的是,《全文》虽为皇皇巨著,但严氏对其辑佚之法却吝惜笔墨,未能描摹全貌,观者多有管中窥豹之憾。
以金石、类书、史籍、子书等为主要类型存在的先唐文学文献与唐代以后转向以总集、别集为主要类型的文学文献,二者在文本存录方式、呈现状态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早期文本的传抄亡佚使得文本自身呈现出断裂化、碎片化的状态;文字的发展演变使得文本在传抄转录中可能会出现不少误读;出于使用者的需要,文本内容可能会经过多次变异、改写。再加上历代层出不穷的窜伪,这些都使得整理先唐文献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严可均整理先唐文献纂辑《全文》,无疑为面临复杂局面如何整理先唐文献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其中所用之法值得仔细斟酌探究。
一、参酌声韵 以补校订
严氏不仅是一位辑佚大家,也是一位音韵通才。他在《全文》草创之际,已因善治《说文》而闻名。他早年游学京师之时,便与姚文田共治《说文》,纂有《说文长编》《说文声类》《说文校议》诸书,颇通古韵之学,亦颇为自矜其才,在《说文翼叙》中言:
国朝崇尚经术,鸿儒硕彦,先后挺生,家谭汉学,户蓄许书,晦冥千年,廓然昭朗。然其求淹贯故训,仅或一二人。余皆沾懘轇固,狃于成说,未能观其会通。虽各有所得,难可谓之通才。[1]
可见,严氏对自己所治《说文》颇为自信,自诩有清一代前者都是未能会通之辈,惟其本尊可谓“通才”,能“语许君所未尽语,通经典所不易通”。严氏自视甚高,亦颇有才学,黄侃就曾赞:“言韵部通转者,以严可均为最妙。”[2]
从《全文》文本来看,严氏之“通”非但在声韵,亦将声韵之学“通”于辑佚之法。《史记》当中并没有《峄山刻石》的作者记载,也没有存录《峄山刻石》的文本,但严可均依据《峄山刻石》的用韵特点将其辑入李斯名下,《全秦文·峄山刻石》文后言:
案: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邪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张守节言《会稽碑》文及书皆李斯。斯狱中上书言:“更刻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其显据也。此文《史记》不载。[3]122
严氏认为李斯之作除了《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碑刻皆为三句一韵,并指出三句一韵是李斯撰写秦刻石的成例,又有李斯《狱中上书》的文句用韵可以佐证。美国汉学家柯马丁也是从韵律的角度勘定此文的创作时间。①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认为:“峄山石刻的文本历史,或许让人疑其真伪,但韵律方面存在的某些证据却使我们相信它实乃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作品。”而早在百余年前,严可均已经更进一步将秦刻石的用韵习惯与李斯个人创作风格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除了从用韵之法归纳创作风格用以辑补佚文,严可均亦以韵律确定阙文位置。如《全后汉文》卷五十五张衡《七辩》:
阙丘子曰:“①西施之徒,姿容脩嫮。弱颜回植,妍夸闲暇。
②形似削成,腰如束素。蝤蛴之领,阿那宜顾。(二语从《文选·洛神赋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补)
③淑性窈窕,秀色美艳。鬓发玄髻,光可以鉴。”[3]775
其中的“嫮”“暇”“素”“顾”“艳”“鉴”,黄侃将之归于匣母、模部之字,王力以其为匣母、鱼部,具备押韵的显著特点。此文引《艺文类聚》五十七杂文部为:
阙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嫮。弱颜回植,妍夸闲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阙)淑性窈窕,秀色美艳。鬓发玄髻,光可以鉴。”[4]1026
可以看到《艺文类聚》中“形似削成,腰如束素”后并无“蝤蛴之领,阿那宜顾”句。而根据严氏所称《文选·洛神赋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其中均仅有“张衡七辩曰:蝤齐之领,阿那宜顾”句,并无任何文序线索可资参照以确定这二句之位置。
此文中:①句尾字“嫮”与“暇”押韵,③句尾字“艳”与“鉴”押韵。那么《艺文类聚》中“形似削成,腰如束素”句后所阙一句应与“素”字押韵。而《文选·洛神赋注》、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注补,皆言张衡《七辩》有“蝤蛴之领,阿那宜顾”句,此句“顾”字恰好与“素”押韵。故严可均将此句补之于“形似削成,腰如束素”句后,以全其文。
二、梳理文思 缀合成篇
对于完章虽佚,零章散篇见于各处文献载录,但各处既有佚文,又有重文,严氏则以文章技法和创作思路为线索,把散落的文本缀合成相对完整的篇章,各处引文出处或注明补处或在篇末统一注明。
如《全晋文》卷四十五中所录傅玄的《鹰赋》一篇,校勘工作就十分依赖文章技法:
①含炎离之猛气兮,受金刚之纯精。独飞跱于林野兮, 复回翔于天庭。(《初学记》三十)
②左看若侧,右视如倾。劲翮二六,机连体轻。句爪县芒,足如枯荆。③觜利吴戟,目类明星。雄姿邈世,逸气横生。(《艺文类聚》九十一,《初学记》三十)
④奋翅不得起,抚翼无所翔。饰五采之华绊,结璇玑之金环。(《初学记》三十)
⑤虽逍遥于广厦,思击厉于中原。(同上)[3]1719
首先,除②引自《艺文类聚》九十一外,其余诸篇均自《初学记》三十。其中,①③来自《鹰第四》“猛气、雄姿:傅玄《鹰赋》曰:含炎离之猛气兮,受金刚之纯精;独飞跱于林野兮,复徊翔于天庭。又曰:觜利吴戟,目类星明;雄姿邈代,逸气横生。”④来自“青骹素羽、华绊金镮:傅玄《蜀都赋》曰:鹰则流星曜景,奔电飞光,青骹素羽,飘雪繁霜。傅玄《鹰赋》曰:奋翅不得起,抚翼无所翔;饰五彩之华绊,结璇玑之金镮。”⑤来自“栖茂树、击中原:焦贡《易林》曰:鹰栖茂树,候雀往来。傅玄《鹰赋》曰:虽逍遥于广厦,思击厉于中原。”[4]731《初学记》的文本编录顺序是①③⑤④,而在《艺文类聚》九十一中,②和③又是连缀在一起的整段文章。从《全文》文本的编录顺序可见,严可均采用了《艺文类聚》引文的原貌,将②和③编录在一起,但调换了④⑤的位置,而其安排则有着非常纯熟的文章学技巧。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五句实际上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由①②句构成的先比后赋结构。①为首句,开宗明义,通过“炎离”“金刚”“独飞”“天庭”的比喻和意象,赋予鹰刚毅的品行和遗世高洁的性格,与②的由目及翅、由爪及喙、由细节描写到整体“雄姿邈世,逸气横生”的赞誉,实际上是构成了先比而后赋的文章结构。第二层是由④⑤构成的比兴结构,其中④运用倒叙手法,先叙述结果,再展现原因,鹰之所以奋翅与不得起、抚翼与无所翔是因为五彩为华绊、璇玑为金环,实际上抒发的是作者虽才华卓越身居高位,但依然苦于掣肘、壮志难酬的悲愤。而⑤句则通过对鹰回归自由后的遐想,表达作者渴望获得自由与建功立业的志向与抱负。第三层是由①②和④⑤共同构成的比—赋—兴结构。
严氏所辑文本先极力铺陈鹰之刚毅高洁,再罗列当前重重羁绊交织的窘境,最后在篇末画龙点睛,抒发出“击厉中原”的慷慨之情,正反并论反复对比,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的安排不仅是严氏的妙思,也是中国古典文章学的基本技法。早在《诗经》中,先比再赋后兴之法已有运用,如《蓼莪》篇前三章皆先比而后赋,第四章用赋,第五、六章皆兴。
再将严氏辑佚文本与《晋书·傅玄传》所言“(玄)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5]1317“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5]1323以及数举孝廉、太尉征辟皆不就,历任谏官,两度做免,奏议颇为关心百姓疾苦,对百官又甚为严苛的一生比较来看,傅玄虽名为赋鹰,实为赋已。
从严氏辑佚的文本更进一步讲,从④抒发作者身居高位却不得以施展平生志向的矛盾,以及⑤句所展露退隐之意以及报国之心不改的抱负,将之与《晋书·傅玄传》对照,“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5]1322。似乎可以推定此赋作于泰始五年(269)前后。
斯人已逝、斯文已佚,颇赖严氏辑佚之功,将散落四处的只言片语汇集到一起,得以让后人清楚地看到《晋书》中“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与《鹰赋》“饰五采之华绊,结璇玑之金环”这样的笔墨,以及力透纸背定格在历史和文海中心照不宣、跨越千年的君臣博弈。
三、比照重文 以补缺漏
严可均在各处文本汇校中,非常重视重文在判断阙文、校勘文本顺序方面的作用。《全晋文》庾阐名下所收录的《为郗车骑讨苏峻盟文》:
1.贼臣祖约、苏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诛。①凶戾肆逆,干国之纪。②陵汨五常,侮弄神器。③称兵攻宫,焚掠宗庙。④遂乃制胁幼主,⑤拔本塞原,⑥有无君之心,⑦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⑧残害忠良,祸虐烝民。⑨穷凶极暴,毒流四海。⑩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
2.咸愿奉辞罚罪,以除元恶。昔戎狄泯周,齐桓纠盟;董卓陵汉,群后致讨。义存君亲,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艺文类聚》作“忠臣烈士,志在死国”)。
3.凡我同盟,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共剪丑类。殒首丧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枭,义无偷安。当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无媿黄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3]1682
严氏注称此文出自《晋书·郗鉴传》及《艺文类聚》。《晋书》卷六七《郗鉴传》:
1.贼臣祖约、苏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诛,①凶戾肆逆,干国之纪,②陵汨五常,侮弄神器,④遂制胁幽主,⑤拔本塞原,⑧残害忠良,祸虐黎庶,⑩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
2.咸愿奉辞罚罪,以除元恶。昔戎狄泯周,齐桓纠盟;董卓陵汉,群后致讨。义存君亲,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正士志存报国。
3.凡我同盟,既盟之后,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枭,义无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5]1799
《艺文类聚》卷三三:
1.贼臣祖约、苏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诛。①凶戾肆逆,干国之纪,③称兵攻宫,焚掠宗庙,④遂乃制胁幼主,⑥有无君之心。⑦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⑧残害忠良,祸虐烝民,⑨穷凶极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
2.咸愿奉辞罚罪,以除元恶。
3.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悬,忠臣烈士,志在死国,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共翦丑类。殒首丧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枭,无望偷安。当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无媿黄泉。[4]589
此文可以比较清晰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历数祖约、苏峻罪状,第二部分引古论今号召群臣讨逆,第三部分为盟誓内容。从引文文献的情况来看,除首句外,文本的三个部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文和阙文,而在此处重文作为辑佚工作的主要线索就十分重要。
《全文》文本中第一部分①至⑩句中,在两处文献出处的原貌分别是①②④⑤⑧⑩和①③④⑥⑦⑧⑨,之所以能连贯成句,其实是由于①④⑧这样重文,成为指引辑佚此段文字的重要参照。如:
《晋书》:①凶戾肆逆,干国之纪。②陵汨五常,侮弄神器。④遂制胁幽主。
《艺文类聚》:①凶戾肆逆,干国之纪,③称兵攻宫,焚掠宗庙,④遂乃制胁幼主。
从上文可见,由于①和④这样的重文存在,②和③共同作为①④之间的并存文句就十分清晰。再考虑“遂”字这一连词,表明“制胁幼主”应是紧接上句并由于上句提及之事造成的结果。故②③相较,③与④相接为宜,于是就有了《全文》文本所呈现的状态。
在④至⑩句中,也是同样的方法。
《晋书》:④遂制胁幽主,⑤拔本塞原,⑧残害忠良,祸虐黎庶。
《艺文类聚》:④遂乃制胁幼主,⑥有无君之心。⑦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⑧残害忠良,祸虐烝民。
可见,由于④⑧重文的存在,⑤⑥⑦均又成为了④和⑧之间的共同文本。而又因为⑤⑥作为恶行罪状实与质,⑦句作为以上罪状造成的结果,先后顺序十分明显,故而有了《全文》的文本面貌。其余部分,亦是同样的方法。
必须指出的是严氏辑佚校勘也有失误。此段文本无论是《晋书》还是《艺文类聚》均采用了“行状+行状+结果”的叙事模式。如:
《晋书》:残害忠良,祸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

《艺文类聚》:穷凶极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

《全文》:拔本塞原,有无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

不过在《全文》文本中,严氏并未遵照后两处引文所呈现的共同叙事状态,而是将后续文本擅自改为“行状+行状,结果+结果”的模式。
拔本塞原,有无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

残害忠良,祸虐烝民。穷凶极暴,毒流四海。

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

此处应遵照《晋书》及《艺文类聚》原文改回为宜,即:
拔本塞原,有无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忧厄崩殂。
残害忠良,祸虐烝民,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
穷凶极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
四、兼采诸说 校辑文本
庾阐《扬都赋》“龙骥汗血于广涂,朱轮击毂而辐凑”此句后面的文本均是残章。其中除了有从《太平御览》《文选》《初学记》中辑录的文本外,还兼采小说及诸注。
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俊。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润。(《世说·文学篇》)[3]1679
《世说新语·文学》载:“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6]从《世说新语》的载录轶事观之,庾阐在此赋中称赞温峤和庾亮。而庾亮听说《扬都赋》已经写好了希望能够拜读。庾阐意识到原作之中,“亮”字犯了庾亮的名讳,所以要改,又因为“亮、望”押韵,既然“亮”字改了,那么“望”字也要一并修改,故改“亮”为“润”的同时将前文“望”一并修改为“俊”。此虽为小说家之言,但言之凿凿举证信实,又有“屋下架屋”之典相互补证,严氏信而采之似亦有据。
除了采信小说家之言,严氏亦采诸注之说。
建康宫北十里有蒋山,舆地图谓之钟山,元皇帝未渡江之年,望气者云,蒋山上有紫云,时时晨见。(《艺文类聚》七引庾阐《扬都赋》注,未审他人为之注,抑阐自注也。今录附赋末,下三条放此。)
烽火,以炬置于孤山头,皆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烽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吴志·孙权传》注,《艺文类聚》八十,《御览》三百三十五,并引庾阐《扬都赋》注。)
今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水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水经·沔水注》引庾仲初《扬都赋》注)[3]1679
严可均认为《艺文类聚》七在援引庾阐《扬都赋》注之时,推测其为庾阐自注,采而用之,列于赋末。
此外,对于他处的考释成果亦可见严氏采纳运用的痕迹。《陶渊明集》中的《四八目》和《五孝传》二文,严氏所据汇校底本的明刻《陶潜集》就有收录。而此二文的辨伪,早在严氏之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成定论。
《四八目》已经睿鉴指示,灼知其赝,别著录于子部类书而详辨之,其《五孝传》文义庸浅,决非潜作,既与《四八目》一时同出,其赝亦不待言,今并删除。惟编潜诗文,仍从昭明太子为八卷。虽梁时旧第,今不可考,而黜伪存真,庶几犹为近古焉。[7]
可见,《总目提要》断言二文为伪作,是清高宗御临亲裁。严可均在《全晋文·陶潜集》中断然删去,未有片言校语,无非是想要与“睿鉴指示”保持一致。
对于文佚过巨、篇章之间又无明显的文本逻辑关系的作品,实难裒合者,严氏则按照不同文献出处的多寡和同一文献出处的卷帙先后予以遵照抄辑。如《全三国文》卷三所辑录曹操的《四时食制》,其中的文本相互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空间或思维逻辑关系,于是严氏随章就篇将《太平御览》九百三十六到九百四十中的相关文本按照卷帙顺序予以抄录,而《御览》篇目较多故居于前而《初学记》寡则列于后。
余 论
从严可均所用辑佚之法可以看到,先唐文献的整理面临着较唐以后文献更加复杂的问题,已远非唐后文献经宋、明两代的整理递修后的状态。在考辨一二作者、批注三四校语、校改五六文字的基础上亟需更加系统的思考。
其一是聚合文本和游离文本的勾连整理问题。先唐文献中有不少像张衡《七辩》这样,在比较整端的聚合文本之内存在阙文,而这些阙文又可能存在于他处的注解、引用、摘录中,是聚合文本外的游离文本。那么此处文本整理的主要工作就要围绕勘定聚合文本与游离文本的关系,确定游离文本在聚合文本中的位置展开。从严可均的整理工作中可见,他已将音韵学、文章学的方法引入其中,而百余年后,无论是音韵学、文章学的新成果,还是新材料的新发现,乃至中西文本研究的新学说,可以使我们在先唐文献整理工作中更进一步。
其二是变异文本和改写文本的溯源还原问题。“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避国讳,避私讳,因时而异、改而不注,“触龙言说赵太后”与“触詟说赵太后”等诸如此类,文本传抄的变异鬼出电入、龙兴鸾集,而史家编史以叙事为要,援引诗文只取片段,类书编者以摹物为纲,裁贴文本多只留肌理。面对如此复杂的文本变异与改写,整理先唐文献已经不仅仅是以哪个本子为底本对校的问题,整理工作的一大要务就是将这些几经变异改写的文本逐一梳理,尽最大可能究其源出、溯其流变,完整其筋骨、丰盈其肌肤。
其三是窜伪文本中真与伪的甄别取舍的问题。先唐文献窜伪的问题同样复杂,像出土的先秦简帛,其抄录文本往往不著作者,而后世的拟作又往往产生文本的“附益”,在后世的整理过程中,使得拟作混入原作。除此以外,既有像《陶渊明集》中《四八目》这样乱入的伪作,也有如《孔丛子》裒合各处传世文献而成的托伪之作,更有像孙星衍所辑《物理论》这样失考误辑而产生的伪文,更无论唐宋以降金石碑刻著作中仅有著录但拓本并无实物可访者的诸多情况,先唐文献的整理终究不免是对辨伪工作的亦步亦趋。然而,严氏在《全文》编纂中对部分伪作否定删略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托名为陆机所作的《周处碑》,作于陆机亡故之后,归于陆机名下似有不妥,但也不可断然删略,而是可以通过略加校语的方式将其置于《全先唐文》中。
西方近代校勘学家A.E.豪斯曼就认为,“对校”是科学,“修正”是艺术,因而校勘既是科学,也是艺术[8]。所谓科学,即是要有规范的方法;所谓艺术,即是要有才思和创造,而严氏的辑佚方法兼而有之。仅仅因为先唐文献有后世的整理,而不去仔细考察区分这些整理工作中哪些是科学、哪些是艺术,就全盘地质疑和指摘从抄本向定本转化中的可信度,亦是过犹不及。至少在《全文》这里,严可均大都以逐一注明文本出处、撰写案语和校语的方式,说明了自己的辑佚校勘依据。溯源和还原虽需功夫,但亦非难事,只要在具体的工作中详察其思、详知其法,犹可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