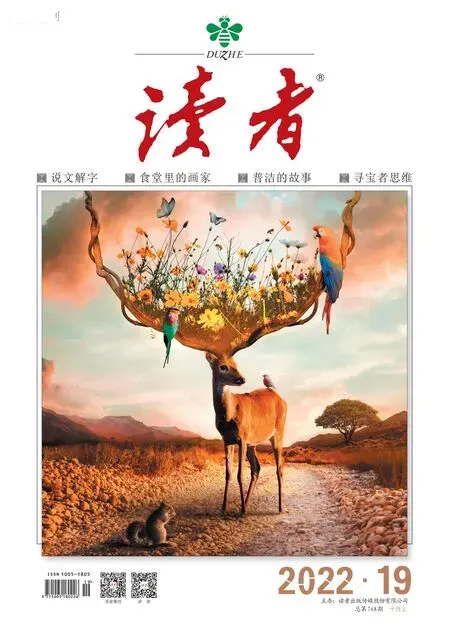馄饨妈妈
☉不贰爷们

——1——
今年春天快结束时,我看到了馄饨妈妈的讣告。
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摆馄饨摊的,而是我爸在研究所里的领导,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归国的博士。
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大家之所以叫她“馄饨妈妈”,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叫作“馄饨”(英文名的谐音)。
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研究燃料催化的,馄饨爸爸老万是研究耐火材料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老万不幸殉职。
馄饨是在国外出生的,比我大1岁,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扬扬自得,被我修理了几回之后,就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当小弟。
馄饨出事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
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一整天,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晚上8点多,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我才想起来,回程时,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于是,我便赶紧下楼扯着嗓子把小伙伴都喊下楼,挨个儿找出去玩的人……然后,整个研究所的家属,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驻军警卫连,全部出动了。
一夜灯火通明,却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民警在儿童公园的人工湖里找到了馄饨。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
城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又不太合群,所以他溜到湖中玩水,其他孩子都没发现。
一个刚刚痛失丈夫的女人,又不得不面对失去独子的悲痛。虽然她是科研领军人物、祖国的栋梁之材,可她是个女人,更是个妈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馄饨妈妈跟所里请了长假,又申请使用家属区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摆了个馄饨摊——她要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的儿子。虽然所有人都为她深感惋惜,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
——2——
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去她那儿吃饭的,大人收两毛,孩子们不收钱,都管饱,想吃多少,自己从脸盆里捞,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
馄饨摊很小,只有两张大圆桌,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开张那天,副市长亲自来捧场。我妈和其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则帮忙切菜、揉面、包馄饨。
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仅有的两张圆桌中,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过了好一阵,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替我儿子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
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但偏偏这句话,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开始怀疑她的动机。
我妈说,馄饨出事,我必须负责任,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他死不了。
其他孩子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一位痛失爱子又精通化学的妈妈,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家孩子复仇,谁又能说清楚呢?
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说是因为看到这些小家伙狼吞虎咽的模样,就仿佛感到自家孩子还活着,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而这些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每长高一点儿,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
然而,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又有谁敢用自己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
最明智的方式,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稽查队员”,面对任何一个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绝对会拿出她的看家本领。
于是,在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比如,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
这些,每位“执勤”的妈妈必定都看到了,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
——3——
馄饨妈妈是研究所的名人,她受欺负这事,很快就传到所领导的耳朵里。
作为孩子王之爹,我爸被研究所的高所长约谈了。
得知我的恶行后,他直接请假回家,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一寸宽的钢板尺。
他是真火了:“你惹祸,我可以容忍。但你欺负一个女人,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对着我爸一阵喊叫,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你们这帮人,一天天净添乱。她要是真想害人,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
当人类复杂的思想,遭遇至简的信任,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一个留过学的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摆个馄饨摊等着警察抓?
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接着,她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馄饨妈妈面前。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立即扶起我妈:“嫂子,你这是干吗呢?我还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
然而,馄饨妈妈没说几句,自己也忍不住哭成了泪人,她确实受委屈太久了。
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也纷纷抱头痛哭。也只有妈妈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母亲的辛酸,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芥蒂之时。
那天之后,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终于被一群在铁皮房顶上撒过尿的小崽子给挤满了。
——4——
我妈说,馄饨妈妈真正在意的,就是我们那一批孩子。因为我们与馄饨同龄,更是馄饨生前最亲密的小伙伴。我爸也说,其实从我们上初中开始忙碌起来后,馄饨妈妈已经走出了失独的心理阴影。她也想过回到工作岗位,但又实在放不下一代代挤进铁皮房、管她叫“妈妈”的孩子。
其实,不仅我的父母,又有几个家长能忍心看着一个女博士天天这样给孩子们当“饲养员”呢?
馄饨妈妈确实跟所里提出过复职申请,但她又同时要求,得跟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以便照顾馄饨摊前的孩子,工资待遇方面她都不计较。
但在多重原因之下,馄饨妈妈的复工申请,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本就左右为难的馄饨妈妈,干脆撤回了自己的复职申请,又办了离职手续,直接在本市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里找了份工作。当大学老师,不但能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本领,还能和学生们一起放寒暑假。平时不上课的时候,她还有精力继续照看她的馄饨摊,继续听孩子们管她叫“馄饨妈妈”。
——5——
2000年,随着本市房地产开发浪潮的侵袭,父亲单位那块本就在市区里而且又依山傍水的宝地,自然被许多开发商盯上了。馄饨妈妈的那间位于住宅区入口的破铁皮房,第一个被纳入待拆除清单。
这个消息传开后,研究所的生活区彻底炸锅了。
当天傍晚,我带了一大帮哥们儿从学校赶回去,捍卫这间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童年记忆的铁皮房。
隔了太多年,几个哥们儿再爬上铁皮房顶也没那么利索了,但站上去后,就用大喇叭开始喊叫:“拆别的跟我们没关系,但拆馄饨妈妈的铁皮房,绝对不行!”
在还算和谐的气氛中,我们和开发商就那样僵持着。大家都在心知肚明地等待,等待着馄饨妈妈回来。
从学校赶回来的馄饨妈妈,在众人的帮助下也爬上了房顶。我以为她想喊两嗓子,便把大喇叭递给她,结果被她抬手打了一巴掌。
馄饨妈妈哭了,哽咽着说:“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现在就给我回家老实待着!”
大伙儿都愣住了,这可真是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们。
馄饨妈妈接过大喇叭喊道:“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我们不能给国家添乱,什么事都可以好好沟通。大家要是认我这个孩子们的妈妈,还是请回家吧,千万不要再闹事了!”
众人茫然,但没有人挪动。
馄饨妈妈急了,直接给大家跪下了。
她这一跪,人群立即像潮水一般四散而去。
我们扶起她的时候,她抱着我们哭得像个孩子。我们太了解她了,没有人比她更想保留这间铁皮房,但为了我们,她宁可失去这个有关她的孩子馄饨的最后记忆。
2000年9月,当在铁皮房吃饭的最后一批孩子走进校园后,用脸盆装馄饨的故事,彻底结束了。年近半百的馄饨妈妈,也回到了真正属于她的那片天地。
——6——
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秘密,尤其像馄饨妈妈那种心地善良又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女人,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早就帮她赶走了岁月的痕迹。参照我妈的年龄估计,她至今顶多70岁。
现在,她走了,真的去见她的孩子馄饨了,我又怎能不让她帮我给馄饨带个话,说声亏欠了太多年的“对不起”呢?
不幸的是,她走的时候,刚好是本地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但幸运的是,我正在做生鲜品运输,所以有一张在疫情管控期间驾车上路的通行证。
清晨5点,天蒙蒙亮,当一行人准备出发之时,驻军部队的指挥车居然闪着警灯来了。司机并没有下车,挥手示意我们跟着他,他带我们进入军事管控的科研区,一路驶过一栋栋壮观的科研大楼,特意在馄饨妈妈曾经奋斗过的大楼下停留了1分钟。
让人感动流泪的是,我们一路驶过的每栋大楼、每一盏亮着灯的窗口,都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向我们挥手,贴在玻璃上的各种纸用马克笔写满了送别的话,诉说着他们的离别之情——这是疫情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作者,在用他们的方式送别馄饨妈妈。
我一路鸣着喇叭驶出科研区后,又一头扎进生活区,一栋又一栋地绕着居民楼转。居民楼上,不少人从窗口探出身子,挥舞着各种纸牌子,上面写着诉说离别之情的话。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场,也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这位让所有人尊敬的馄饨妈妈。
馄饨妈妈走了。今天可能不会再有她那样“自甘平庸”的故事,更不会再有用脸盆装馄饨的壮举了。但所有从脸盆里捞过馄饨的人,永远忘不了她。
她已经与过去那些岁月“同框”了。
(田宇轩摘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本刊节选,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