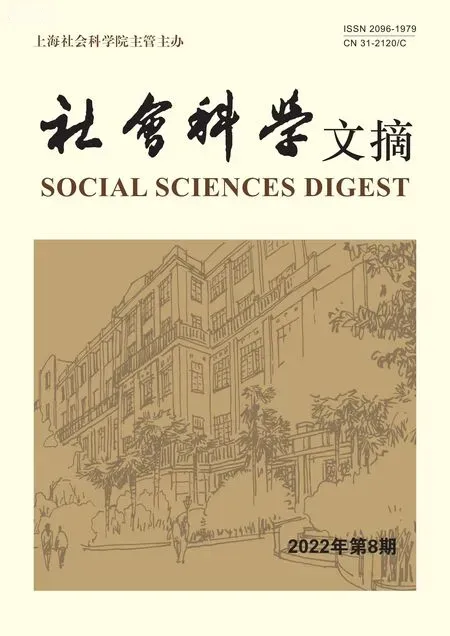论想象
——一种社会学的概念化
文/郑震
作为一个概念的名称,想象在社会学的历史中近乎是缺席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想象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从社会学思想的历史中寻找一些重要的切入口,以展现想象如何以某种隐蔽的方式早已存在于社会学的思想之中。当然这并不是对想象本身的直接研究,但思想史的中介作用对于一个尚缺乏概念化的问题而言,无疑具有某种开拓性的间接作用。正是思想史的启发与反思性的重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想象活动的形式化特征和意义提供了出发点。
社会学思想中的想象因素:表象与错觉
许茨认为那个在原初经验中的活生生的主观意义的世界从不是陌生的匿名存在,这意味着任何客观化的把握都有可能错失主观意义的丰富性。然而看似悖论的是,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这确保了人们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理解和沟通的可能性,即当作为社会化建构的主体间性的共享知识能够有效地为面对面互动提供支持的时候,人们似乎并不急于去探究那个黑箱式的主观意义的世界本身,而是停留于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类型化的想象,这就是主体间性的文化或意义结构。许茨理论的焦点就在于“类型化”,它首先是排除各种独特性的具有社会客观性的常识构造,而社会科学的类型化建构则是基于此种常识构造的更高层次的客观性建构。如果日常类型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一种想象的维度,那么科学的解释就可能意味着对想象的想象。毕竟,类型化是基于许茨所谓的主观意义世界的不透明性,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支撑他人行动的那个意义的变幻不定的独特方面,类型化仅仅是一种强加的一般性构造,它用类型来取代活生生的经验现实,它的普遍主义的效率是以牺牲特殊主义的生动性为代价的,它将经验的不确定性还原成对一种确定性的想象。
许茨所追求的那个基于常识经验的构想而建构起来的科学概念的构想,在加芬克尔的眼中也只能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以科学的偏见想象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而这两者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与此同时,我们不难推论出,日常行动者对主观意义的类型化解释也同样无法得到加芬克尔的认可。在加芬克尔看来任何客观化都将导致意义的丧失,也就是导致对现实的想象和歪曲,唯一不同的也许只能是,社会科学由于其客观化的程度更高,从而更加彻底地导致了现象的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常人方法学并不宣称提供一种有关其对象的高度概念化的命题陈述,拒绝采用一种相对客观化的方式来概念化(类型化)其所研究的现象,因为这只能导致现象或细节的丧失,从而无法真正地理解其所研究的现象。我们甚至不能将此种做法视为是通常意义上的研究,因为“常人方法学的成果与根本的秩序现象是同一的”,研究只是对现象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去实践现象本身。这一做法的消极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它放弃了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它在拒绝想象社会现象的同时却没有意识到,成为“对象”本身也就意味着接受对象所存在的问题,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对象”也就意味着像“对象”一样误解自身,从而以其自身的实践而重现了社会现象自身的想象,因为这个想象也许正是社会现象所无法回避的构成。
布迪厄所谓的误识恰恰是加芬克尔所坚持的自然态度中的错觉,似乎现实从来就是如此,在所有人的相似的实践中进行着一种社会的实验验证,作为结果的可重复性正是这一实践继续进行的动力本身,反复的实践证明了实践自身的合法性,这是社会逻辑中最荒谬的逻辑之一:循环论证。然而这种自然态度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理所当然,它的自然表象完全可能成为最隐蔽和坚固的枷锁。对误识的揭示可以视为是对现象学保守主义的一种批判,而加芬克尔则无意之中陷入这种保守主义的阴影中。误识意味着对自身的行动和处境采取一种理所当然的立场,从而拒绝反思这一行动及其处境的合法性,这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将生活世界的信念视为是前科学的原初自明的真理。然而误识正是想象所制造的错觉,即想象中的幻想因素(不是有意识的幻想),当人们以类型化的方式来想象他人的形象时,却误以为抽象的类型即是他人的形象本身,从而无视这一形象的社会历史性建构及其所可能隐含的暴力。在布迪厄的语境中,想象的不言而喻性超越了意识哲学的狭隘视角,在一种无意识的错觉中揭示了社会暴力最深层次的基础。由此,人们无需将想象理解为行动者有意识所进行的某种形象化或表象化活动,因为社会表象的生成就其最隐蔽的机制而言,恰恰是一种没有被意识到的身体现象,也正是因此表象并没有被视为是表象。一种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表象被误以为是社会的实在本身,仿佛它是客观给定的事实,获得了某种自在的规律性或自然性的特征。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游戏(自证预言),那些被误以为是实在的现象被赋予了一种符号化或象征化的特征,从而为其存在带来了某种虚构的稳固性。
社会学思想中的想象因素:表象与真相
在类型化的运作中不只有误识与暴力,与所谓真相的不一致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生存的压迫与剥夺。我们甚至不能将此种不一致一味地视为是完全消极的现象,戈夫曼有关印象管理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让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表演失误时的观众举措,这一举措揭示了表演并非只是一种单向度的演出和接受,而是表演者和观众共同投入的情境互动,正是在此种共同投入的互动实践中社会结构的秩序特征才得以被生产和再生产。观众也同样投入到印象管理之中,也就是去捍卫那个表演者所制造的假象。与其说人们在此所捍卫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还不如说人们是在捍卫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表演的伪装和观众的得体都是为了维持或建构一种理想化的互动形态,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反倒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动力所在,这其中自然有合乎各方生存的现实利益的左右。真相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可怕之物,观众期待着表演者的适当性,尽管已经意识到这也许只是一场表演。这充分揭示了社会现实并不是什么客观给定的绝对的事实,也不是逻辑上完全统一的单一形态,而是存在着多重的面孔或不同的建构。有的时候人们更热衷于寻求所谓的真相,厌恶那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有的时候,人们却更乐于沉浸在想象之中,似乎真相是可怕的,唯在想象中方能生存。
社会学思想中的想象因素:想象力
米尔斯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另一幅面孔:想力。想象力是一种有助于缩小认知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性的创造性能力,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将带来绝对的真理,但它有助于超越传统的掣肘与局限,从而推动迈向对现实的更加充分的认知。由此可见,想象或想象力也可以成为一种打破幻觉的束缚、推动创造性认知的力量。归根究底这是因为想象是一种不确定性,它并不遵循工具理性化的科学逻辑,不是严格执行的程序法则,而是不被现实所束缚的创造性的力量。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思维的意识层面,我们会发现这种由不确定性所主导的创造性弥漫于想象的各种面孔之中(我们用想象力来命名此种创造性)。在日常生活的类型化想象中,它促使人们忽略了那些难以把握的变化不定的直接经验,从而在一种类型化的想象中构造出日常生活世界的图像。这种创造性也同样可以在一种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捍卫某种道德的秩序,即将一种社会历史性的道德要求想象成特定情境中理所当然的秩序,即便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表演也还是在事实上捍卫了这一想象的表象。进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想象的创造性产物既可能成为阻碍合理认知的科学的错觉,也可能成为颠覆这种错觉与暴力的创新的力量,这正是想象的奇妙之处,它的不同面孔向我们揭示了想象那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意义。
结束语:想象的社会学分析
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想象几乎是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现象,其存在的原初根源是直接经验世界的不透明或半透明及其变动不居的状态。正是基于此种不透明和不确定,想象成为社会行动的一般性特征之一,我们甚至可以以一种略显夸张的口吻说,人类正是生活在他们自身所想象的世界之中。这并不总是一种有意识的算计,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一种不言而喻的过程为其特征。
因此,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有意识地展开一种表象化的活动,以此来扭曲现实的形象,相反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偏好与视角、理想与好恶在无意之中已经作为一种想象的要素而存在于他们的行动之中。当人们以相似的方式在实践之中去想象现实的时候,这种未经筹划的共谋使得想象的现实仿佛就是那个被想象的现实本身(行动之间的相互印证,但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不会再有所谓的真相与想象的碰撞,这种自证预言式的处境更加强化了对想象的执着。
在一种缺乏高度对象化的意识活动介入的情况下,想象的世界仿佛就是那个真实的世界本身。当人们以共同的想象投入到共同生活的建构之中的时候(这当然是一种偏重主观视角的分析),想象与真相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人们把表象视为真相,把暴力当成法则,在一种非反思的盲从中被自身所参与建构的想象所奴役,这恐怕是想象最消极的意义所在了吧。但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在社会暴力与压迫伪装成受害者的自我想象而实施奴役的同时,想象也可以成为一种共存的积极力量,对于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类而言,想象出一种道德的模样,这看似消极却蕴含着积极的力量。当人们共同为了一种情境的道德定义而努力维持的时候,这种被各方视为理当如此的适当性与所谓的真相又有什么区别呢?即便类型化的想象偏离了它们本来试图把握的直接经验本身(例如那个表现出道德模样的人其实采用了非道德的表演),但当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不断地以这种类型化的方式来生产和再生产生存的过程,那么它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真相呢?
我们将想象与现实的此种转化关系称为是想象的辩证法,它从一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世界的高度复杂性,那种将社会历史现实想象成客观给定的事实的做法,充其量只是为这个复杂性增加了一个辩证的因素,当然这取决于这一想象被信仰的程度。事实上,那些被想象所遮蔽的“真实的经验”其实还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建构,只是与那个试图把握它的类型相比,它构成了一种更具原始性的事实(这种原始性仅仅意味着类型化的常识运作的相对缺乏)。我们并不否认认知上的扭曲的确是一种社会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永恒绝对的事实,它们只是在不同层次建构的事实之间所做出的一种比较。因此,我们不应当将想象仅仅视为是对事实的偏离,想象的实践及其后果也同样是社会历史性的现实存在,它既存在于那个想象化的过程之中,也存在于那个被想象化的事实之中(区别仅仅是层次性的,是在作为理想极点的完全没有类型和纯粹类型之间的层次变化)。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更具建设性地看待那种对情境中的道德模样的想象,基于不同场合所采用的得体的行为举止正是这种想象的展现,至于那些举止之中是否蕴含着一种投入的信仰,只是在社会行动的层次划分中具有某种实际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那些与他人共同生活的道德想象在维持着某种基本的社会秩序,这当然是撇开各种消极因素的理想类型式陈述,但它的重要意义却不可忽视。被想象将以一种道德的模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和承认这种想象的合法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不正是建构一种共同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吗?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盲从中被想象所奴役,同样也在盲从中被想象所涵养;我们不只是在想象中误入歧途,也在想象中理解并积极地生产和再生产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想象的辩证法。只不过想象很少是以某个单一的面孔出现,它由此才涵括了一种生活的丰富性。正是社会经验世界的不透明(或半透明)和不确定使得想象成为每一次遭遇的内在构成,尽管想象因此而包含着对明确性的寻求。但因为社会经验世界的不明确性是无法彻底消除的本体论事实,想象自然也难以通过规律性的方式来获得其存在的有效性,更何况绝大多数想象本身就是以不言而喻的实践方式在发挥作用,想象正是其想象的那个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因素,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确定性的烙印。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想象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相同的现实完全可能激发出截然不同的想象),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想象本身就增加了这一现实的晦涩性。但这的确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创造性,想象的不确定性无疑为生活增添了多样化的事实。这种多样性的能力虽然与科学的创造性在结果上往往大相径庭,然而它们摆脱成见存在的勇气却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只不过科学需要一种强烈的意识介入,需要将打破成见的束缚作为一种明确的对象化需求来加以实践,而日常生活的想象却主要在一种前反思的理所当然之中铺展其创造性的变换能力,这当然也使之更容易陷入各种错觉与暴力的统治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说,想象是一种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社会表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及其结果,它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但无论怎样,想象都不能摆脱一种社会历史性的表象化特征,这正是人之存在的社会历史局限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