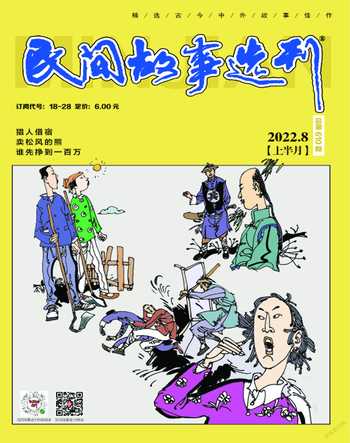车辆转弯
李方
老城在南,新区在北,火车站建在清水河东岸。住在老城、新区的人,要到火车站,都要经过清水河上的斜拉桥。五湖四海的旅人到了这儿,从火车站涌出来,无论坐出租还是乘公交,也都得透过车窗,看着桥上的铁索,望着河道里一线清浅的流水,过桥,或左转,往老城而去,或右拐,奔向新区。
我对这座桥毫无感觉,也对过往的旅人不感兴趣。我之所以每天不少于四趟跨过这座桥,是因为清水河镇政府所在地和火车站一样,都在河的东岸,中间只隔一站地。
饭碗在那里,岂可大意。
我原住在老城。街道坑洼不平,楼宇低矮逼仄,下水道不畅,秋天一场大雨,老城的人就后悔没买一艘冲锋舟。但老城也有好处,学校、医院、菜市场、酒店、银行、寿衣店,从生到死所有用得着的名堂全有。况且,每条街道两侧,都有绿塔一般的古柳,夏撒阴凉秋飘叶,春天柳絮如冬雪,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安心地住在这么个地方,也算祖上有德了。
但是一封信,把我搞烦了,到纪委“喝过两次茶”,折腾了大半年,虽然查无实据,没有问题,还是从县直部门调整到了清水河镇。我就把老城的房子留给儿子,在新区购买了新房自己住。新区离镇上当然要远一些,但对临近退休、升迁无望的我来说,时间是最不宝贵的。
每天在始发站乘公交,都有座位,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靠窗的位置。每当公交车即将驶上斜拉桥的时候,那个早已设置好的女声就会提醒人们:“车辆转弯,请抓紧扶好。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下一站,桥头东站。”
在桥头东站下车的人不是很多,有时候甚至只有我一人,这让我多少有点儿优越感,认为这个站点就是为我设立的。更多的人,是奔着下一站即火车站去的,而到镇政府上班、办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开着私家车的。普通民众要办事,都是去民生大厦,不会到镇政府来,除非是上访或者是往纪委的举报箱投匿名信。
在“车辆转弯”的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桥西头的那个修鞋摊点,但因为那里并没有公交车站,所以从未驻足。今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因为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前面大桥上发生了车祸,造成拥堵,我只好提前下车,步行前往。
那个修鞋的摊点上,撑着一把印有啤酒广告的遮阳伞;伞下,一辆轮椅上坐着修鞋的年轻人,旁边蹲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尽管我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但在“车辆转弯”声里睁着一双酸眼看风景的人,也能推测出这一“景”的大致内容。但渐渐密集起来的雨点儿,还是把我逼到了遮阳伞下。
“师傅,您是要修鞋吗?”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抬头问我,一张笑脸。
那个蹲着的白发老人不等我回答,就动作敏捷地直起身来,将一张蒙着软垫的小凳递到了我脚下。
我的脚确实有点儿问题,哪怕是新鞋,行走一段时间后,鞋的脚后跟外侧就会磨损。今日天假其便,已经到了别人的“屋檐下”,顺带收拾一下也无妨。
“钉个掌。”我坐下来,开始脱鞋。
老人又递过来一双塑料拖鞋,说:“快穿上,今天下雨,地上潮,别凉了脚。”
钉掌没用两分钟,我之所以坐著没动,是因为年轻人脱了手套,接着遮阳伞上淋下来的雨水洗了手,和老人开始吃早餐。老人说:“您不吃早餐的话,尽管坐着,等雨小了再走。一大清早,没什么顾客。”
“孩子和他娘,也是因为车祸。娘走了,孩子的双腿残了。我呢,修了一辈子鞋,只好将手艺都传给他。他一辈子的路还长,总得有个手艺在身,赚钱活命。”
年轻人用手托着塑料袋,吃着还冒热气的包子,轻声说:“爹,说这些干啥。”
老人伸着胳膊用卫生纸擦去年轻人嘴角上的菜屑,又用一个小勺子,将装在塑料袋内的辣椒蒜汁舀出来,小心翼翼地倒进被年轻人咬破的包子里,笑着说:“没关系的,对陌生的顾客说说这些,就是个排遣嘛。好多难受的事,不和人说道说道,一直藏在心里,慢慢就会积攒成毒素的。您说对不对,师傅?”
“您老说的话,没错。”
年轻人一口一口地吃着,老人一勺一勺地添加着蘸汁。
雨点儿渐稀,车辆开始缓慢地移动。
我问清了他们居住的村组后,对老人说:“等天晴了,您抽空拿上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孩子的残疾证,到桥东的政府大院来找我。我不是陌生人,我是咱们清水河镇的镇长。”
如今,我还是每天在始发站乘公交,在桥西头车辆上桥转向火车站的时候,那个女声依旧说着“车辆转弯,请抓紧扶好……”,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转过头去,看一眼车窗外。那个原来在遮阳伞下的摊点已经不在,桥头显得空荡荡的,但我的心却格外踏实。
选自《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