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养老,为体面养老“保驾护航”
文 王环环

近年来,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其中,相比于城市,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城乡差异的进一步扩大,空心村等现象加剧,农村养老形势日趋严峻而复杂。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而如今,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仅靠家庭养老已无法满足农村养老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导致父辈与子辈分离的情况越来越多,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等问题更为凸显出来。如何让农村老人体面养老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难题。
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熟人社会中村社共同体的优势,互助养老模式开始出现并兴盛起来。这种“以老养老”的互助式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农村的养老压力,让体面养老成为可能。
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
近年来,相较于城市,农村养老受制于代际分离、经济水平等主客观因素而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农村养老形势严峻而复杂。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三方面特点:
一是相较于城镇,老龄化程度更高。二是老龄化速度加快。
三是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体面养老显得更为艰难。农村老人普遍仍在参与农业劳动。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于大多数留守老人而言,力不从心成为他们劳作时最明显的感受。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对信息技术使用存在数字鸿沟,新信息接受较慢,难以及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生产,再加上他们对于新生产技术与模式的接受度较低,难以进行转型升级,“种粮不指望挣钱,够自己吃就行”成为了许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与此同时,我国养老体系的建设也尚不健全,对于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而言,他们尚未被纳入高水平的养老体系之中,而仅凭借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他们每月的所得并不多,有的地区甚至不足百元,生活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失能老人问题也更为突出。对于失能老人而言,自给自足尚难以达到,体面养老更是奢望。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失能比例将只升不降。体面养老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


互助养老,开辟农村养老新模式
在这一背景之下,为更好应对当下农村的老龄化危机,全国各地纷纷就农村养老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其中,河北肥乡县的互助养老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互助养老,是一种介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模式,通过集中居住、互相帮扶等方式,使老人的生活得到照顾,精神得到慰藉。这种“以老养老”的模式强调自助与互助,不仅可以缓解农村养老压力,同时也可以唤醒低龄老人的生命活力,使其价值得到发挥。
2008年8月,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村委会出资在村里闲置的场地建立了首家“互助幸福院”,将村里60岁以上的、生活可以自理的老人聚集到一起生活,老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生活。
这一“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低成本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推行之初并不顺利。彼时,一村干部曾表示,“刚建院时,有些群众不理解,认为建不起来,建成了也没人住”。
但随后,随着“互助幸福院”的落成,其以“费用低,有年纪相仿的人交往,老人之间又能相互照顾,子女无后顾之忧”的优势最终“俘获”老人们的心,他们开始慢慢接受了这种养老方式,申请的人越来越多。一居住在此的老人表示,“住在这里和在家花费差不多,不同的是我们这些老人可以凑在一块自己做饭,开展娱乐活动,心里乐呵”。
随着“互助幸福院”的成功实践,一时间肥乡县前屯村成为各地跟风效仿的对象,互助养老模式开始在多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011年,湖北省探索建立“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模式,在全省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试点,以解决农村老人日间生活照料、情感交流、文体娱乐、精神慰藉等问题;2020年,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朱所村通过乡村振兴战略,重新整合了土地资源,把村内部符合“危房改造”的用地置换出来,用以建成居家养老服务站,同时,还发挥慈善力量,引导乡贤能人及社会爱心人士以捐资捐物、上门服务等方式,参与到农村居家养老志愿服务中。
随着互助养老实践的不断推广,互助养老模式逐渐类型化,主要以三类为主: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模式、能人带动型互助养老模式和群众自治型互助养老模式。
干部领导型互助养老模式,即村干部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并主导互助养老服务的运作过程。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村集体收入、社会慈善募捐等。比较典型的是上海堰泾“幸福老人村”模式。上海堰泾在完整保留农村老宅原样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内部设施改造和功能植入,在市郊乡村建设“更接地气”的养老社区。
能人带动型养老指的是由村庄中有能力、有影响的人发起并组织,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兴办的老年人互助事业。资金来源包括村“两委”拨款、会费以及社会捐赠等。主要特征是自治性强,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的力量。比较典型的是湖北赤壁曙光合作社。“合作社+农村互助养老”的形式,可以将流转土地冲抵部分养老费,老人入住养老院后集中供养。
群众自治型互助养老模式指的是村民直接决定和参与村庄的养老服务,互助养老实践的推动力量来自群众。典型类型有亲友互助、邻里互助、结对互助等。比较典型的是陕西安康结伴养老模式。结伴养老模式更为灵活,成员间相互了解,知根知底,熟悉各自脾气秉性,生活中容易形成默契,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关系稳定长久,但相对来说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范围较窄,只能覆盖到小部分群体。
此外,时间银行这一概念也开始被引入到农村养老工作中,在河南新乡市、江苏张家港市等多地的农村地区获得成功实践,并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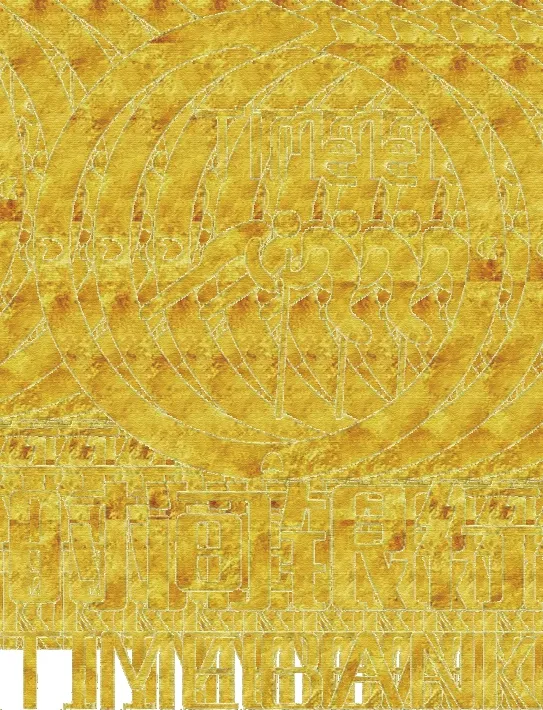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新型互助模式,近年来多被应用于社区互助养老中,于农村地区应用较少。但这一理念的引入,对于农村互助养老体系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倡导身体较健康的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待自己需要帮助时,提取志愿服务时间兑换养老服务。这种互助模式的出现,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偿互助。对此,有专家表示,“时间银行若能更多落地乡村,将会有效填补农村养老需求,帮助留守老人解决生活困难。特别是对生活自理存在困难的农村老人来说,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有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互助养老,未来可期
近年来,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多地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有效缓解农村养老压力提供助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互助养老这一模式的盛行绝非偶然,其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
互助养老在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不独亲其亲”“老吾老及人之老”是中华文化传统美德,互助养老模式便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延伸,将这一传统发展为一种互助模式,变成一种制度设计。亲邻互助的文化基因,让互助模式的推广得以在农村顺利进行。
互助养老也是顺应社会化养老趋势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养儿防老”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老人往往和自己的儿女生活在一起,由子女养老。但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打工,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养老功能不断被弱化。对此,有专家指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必须进行社会化的制度安排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互助养老模式便是在这一形势下产生的。一定意义上来说,互助养老是应对时代发展的产物。
互助养老模式的火热发展之下,不禁有人展望:未来,互助养老的模式会否在农村得到普及?
对此,有专家表示,“当前,互助养老仅为现有养老模式和体系的一种补充,不太可能成为主要模式。单靠互助养老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尚不太现实。”
而当下,随着互助模式在全国多地区的不断应用与推广,问题也逐渐涌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农村互助养老基础设施不足、对农村互助养老认识不够、农村老人互助功能发挥不充分。
其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除了部分行政村里有互助幸福院以外,大部分农村没有足够资金配备公共的养老设施与场地,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其二,人们对互助养老的认知仍显不足,受限于传统养老观念,互助养老的推行力仍显不足。
其三,相关体系建设不完备,农村老人的互助养老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目前的互助养老面临很多机制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困扰。比如,今天我帮助了你,明天谁来帮我?这个不是有钱、有承诺就可以解决的。”有专家表示。但对于互助养老模式未来的发展,他持积极观望态度,“这种符合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的互助养老模式,有着极高的发展前景。”
针对当下存在的种种问题,相关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中,重点在以下几方面进行: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互助养老政策体系。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将确保互助养老运行过程中有法可依,避免实践初期的乱象和法律缺位问题,避免“人人参与”带来的“无人问责”困境。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促进服务内容多元化。通过建设多种老年活动场所,积极组织老人开展琴、棋、书、画、舞、太极等各种健康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等措施,满足老人实现老有所乐的愿望,提高老年群体的精神健康水平。
扩大养老参与主体,实现多元互助养老。政府与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探索共同参与、多元治理的新型互助养老模式。在主体准入、投资、治理主体等方面实现多元化,充分发挥不同参与主体的优势,集思广益,在界定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避免单一主体由于认知局限而出现的能力不胜任现象。
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初步形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格局,让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让老年人“体面养老”,成为我们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努力的方向。互助养老模式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助益。相信在未来,随着相关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将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