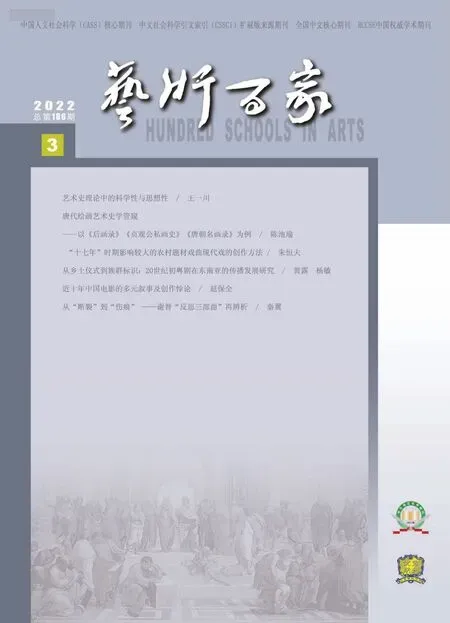“东坡笠屐”的图文生成及其多重阐释*
——一个跨媒介艺术史研究的个案
陈琳琳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苏轼戴笠着屐的形象,最初源于其谪居儋州的生活片段,经由后人的文学书写与绘画形塑,这一形象被附着上丰富的精神寄托与文化意涵,成为苏轼最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从儋州遇雨借笠的历史本事,到“东坡笠屐”主题图绘,再到《东坡笠屐图》的题咏书写,“东坡笠屐”在不同场域、不同门类、不同维度上被叠加演绎,最终衍化为一种可视化的精神象征,在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上产生独特而广泛的影响。关于“东坡笠屐”的本事及其文化意蕴,既往研究多局限于文字材料,而《东坡笠屐图》的研究则集中于传统美术史视阈,侧重于绘画图式、技法风格等方面的梳理总结①。鉴于此,有必要将文字与图像两方面的存世材料综合起来,采用一种跨媒介的研究视角,重新梳理“东坡笠屐”生成演变的历史过程,探讨不同媒介对“东坡笠屐”的形象塑造及其意义阐释,进而尝试为苏轼形象的经典化机制提供新的解读。
一、从故实到画像:“东坡笠屐”的本事溯源与图像呈现
关于“东坡笠屐”故实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周紫芝的《太仓稊米集》:
东坡老人居儋耳,尝独游城北,过溪观闵客草舍,偶得一蒻笠,戴归,妇女小儿皆笑,邑犬皆吠,吠所怪也。六月六日,恶热如堕甑中,散发南轩,偶诵其语,忽大风自北来,骤雨弥刻
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1]58-59
周紫芝在诗题中记叙了戴笠事件的时间、地点、核心情节,以及苏轼形象的大致轮廓,正文针对“东坡戴笠”之事有感而发,以简净的诗笔提炼了居儋时期的东坡老人形象,抒发对其旷达人格的认同与向往。在诗歌结尾,周紫芝洞察了苏轼戴笠形象蕴含的画意,呼唤王维绘就一幅《东坡戴笠图》。据此可知,“东坡戴笠”在两宋之交并非广为盛行的画题,至少尚乏人尽皆知的佳作,没有引起文人圈的普遍关注。周紫芝的叙述奠定了“东坡笠屐”故实的基本雏形,此后,“东坡笠屐”开始频繁进入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南宋费衮《梁溪漫志》记载此事,不仅补充“着屐而归”的内容,使“东坡笠屐”的形象更为完整,还指明借笠的直接原因乃“过黎子云,遇雨”。儋州士子黎子云从苏轼问学,与其往来密切,苏轼集中有多处与黎氏兄弟的交往记录,“访黎”合于苏轼谪居岭海的真实经历。费衮又言时人所画“多俗笔也”,可知“东坡笠屐”是时已被图入卷轴,但创作热度与流传范围犹有局限,文人画家还未充分参与,苏轼戴笠形象的文化内涵尚待进一步的发掘。[2]204《梁溪漫志》的著录文字迅速流传开来,周紫芝的诗题反而逐渐为人遗忘,仅诗歌文本得到保留。南宋祝穆所编《古今事文类聚》,收录苏轼遇雨戴笠的事迹,便采用了《梁溪漫志》版本。[3]504
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4]11-12张端义将苏轼访黎的目的落实为“玩诵柳文”,并补充了苏轼自赞《东坡笠屐图》的细节。苏轼文集未收此赞,与张端义同一时代的魏了翁题写《东坡笠屐图》,则将“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记为东坡语,非其自画赞。[5]12-13考虑到《贵耳集》的引据屡见舛误,行文不甚谨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6]1047,将苏轼本人引入《东坡笠屐图》的创作活动,可能意在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真实性较为可疑。不过,将戴笠着屐的偶然行为系于“玩诵柳文”的贬谪语境之下,其中深意值得玩味。“邑犬群吠,吠所怪也”语出屈原《九章·怀沙》[7]545,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援用此句,对韩愈因收招后学、抗颜为师而遭“邑犬群吠”深抱不平。[8]2176-2179回溯这一历史语境,那么这则笔记不仅契合苏轼因“戴笠着屐”为人讪笑、为犬群吠的贬谪经历,更映射出苏轼屡遭诬陷的政治处境,可以说是一种“融入谪臣想象”的文学书写。[9]
从周紫芝诗到张端义《贵耳集》,宋人对“东坡笠屐”的记载呈现出不断丰富化、细节化的趋势。入元以后,苏轼访黎的事由、途中值雨的情境、借笠着屐的情节、“人笑犬吠”的旁观效果,基本固定下来,鲜少发生改动。与此同时,“东坡笠屐”开始频繁进入画家的题材视野。绘画图像以其直观性、形象化的优势,有力推动“东坡笠屐”在各个社会领域、阶层、群体之间广泛流播,加速了苏轼形象的经典化进程。据画史著录,历代创作《东坡笠屐图》的画家,有宋元时期的李公麟、张逵、赵孟坚、赵孟頫、钱选,明代的唐寅、尤求、孙克弘、朱之蕃、曾鲸,以及清代的陈洪绶、黄慎、华喦、朱鹤年、居廉等等。其中,北宋画家李公麟,被公认为是《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然而,李公麟是否画过《东坡笠屐图》,虽有研究者加以考辨,但由于早期文献与存世画作的缺失,至今尚无确说。[10]无论首创者是谁,最晚至南宋中叶,“东坡笠屐”已从本事衍化为绘画母题是不争的事实。入元以后,当人们谈及“东坡笠屐”之时,往往自发联想起《东坡笠屐图》卷轴上的苏轼形象;到了明清时期,人们甚至是通过《东坡笠屐图》来检验、确认心目中的苏轼形象,“东坡笠屐”本事反倒鲜少被提起。
经由后人的文字加工与想象叠加,“东坡笠屐”的叙事内容渐趋完整,伴随着情节、人物乃至场景的扩展,苏轼形象也愈加鲜活丰满。这些丰富多样的叙事元素,为绘制《东坡笠屐图》的后代画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与创作灵感。有意思的是,通观“东坡笠屐”题材的存世作品②,笠屐本事的场景与叙事情节甚少吸引画家的创作目光。绝大多数画家笔下的“东坡笠屐”,无非是一幅苏轼戴笠的肖像画。他们袭用文人肖像画的程式套路追摹苏轼形象,至于笠屐本事的日常场景,诸如遇雨的戏剧性情节、围观的乡民邑犬,在画面上难寻踪迹。画家通常设置空白背景,将表现重心放置于苏轼的人物造型之上,精细刻画其体态神情,力图展现苏轼作为典范文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气质。作为连接“东坡笠屐”故实的唯一线索,斗笠与木屐是《东坡笠屐图》不可或缺的肖像道具,与之相配的往往是衣带飘逸的广袖宽袍,被用以揭橥苏轼旷放洒脱的精神面貌。至于苏轼的五官面容,或严格遵照文献资料加以细谨的描绘,或行笔率放,仅给出一种概括化的综合想象。不妨看清代朱鹤年的两幅《东坡先生笠屐像》(图1、图2),是较典型的“东坡笠屐”主题绘画。因是临摹砚背之作③,画像的尺幅不大,戴笠着屐的苏轼是画面唯一的表现对象。画家采用四分之三侧面刻画苏轼状貌,细目疏眉,须不甚多,然两颊颧骨并不突出,神色平淡温和。衣道袍,面左,身体稍向前倾,倚杖而立,长长的竹杖衬得身形颇为瘦小,这种略微失调的人物比例,渲染出苏轼贬居形象的沧桑感,亦暗合暮年流落岭外的真实经历。稍晚的清代画家吴筠画《苏东坡造像》(轴,纸本墨笔,现藏捷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构图造型皆取法朱鹤年,着意描绘苏轼双手扶杖的体态,但面容刻画采用更为通行的“髯苏”造型,图写“大胡子”的苏东坡,画家以流畅飘逸的衣纹刻画苏轼的闲放意态,直立的身形呈示一种抖擞的精神状态。比照朱作,尽管画面构图和造型元素如出一辙,但细节处却暴露了画中苏轼不同的思想感情。可见,虽然取自同一本事,但对苏轼形象的描绘与重塑,有的画家忠实于文献资料,有的画家更在意描绘自我心目中的苏东坡。

图1 〔清〕朱鹤年《东坡先生笠屐像》,绢本淡设色,62.0 cm×31.3 cm,韩国涧松美术馆藏(左);图2 〔清〕朱鹤年《东坡先生笠屐像》,绢本淡设色,尺寸不详,韩国私人收藏(右)
总的看来,以肖像画为基本图式的“东坡笠屐”图绘,皆注重描绘苏轼戴笠着屐的外在装扮,但对苏轼性格气质的视觉表现各有侧重:有的精神昂扬,仿如玉堂翰林的风华正茂,有的鬓衰体弱,合于贬谪岭外的风烛残年;有的几乎泯灭岁月的痕迹,仅是符合传统审美的、概念化的文士形象。绘画创作与文学书写中的“东坡笠屐”,在表现重心、情感寄托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存有明显的差异。文本语境中苏轼略显狼狈的贬谪经历,在后世的卷轴上几乎不复存在。画家依据自我理想中的文士典范,创造出一个新的苏东坡形象。画家对苏轼形象的描绘与再现,可以视作对笠屐本事的一种跨媒介叙事。一方面受特定媒材与技法语言的影响,“东坡笠屐”在绘画艺术中的形象表达具有程式化的倾向。图像媒介中的苏轼形象,某种意义上是对笠屐本事的一种简化与提炼,画家往往将“笠屐”视为肖像符号,直接移植到文士肖像的传统程式中,原创性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不同艺术家的主体意志也有一定程度的发挥。苏轼戴笠形象的不同表达及其意义阐释,源于画家不同的观照角度与审美取向,同时也渗入了明显的时代文化因素。
二、图绘与题咏:“东坡笠屐”形象的生成路径及其意义阐释
历代画家对“东坡笠屐”的视觉塑造,往往选取单一的人物造型或叙事场景,受限于静态的画面、局促的空间,这种图像描绘是高度概括化的。历史记载与文学书写中的苏轼戴笠形象,本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情感张力,一旦走入卷轴,便脱离了最初鲜活的文学语境,渐趋固化为画家自我抒情的视觉符号。不过,“东坡笠屐”的形象表达,并非是由文本到画像的一次性转译,在图绘活动盛行的同时,相关的文学题咏也频繁出现。环绕在《东坡笠屐图》周围的题咏诗文,不仅是《东坡笠屐图》的“副文本”,为观者提供珍贵的画史信息,揭示画家不为人知的创作意图,也是相对独立的二度创作,在阐发画面意蕴的同时,对苏轼形象展开了新的想象与重构。在图文交织之间,“东坡笠屐”的多重内涵得到深度的挖掘与拓展。
(一)“风雨海上苏”:历史语境与政治意涵
尽管“东坡笠屐”在后世的流传中被叠加了种种浪漫的想象,然而,回归历史现场,这一看似意外的离奇扮装,映射的却是苏轼令人唏嘘的贬谪遭遇。仕途的偃蹇,生活的窘迫,暮年的落寞,仿佛都深藏于戏剧化的记述文字之下。这种复杂幽微的文本意涵,越出了绘画艺术的表现范畴,只能付诸想象空间更广阔的文学语言。后世观看《东坡笠屐图》的诗人,常常穿透苏轼温和平静的面容,追寻其内心真实的情感微澜,竭力发掘“东坡笠屐”背后的情感寄托,及其为画面所遮蔽的政治隐喻。
早在周紫芝诗中,苏轼戴笠形象的政治意涵已有所掘发:“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1]58苏轼与苏武不仅姓氏相同,更具有放逐蛮荒的类似遭遇。周紫芝取“苏武牧羊”的典故譬喻流贬岭海的苏轼,既是实写儋州蛮荒之地的恶劣环境,也意在凸显苏轼刚毅坚贞的政治气节。“海上苏”的称谓直指苏轼屡遭谗毁的政治生涯,在绘画形象与贬谪经历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元代文人延续这一思路,视苏轼为苏武后身,由画面形象联想其岭海贬谪生活之艰辛,推重苏轼在绝境中坚忍的精神品格。虞集的《东坡戴履图》即是对“风雨海上苏”精神风貌的正面揭示:
谪居荒滨,无谁与语。言从诸黎,归在中路。风雨适至,借具田父。狺童怪随,传像画者。笠以雨来,屐以泥行。匪以为容,用适其情。朝衣轩车,固将若惊。恒服尔假,犹不予宁。含德之厚,混迹于俗。巍巍勋华,天章转烛。幽囚野死,曾莫指目。我不自忘,的致凝瞩。伟哉天人,其犹神龙。其来无迎,其去谁从?形拟犹差,矧是饰容。世无其人,神交或逢。[11]6
虞集对《东坡笠屐图》的题赞亦如画家手笔,先以简笔勾描“东坡笠屐”的故事始末,继而点破苏轼戴笠形象的精神要义。所谓“含德之厚,混迹于俗”,透过戴笠着屐的野服形象,虞集提炼出宋代士大夫特有的“民胞物与”的政治情怀;对“大俗大雅”的明辨洞察,可见出虞集对苏轼政治人格的理解与认同。在此基础上,虞集的诗笔越出具体的画面与故实,展开了汗漫的联想,浓墨渲染了苏轼的政治品节与人格魅力,“神交东坡”的热切渴盼更是流露无疑。对虞集而言,为《东坡笠屐图》写赞,观画仅是一个偶然的创作契机,更深层的意图则落于对苏轼政治遭遇的诠释,以及对其人格精神的赞颂。
戴表元《东坡雨行图赞》云:“玉雪心肝,泥途巾屦。赤壁矶前,褰裳徐步。宜乎马吕诸贤,援之銮坡禁苑而不为荣;章蔡二子,投之蛮烟瘴雨而不加惧也。”[12]415虽然未见笠屐造型的细致摹写,但“东坡雨行”的命题应与儋州借笠的故实密切相关。戴表元由“东坡笠屐”的轶闻,延伸到苏轼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借由并置“銮坡禁苑”与“蛮烟瘴雨”这两个悬殊的人生片段,彰显出苏轼荣辱不惊的政治品格。构思相近的解读方式,还有张雨的题画诗《东坡笠屐图》:“海上得生还,所养浩然气。束带立于朝,毋使庬也吠。”[13]302虽是题画,却宕开画面的具体形象,热烈讴歌苏轼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尤其是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的政治操守。郑元祐《东坡笠屐图》:“得嗔如屋谤如山,且看蛮烟瘴雨间。白月遭蟆蚀不尽,清光依旧满人寰。”[14]356全诗未指涉任一画面细节,仅是回溯苏轼借笠的历史语境:“嗔谤如山”直揭深陷诋毁的政治遭遇,“蛮烟瘴雨”言明远谪岭海的恶劣环境,“白月遭蟆蚀不尽”以形象的譬喻揭显苏轼刚正高洁的人格境界。与其说是题画诗,不如说是一曲标举苏轼政治品节与独立人格的颂歌。再如杨维桢的《儋州秃翁图》:
儋州之秃列仙儒,前身自云庐浮屠。十年读尽人间书,人间游戏随所如。玉堂雪堂两蘧庐,梦中赤壁骑鲸鱼。蜑乡敢欺牧羊奴,作诗曾弹台上乌。黎家生儿殊不粗,旧雨菜人今在途。异俗孰借东家驴,野人一笑来挽须,田家雨具侬岂拘。君不见,冠铁豸,舄青凫,触藩罣网胡用渠。不如箬顶两木趺,长作识字耕田夫。何物老妪相胡庐,异乡老稚皆吾徒。呜呼,麒麟冠剑粉墨疏,村中笠屐千金摹,乃知儋州之秃绝代无。绝代无,天子何不唤取归清都![15]274
苏轼自流放儋州之后,鬓发尽脱,黄庭坚曾唤其为“儋州秃鬓翁”[16]519。此诗所题《儋州秃翁图》描绘贬居儋州的苏轼形象,应是“东坡笠屐”主题绘画的另一变体。杨维桢撷取儋州日常生活的戏剧性片段,回顾了苏轼坎坷多艰的仕宦遭遇。轻快戏谑的诗句看似是对笠屐本事的解构,驱散贬谪生涯的阴霾,实则隐含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杨维桢仕途多舛,与苏轼可谓同病相怜,他曾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政治活动,然而狷直耿介的个性使其屡遭挫折与冷遇,加之战乱,他终是未能实现最初的政治抱负。题诗对画面所作漫画化的“变形”,隐微透露出诗人内心的愤懑与郁结。结句的一番自我感慨,犹未忘却政治理想,希冀获取明君的垂青。在谐谑的言语背后隐含着严肃的政治态度,诗人借助吟咏苏轼画像,再度抒发了用世之心。
综合上述题咏诗文可知,元代文人对苏轼戴笠形象的阐释,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他们由画面形象联想起苏轼贬谪儋州的历史遭遇,或悲慨其大起大落的仕途际遇,或讴歌其忠贞刚正的政治品格,或赞美其荣辱不惊的人生境界,总之是基于政治立场阐发“东坡笠屐”的形象内涵。对苏轼戴笠着屐形象作政治方面的暗示,或许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汉族文人将戴笠着屐的苏轼与北海牧羊的苏武联系起来,强调“风雨海上苏”的政治形象,应是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与此同时,仕进无望、理想落空的现实处境,又促使元代文人在苏轼身上找寻到了精神共鸣。对“东坡笠屐”的政治化解读,亦是此种时代精神的真实投射。
这种政治化的形象阐释,在入明以后逐渐削弱,仅留有些许余响。例如,顾允成《题坡翁儋耳小像》表面上以嬉戏口吻书写《东坡笠屐图》的观感,实则蕴含明确的政治立场:“宁与农家共箬笠木屐,而不与章惇吕惠卿共冠裳。”[17]80称颂苏轼刚正不屈的政治态度的同时,隐含作者以苏轼为榜样的自我勉励。再如明人陆树声《题东坡笠屐图》:“当其冠冕在朝,则众怒群咻,不可于时;及山容野服,则争先快睹;彼亦一东坡,此亦一东坡;观者于此,聊代东坡一哂!”[18]24冠冕公服的苏轼受尽诬陷排挤,戴笠着屐的东坡却令世人争先快睹。辛辣谐谑的“一哂”背后,是陆树声对官场人心的深刻观照,亦在影射其不与当局投合的现实境况。
我们不妨对比苏轼早年在《定风波》中所绘的自画像:“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19]356词前小序所言“沙湖道中遇雨”,俨然如同儋州借笠之先声:同处贬谪之地,同是途中遇雨的寻常小事,同为身着野服的苏东坡。然而,贬谪黄州的苏轼直言“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暮年到了岭海之外,却不得不向农家借来了雨具,戴笠着屐,狼狈而返。对待自然风雨的不同态度,便象征着苏轼面对政治风雨与人生挫折的不同心境:早年犹能高呼“一蓑烟雨任平生”,以荣辱不惊的心境迎接瞬息万变的政治风暴;而暮年时分,面对众人争笑、邑犬群吠的现实境况,却只能自叹“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两相对比之下,履险如夷的昂扬精神、无畏无惧的兀傲性格,仿佛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这种政治理想的幻灭心态,以及流贬海外的落寞情绪,正是笠屐本事中东坡老人形象的精神底色,这种政治隐喻与情感内涵也因其深曲难解,只能诉诸非直观性的、表达空间更为广阔的题咏文字,始终鲜少受到后世画家的关注与表现。
(二)坡仙风流:文人典范的文学想象与肖像程式
在深沉厚重的政治意涵之外,借助可视化的笠屐符号,“坡仙风流”的形象表征也得到放大与凸显。东坡之风神,在其当世之时已备受世人认可,黄庭坚直呼为“谪仙”[16]598,李之仪称“东坡仙人”[20]101。 南宋何薳《春渚纪闻》始以“坡仙”指称苏轼[21]75。此后,唐有“谪仙”,宋有“坡仙”,几成定说。“东坡笠屐”原是平凡琐事,但出于后人心目中的“坡仙”共识,在后世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染上了浪漫色彩。淡化贬谪经历的现实苦难,对“东坡笠屐”形象予以诗意化的观照、传奇化的变形,在元人的笠屐图咏中已见端倪。以吴澄的《题东坡戴笠着屐图》为例:
白鹤峰前井赤鲩,远徙又化南溟鲲。城南白昼魑魅现,赖有东黎诸弟昆。腥咸满口无异语,似人慰意聊过门。竹刺藤梢归路晚,濛濛雾雨天欲昏。御人不识藏纥圣,抖擞雨具相温存。天涯禹跋不到处,要使旧撵留新痕。荷笠俄成牧羊叟,谁令海上属国孙。襄童拍手接篱倒,庸犬惊吠扶桑暾。先生招怪每类此,白首幸免长鲸吞。何人为作野老像,风流不减乘朱轓。谪求天仙堕尘网,化身千亿难名论。我从像外得真相,神交心醉都忘言。[22]322
此诗名为题画,实是由观画引发的一次想象之旅。诗人串连诸多儋州生活的场景,以荒僻的意境与幽怪的物象渲染出贬谪岭海的艰难境况;又叠加了数个历史人物典故,暗指东坡为当世孔子、再世苏武。吴澄追溯笠屐本事,虽以夸张与联想为主调,却随处流露对苏轼政治遭遇的深挚同情。诗歌末尾,吴澄回归画面:“何人为作野老像,风流不减乘朱轓?”苏轼本是堕入尘网的“谪仙”,观看东坡画像,便如同与这位谪仙“神交”,这种精微的观感来自画外之画、象外之象。由此,诗人不仅盛赞《东坡笠屐图》传神写照之精妙,更直接点出苏轼形象的“谪仙”本质。在他看来,戴笠着屐无非是“坡仙”谪入人间的连锁反应,来自蛮荒之地的襄童庸犬,自然难解其风流之致;面对绝望的处境,苏轼竟毫无芥蒂、安之若素,这难道不是“谪仙”才拥有的气度与胸襟?结合吴澄的《赤壁图》题咏:“坡公以卓荦之才、瑰伟之器,一时为群小所挤,几陷死地。赖人主保其生,谪处荒僻。……公视操如鬼,鬼犹可也。当时害公者,沙虫粪蛆而已矣。人间升沉兴仆,不过梦幻斯须之顷,公岂以是芥蒂于衷也哉?”[23]553-554所谓“坡仙”风流,并非纯粹的避世态度,而是在洞察仕途险恶、看透世态炎凉之后,仍旧葆有的豁达胸襟与乐观心境。对这种精神境界的揭橥,才是“坡仙”称谓之于苏轼的根本意义。
类似的诠释方式见于元人贝琼的《题东坡戴笠图》:“两屐新泥蒻笠欹,满村风雨独归时。玉堂天上神仙客,妇女儿童总未知。”[24]327该诗将“人笑犬吠”的闹剧效果归结于寻常百姓的浅陋无知,传达对“坡仙”谪落人间的惋惜,同时透过“风雨独归”的画面形象,提炼苏轼超越尘世的精神气质。元代刘仁本《题东坡居士著屐图》则以温和的诗笔抹去儋州生活的困顿辛酸,对苏轼的贬居生活予以积极观照。苏轼戴笠的偶然行为,被重塑为飘逸落拓的洒脱形象,“坡仙”的风流意趣得到了再度落实。[25]186明代王鏊《东坡笠屐图赞》对苏轼形象的题咏也有“谪仙化”的倾向:“长公天仙,谪堕人界。……戴笠著屐,亦维东坡。出入诸黎,负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26]471不为人界所容的苏轼,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宠辱不惊,超脱凡尘的“坡仙”形象由此见出。
为了呈示自我心目中的“坡仙”理想,《东坡笠屐图》的题咏者在观看的基础上叠加了诸多文学想象。有两种手法最为常见:一是将前代文人的离奇传说移植到苏轼身上,如借用李白传说作“东坡骑鲸”之想④,将远谪海南的不幸遭遇美化为“登仙”的浪漫幻象;二是将发生在苏轼笔下的奇人异事,巧妙地化入“戴笠著屐”的具体语境,如苏轼偶遇“春梦婆”之事⑤,在题咏《东坡笠屐图》的作品中被反复提及,既呼应“人生如寄”之叹,又赋予其“悟道成仙”的传奇经历。“春梦婆”故事的发生情境与儋州借笠之事颇为一致:垂老投荒的苏轼背负大瓢,行歌田间,被儋州老妇一语道破平生,人生不过是大梦一场,所谓仕进功名,转头即空。这大概就是苏轼“人生如梦”观念的一种戏剧化呈现。南宋诗人姜特立洞悉“春梦婆”故事深藏的画意,叹惋李公麟不为写作《东坡海外郊行图》。[27]24198可见,在笠屐本事上叠加“春梦婆”故实,可丰富与深化“坡仙”的形象内涵:“戴笠著屐”这一偶然举动被有意解读为对追逐功名的懊悔,从中折射东坡老人对世事人情的洞察,映现“坡仙”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由此,《东坡笠屐图》的题咏者可以宕开单一的视觉画面,自由驰骋于种种文学想象,将众多本不相关的东坡故实串联起来,从而拓宽了苏轼形象的阐释空间。
与此同时,“坡仙风流”的视觉塑造,也因契合文人肖像的艺术传统,成为《东坡笠屐图》的创作主流。例如,款为元初画家钱选的《东坡笠屐图》⑥,画苏轼戴笠着屐,身体前倾,面稍朝下,双手提起衣袍,目光温润平和。画家以流畅飘逸的线条勾勒衣纹,重在刻画苏轼儒雅恬淡的文士气质。卷上有元明人题跋数则,皆在称赏“坡仙”风神。画像与文字配合着展现苏轼的精神气度,但总的看来,仍是一幅概念化的文人肖像,苏轼的独特性并不突出。明代唐寅也有丰富的《东坡笠屐图》创作活动,现有数件唐寅款的画作存世,多系后人伪作。据这些画作来看,唐寅写像的运思方式也是借用通行的肖像程式塑造苏轼形象:虽头戴草笠、脚着木屐,却着文人常服,面容清秀,双手略微拎起衣角,似在回避路途的泥泞,动作较为克制,未见过多情绪的波澜。明代孙克弘的图绘方式较为典型(图3):苏轼头戴斗笠,足蹬木屐,一手持杖,一手提衣,双目凝视远方。微胖,方脸,细目长髯,与文献记载中的苏轼状貌不甚吻合,应是画家基于创作经验的想象性重塑。观画上抄录的唐寅诗:“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画家并不在意苏轼的真实相貌,仅以简净的笔墨勾勒心目中的“坡仙”形象。行云流水的衣纹,深邃如水的目光,别具象征意味的竹杖意象,共同营造出一种简淡清旷的审美效果。再如,清人宋荦刻《施注苏诗》,在卷首附“元人笔”《东坡先生笠屐图》(图4),感叹道:“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六百余年后犹可想见。”[28]323然而,从画面看来,戴笠着屐的苏轼俨然一副儋州老农装束,嘴角还挂有微妙的笑意。这种图式结构显然发源于苏轼形象的另一种世俗化的生成路径,所谓“谪仙”的观感只是沾溉了宋荦美好的自我愿想罢了。可见,关于“坡仙风流”的视觉建构,便是将文人肖像的传统图式嵌于“戴笠著屐”的文学语境之下,配合着题诗共同阐发“坡仙”的形象内涵。这种创作思路自然难免落入程式化的窠臼。

图3 〔明〕孙克弘《东坡笠屐图》轴(局部),纸本设色,68 cm×32 cm,天津博物馆藏(左);图4 《施注苏诗》卷首《东坡先生笠屐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书影(右)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坡仙”形象的重要道具——“斗笠”与“木屐”,皆具有特殊的宗教内涵与民俗意义。据朴载硕的考证,“木屐”乃宋代民间传说中道教仙人的装束。[29]486这种基于民间想象的视觉道具,促成了苏轼形象的“神仙化”解读。不过,所谓的“坡仙”风流,重要的并不是出人意表的外在装扮,而是孤傲不羁的性格,流芳盖世的文采,以及脱尘绝俗的精神境界。陈继儒的《东坡笠屐图赞》即道破此中真意:“问汝无风无雨,何为戴笠披蓑。不是乔妆打扮,曾经几度风波。”[30]208“披蓑戴笠”不过是“坡仙”风流的一种外化,常人无法企及的超然胸襟,超越生死羁绊的逍遥境界,方才是苏轼作为“坡仙”的精神实质。
(三)诙谐东坡:文人传统的背离与超越
尽管关于“东坡笠屐”的文学书写,并未透露苏轼有意为之的扮装意愿,但这一形象所附带的戏剧化观感,彰示出一种背离文人传统的精神姿态,隐含有自我形塑的扮装意味。这种扮装意味的形成,有赖于文本和图像两种媒介的双重助推。在文本层面上,随着笠屐故事的渐趋丰满,苏轼戴笠的传奇色彩愈加明显;在图像层面上,这种扮装意味的表达更为明确,画家有意在《东坡笠屐图》中注入喜剧色彩与诙谐气氛,借助苏轼的神态、姿势等画面细节揭显其幽默潜质,这种图绘方式也影响相关的题咏文学,进而共同促成了东坡形象的另一种建构方式。
尽管元人所绘《东坡笠屐图》大多不存于世,但关于“东坡诙谐”的形象构建,在元代题画诗中即已出现。冯子振的诗歌便淡化了苏轼贬谪岭海的政治苦难,以明快的笔触描绘谪儋生活的日常情境:“东坡道人儋耳谪,田畯往往分坐席。孰黎子云久莫逆,天晴散步为尔出。忽然中路逢沾浥,竹鸡湑湑挥洒疾。河桥冠盖无处觅,瘴屩何异廊庙舄。老翁家具姑副急,箬顶齿蹑亦妙剧。”[31]279这些生动具象的乡村生活片段,不太可能是对画面的直接描绘,而是诗人基于日常经验的创造性想象。这种超越画面的活泼泼的生活意趣,正是对“东坡笠屐”诙谐内涵的精彩呈现。更为直观的“诙谐东坡”形象出自明代以降的《东坡笠屐图》。明代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图5)是一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据画家自题,这幅作品乃临摹李公麟写像之作。画中的苏轼呈现出略显笨拙的姿态,面朝下,佝偻着背,双手提起袍子,露出裤管。除了标志性的草笠木屐,苏轼的着装体态也稍嫌粗野:衣领完全敞开,胸膛袒露,袖子高高卷起,露出前臂的大段肌肤。造型犹如忙于耕种的儋州老农,与史册上记载的富有书卷气的“苏学士”可谓大相径庭。比朱之蕃稍早的明代画家尤求也曾画过《东坡笠屐图》,可惜原画不存,流传下来的仅有一件晚清画家潘振镛的临本,现藏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此轴在构图和形象上与朱之蕃的作品相近,唯东坡的面容神情稍有差异,悠闲而自得,虽是老农装束,仍留有明显的文士趣味。若潘氏临本为真,则说明这种具有幽默意味的苏轼形象,早在吴门画家笔下即已出现。此外,晚明苏州人物画家张宏所作《东坡笠屐图》也流露出相似的诙谐趣味。原画已佚,从清光绪年间陆恢摹本来看,画家通过截取“妇人小儿相随争笑”的热闹场景,衬写苏轼戴笠行为的荒诞意味⑦。戴笠着屐的苏轼形象在画家笔下出现了稍许变形,依然是后背佝偻,双手拎着袍脚,面容和蔼,然体形尤其短小,更像是寻常的儋州老农,画面附有数则题跋,呈示出截然不同的几种观感:既有脱离画面、旨在讴歌苏轼人格的,如唐寅题诗;也有为画面作自我诠释的,如沈颢题诗:“无雨无风笠屐过,风流狡狯笑东坡。功名两字谁拈破,拍手输它春梦婆。”该诗将画中苏轼的会心笑容归于偶逢春梦婆,点出苏轼参透功名之通脱;还有根据画面形象臆想苏轼戴笠的历史情境的,如程玑题诗:“学士何如屐笠轻,爱穿不脱雨和晴。妻孥自解先生意,乳母无知笑里惊。”在这类绘画作品中,画家的观照视角与表现重心,与此前标举文士风度的《东坡笠屐图》存在显著的差异,苏轼形象中“接地气”的一面得到了强化。

图5 〔明〕朱之蕃《东坡笠屐图》轴,纸本设色,92 cm×29 cm,广东省博物馆藏
这种诙谐东坡的视觉形象,也延续到清人的绘画作品当中。清人开始采取一种近于叙事画的图式刻画“东坡笠屐”形象。譬如画家黄慎所绘《苏长公屐笠风雨图》(图6),苏轼面左,体胖,长髯,作冒雨行进之状,神情淡定自若,衣纹以顿挫的草书笔法写就;反观围观的儋州百姓,面对突来的风雨似有些措手不及,纷纷向戴笠着屐的苏轼投来惊异的眼光。画面的整体布局殊有深意,有研究者总结为“特设呼应关系”[32]236-237,即安排一名小童,由图右侧向围观人群奔来看热闹。这种结构暗示画外还有更多的围观百姓络绎不绝地涌来,带来了画外之画的效果,从而将东坡戴笠的偶然之举,扭转为一场意料之外的乡村喜剧。

图 6 〔清〕黄慎《苏长公屐笠风雨图》卷(局部),纸本设色,杭州西泠印社藏
与黄慎生活时代相近的画家马咸,亦有一幅“东坡笠屐”题材的作品传世,现藏天津博物馆。此画纯以人物为中心,东坡戴笠着屐,手持竹杖,神态自若。旁有农夫拍手相笑,邑犬随之而吠;身后引来了一群围观的群众,有孩童笑指,有少妇抱子,有农人下担,脸上都挂着难以置信而又津津有味的夸张表情。苏轼怡然自得的神态,与围观人群看热闹的惊讶表情,构成了微妙的反差与衬应,既传达出层次丰富的情感张力,又注入了令人玩味的幽默意趣。马咸的传世画作不多,据画史记载,凡番舶入市,必购其画以归,足见其画畅销程度之高。马咸对苏轼戴笠形象作通俗化的改塑,或许是受到时兴的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民间题材的影响。不过考其画跋,马咸对东坡本性有着通透的理解:“东坡先生之在儋也,尝访黎氏伯仲,途遇暴雨大作,既霁,假野老笠屐,戴负而归。乡人咸相争笑,先生优哉自得,其天真之乐如此。余尝见王竹君作是图,幽野之趣乃见于笔端,因摹其意而为之。泽山老人马咸。”在画家看来,戴笠着屐这种背离文人传统的古怪行为,正是苏轼“天真之乐”使然,这与晚明陈继儒的观察颇为一致。陈继儒《题东坡笠屐图》云:“无雨无风,戴笠戴屐。此老童心,也消不得。”[30]26画面上饱经风霜的人物形象背后,包裹着一颗充满童趣的心。这种世俗化的艺术变形,也透露出创作者对苏轼幽默特质的认可。
苏轼在其生前就以幽默善谑闻名,时人多云东坡“善嘲谑”[33]191“好戏谑”[34]137或“多雅谑”[35]46。 这种幽默特质在其文学作品中也有丰富多样的显现⑧,即如黄庭坚所言“嬉戏怒骂,皆成文章”[36]557。除了文学创作,超越悲哀的人生观也渗透到苏轼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发展为一种东坡式的幽默范型。这种幽默范型在苏轼生前已是“尤为士大夫所爱”[37]42,其后更是衍生出诸多风趣幽默的逸闻趣事,成为明清戏曲小说改编的重要素材。明清画家演绎戴笠形象的诙谐内涵,大抵受这些机趣幽默的东坡故事影响。不论欢快诙谐的喜剧场景,还是古怪滑稽的神情体态,这些生动喜感的画面表现,在传统的文人肖像画中是极其少见的。在这一意义上,“东坡笠屐”的幽默趣味亦为文士题材绘画注入了新质。
三、小结:从跨媒介的角度考察“东坡笠屐”形象的经典化机制
从“东坡笠屐”本事,到《东坡笠屐图》,再到《东坡笠屐图》题咏,穿梭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苏轼,受到不同性质、不同方法及不同程度的形象塑造。这些不同的形塑方式,正体现出不同媒介之于苏轼形象生成及其意义阐释的不同影响。换言之,“东坡笠屐”的故事,经由不同媒介的呈现与传达,形成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同题作品及其不同的艺术趣味。在前述三种“东坡笠屐”形象的生成路径中,文字与图像所发挥的媒介功能不尽相同,它们之间既存在借用、转换、融通等多重关系,又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媒介竞赛,具体而言:
第一种生成路径最接近历史本事,借助“风雨海上苏”的政治隐喻,还原苏轼贬谪儋州的真实经历,对其戴笠形象作原境式的解读。由于语言文字能够直抵读者心灵,因而对于苏轼形象政治内涵与情感意蕴的阐发,无疑具有媒介优越性。
第二种生成路径致力于将苏轼打造为趋于符号化的文人典范,甚至用“坡仙”称谓予以神圣化提升。在“坡仙”形象的视觉构建当中,文字与图像呈现出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东坡笠屐图》是对文人肖像传统的提炼与升华,而环绕画像的题咏诗文往往宕开画面的具象细节,展开丰富的文学想象和联想,为观者提供广阔的再创造空间。
第三种生成路径通过放大笠屐本事的个别细节,渲染了苏轼戴笠事迹的戏剧性色彩,是基于笠屐本事的合理改编与创造性发挥。对苏轼形象诙谐潜质的发掘,图像媒介以其直观形象的表现特点占据优势,尤其是叙事画图式的引入,更是拓宽了图像表达的艺术空间,增强其表现效果。同时,经由特定的图像机制,苏轼形象还频繁进入版刻插图、石刻拓本,以及笔筒砚背等文房用具,这些通俗化的视觉形式,也更契合于诙谐东坡所隐含的艺术趣味。
在苏轼形象生成演变的过程中,文图之间的裂隙与张力带来了意义的累加与增殖。李军先生在讨论“跨媒介艺术史”时,把这种新意义的获得总结为艺术家的主体性(“艺术意志”)与新媒介的物质性(“艺术潜质”)相互磨合与调适的结果,并指出“这种新意义还会在进一步的媒介转换中辗转流变,甚至回馈给原先的媒介”[38]24。借助图文两种不同媒介表达的苏轼戴笠形象,每当移植到一种新媒介时,就从原有意义中产生新的意义,这种新意义也将回馈并影响到原先的媒介。譬如,回看宋代诗人对苏轼戴笠本事的援用,诸如南宋的李昴英、胡仲弓等人的诗篇⑨,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文学事象的“东坡笠屐”,与元代而后题画诗中的“东坡笠屐”,在意义内涵上确有明显差别。虽然同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但背后却存在着“本事—文学事象”与“本事—图像—文学题咏”两种写作逻辑。这就表明,《东坡笠屐图》的观看经验已悄然作用于诗人的二度创作,即使是回归原先的语言媒介,作为观者的诗人通常无法忽略图像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与直观感受。更进一步,这种题咏传统逐渐固定下来之后,当明清诗人书写“东坡笠屐”之时,哪怕观看《东坡笠屐图》不是直接的创作契机,他们的诗篇也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应苏轼的视觉形象。可见,一种故事或主题在不同媒介间的辗转流变,同时伴随着意义生成衍变的复杂过程。历史本事、文学书写、图像描绘等文化实践之间,并非是从文到图或从画到诗的单方向转译,而存在着相互转化及彼此缠绕的复杂关系,或许可以说是艺术形象的另一种生成史。
由“东坡笠屐”的个案入手,也可以观察艺术创作过程中微妙的“媒介竞争”:文字与图像在苏轼形象的生成及其经典化历程中,分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媒介功能。就诗文而言,当“东坡笠屐”流传于文人笔记和知识性类书时,尚属记述式文字,进入文学书写之后开始注入诗人的自我想象,作为图画题咏时,则在观看的基础上叠加诸多文学技巧,譬如使事用典以实现历史空间的延展、文化内涵的增殖等等。就绘画而言,一方面,无论画家如何精心描摹苏轼形象,符号化的肖像程式难免折损苏轼形象应有的复杂内涵;但另一方面,线条色彩的直感性和形象性,又给予苏轼生动鲜活的视觉生命,拉近后代读者与苏轼在心理上的空间距离。藉由图像媒介的传播,“东坡笠屐”视觉形象的大量复制与广泛流传也成为现实。由此可见,这两种不同的媒介表达,既有其各自的符号形式与技法取向,又存在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在图绘与文学之间,我们可以看到选择与取舍、重释与改塑、契合与背离等多重关系,这固然根植于不同的门类艺术传统,但也折射出不同艺术家各自的“艺术意志”,展现他们不同的观照角度与审美取向。当然,媒介可能被特定时段的文化语境赋予特定意义,在不同的媒介语言背后,其实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交织与碰撞。以“坡仙”风流为主导的图绘与题咏,如元代的吴澄、虞集,清代的翁方纲、朱鹤年等,终极目的在于将自身落实为苏轼的后继者,是士大夫身份趣味的宣示与展陈。而诙谐东坡的形象,更多地受到非精英文化的渗透影响。晚明以降,在各种流行的通俗文化形式中,诸如“东坡戏”、东坡小说、东坡题材工艺等等,苏轼诙谐滑稽的艺术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张宏、黄慎、马咸等画家对苏轼形象的世俗化改塑,归根结底也是这一文化趣味的集中呈现。总的来说,正是在图、文媒介竞争或合作之间,“东坡笠屐”被注入了丰富的形象内涵,而其作为“文化符号”的经典意义随之也获得更为深刻的确认。
① 关于《东坡笠屐图》的研究成果,以Jae-Suk Park (朴载硕)的博士论文最为翔实全面。朴载硕系统调查了大量存世的《东坡笠屐图》,对这一主题绘画的图式规律与艺术特征作详细的分析归纳。梁慧敏的硕士论文《诗人之笠:杜甫和苏轼戴笠肖像史及其文化意蕴——兼论唐宋士人文化精神之异》将苏轼戴笠与杜甫戴笠作了翔实的对比论证,并将二者置于“唐宋转型”的理论框架下,探究苏轼与杜甫个体精神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时代文化因素。朱万章《明清文人为何钟情〈东坡笠屐图〉》和《贬谪与超然:明清时期〈东坡笠屐图〉研究》两篇文章,皆针对《东坡笠屐图》的图式特征及其渊源展开了深入分析。总体来说,在艺术成就之外,《东坡笠屐图》的文本渊源、文学意蕴乃至文化影响,仍留有广阔的讨论空间。详参Jae-Suk Park,“Dongpo in a Humble Hat and Clogs: Rustic Images of Su Shi and the Cult of the Exiled Immortal”,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8。梁慧敏《诗人之笠:杜甫和苏轼戴笠肖像史及其文化意蕴——兼论唐宋士人文化精神之异》(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朱万章《明清文人为何钟情〈东坡笠屐图〉》(《读书》2020年第1期)、《贬谪与超然:明清时期〈东坡笠屐图〉研究》(载王明明主编《大匠之门》第2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8-65页)。
② 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辑有“东坡笠屐”主题绘画近三十幅,除了一件款为元人钱选的作品,其余尽出于明清画家之手。
③ 朱鹤年的临摹对象是翁方纲所藏“东坡笠屐图砚”,其砚背为宋代画家赵孟坚所绘《东坡笠屐图》,据翁方纲考证,赵氏所绘砚背图的粉本即李公麟《东坡笠屐像》。
④ “李白骑鲸”的传说始见于晚唐诗人贯休的《观李翰林真》:“宜哉杜工部,不错道骑鲸。”杜甫诗《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有一本作“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宋人开始将李白骑鲸与其捉月溺亡的传说联系起来,如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云:“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即指李白身死之后,骑着鲸鱼重返天庭。陆游题苏轼画像又云:“惜哉画史未造极,不作散发骑长鲸。”后人或受此启发,以“骑鲸”传说渲染“坡仙”气质。
⑤ “春梦婆”的故事,出自苏轼诗《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此诗以谢鲲戏东邻女之事谐谑符林秀才,末句所云“逢春梦婆”,当是东坡儋耳亲历之事,至于具体所指,历代注家多不能确解。宋人赵令畤《侯鲭录》提供了较完整的一种注解:“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详参(宋)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3页。
⑥ 传钱选《东坡先生笠屐图》,纸本墨笔,私人收藏,载《朵云》1987年第13期。画面题“东坡笠屐”轶事并周紫芝诗,落款“景定三年望赐进士钱选舜举画”。清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另载有“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石久失,有拓本存世,图为东坡戴笠着屐冒雨状,据其跋语,当与《朵云》所载钱选画有所不同。近人蔡莜明摹写的《东坡笠屐图》(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亦有画家题识云:“景定三年望赐进士钱选舜举画。丙寅寒露蔡莜明临绘于露香书屋。”
⑦ 清代陆恢《临张宏东坡先生笠屐图》轴,纸本设色,30 cm×39 cm,系北京东方大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秋季拍卖拍品。画上款识:“壬辰二月写张宏,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吴江陆恢临并录原题。”
⑧ 详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观点:“宋以前的诗,以悲哀为主题,由来已久;而摆脱悲哀,正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使这种摆脱完全成为可能的是苏轼。”见[日]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李庆、骆玉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⑨ 直接援用“东坡笠屐”故实的诗歌作品,有李昴英《题彭昌诗〈下车录〉》、胡仲弓《早行》等。详参(宋)李昴英撰、杨芷华点校《文溪存稿》,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第64页;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