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越南政区的时空分布与变革特征
韩周敬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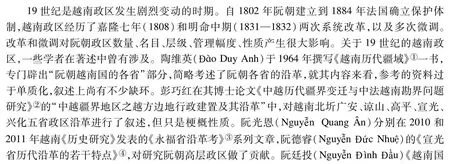


(一) 政区数目历时性演变
1802年阮朝初立时,全国分为中部营镇区、北城地区和嘉定镇地区三部分。中部营镇区以富春京为中心,北有广治、广平2营及乂安、清化内外3镇,南有广德、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7营,南北共12营镇之地。北城地区包含山南上、山南下、山西、京北、海阳、谅山、太原、兴化、安广、高平、宣光11镇之地。嘉定镇地区包含藩镇、镇边、永镇、镇定4营和河仙镇。
嘉隆七年(1808)在中部和南部进行政区改革后,政区面貌也随之变化。至嘉隆十八年(1819),全国共有中部营镇区、北城和嘉定城三部分: 中部包括直隶广德、广治、广南、广平4营,清化、乂安、广义、平定、富安、平和、平顺7镇和清平1道;北城包括山南上、山南下、京北、太原、山西、兴化、宣光、高平、谅山、海阳、安广11镇;嘉定城包括藩安、边和、定祥、永清、河仙5镇。
明命十三年(1832),阮朝完成政区改革,全面建立了省制。因此,以明命二十一年(1840)春正月(1)之所以选本年春正月为限,是因为不少政区是在本年的春二月和三月发生变化的。春二月,如永隆省静边府,于此月改隶河仙省。春三月,如乂安梁山、义棠、甘灵县,系此月新设之县,改隶之府如乂安镇靖、乐边府,县如乂安甘吉、甘门、深源、燕山、梦山县。为限,全国南北共有承天1府及30省之地: 中部直畿区包括广平、广治、乂安、河静、清化、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平顺、庆和11省;北圻地区包括河内、宁平、南定、兴安、海阳、广安、山西、兴化、宣光、北宁、太原、谅山、高平13省;南圻地区包括嘉定、边和、永隆、定祥、安江、河仙6省。
1840年明命去世之后,阮朝疆域发生两大变化。第一,镇西城的丧失。在镇西城刚丧失的绍治七年(1847),高层政区数目和名目还与明命二十一年相同。第二,1862年阮朝将嘉定、边和、定祥3省割予法国;1874年又割让永隆、安江、河仙3省,南圻境土全部丧失。至1883年底,阮朝仍管辖承天1府,以及两圻25省道之地,其中中圻包括清化、乂安、广平、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9省及广治、河静2道;北圻包括河内、宁平、南定、兴安、北宁、太原、山西、兴化、宣光、高平、谅山、海阳、广安12省及美德1道。
在明确高层政区数目后,笔者又对统县、县级政区复杂的新设、合并、析置、拆分、改隶情状进行了详细考证,进而对各级政区数目做了统计(表1)。

表1 1802—1883年阮朝政区数目变动
表1中,1883年各级政区数只包含北圻和中圻辖区。若加上南圻的政区数,其县数超过300个。需要注意的是,县级政区包括县、州、道三类,嘉隆元年(1802)县级政区共238个,其中县188个、州43个、道7个。嘉隆十八年(1819)县级政区共249个,其中县(道)207个、州42个。截至明命二十一年春正月,县级政区共342个,其中县303个、州39个。绍治七年,县级政区319个,其中县281个、州38个。以1883年底为限,县级政区共280个,其中县243个、州37个。
1802—1847年,跨高层政治区、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的数目均有波动。高层政区波动幅度不大,跨高层政治区、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则较大。跨高层政治区在1832年明命改革后消亡,所以表1中在1840年后跨高层政治区均为0。统县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化是一体的,如果只看以全域为统计对象的1802—1847年,可知在这40余年间,统县政区增长近两倍,县级政区增长约三分之一。
统县政区数目的增长,是由县级政区数目增长直接推动的。县级政区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三,即人口生息与位移、境域新辟与整合、政区析置与升格;后两种因素对县数增加的影响更大。境域新辟与整合方面,主要有1827年和1835年两个节点。1827年万象为暹罗攻破,原先由嘉隆赠予万象的乂安西部镇宁等府重归版图,置乐边、镇宁、镇靖、镇定、镇边五羁縻府,受此影响,甘露地区的纳贡部落也归附朝廷。1835年春,阮朝在东高绵地区建立镇西城,由安江省管辖,至1840年时镇西城共辖10府23县之地。这两个节点发生的事件,直接推动了县数的小幅跃升。政区析置和升格方面,1840年以前,阮朝新置的县约有50个。
总的来看,阮朝各级政区的总数,在明命二十一年达到顶峰。随着明命帝离世,后继者绍治帝经略政策趋于保守,镇西城境域日渐缩减,其地所设府县也重归高绵之手,这导致阮朝县级政区数目下降不少。直到1884年法属时期,虽还有新县设置,在总数上再未回到1840年的水平。
(二) 政区共时性分布演变
上文考察了阮朝政区的历时性演变,下面仍以1802、1819、1840、1847、1883五年为基准,来考察阮朝政区的共时性分布情况。由于阮朝国土分为北、中、南三大区块,笔者对各个区块内的政区数目进行了详细统计,参见表2。

表2 1802—1883年分区政区数目变动
由表2可知,1802—1883年,尽管在高层政区和统县政区数目上,北部与中部地区相差不大,但在县级政区上,除1840年外,北部地区数目始终多于中部和南部总和,这种差异在1802年最为悬殊: 1802年北部县级政区数量为153个,而同期中、南部相加才85个,北部政区要比中、南部的总和还要多近一倍,此后随着中、南部县级政区不断新设,这个差距有所缩小。1840年,中部加南部县级政区数之所以超过北部,是因为阮朝占领了高绵东部地区,将之纳入了经制体系。不过,尽管疆域外拓导致政区增多,此时南、中部县数总和仍只略多于北方。随着1847年阮朝从高绵撤军,这些县级政区也被取消,中、南部县级政区之和再次不及北部。由此可知,1802—1883年在三大区块内,北部政区数目占绝对优势,且北部多于中部,中部又多于南部。
此时期政区管理幅度变化也不小。这5个基准年中,高层政区所辖统县政区的平均数依次为2.03、2.10、3.77、3.54、3.03个,统县政区所辖县级政区的平均数量分别为4.07、4.22、2.83、2.90、3.58个。在实际设置中,阮朝府的辖县数量一般为2—3个,明命曾言:“府之所统者三四县或五六县,其地广则其路远,巡防之势难周。”(2)〔越南·阮〕 国史馆: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五四,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6年版,第10页。对超过3个辖县的情况,阮朝的解决办法是设置分府和析置新府,以使每府辖县数量重新接近均衡数。
增加新府会导致政区密度加大。从省际比较来看,管辖政区数量最多的省,其政区密度未必最大。如1840年乂安省设有31县,其政区密度其实小于设15县的河内省。但在境域不变的前提下,政区密度加大,必然意味着政区数目增加。随政区密度增大而来的,是政区定位的清晰化和职能的完善化,这又使政区圈层愈加细致和规整。在阮朝政区数目增加过程中,除了京畿直辖区面貌基本不变外,其他政区圈层都有变化: 经制区范围有所扩展,间接行政区表现出越来越浓的越化特征,而藩属国地区也历经升格与降维的反复。
随着政区密度增加,高地和低地政区数量对比失衡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缓解。越南很多省份都沿山兼海,无法严格区分何者为高地省、何者为低地省,往往是每个省甚或每个府县,都是将政治经济中心设在低地,同时保有对高地的控制权,低地政府通过对高地的开发和人口管理,加强不同海拔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为既有政区的细化和政区的新置奠定了基础。虽然由此而设县的情况不多见,主要是“总”(3)总即“总合”之意,每总通常下辖五至九个社不等,是一级介于县和社(相当于今日之行政村)之间的区域,是古代越南独有的基层组织,相当于今日的乡镇。总主要设置于阮朝北部地区,以1889年为例,本年北部十三省共有1 178总,其中海阳省187总、山西省176总、北宁省162总、南定省140总、河内省127总,共792总,占比67%;其余八省辖“总”数目俱在100以下,最少的广安省只有寥寥18个。等基层区域的建立;但由于它们也受低地管辖,因而可以看做低地政区管理幅员有所扩大。也要看到,阮朝的统治仍有明显局限性,粗略统计,设在低地地区的县级政区治所占总数比重仍在70%以上,这表明阮朝对高地地区的控制仍然乏力,这种情况至1884年法国殖民者大力经理高地后才开始改变。
二、 19世纪越南政区的变革特征



(一) 嘉隆七年政区变革特征
嘉隆七年在中部广德营以南和南方嘉定地区的政区改革,是阮朝初期深化统治力度、扩大管理幅度的重要举措。阮朝初立,山河初安,内乱未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1802—1808)嘉隆保持了三国时期“营”的建制,以军管区代替政区。这符合当时实际,既能保证社会资源的整合,又能避免政区升格与降维过程中生发种种问题。但到嘉隆七年,内乱基本肃清,阮朝实力亦已坚固,军管区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军管区的掌奇、该队(4)“奇”和“队”是越南阮朝的军事单位,每奇辖500人,长官称为“掌奇”;每奇分为10队,每队辖50人,队长称为“该队”。“该”(越南语: cai)即“管制”之意。等官驻屯一方,对当地各种资源都有调配权力。长此以往,轻则扰乱民政,弊蠹一方;重则或有拥兵兴叛之举。其各项制度也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和国力增长。凡此种种,表明军管区已成为阮朝集权之障碍,需要加以改革。嘉隆改革体现在政区结构上,主要包括改镇为城、撤营建镇、设直隶营、升县(州)为府、升总为县、空地置总六个方面。
改镇为城与撤营建镇,即将嘉定地区的跨高层政治区与高层政区升格至与北城同级。在嘉隆七年改革前,嘉定是以“镇”的名义,统辖藩镇、镇边、镇定、永镇4营与河仙1镇之地。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中部和南部等地的“营”,在政区层级上属于高层政区,与北城下属的内5、外6镇以及中部7镇1道,在层级上是平等的,但彼名为“镇”,此名为“营”;在中部和南部各自区域内,高层政区既名“营”,又名“镇”。这种通名互异的情状是黎中兴时期郑阮对峙的遗留,带有分裂色彩,不利于王朝一统观念的塑造。第二,不唯高层政区通名互异,跨高层政治区亦是如此。嘉定镇虽名为“镇”,但在政区层级上与名为“城”的北城又是平等的。如果仍以“镇”称,或误认为与北城辖下之“镇”同义。因实予名,是政区改革应有之义,因而嘉隆七年将嘉定由“镇”改为“城”,同时将辖下之“营”改为“镇”,遵循了向北城地区看齐的规整化路径。
升县(州)为府、升总为县和空地置总,与改镇为城、撤营建镇同步进行。这体现了此次改革的整体性,以及中央权力下行的努力。如果说中部广德营以南地区和南方嘉定地区跨高层政治区、高层政区通名都比北城实际对应政区低一级,其统县政区、县级政区和基层政区则不同。在嘉定地区,“营”以下未设府;而县级政区和基层政区与北城情况一样,县级政区亦为县或州,基层政区亦为总。因而,以北城为样本进行改革,首要是要加入统县政区这一级别,阮朝对此采取的做法不是设置新府,而是升县为府。这一举动引起了链式反应: 县在被升为府之后,原有县级政区消失,为了填补政区缺环,又升总为县。对此,《大南实录》有集中记载:
(改)藩安新平县为新平府,平阳总为平阳县,新隆总为新隆县,福禄总为福禄县,平顺总为顺安县。边和福隆县为福隆府,新政总为福正县,平安总为平安县,隆城总为隆城县,福安总为福安县。永清定远州为定远府,平安总为永安县,平阳总为永平县,新安总为新安县。定祥建安县为建安府,建登总为建登县,建兴总为建兴县,建和总为建和县。(5)〔越南·阮〕 国史馆: 《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三四,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第1页。
升总为县的同时,又在县域之中重新疆理,在空白区域中补置了许多总。“总”属于基层范畴,在政区序列中隶属于县,其下管辖数目不等的社、村、坊等聚落单位,起着以皇权为代表的县以上政区和以乡豪为代表的村落力量间的沟通渠道作用。“总”数的增多,分布密度的增大,是对阮初薄弱的地方控制能力的补充。
设直隶营,即把广平、广治、广德、广南四营加以“直隶”之名。此四营之前已有直隶之实,这次改革时只是因实予名。直隶四营的划定,具有三点意义。第一,在地理环境上,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控制了完整的地理单元。直隶四营北界横山,南界海云山,此二山是阮朝的天险之地。第二,在政区圈层明确了阮初中央直辖区的范围,从而使阮朝政区“中心—边缘”的特点更为显明,构建出政区上的差序格局。第三,直辖区的设置,兼顾了低地与高地,对于台地地区“源”以及上游地区诸蛮的控制力度都有所加深。
嘉隆年间撤营建镇的尝试,实际上是促进阮朝区划由军管区向行政区转变之举。与镇边等营的纯粹军事性质不同,镇的长官为总镇、协总镇和副总镇,其下则有该薄、记录、府丞等,其职能除了军事征战外,还要监理民事。镇下所辖之县,县治一般都集中在镇涖所,而不在诸县分辖之地别设治所。嘉隆十二年(1813),县衙开始陆续在各地兴设,知县及其属吏也正式派任,但“府衙则省减之,其事权都归镇官钤管”,可知其政区结构虽有变化,但行政序列并无大动。府衙的省减、以镇官直接管理县级政区、县涖所的集中布局,都显示出嘉隆帝的集权决心,也表露了其隐收权力的政治策略。
嘉隆帝在撤营建镇的同时,还进行了“以县为府,以总为县”和“又增总名,各立界限”(6)戴可来、杨保筠校注: 《〈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的政区圈层调适。这种调适的结果是府、县、总数目增多,辖域缩小。这不但对地方释权有效用,对行政效率提升也有助益。此外,嘉隆七年的政区改革实践,也为明命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即通过对纵向政区层级的调整来影响横向政区空间,再以政区空间调整来对行政序列进行规范,进而收取中央集权之效。这要求政区制度和职官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其后明命改革也正是遵循了这一思路。
(二) 明命中期政区变革特征
如果说战时区划在国家建立之初有安定作用,那么随着内乱勘定,国家日益升平,它便不再适合当局需要,也与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龃龉。因此,明命年间阮朝顺应形势,进行了大规模撤镇建省的区划改革。明命政区改革,主要集中在十二年(1831)至十三年施行,虽然在明命十五年(1834)南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叛乱,但在改革当时,政区改革进程是较为顺利的。此后,明命帝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加精密的调整。明命政区改革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区名目改革。不但涉及改“县”为“府”、改“镇”为“省”的通名变化,还包含许多专名更动。在名称变动过程中,还附有政区数目增删。
第二,政区层级和性质改革,即罢除城级政区、撤镇建省。在城辖时期,阮朝地方政区有城—镇—府—县四级之多,设省之后,城级政区被废除,只余三级,节省了行政资源,提高了行政效率。城、镇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改设省后,职官设置分缺控官、各有专司、分权制衡,行政和军事体制分离,政区的军事性淡除。省的设置,是中央加强地方控制的体现,基本解决了权力集中、吏员冗杂、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问题,瓦解了“京—城”政区区块结构,使得中央权力空前加强。
第三,政区边界改革。罢除城级、改镇为省这种重大的层级变更,必然涉及重划省域的问题。基于嘉隆时增多数目和简化层级的政区改革理念,明命时进一步对原依山川形势划定镇界进行解构和重建,具体包括大镇分割、势镇共险、边镇碎化、镇域重构四个方面。首先,大镇分割,即将境域广袤之镇加以分割,肢解为数省或从中析出某省。如藩安省最初占地广阔,将其中一部分割出,隶于永隆省。其次,势镇共险,即对某镇的山川界限进行调整,使两个或多个省共同占有险关,以收化险为夷之效。以定祥镇和藩安镇为例,此二镇之间原以前江为界,但改营为镇后将美湫市和丐比县以及二地南边的前江江段划归定祥镇,丐礼县、鹅贡市及其相邻之江段划入藩安镇,四地之间正好插花分布,可收弱支互制之效。再次,边镇碎化,即由于边镇距离中央较远,不易控制,因此将其打小,便于掌御。最后,镇域重构,即将镇内的府县进行合并和裁分,或进行镇际分划。
明命帝的政区改革是其整体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从不同维度和侧面来加强中央集权,以扭转自嘉隆时期就存在的地方分权偏重之局。伴随政区改革而来的是行政制度的变化。首先,系统建立了兼理、统辖、并摄、兼摄、兼署制度。这使各级政区能有效管控辖区,节省行政资源,透露出阮朝集权能力的强化。其次,仿效中国清朝的做法,建立了“冲繁疲难”四缺任官体制。四缺法的施行,打破了原有的官吏选任方式和权力分配格局。从凭借经验的失序任官,发展到简单的大小县,再到复杂的冲、繁、疲、难制度,说明阮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区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控制越来越严。可以说,明命年间的改革,是纵贯式、全景式的改革,其力度也是嘉隆改革所难以比拟的。
总的来说,明命推行的政区改革措施,是为实现中央权力下行而铺路。行省制的推行和省—府—县实三级制的确立,一方面是对原有地方政区军事性的化约,另一方面除了强化中央、地方之间分寄与达权的控制关系外,还理顺了地方政区的层属和交叉制衡关系,使行政序列和秩序规整化。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触动当地武人和豪族的既得利益,进而引起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种矛盾在阮朝南部地区最为突出,正如基斯·泰勒(Keith W. Tylor)所指: 明命改革的推行过程,在南方要比北方坎坷(7)Keith W. Tylor, A History of Vietnam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18.。
阮朝初期南、中、北三部地区在政区地位上的差异耐人寻味。与属于京畿直辖区的中部、受儒家忠君思想深浸的北部地区相比,南方地区相对独立(8)Choi Byung Wook,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Reign of Minh Mang(1820-1841): Central Policies and Local Respon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5.,这种反差实际上是当地风土、政情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地理圈层来看,南方处于阮朝政区地理圈层的外围,又具有复杂的民情。而在结构圈层上,南方属于经制区域,又处于政区圈层的内围。这种处于地理圈层外围和结构圈层内围的矛盾,导致南方地区在朝廷视野中具有一定特殊性,需要统治者有针对性施政。讲求针对性不意味着妥协和退让,而是战略性中和。嘉隆和明命前期通过重臣镇守,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南方的地情和人情,在政区设置上讲求“人地相宜”(9)“人地相宜”是阮朝政府在政区设置时的重要原则,它体现了对地情、政情和民情的尊重与利用,嗣德帝曾言:“官方澄叙,而在职无冗员;人地相宜,而在民无烦扰,可以行之无弊矣。”参见〔越南·阮〕 国史馆: 《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四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7年版,第15页。,不进行过多和过细的干预,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南方地区的圈层矛盾。在黎文悦主政南方时期,虽然具有分离主义倾向,但并未在明面上与中央分庭抗礼,这固然是黎文悦对嘉隆帝的个人情义所致,但更重要是得益于嘉隆实行的差异化统治策略。
明命前期延续了嘉隆时期的策略,但明命改革时推行的政区改革政策,逐步放弃了差异化的治理方式,而是讲求整齐划一,试图促成南方经制区地位的实化。实化的方式,是将从农业地区生发出来的威权体制硬性加诸南方这一新开辟、多民族、军事性及商业风气更为浓厚的地域之上。从《大南实录》的记载来看,当时朝廷对南方的复杂性是有认知的,明命在南方开始改革晚于北方一年,似乎也表明明命在寻求一种适合南方的节奏。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紧迫性,可能使明命有意无意忽视了南方的复杂形势。南、北方风土人情差异很大,要近乎同时推进相同程度和性质的改革,出现混乱不足为奇,最终激起黎文傀的大举叛乱。因此,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认为黎文傀叛乱事件是明命帝“制造”出来的(10)克里斯托佛·高夏著,谭天译: 《越南: 世界史的失语者》,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8年版,第109页。,有一定道理。
黎文傀叛乱波及范围广、牵涉人员杂,并一度取得辉煌战果。它爆发于藩安,迅速蔓延至六省全域,受其扰动而出现的流民、乱兵北向波及平顺,西向搅动高绵,交好已久的暹罗也趁机派兵前来掠地,阮朝西疆乱局就此开启。正是在平定黎文傀之乱的过程中,阮朝一方面更加清晰认识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暹罗,将藩属国高绵纳入经略视野。在平乱后期,藉由高绵国王去世的时机,明命不再视高绵为藩属国,而是纳入经制区直接统治,将高绵和越南南圻通盘考虑,进行了一系列政区改革。南圻的秩序最终得以维持。但高绵的改革收效甚微,以恢复藩属地位而告终。
(三) 明命以后的政区变革特征
明命改革的完成,为此后阮朝政区定立了成式,它所构建的政区格局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南部20余年,北部和中部40余年)保持稳定状态。嗣德(1848—1883)中后期内乱频仍,为了剿匪安蛮进行了一些非常措置,如设置山防衙门、建立新“道”(如美德道),但这些措施或是对原有体系中某种功能的突出化,或是对体系内部要素进行的有限调整,明命所确立的主体政区格局基本稳固不移。在当时蛮匪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有大臣提出在沿边废流还土,允许土司世袭,对其辖地量征赋税。嗣德君臣对此意见不一,尤其是对于土司世袭问题,最后交廷臣讨论无疾而终(11)〔越南·阮〕 国史馆: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五,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第7—8页。。这一方面是由于嗣德一朝多谋少断,另一方面则是明命遗留的框架制约性太强的缘故。
直到法国人到来,在南部确立殖民体制,在中部和北部确立保护体制,明命所确立的政区格局才开始变化。1884年《甲申和约》最初签订时,法国人在越南北部和中部面临不少困难,最主要是阮朝官员和文绅不合作,且法人因税收和信仰等问题致使民情汹涌。前者触发了勤王运动,因后者而扩大,导致时局混乱、平教相仇,“有以勤王为名,有以平西为事”(12)〔越南·阮〕 国史馆: 《大南实录正编第五纪》卷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第32页。,法国不得不动用大量精力和物力稳定动荡局势。在此之前,由于财政预算限制,法国人将精力集中在港口和商政方面;平乱过程中,他们通过在中部和北部所有省城驻军、设置各种层级和性质的政区、勘测和弹压边界地区,实现了权威的下行和权力的细化。

结 语
通过选取越南阮朝的1802、1819、1840、1847、1883五个基准年代,考察各个年代的政区空间分布和不同年代间的政区空间演变。从共时性来看,阮朝北部政区数量多于中部和南部;从历时性来看,阮朝高层政区数目最为稳定,统县和县级政区数目前后起伏较大,各级政区数目至1840年达到巅峰。在管理幅度上,高层政区平均管辖约3个统县政区,统县政区平均管辖约3个县级政区。随着时间的推移,阮朝政区密度也在不断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低地对高地控制的强化。而从阮初至法属时期,由于时势的变异,导致各个时代的政区变革具有不同的特征: 嘉隆时期主要是促成了政区军事性的淡除,明命时期主要引进了清朝的省制,明命以后主要是在继承基本政区格局的前提下,进行修补式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