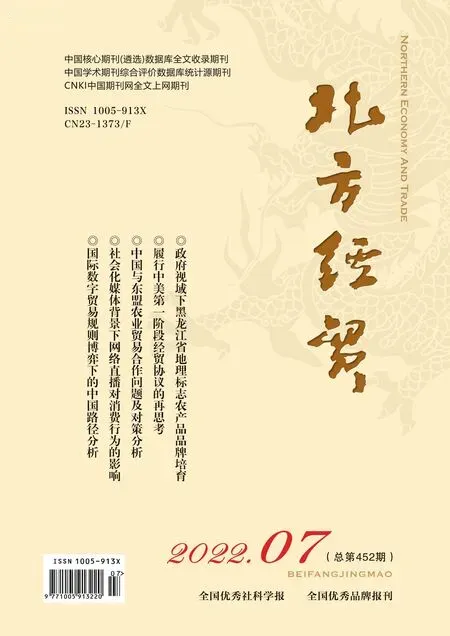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下的中国路径分析
郭力宁,杜志英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郑州 450046)
一、引言
数字贸易的出现是当前以及未来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除了传统货物外,对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增多,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大大提高服务的贸易性。另一方面,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各国相继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严重打击了实物交付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这时数字贸易的虚拟性和无接触性就发挥出巨大优势。根据UNCTAD 的统计数据,2020 年全球可交付数字服务的规模为31675.9 亿美元,虽然与上年相比下降了1.78%,但是相比商品贸易下降了7.36%,依然可以看出数字贸易在维持全球贸易上的重要作用,而且可交付数字服务贸易占整个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经达到63.6%,比上年提高了11.8%,进一步说明了在疫情冲击而全球贸易受阻的情况下,数字贸易正在加速发展,而且潜力巨大。
一种新经济模式必须要依靠恰当、完善的规则制度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当国际贸易方式发生巨变时,就必须对以前的经贸规则进行变革与创新以适应数字贸易的发展。但是,数字贸易的发展需要依托于数字技术,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大不相同,所以在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上,各国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另外,数字技术的网络性和虚拟性等特征,使得数字贸易涉及的范围十分之广,除了经济外还牵涉了主权、安全和道德等多个敏感话题,进一步加大了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难度,导致了各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博弈。
二、数字贸易的内涵
(一)数字贸易的概念
“数字贸易”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2013 年发布的《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1》中将其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交付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活动”,此定义的范围过于狭隘。随后,USITC 在2014 年和2017 年又分别对数字贸易的内涵进行了扩充,最终在2017 年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1:市场机遇和主要贸易限制》中,将数字贸易定义为“任何行业部门的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相关产品,如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传感器。虽然它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和相关服务的提供,但它不包括在线订购的实体商品的销售价值,以及具有数字对应物的实体商品(如书籍、电影、音乐和在cd 或dvd 上销售的软件)的销售价值”。此定义与美国2013 年第一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相比,增加了电子平台等新型经济模式,但是把电子商务中的跨境货物贸易排除在了数字贸易之外。欧盟与美国相似,在2015 年《数字单一市场》中将数字贸易定义为“利用数字技术向个人和企业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和日本在定义数字贸易概念时,将电子商务也包含在其中。日本在2018 年《通商白皮书中》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买卖的商品,以及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的服务”。中国在2019 年《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中将数字贸易定义为“信息通信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形式”。两者相比美国和欧盟对数字贸易范围的界定要广泛得多。
除主要国家在积极部署数字贸易发展外,WTO等国际组织也在尽快调整贸易规则以适应数字贸易的发展。2020 年OECD、WTO 和IMF 联合发布《关于衡量数字贸易的手册》,对数字贸易的内涵和测算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数字贸易大致可以分为数字订购贸易、数字交付贸易和数字中介平台贸易。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依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对数字贸易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例如,中国在电子商务上拥有巨大优势,所以中国将电子商务包含在了数字贸易的框架之内,而美国正好与之相反。为了下文尽可能客观地对各国数字贸易的规则进行分析,本文采用认可度较广的OECD-WTO-IMF关于数字贸易的定义。
(二)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区别
从国际贸易的主体来看,数字贸易将中小企业和个人融入了国际贸易的范畴。过去由于国际贸易的巨大交易成本,使得国际贸易一般由大型的跨国公司进行。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中介平台的发展,交易前的信息成本、交易中的沟通成本和交易后的履约成本大大下降,拓宽了国际贸易的主体范围。
从国际贸易的对象来看,数字贸易拓宽了交易对象的种类。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增加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例如近几年发展迅速的云旅游等。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数字产业,随着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以软件、数据等为交易对象的国际贸易也开始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交易对象的范围。
从国际贸易的交付模式看,一方面数字贸易开始由传统的实物交付向数字交付转变。除数字产品本身就依靠数字技术传输、应用外,服务业也开始出现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形式。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也使得部分货物贸易可以数字化并进行交付。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开始由传统的中间商模式向数字中介平台的模式转变。数字中介平台作为一个虚拟的市场,可以使国际贸易中的供给双方直接联系,解决了之前国际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三、主要国家的数字贸易规则
不同国家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对数字贸易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相应的数字贸易规则。由于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大不相同,所以在数字贸易的部分条款上存在矛盾。本部分主要从数字税、数据流动和知识产权的角度并结合具体条例介绍各美欧日中的数字贸易规则。
(一)美国的数字贸易规则
无论是数字贸易规模还是规则的完善程度,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美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更加强调自由化和便利化。在税收方面,美国是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最早倡导者,出于对美国数字服务商龙头企业的重视和美国在数字服务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不仅坚持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而且强调对经电子传输的内容免征关税。在美墨加协定(USMCA)中提出“任何一方不得对以电子方式传输的数字产品的进口或出口征收关税或其他费用”。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由于美国的数字龙头企业对数据的巨大需求,因此美国倡导数据跨境完全自由流动。在USMCA 中提出“任何一方不得禁止或限制通过电子方式跨界传输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由于美国是知识产权的输出国,所以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美国高度重视的关键议题,其主张对知识产权进行严格保护,主要体现在计算机设施本地化和源代码公开等方面,坚决反对将计算机设施本地化和源代码公开作为在东道国开展业务的条件。
(二)欧盟的数字贸易规则
欧盟作为数字贸易领域的另一重要力量,与美国相比,政策倾向相对保守。在税收方面,欧盟认同当前时期对电子通信免征关税,但是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免征关税和美国提出的永久性免关税的条款存在异议;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由于本土价值观的影响,欧盟极其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比较典型的是2016 年发布的保护数据隐私的高标准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以尽管欧盟也允许数据跨境流动,但是自由流动必须要在个人隐私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欧盟作为知识产权强国,也坚持主张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日本的数字贸易规则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之一,也很早就注重数字贸易的发展,日本的数字贸易政策与美国相似,都推崇宽松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税收方面,日本与美国一样主张对电子传输和传输内容免征关税,以便利数字产品跨境流动;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日本与美国略有不同,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发展与进步协定(CPTPP)中主张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但是也承认各国在电子传输信息上有自己的监管要求;在知识产权方面,日本科技发达,也坚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国际上与别国不存在明显的敌对关系,加之日本本国的资源较少,所以在产品和服务贸易上相比美国来说会更加自由。总体来说,日本推行的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程度相对于美国来说甚至更高。
(四)中国的数字贸易规则
我国是电子商务大国,所以我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比较偏向于贸易便利化等措施,对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等方面谈论较多。其次随着我国数字产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为了禁止反竞争的行为,在2020 年签订的RCEP中,将“竞争”作为单独的一章。而在国际上争议性较大的议题,如税收问题、数据跨境流动和知识产权保护,由于中国目前的技术和监管水平还相对落后,所以尽管中国积极地向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靠近,也主张减免数字税和保护知识产权,但还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
总体来说,在对数字产品征税问题上,各国之间的矛盾相对较小,尽管对数字产品免关税现在不利于中国,但是通过这项条款,也可以倒逼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使中国加快向高标准贸易体系靠近;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尽管都提倡数据自由流动,但是欧盟、日本和中国都对其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尤其是欧盟,对其限制更大,这也是欧盟与美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的主要矛盾;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各个国家的矛盾也较小,都主张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尽力实现高标准规则。从以上可以看出,尽管还有部分争议条款,但是随着数字技术和监管水平的提高,数字贸易规则的未来趋势一定是自由化,我国部署数字贸易的发展也需要逐渐向自由化靠近。

表1 美欧日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倾向
四、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方向
从本文第三部分对各国数字贸易的政策分析可知,各国都在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制定数字贸易政策并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进行推广,尽管大部分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和,但是也有无法协调的矛盾。为了保证我国数字贸易的良性健康发展,本部分将在上述对各国数字贸易政策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数字贸易提出一定的建议。
(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数字贸易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个方面都还不成熟,我国要想在数字贸易的潮流中把握先发优势,就必须加强数字贸易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二是数字贸易测度框架的构建。我国在电子商务上具有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国际上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还存在争议时,我国一定要基于本国国情并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数字贸易的内涵提出自己的认识。在数字贸易测度上,我国应积极构建本国的测度框架,并优先在上海等自贸区进行实验推广,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参考。当然,无论是在数字贸易内涵还是测度方法的研究上,除符合国家利益外,还必须兼顾国际标准,以便增强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贸易是依靠数字技术兴起的,为了获得数字贸易的领先地位,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要先行一步。在建设“铁—公—机”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要兼顾“云—网—端”等新型基础设施,重点加强对5G、物流网、区块链等设施的投入研究,重点关注国内和国际的数字鸿沟问题,扩大数字化服务的覆盖范围。其次,我国应加快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完善跨境电子支付体系,推动建立覆盖全球的网络支付结算体系。
(三)促进产业升级
数字贸易时代,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大幅提高,国际贸易开始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技术为基础,加快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提高我国的产业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数据的虚拟性和可复制性,使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数字贸易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不能再走以前的模仿———创造的道路,应该加快创新,从根本上倒逼产业升级。
(四)完善法律法规
国内的法律法规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谈判的基础,是一个国家输出话语权的载体,所以完善本国数字贸易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参考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争议,我国也应重点关注数字税、个人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尽管中国现在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但是相关的法律条文仍需要明确,相关的配套法律仍需要相继出台,其中还要重点关注电子商务规则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关系,数字贸易规则与其他相关配套措施的关系。其次,在法律制定的同时,要注意与国际公约相结合,以便促进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贸易谈判。
(五)加强国际贸易谈判
数字贸易规则最终要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一个统一框架,当部分数字贸易条款还存在争议时,各主权国家就会积极地推行本国的数字贸易规则,以期获得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这时自由贸易协定成为规则推广的重要载体。我国为了防止西方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上对本国利益的侵害,也为了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应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谈判,与别国在协调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深度合作。多边层面,我国应积极向WTO 等国际组织提交提案,助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区域层面,我国应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双边层面,中国应以中韩FTA 和中澳FTA 为基础,积极与周边国家、经济规模相近国家进行谈判,求同存异,达成共识。除此以外,也可以借助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势地位,积极开展非官方的合作谈判,如阿里巴巴提出的e-WTP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