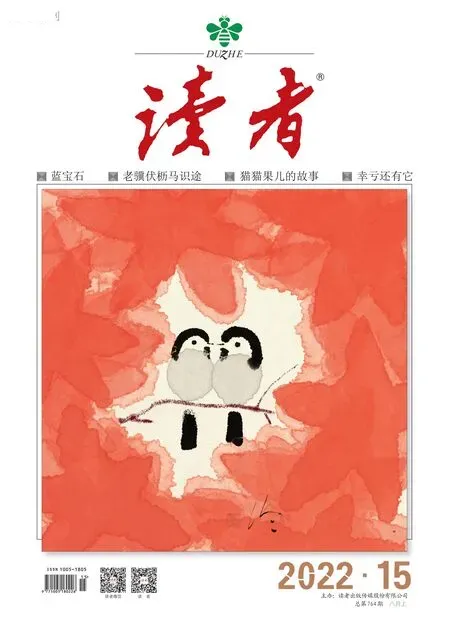不留遗憾的告别
☉尚 书
我小时候,爸妈特别忙,一到寒假我就被扔在姥姥家。姥姥知道我喜欢下象棋,就拉着我,让我教她下棋。她都70多岁了,耳朵还背,我几乎是用嘶吼的方式完成教学的。
她不但耳朵背,还眼神不好,经常拿我的炮当她的车,“啪”,砸得特别使劲,喊得也很有气势:“将军!”就她那技术,她一回都没赢过我,但没事还总拉着我:“来啊,杀一盘啊。”
同样眼神不好的还有我姥爷。姥爷更逗,每当家里就剩我们俩的时候,他就凑过来说:“你可有口福了,我给你露一手啊。”然后过了一会儿,给我端过来一碗面。
其实姥爷不会做饭,但是他不舍得让我饿着,就在芝麻酱里放了很多盐,然后用芝麻酱拌面条,美其名曰“麻酱面”。说实话,他做的麻酱面是真咸,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它怎么这么香啊,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
打那以后,我每次去姥爷家,都要吃姥爷做的麻酱面。姥爷每次都坐在我旁边,乐呵呵地看着我把面吃得一干二净。
就是这碗从小吃到大的麻酱面,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了——一个多月前,姥爷在他90岁生日的那一天走了。
姥爷走的当天,我还算比较平静。可晚上吃饭上调料的时候,看到有人端上一碗麻酱,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原来,味觉承载的不仅是食物,更是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尤其是对亲人的记忆。那碗麻酱面对于我来说,是姥爷,更是关于姥爷的一切。

就像歌手毛不易写的一首歌——《一荤一素》。歌的名字和食物有关,歌词全篇没有一处提到“母亲”这个词,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母亲。
歌手的母亲是因为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所以吃不进去东西,即便吃了也会吐出来,但她还是努力地活着。因为她的孩子还没有成家,她放心不下。她临死之前还惦记着儿子的每一顿饭应该是一荤一素的搭配。她说:“如果我走了,谁来照顾他?”
歌手把对母亲的这种遗憾写进了歌词中:“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地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她有没有哭……”
这首歌的评论区有很多条留言,每一条都是关于亲人离世后大大小小的遗憾。有人悔恨地说,自己总是打断母亲的叮嘱,对她总是不耐烦。有人说,自己有一个素食主义的奶奶,她却总是给自己做一整盘肉,而自己从来没跟奶奶说一声“谢谢”。甚至有人写道:“爸,我不怕鬼了,您能来梦里看看我吗?”
其实对姥爷,我没有什么遗憾。但对姥姥,我是有遗憾的。
那时我还小,姥姥得了肺癌,病重住院了。爸妈带着我去医院看望姥姥的时候,我对姥姥的病情没有概念,走到已经昏迷的姥姥床前,摇晃着她说:“来啊,杀一盘啊。”但是这一次,姥姥没有回应我。
那一瞬间,我才知道,以后的寒暑假里,再也没有人陪我下象棋了。我当时就想,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让姥姥认认真真地赢我一回呢。
姥姥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下过象棋,但是我多了另一个习惯,就是到墓地陪姥姥聊天。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只要遇到大事,我就会去跟姥姥商量。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车很少,但是红绿灯很多,它们就是我跟姥姥之间的暗号。如果姥姥觉得这件事我做得对,她认可,她同意,她让我遇到的就会是绿灯;反之就是红灯。
也许就是这一个又一个的红绿灯,弥补了我曾经因为姥姥的离世而留下的遗憾,也让我可以更坦然地面对与亲人的离别。
童年的时候,妈妈的呼噜声让我备受折磨。我妈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那种。一到晚上,我妈那撼天震地的呼噜声就让我无处可逃。我就感觉一会儿是一支战斗机编队飞过,一会儿可能是一列鸣着笛的火车呼啸而过,一会儿又像在播放一部非常激烈的战争片,然后打着打着就没动静了,好像悬疑片一样。
那时候我不知道,未来有一天我会那么期待听到妈妈的呼噜声。
那是一个周一的早上,“三高”缠身的妈妈突发脑血栓。我们分秒必争地抢救,终于把我妈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溶栓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躺在我妈旁边的陪护床上。由于水肿还没消除,所以我妈的病情还在加重,她睁不开眼睛,也不能说话。
作为医生,我从我妈发病那一刻开始保持镇定。在救治的整个过程当中,我有20多个可能犯的错误,每一个错误都能要了妈妈的命,但是我一个都没犯。即便镇定如此,我内心还是十分害怕。整个过程我一直在祈祷:“瘫不瘫无所谓,给我妈留口气,以后我好好孝顺她。”
深夜的病房特别安静,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呼噜声。这不就是我那个胖妈妈的呼噜声吗?我之前从未觉得,打呼噜的声音原来这么好听。
那是已经不能说话的妈妈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儿子,妈没事。”
在做医生的头10年,我在肿瘤科经历了2000多个患者的死亡。每一次,毫无例外地,患者的亲属都痛不欲生——他们没有准备好面对与家人的离别,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自责和悔恨。
因为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来不及做的事,所以我想帮助他们减少遗憾。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个医学人文项目,这个项目叫“生死教育”。
就像我知道,我妈终有一天会离开我,我们身边的人也会一个一个地离开我们。但我更清楚,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我们的家也不会因为家人的离去而不复存在。
因为只要我还在,只要我对他们的爱还在,那么这个家就一定在。对此,我深信不疑。
有一年清明节,我带着三岁半的儿子去墓地看姥姥。我问儿子:“如果有一天爸爸死了,你会害怕吗?”儿子说:“不会啊。我也会开着车去给你送花,陪你聊聊天。”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