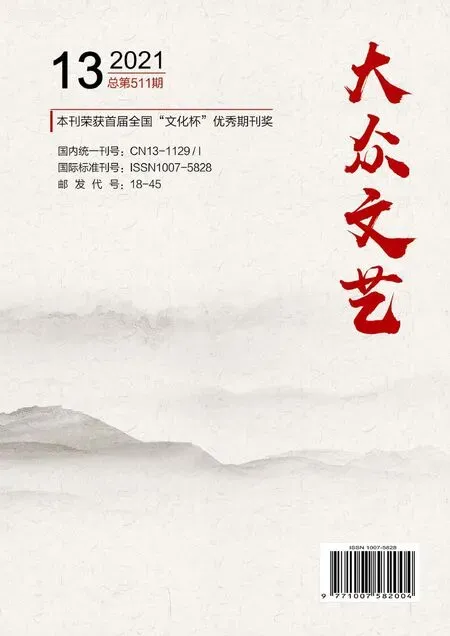创伤理论视角下《阿甘正传》中丹泰勒的创伤解读
谢明霓 李凤萍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300)
一、引言
《阿甘正传》的作者温斯顿·格鲁姆(Winston Groom)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由于在大学中的文学编辑经历,他成了一名作家。温斯顿在1965年到1969年参加了越南战争,这也是他后来作品《Better Times Than These》《Forrest Gump》等大多涉及越南战争的起源。《阿甘正传》这本书是温斯顿最著名也是影响世人最深的一部作品,以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让更多人得到了激励和积极生活的动力。大多数读者看到阿甘的经历仿佛自己的人生也得到了救赎,有了希望的光。
在对《阿甘正传》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更多根据同名电影对文化、语言、摄影艺术等角度进行分析,少有人以小说《阿甘正传》进行文学解读。鉴于战争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主题,如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等,血淋淋的战争导致了无数生命的丧失也导致了无数人的身心创伤,因此本文拟从战争入手,依据创伤理论,以小说《阿甘正传》中的丹泰勒少尉为例,通过分析丹泰勒受创伤而表现出的症状,总结导致丹创伤复原失败的原因,旨在通过创伤理论的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丹泰勒少尉这一人物形象,剖析战争对人类不可修复的创伤。
二、创伤理论
希腊语“τρυμα”是“创伤”一词的起源,最早人们定义“创伤”为外部力量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1860年英国医生约翰·埃里克森在针对部分经历火车事故受害者的研究发现,其中大多数人受到了“震惊”后的不幸和强烈的被冲击感。此后,创伤的定义逐渐扩向精神和心理领域。
在创伤理论研究的发展史上弗洛伊德的贡献是开创性的。20世纪的创伤理论基本上与向弗洛伊德思想的回归和新阐释保持同步发生的态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弗洛伊德提出:“在机械性的严重震荡、火车相撞和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就会出现一种人们早就认识到、并称之为创伤性神经症的情况。刚刚结束的可怕战争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大量发生,至少不再使人们以由于机械力量的作用导致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伤为基础来解释这种疾病”。
二战及越战以后,反战主义与和平主义成了部分国家政治背景的主要基调,越来越多人注意到退役老兵出现的战后创伤症状,并不断深入研究这类创伤性神经症。有关专家学者在对退伍越战老兵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创伤对个体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大多数的退伍老兵身上得到了体现,其容易产生绝望、焦虑和沮丧等情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一生都会与这些症状相伴。
本文正是从战后创伤及其复原过程展开分析丹泰勒少尉。
三、《阿甘正传》中丹泰勒少尉的创伤症状体现
创伤事件摧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与合理性。小说《阿甘正传》中的丹泰勒少尉是一名典型的战争受创者,他的创伤主要来自越南战争,战场上的经历对他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影响是深远的。
丹泰勒来自康涅狄格州,曾是一名历史老师,由于他的聪明军队派他到军官学校当少尉。越南战争中丹在坦克内被炸伤,全身烧伤,肺部穿孔、断肠断腿。根据赫尔曼的理论,“过度警觉”“记忆侵扰”“禁闭畏缩”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越战之后,丹泰勒的创伤症状体现为以上三类。
1.过度警觉
丹泰勒少尉首先体现了过度警觉的症状。过度警觉对于创伤患者而言是一种心理上和行为上都极其敏感的反应。
丹与阿甘在岘港医院分别后,两人一直都没有联系。直到有一天阿甘在搞砸了白宫的总统见面会后流落大街上避雨时,才又一次遇到了丹。起初阿甘并没有认出躲在垃圾袋底下的丹,出于好奇用脚尖轻轻触碰了这个塑料袋,而塑料袋的反应却非常的激烈,丹所在的垃圾袋往后跳了四尺远,一个声音从袋子底下传出:滚开!
第二次相遇之时丹正在擦皮鞋维生,阿甘在认出他的塑料袋和底下的手推车后高兴地一把掀掉了丹的塑料袋,这时丹敏感的反应和初次一样,对着阿甘大喊:把袋子还给我,你这个大笨蛋!。
由此可见丹在经历战争创伤后他的反应是剧烈而敏感的,任何贴近他的人或物他都会表现出极大的反应。丹剧烈的反应印证了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PTSD症状的解释:“害怕”“无助”和“恐怖”。表现出丹作为一个在战场上经历了炮火的轰炸后,拖着残破的身躯回来的士兵形象,任何触及他的都可能是恐怖的威胁,这是一名士兵的本能防御更是一位创伤患者可怜的过度警觉心理反应。
2.记忆侵扰
赫尔曼认为记忆侵扰是指受创者在脑海中不断地重复经历创伤事件,这就导致了受创者无法像经历创伤前那样正常生活,哪怕环境再怎么安全,对受创者来说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其痛苦记忆不会被唤醒。
而丹在试图与自己和解的过程中,每当他想要挣扎摆脱战争带来的影响,战场上曾经历的痛楚就会不断侵入他的脑海诱发出他最痛苦的回忆,这是导致他最终放弃的主要原因。在与阿甘的对话中他提到了自己保留的几十枚勋章。“它们让我想起一些事,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事——战争,当然,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勋章是他对战争的记忆,也是他经历过战场洗礼后的荣誉。这些勋章是丹存在感的唯一表现形式,所以即便每当看到勋章都会追忆起战争带给他的伤痛,他也始终保留着他们。由此可见,丹在患有战争创伤后的人生经历是十分悲惨的,家人和社会都抛弃了他,而这段痛苦的战争记忆也存在勋章中借着所谓荣誉之手反复撕开他内心的伤口。
除去勋章对丹的影响之外,他身体的残缺也是导致战争记忆时刻侵扰他的一个原因。他在文中对阿甘说道:“瞧瞧我,我有什么用?我是个他妈的缺腿怪物。一个混混。一个醉鬼。一个三十五岁的流浪汉”。由于身体残缺的原因,每当他由于残疾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他痛苦的战争记忆就会侵扰他的脑海,不断地折磨导致丹无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他找不到生存在这个社会的方式,找不到努力生活的理由,他的心理防线崩溃,最终放弃了自我。
3.禁闭畏缩
当创伤的经历让丹对生活的希望破灭后他便进入了禁闭畏缩的阶段。
全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复员研究是一个最大规模、最广泛的调查研究,它也提出几乎相同的发现:绝大多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对酒精都有很大程度上的依赖。滥用酒精或酒精成瘾是创伤患者逃避现实禁锢自己的一种方式。
丹染上酒瘾,文中常提及丹一直在喝“红匕首”,丹在放弃自己的人生以后以酒度日,丹对阿甘说:“我想我大概是在等死吧”。丹通过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的生活,把自己禁锢在醉酒的世界,进行自我封闭。
丹的禁闭畏缩不仅表现在酗酒成瘾,他抛弃曾经信仰的行为也是其中表现形式之一。赫尔曼提道:由于经历了创伤事件,受害者的内心不再对安全感、自我价值和世间万物合理秩序认可。丹曾对阿甘说过自己的“自然法则”,他认为世界的任何事都是由宇宙的自然法则所掌控的。丹在离开阿甘时给他写的一封信中提道:遇到逆流浅滩时奋力抗拒,千万别屈服,别放弃。但是丹的心理却在创伤以后发生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他对曾信奉的理论称为“净是狗屁”,也不再愿意去听信徒们的祷告,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以这种方式博得同情,他宁可继续流浪。丹放弃了自己信仰,也不对生活抱有希望,他的安全感在战后被瓦解,留下的是他自我禁闭畏缩的懦弱心理。
四、丹泰勒少尉创伤复原的失败
赫尔曼认为创伤复原可以分为重建主导权、追忆创伤事件、融入社会群体三阶段。然而丹泰勒在经历这三个阶段都以失败告终后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
1.重建主导权的失败
精神创伤会夺走受害者的力量和主控的感觉,恢复其力量和主导权是复原的指导原则,而复原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起创伤患者的安全感。对丹这样一个身体残疾的战争受创者,安全感最重要的是来自自己对生活重拾希望。
与阿甘的相遇让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他跟随着阿甘来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寻找珍妮。在这里一个偶然的机会丹和阿甘找到了赚钱的好路子—摔跤。当然这不是职业的摔跤比赛,而是一种以幕后黑手操盘比赛的肮脏赚钱手段。丹和阿甘在打完几场比赛后攒下了不少的钱,但在一场对战“教授”的比赛中,丹和阿甘决定将身上攒下的所有积蓄孤注一掷赌阿甘会获得胜利从而赚得翻倍的钱,但结局是阿甘输了比赛。这一次的失败不仅是丹和阿甘在生意上的失利,突然的意外又重新触发了丹心底的创伤,这也是丹对自己又一次的失望。原文中他认为自己闯下了大祸,一切的错都该归咎于他。丹最终选择了离开阿甘,他在身心摧残的情况下已经从心底认知自己是一个废人,他对自己的存在以及价值给予了否定,他笃定是自己害了阿甘。阿甘的出现和两人一起准备筹钱做养虾生意是对丹的一次拯救,在这一过程中丹试图重拾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但这短暂的希望也在意外中彻底磨灭,最后丹离开阿甘重新沦为流浪汉的结局既表明了他对安全感的丧失又宣判了他重建自我主导权的失败。
2.追忆创伤事件的失败
丹在追忆创伤事件的过程中有主动与被动的两种形式。
主动形式指的是丹自身不愿与创伤事件和解。文中阿甘告诉丹,他在一场反战游行中丢掉了自己的参战勋章。而丹也曾试图加入反对越战的游行但最后并未参与,同时他在文中提及:我不会扔掉我的勋章。对丹来说勋章是一种精神寄托,那场战争夺走的一切都好似埋葬在这些勋章里,就如前文所提,勋章对丹的意义就是他仅有的存在感和荣誉,但也因此,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也时刻缠绕在丹的心头。
被动形式指的是丹被迫追忆起创伤事件。在华盛顿时,当地正在举办为参加过越战的人建造的纪念碑的揭幕典礼,那些人见到丹的模样和了解了他的故事后便邀请他发表演说,可他最后在接待会上喝得烂醉,忘记了所有的演讲稿,在演讲时那些人关了他的麦克风将他赶走。这场越战的纪念反而从丹心中引出了内心的悲痛,这些纪念碑究竟是为了纪念那些死于越战的士兵们还是为那些像丹一样苟活在世的可怜虫。这不公义的战争让丹无法放下,身体的残疾也无法让他忘记曾发生的一切,他喝醉麻痹自己,无法与创伤和解。这也是丹在追忆创伤事件中失败的体现。
3.融入社会群体的失败
丹在全文中一共有两次机会试图融入社会群体,但都是以失败告终。
工作方面丹在退伍返回康涅狄格州后,他想重新成为一名历史老师。由于历史这门课已没有空缺的位置,学校就安排给他教数学。丹对数学本身并不感冒,不仅如此数学教室在二楼,丹的残疾导致他上楼非常不便,于是丹放弃了这份工作。在家庭方面,他老婆以“性情不和”为由和另外一个人跑了。退伍回来后的丹经历了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失败,丹的第一次融入社会群体也宣告失败。
第二次是丹阿甘又一次的相遇,但这次丹是在一个人行道上替西装革履的人擦皮鞋。丹对阿甘解释他是为了羞辱那些资本主义的奴婢才去擦皮鞋的。在他的眼里那些资产阶级的家伙都是穿着锃亮皮鞋的废物,而他擦的皮鞋越多,越能把这些废物统统送入地狱。但同时他又矛盾的认为自己这副德行的人并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人。可见丹表面上似乎是融入了社会,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他内心早已失去了对社会的信任。他好似一枚工具,在战场上或许他是荣誉的,但退役后的他只能作为一个残疾人苟活在这世上,他恨这些无作为的人更恨自己这副惨败的模样。赫尔曼在书中提到战后军人等受创群体在得不到求助回应时,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就会被磨灭,从而不再信任他人。受创者也会因此感到被完全抛弃的孤独,一旦信赖感丧失,受创者觉得与其说他们还活着,其实更像是死了。
这也彻底宣告了丹泰勒创伤复原的失败。
结语
《阿甘正传》中丹泰勒少尉只是一个小配角却真正表现出了一个饱经战争摧残的军官在退伍之后成为流浪汉的心酸人生。由此可以折射出战争对国家、对人民的影响,战争带来的只有痛苦和绝望,而且战争的创伤是不可修复的。丹失败的复原经历正是他无法与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解,对丹来说身体的残疾进一步导致了他与这个社会脱轨,大部分人对像他这样的受创群体的不作为也让他心理上失去了对生活和人生的希望。丹泰勒少尉最终并不美好的结局或许正是许许多多现实中饱受创伤的退役军人的缩影,温斯顿曾作为战地记者亲自经历了越战,他笔下的丹泰勒是对这场不公义战争的控诉,更是批判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