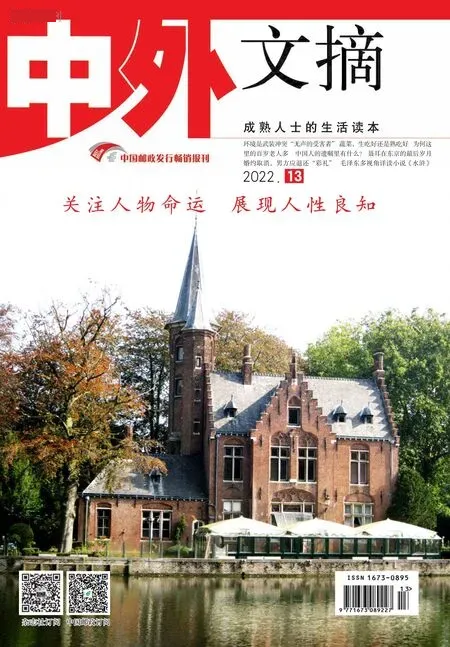隐居的年轻人:贫穷不一定限制想象力
□ 石悦欣

有人在挣物质,有人在挣健康;有人在存金钱,有人在存生命。没有快慢,甚至也无对错,选择不同而已。
过完春节,守静回到了湖南湘西山脚下的村子,这是搬离秦岭山麓后的第二个隐居地。春天来了,她们要开始种菜了。
四年前,她和朋友辞掉工作,告别城市,来到山中生活。看云卷云舒,赏高山流水,抚琴喝茶,看书作画,舞文弄墨——这些都不常有,常有的是劈柴挑水、洗衣做饭、翻土犁地、除草种菜。
“没当农民时觉得农民好苦,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腰弯背驼人憔悴。当了农民后,觉得……农民是真的好苦。”守静在自己的公众号“守静隐居”中写道,“但这种苦跟城里人的苦不一样,就像白酒都烈,但各有各的味。”
“就像去赴一场约”
守静从小乖巧懂事,一直按部就班往前走。小学、中学,重点学校、重点班,读大学、找工作,照着这个轨迹走,下一步就是成家育儿了。
但26 岁这年,她一个激灵想到,人生怎么能这么过?
在此之前,守静对人生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但隐约觉得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办公室白领,朝九晚五,上班下班。可真正踏入职场后,她更加确信,那些天天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日子只是对生命的消耗。这样的生活令她身心俱疲。
虽然才二十出头,她早已是一个“老失眠人”。
她高中是寄宿制学校,住在十多个人的集体宿舍。晚上室友的磨牙声、呼噜声、梦话声此起彼伏……高二左右,持续的失眠开始了。
最严重的时候一晚上一个小时都睡不到,凌晨好不容易刚睡着,学校做操的大喇叭又响了,所有人都像弹簧一样“嗖”地弹起来,然后又像打仗一样抢厕所、刷牙、洗脸,最后又“嗖”地一下冲到操场集合、做操、跑步……
高考时,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进了一本大学。大学期间,梭罗的《瓦尔登湖》逐渐成了守静的心之所往。清澈的天与湖,宁静的日与夜,就这样在她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山里隐居的想法渐渐萌芽了。
毕业后,守静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天天敲键盘、盯电脑,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她尝试过许多治疗失眠的办法,吃药、吃补品、冥想,因为怕吵戴耳机,怕光戴眼罩,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但还是经常瞪眼到天明,身体的其他地方也发出了紧急信号。
“当身体三番五次发出危机信号时,我从接收到反思,然后醒悟——我要的究竟是什么?没了健康,其他还有意义吗?需要那么拼命地拿健康去换物质吗?基本生存所需似乎也用不了多少,多余的物质都在喂养多余的欲望……”
索性就隐居吧。
一起同行的两位,是和她有着十多年交情的好友,她们对于守静来说就是家人般的存在。她俩虽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也认为没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在慢慢地损耗生命。
她们很快一拍即合,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寻找隐居的目的地。
“就像是赴一场约一样”,瓦尔登梦真的实现了。
隐居也不是岁月静好
四年前的夏天,守静和两位好友扛着大包小包的全部家当,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了隐居地。
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装着事先准备好,用来运行李的自行车。山路蜿蜒狭窄,陡峭曲折。给司机师傅加了钱才勉强继续往前走。
路越来越窄,车无法开进去了。两旁密布着灌木荆棘,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三人只能步行前往。自行车驮着一捆行李,每个人身上又扛着一包,晃晃悠悠地向前走。举步维艰。
走到半路上,又下起了雨,行李都被浇湿了。小路变成了泥潭,守静两次连人带车滚下了悬崖,好在没受伤。
终于到了家门口。这是一栋年久失修的土房子,孤零零矗立在深山中,主人十几年都不曾上山来看过了。
把湿漉漉的行李拿出来晾晒后,她们就开始打扫屋子,砍竹断木,建造家具。
收拾完毕后,她们便下山同房东签合同。谁都没想到麻烦事来了——房东突然要求涨房租,从之前电话里谈好的第一年免费,后四年每年六百,变成了一年一千,一次缴清。
这间房子本是守静和朋友利用辞职前的假期,走遍了终南山、秦岭和广东等地,寻了一年才寻到的。找到这间房子本就不易,如今再寻别处更是难上加难。
三个人看着眼前这位眯眯眼,鹰钩鼻,挺着大啤酒肚的中年男子,又气又无奈,只能想尽办法选择折中方案。
麻烦事还没完。一个老妇人怒气冲冲地用方言冲她们喊道:“你们要在这儿种菜也行,给一百块钱!”
之前在这栋房子住过的一个老人也来了,指着黑乎乎的电线要一百元,因为这是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山民,趁家里没人时偷菜,捅破窗户纸偷眼镜……
但同样还是这些人,之后却成了关系亲密的近邻。或是时不时来找守静闲聊,帮忙缝补衣服,或是带着自家种的枇杷、黄杏、蔬菜等送给她们。她们也礼尚往来,有时会送些村民们从未见过的网购品。
“我想,他们大概都曾吃过陌生人的亏,所以才会把心底的委屈、愤恨发泄到初来乍到的外人身上。待到熟络后,发现这些外地人并没让他们吃亏(偶尔还能得点小便宜),又逐渐把心底另一角落的善意释放出来。”守静后来也渐渐理解了他们。
贫穷不一定限制想象力
守静她们晚上很少开灯。每天晚饭过后,她们就静静地等待着夜晚的降临,没有任何杂念地享受黑夜。
黑夜中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她在漫天的星空下夜跑,夏夜,伴着蝉鸣虫啼,在门口的草地上铺开瑜伽垫,光着脚轻轻地踩上去,双手合十,高举头顶,弯腰,劈叉,倒立,起身。
在极度静谧中,守静感觉自己的细胞都在流动,练一会儿,再练一会儿,好像连灵魂都有了样子。
就为这一刻,她觉得荒野独居也值了。
守静的瑜伽是自学的,自己拆解动作,在纸上一个一个画瑜伽小人图,照着练。
“实际却是因为穷,没有wifi,跟视频练瑜伽用手机的流量,太耗流量了,尤其是跟直播时,每天至少一只鸡(G)。于是就自己把动作记下来,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跟着视频练了,又省下一袋米。”守静调侃道。
结束运动后,身上已经冒起了汗,正好赶紧洗个澡。没有浴室,只能在户外洗澡。夏天倒没什么,难的是冬天。感觉寒风从身体钻进钻出,守静就这样切身地体会到了“寒风刺骨”的真正含义。
在山中生活久了,守静时常感慨古人造词的精确,比如风刀霜剑、汗如雨下、饥肠辘辘、口舌生烟……贴切真实,细致入微。
她们隐居在陋室中,闲来无事也就更能“咬文嚼字”了。“这大概源于他们对自然的深刻体会吧,字词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书本上的方块,而是源于自身五感六觉的真实反馈。现代人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能深刻体会到冷、热、痛、饿、渴此类词语的机会少之又少。”
不过当守静真正开始感受天和地时,寒冷这件事也渐渐被模糊了。黑暗中,仿佛置身虚空。“抬头看见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天花板,而是浩瀚夜海,璀璨星空。星星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亮有暗,有密有疏,真实而又遥远,偶尔还会有几颗流星划过天际。这时甚至会忘了是在洗澡,而像是在看一场沉浸式的太空电影。”
洗完澡擦干身子回到屋里,发现没暖气也无空调,平时穿着衣服都觉得四壁漏风的屋内竟如此暖和,暖和到不穿衣服也丝毫不觉得冷,幸福果然是对比出来的。
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年,每次偶尔去城里住几天宾馆,哪怕只是百来块的便宜公寓,也会觉得舒适满足。
而有时出远门徒步爬山,风餐露宿几天后回来,家徒四壁的居所也成了天堂。
她们吃得也很简单,很少吃肉,也没有太多的调味品,一来因为下山买肉麻烦,且没冰箱不易储存,二来因为没有收入,要全方位节流。
没了味厚汤浓的肉覆盖,清新的蔬菜味道也就慢慢显现出来了,细嚼慢咽久了,自然会发现蔬菜的清香美味。
但穷也并不一定限制想象力,也可能“迫使”她们做不同的尝试,从而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她们摸索出了一些“黄金搭档”。比如用西红柿或者橘子来代替醋,不仅有醋的酸味,且有它们自身的清香,还为菜增添了一抹色彩。用橘子或西红柿炒的酸溜土豆丝,比用醋炒出来的还好吃。
再比如用秋葵、丝瓜或土豆代替芡粉勾芡。土豆本身就含有大量淀粉,秋葵和丝瓜则富含黏滑的汁液,取些许土豆、丝瓜或秋葵掺入其他菜中,就能达到汤汁浓稠的效果,营养也更丰富了。她们自创的秋葵青豌豆鸡蛋豆腐羹,貌如翡翠碧玉,清新脱俗,味如燕窝银耳,丝滑浓郁。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如用清甜的胡萝卜或洋葱代替白砂糖做糖醋鱼、用月季花代替玫瑰做冰粉、用鸡蛋或蘑菇代替味精提鲜、用自己炸的芝麻代替香油增香、用自己腌的纳豆代替酱油添浓……
“其实大自然的味道已经足够丰富了,我们缺的不是味道,而是一张慢下来细细咀嚼、静静品尝的嘴。”守静总结道。
极简生活
每顿饭从种植食材起,都是由守静和朋友亲自完成的。她以前总是看到“好吃到哭”这个表达。“那些好多都是噱头,但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却真的有哭的冲动,那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感动。”
要想吃上亲手种的菜,就得进行开荒、翻地、播种、移栽、浇水等一系列工作。
仅翻地一项就是个大工程。守静记录:这里的土并非松软的沙土,是硬邦邦的黏土,挖下来都是大块大块的。只能用锄头刃挖出一大坨土块后,再用锄头背将土块敲碎。一挖一敲,一敲一挖,不一会儿手掌心就起泡了。可怜这双只摸过笔杆子的手,几天下来,泡被磨破,磨破了又起新的。
一个星期后终于磨出来了茧,糙是糙了点,但至少不会轻易起泡了。往后这双手,洗衣、割草、挖地、提水、劈柴,无所不干,也就更无法看了。
“世人关于隐居种种美好的幻灭,或许就是从纤纤玉手被毁的那一下开始的。然而,无论何种生活,再浪漫再美好,都有其代价和苦楚,但也正是这代价、这苦楚,才让亲手编织的生活弥足珍贵。总之,选择了远方,就风雨兼程,选择了种菜,就继续挖地吧。”
山上做饭也不容易,连自来水都没有。拎两个桶去几百米开外的山涧里提水,把桶按入水中,屏住呼吸、小心翼翼,避免把底部的沉泥碎石扬上来,否则把水搅混了得等上一个小时才能恢复纯净。水灌满后,提上两大桶水,上陡坡、踩石阶、跨门槛,到家后已是气喘吁吁。
厨房里也没有水槽,没有煤气灶,没有电磁炉,没有高压锅……在这样简陋的厨房做饭,所需时间五倍于城市厨房。
守静看李子柒在镜头前做菜时,总是那么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很羡慕。“但无论如何,只有能经受住前面鸡零狗碎的繁杂,才能享受最后饕餮盛宴的美味。柴火锅炒出来的菜,是真香。”
当然,并非所有简陋的环境都让人乐在其中,有时是真真切切的痛苦,比如冬天早上洗菜切菜时,手指冻得钻心地疼,伸都伸不直。
痛则思变,后来索性把早餐去掉了。为什么一定要一日三餐呢?
守静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山中的猴群每天只吃一顿午饭,其他时间都用来玩耍和探索,不也活得很好吗?
她们果断缩减为一日两餐。本以为会饿得受不了,结果却发现足够了。
她们也不愿意在吃上花费太多时间。以前守静做馒头,会花很长时间把馒头做得像卖的一样漂亮,现在的馒头都是随手一捏就往蒸锅里放。“并不是变懒了没追求了,而是跳出固定模式,看看随机演变究竟会怎样,也可以说是不‘着相’了,随缘安定。”
隐居的四年,她们搬了两个地方,都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口锅和一个烤箱,什么家具都没买过。
她们的生活主要靠积蓄,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所以能自己做的就尽量不买。当然有些东西买了也很难运上来,比如说床。就算小巧轻便的折叠床勉强能扛上去,但搬家时又是一大负担,扔又舍不得扔。
她们从家旁边的竹林里砍下几十根竹子,做了一个开放式衣物柜,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次日,再去砍几棵松树,做了一张宽敞结实的床,又用了一整天。
“穷人并非没资格隐居,反而自然地过渡到了极简生活,了解了哪些才是生命必需品。”守静说。
上班时,作为打工人,再努力也是一颗在局部磨炼的螺丝钉,如今,她们的整个生活生产,从零开始,都得自己全程规划布局打理。
守静不认为隐居就是躺平。“如果勤勤恳恳、自食其力也叫躺平,那躺平可能比站着,甚至跑着更累。我认为只要没有放弃对生命的探索和精进,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不能叫躺平。”
在她看来,人生不是一个不停搭积木、只要一直增加就持续幸福的过程,也不是只要有财富就能一切如意的私人订制,而是有取有舍的精神和感官体验之旅。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拿健康换钱是不可取,但没办法,大家不都这样嘛!”
“结婚生子确实有不好的地方,但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嘛!”
……
每次妈妈都这样劝守静,她常无奈地回道:“‘大家’到底是何方神圣?跟我有什么亲密关系,以至于能如此左右我生命中所有最重要的决定?”
守静本就生在农村,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全家才能团聚一次。守静和父母的关系算不上太亲密,但为了隐居这件事,守静曾经也跟父母周旋了很长一段时间,父母的态度经历了坚决反对——无奈接受——支持的过程。
守静并不拒绝结婚生子,但她觉得目前更重要的事还是着眼于自身。“只能跟他们说先把身体养好再说,不然对以后要生的孩子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反正随缘吧,成家后也是可以继续隐居的,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家庭,但这就是后话了。”
有人问她,父母辛苦供养你上大学,你却归隐乡野,何以为报?
对此,守静也曾羞愧过、自责过,但如今,已经有了答案。
“好的报恩并非牺牲自己成全父母,而是把自己活好、活明白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父母获得思想上的觉悟,让他们也活得通透明白,不再一直为已经成年的子女操心。因此我不会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而牺牲自己,做自己想做的、能做的、该做的,如果父母还是反对,那也没办法了。”

守静的报恩方式是“按需分配”,而不是一味地去顺从。她每年回家一两次,帮他们做做家务,给他们普及健康知识,送他们精心筛选的医学书籍。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守静觉得隐居的日子像是开启了四倍速,明明感觉才过一年,转眼四年过去了。
她不认为自己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休整、思考、磨刀。“有人在挣物质,有人在挣健康;有人在存金钱,有人在存生命。没有快慢,甚至也无对错,选择不同而已。我很敬佩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毅力,这是一种不急不躁的智慧,我需要,这个时代也需要。”
“至于以后的日子,可能等我身体和思想都达到了理想的状态,就会选择回归城市,如果在农村能够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可能就不出山了吧。”守静说,“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按部就班,就是对生命的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