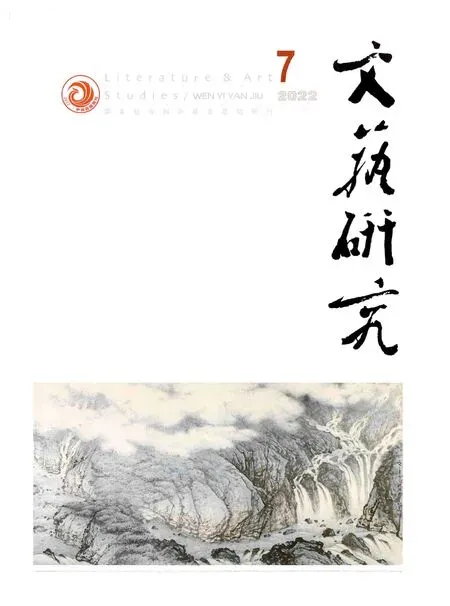“荷兰人的书”与说“不”的游戏
——张枣20世纪90年代中期诗学转变研究
李海鹏
2011年5月下旬,诗人张枣刚刚过世一年有余,《名作欣赏》刊发了臧棣的悼亡诗《万古愁丛书》的创作谈《可能的诗学:得意于万古愁——谈〈万古愁丛书〉的诗歌动机》,忆及张枣生前,二人友谊甚笃时有趣的诗歌交往。其中有一段谈到臧棣赠书给张枣的往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有一度很喜欢我寄给他的荷兰人写的《游戏的人》。他曾夸张地说,兄弟啊,我才不过壮年,有不可限量的才能,怎么就写不动了呢。这下好啦。你寄来的《游戏的人》,让我又恢复了写诗的冲动。”
这“荷兰人的书”为荷兰学者约翰·赫依津哈所著,1996年在国内出版了中译本,臧棣所赠,张枣所读,正是此书。书中如此定义“游戏”这一概念:“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此外,该书第七章《游戏与诗》中,有如下观点:“[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游戏功用。它在心智的游戏场、在心智为了诗所创造的自身世界中展开。在那里事物具有一副迥异的面貌,它们披戴着‘普通生活’的装束,并受到不同于逻辑因果律的关系的约束。如果严肃的陈述可以定义为清醒生活中产生的陈述,那么诗就永远不会提升到严肃性的层面。”我们可以将这两段话整合为:诗是一种心智的游戏,它以语言呈现日常生活的图像,但在逻辑上与日常生活却又迥然不同,诗不受日常生活之法则的约束,如果说后者是严肃性的,或乏味的,那么前者则是游戏性的、有意思的。
作家的回忆文字往往有虚构的成分,甚至有时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但张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文本,以及相关访谈、通信等外部资料,能够清晰印证臧棣这段回忆文字。这种印证,实际上指向了张枣在9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上述“游戏”观念的启发,对原有诗学策略进行了自觉的调整。本文意在结合相关资料,揭示这一转变的内在诗学逻辑,及其在诗歌文本面貌上的呈现,并对其得失限度试做反思与评价。
一、元诗意识与“该怎样说‘不’”
张枣一生写诗共一百多首,考其创作年谱,在1996年之前的几年内,其实仍有一定的创作量:1994至1996年,目前可以查到的作品共有十几首,参照其一生的创作总量,这两年的密度并不算低。而且,张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十四行组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正是完成于1994年,即使此后一两年内仍不乏佳作,代表性作品有《厨师》《纽约夜眺》《祖国》等。那么,张枣口中的“写不动了”,该作何理解?这一表述,其实与其著名的元诗意识相关。
在谈论好友柏桦名诗《表达》中一连串莫名的追问时,张枣曾言:“对这一切不会存在正确的回答,却可以有正确的,或者说最富于诗意和完美效果的追问姿态。”这句话用来揭示柏桦这首诗中呈现的诗学意识相当合适,而用来整体性地揭示张枣自己的诗学意识,则更合适。它的意思是:面对这种追问,作为结果的回答并不是目的,而追问这个动作本身才是目的。此外,这种意义上的追问具有一种乌托邦的气质,不是在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回答,而是在西西弗斯式地不停刷新追问这个动作。实际上,我们从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中可以找到一段话,它的内在逻辑,与张枣这句表述之间构成了互相阐释的关系:“新事物乃是对新事物的渴望,而非新事物本身。这正是所有新事物的祸因。由于是对旧事物的否定,新事物在自认为是乌托邦空想的同时,也从属于旧事物。”从逻辑上讲,张枣所说的“追问姿态”便对位于阿多诺口中的“对新事物的渴望”,也就是说,“追问姿态”意味着永远的追问,每一次追问都与之前的追问构成否定关系,如是演进,永无终结,这便是对新事物渴望的乌托邦,也是“追问姿态”的乌托邦。
如果对现代主义有所了解,便会知道,这样的追问逻辑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核心理念。而张枣在当代诗人中,可谓是对这种西方现代主义理念最自觉的支持者之一。他曾说过:“我个人是要求在学术上将这‘现代性’定义为‘现代主义性’的辩争者。”在他看来,中国新诗现代性追求的成败,并不在于习得多少现代主义的文学技法,其关键正是能否建立起这种本体性的“追问姿态”:“中国文学在遵循白话这一开放性系统的内在规律追求现代性时,完成现代主义的文学技法在本土的演变和生成并非难事,成败关键在于一种新的写者姿态的出现,偏激地说,关键在于是否在中文中出现将写作视为是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写者。”所谓“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其内在逻辑与前面所述的“追问姿态”相同。落实到诗人身上,即诗歌的语言不是用来传达一个固定的信息或内容,其形式本身构成了诗歌写作的本体与目的。因此,这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诗人才能的标志,在于是否有创造足够多变且有效的崭新语言形式的能力。用索绪尔的理论来说,这种才能指向了“命名”的能力:具有此种“追问姿态”的诗人,致力于打破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系统中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约定俗成意味着传达信息与内容的便利),并敏感着个人与整体的存在、伦理状况,由此书写出一个个有效的语言符号系统,这便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诗。这种“追问姿态”,是张枣元诗意识的核心。
实际上,这样的“追问姿态”经常会遭到质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为什么这样的姿态就是现代主义的,其历史依据何在?面对这样的质疑,许多回应都只是对结论的同义反复而已,要解释清楚其历史依据,需要从现代主义文学的符号模式与意识形态关联的角度给予回答。詹明信曾以符号学的方式,对前现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词、物关系模式进行了整体梳理,以此说明每种模式并非简单的书写技巧,而是有着深层的历史依据。在前现代时期,对应于森严的现实等级秩序(要么是古典帝国秩序,要么是中世纪宗教秩序),文学书写中也存在着一套“专制的指符”(despotic signitiers),比如但丁的写作虽然充满人文主义精神,但仍是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贝雅特丽齐的位置必须属于天堂,只有这样的书写模式,在当时才是有效的。而在现代时期,这套秩序开始解体,相应的文学书写体系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个阶段便是现实主义,它对应于早期资本主义,其符号模式是对秩序解体的书写,现实中的物体、事件作为“参符”(referent)的意义凸显出来,并与能指和所指紧密呼应。这意味着经验世界作为客观对象,本身具有了书写的价值与必要。人的世俗意义与经验可以被书写,而不必皈依于某个既定的书写秩序,这便是现实主义的书写原则,它是现代性符号模式的第一个阶段,本质上造成了前现代书写秩序的解体。而现代主义原则对应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它试图以写作者个人化的方式重新建立书写的秩序。由此,前面所述的“命名”原则出现了,这首先意味着与经验事物同构的参符与能指、所指之间产生了断裂,语言不再随着现实/参符而变动,而是具有了自律性,写作者可以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命名,由此在符号系统中建立起自己想要的秩序。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的特质是不存在一个前现代式的固定的秩序体系,所以,现代主义者不可能因一次命名而一劳永逸,只能不断命名,不断追问。正如张枣《空白练习曲》这一标题所揭示的,现代主义的书写原则本质上是朝向价值、秩序之空白的言说与追问。理论上,现代主义者在一部作品中只能完成一次命名,作品的完成便意味着命名的终结,他必须创造出新的命名以完成一次次新的写作。当然,这种一次性几乎不可能,但自觉的现代主义写者总会在写作中创造出许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崭新命名方式的实践、完善与否定,并在否定中抵达下一个命名方式。而后现代主义对应于资本主义晚期,是继参符的断裂之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后现代书写者不再在意重建秩序,不再关注命名,而是彻底的解构者,他们笔下的符号,宛如精神谵妄者的呓语。总之,参考这样的符号学探究会让我们明了张枣所谓“与语言发生本体追问关系”的现代主义内涵。
张枣所青睐的现代主义书写原则,包含两重否定意味。其一,参符的断裂所指向的,是对现实逻辑与语言惯习的否定,它以命名的方式致力于对现实进行符号重构,从而透过纷乱的现代经验世界,建构起一个语言内部的逻辑和秩序。这样的书写者是语言的异端,他们经由语言的自律性而完成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其二,追问的无止境意味着每个命名都是对已有命名方式的否定。对于现代主义写者来说,由于秩序实际上是转瞬即逝的,是经由每次命名而闪现出来的,因此,由命名建立的秩序并不重要,命名这个行为本身才是书写的本体。诚如张枣所云,不存在正确的回答,但可以有完美的“追问姿态”:现代主义写者是词语的西西弗斯,是词语的异乡人。实际上,这两重否定指向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参符的断裂所造成的否定,是现代主义写者永恒的否定词,这使他们面对现实的风云变幻时处变不惊,永远在语言的本体追问中言说现实。“追问姿态”则意味着现代主义写者在处变不惊之外,还需要在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上时时而变,不断创造崭新的命名方式,并以此保持有效言说变化中的现实的能力。可以说,每个现代主义写者都是能够在这两重意义上说“不”的人。
在考察了现代主义书写方式的内涵以后,我们得以回答这部分开头的问题:张枣口中的“写不动了”该如何理解?它并不肤浅地意味着写不了诗,或者说创作量匮乏,否则这几年并不低的创作密度便无法解释。它的意思其实是张枣在传达自己作为现代主义写者的危机:在前一种命名方式已经饱满后,尚未找到一个新的命名方式。实际上,张枣这句看似“诉苦”之语,与他对鲁迅《野草》的理解之间存在着隐秘而重要的关联。在张枣看来,鲁迅创作《野草》时也同他一样,“在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之后面临着一个写不下去的危机”。这种“写不动”的危机,通常会被单纯负面地视为作家“创造力的损毁,精神的颓靡”,然而,若以元诗的观念来看,其中却恰好蕴藏着“语言的增殖力”,指向“危机与战胜危机的意志、失语与对词语的重新命名”。将张枣对鲁迅《野草》时期“写不下去的危机”的理解方式,与他对臧棣所说的“写不动”的危机对比来看,便会在元诗理论的层面上印证臧棣的回忆绝非虚言。
当然,如果仅以上述经典的理论模型来得出这个判断,是不充分的,我们还必须从张枣这一时段的作品与相关谈论、资料中找到印证。笔者发现,张枣在这几年的诗歌中以“该怎样说:‘不’”来传达这一“写不动”的危机,极具元诗意味。张枣最早以“不”作为元诗信号的作品,是1992年的《护身符》。此外,完成于1993年的《今年的云雀》和《空白练习曲》,以及这一时段许多其他作品中都出现了极具元诗意味的否定性表达:
灯的普照下,一切恍若来世
宽恕了自己还不是自己
宽恕了所窃据位置的空洞
“不”这个词,驮走了你的肉体
“不”这个护身符,左右开弓
你躬身去解鞋带的死结
——《护身符》
但最末一根食指独立于手
但叶子找不到树
但干涸的不是田野中的乐器
总之它们不是运载信息
这是一支空白练习曲
——《今年的云雀》
天色如晦。你,无法驾驶的否定。
——《空白练习曲》
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不”作为元诗信号的意义。首先,现代主义书写原则试图重建秩序,但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秩序已经不可能恢复到前现代阶段,它本质上是词语的乌托邦,一种空白。张枣的诗中经常出现“空白”“位置的空洞”等词汇,其实正是在言说词语的乌托邦。其次,这一以“空白”为秩序的现代主义书写原则,正如“最末一根食指独立于手”所示,具有独立性与自律性,其功能“不是运载信息”,因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工具论式语言构成一种否定,它与语言之间所发生的正是前文张枣所说的“本体追问关系”。最后,追问、命名的永恒性意味着说“不”的永恒性,“笛卡尔告诉我们,只有‘不’是永恒的”。因此,危机永远存在,不懈地命名即不断地否定,正是这一逻辑塑造了“空白”的秩序。《空白练习曲》中的“你”就是对“空白”秩序的指认,它是“无法驾驶的否定”,与西西弗斯的宿命一样,现代主义写者对它也是“无法驾驶”的,他能做的唯有不停说“不”与追问。
从前引的三首诗来看,《空白练习曲》复杂而完整,《今年的云雀》看起来像是对前者的说明,而《护身符》则是一首元诗信号明显的诗,正如诗中“驮走了你的肉体”所暗示的,它就像一副骨架,除了反复将“不”指认为“护身符”和元诗信号外,再无任何语言的趣味。这首诗的内在缺陷,从黄灿然1996年对张枣的访谈中可见印证:“我不满意我92到93年一段时期的作品,比如《护身符》《祖国丛书》等,我觉得它们写得不错,技术上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太苦,太闷,无超越感,其实是对陌生化的拘泥和失控。”由此可见,张枣对自己写作的状况极为自觉。一个足够优秀的现代主义写者,不仅需要认识到“不”的本体性价值,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以足够独特且创造性的方式将“不”说出来,并且投射自身及历史的伦理性与真理性。按照这一要求,《护身符》这样的作品缺陷明显,是对“不”的概念化,整首诗看起来像是关于现代主义书写方式的咒语,它只是在说“不”而已,诗人独有的方法论与命名方式并未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现代主义写者要做到的,不只是在诗中说“不”,而是显示出自己究竟是怎样说“不”的。对于这一问题,张枣依然是自觉的,在完成于1994年的十四行组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结尾,他就发出了这一重要的追问:
对吗,对吗?睫毛的合唱追问,
此刻各自的位置,真的对吗?
王,掉落在棋局之外;西风
将云朵的银行广场吹到窗下:
正午,各自的人,来到快餐亭,
手指朝着口描绘面包的通道;
对吗,诗这样,流浪汉手风琴
那样?丰收的喀秋莎把我引到
我正在的地点:全世界的脚步,
暂停!对吗?该怎样说:“不”?!
这首组诗在“我”与知音,即俄国白银时代女诗人马琳娜·茨维塔伊娃之间的对话中展开。对话临近终结的时刻,诗中写到的物象看起来已安居于“此刻各自的位置”,正如“丰收的喀秋莎”所隐喻的,这是语言丰收的时刻,“我”也被她引到了自己此刻该在的地方,“此刻”万物“暂停”,它是现代主义书写意义上的秩序显现的时刻。还是在与黄灿然的访谈里,张枣谈到了这首诗:“我的起步之作是84年秋写的《镜中》,那是我第一次运用调式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出国后情况更复杂了,我发明了一些复合调式来跟我从前的调式对话,干得较满意的是《祖父》和《跟茨维塔耶(伊)娃的对话》。”熟悉张枣的诗歌历程的人会知晓,这首诗昭示了张枣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写作阶段的饱满与终结。有论者曾将这一阶段概括为“‘知音对话’模式又被创造性地转化出来,作为对其自身孤独困境的解救”,该阶段肇始于张枣1986年赴德留学,到这首《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则抵达了饱满,可以说,这首组诗是张枣这一阶段的最高成就。张枣最好的诗往往能做到将现代主义写者姿态与具体的伦理处境、时代感受结合起来。“孤独困境”构成了孤悬海外时期张枣的处境,而与知音之间的对话则构成了现代主义写者意义上的“解救”。这首组诗的优点无须赘言,已受到广泛的赞誉,是张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问题在于,对现代主义书写原则来说,否定才是永恒的,而秩序只是转瞬即逝之物,诗人依然要不停地问“对吗”,对于现代主义写者来说,只有“不”才是唯一的“对”。因此,这首诗结尾的一行便极具元诗意味:既然此刻已如此完满,万物的位置与秩序看起来都这么“对”,那么该怎么对它说“不”?找到一个新的命名方式无疑是困难的,每一次寻找的过程,都意味着诗人与言说的危机缠斗的过程。在“知音对话”这一命名方式抵达“丰收”之后,崭新的命名方式在哪里?崭新的诗歌可能性又在哪里?这便是张枣所说的“写不动了”的真实含义。
“知音对话”是孤绝的诗人在日常生活缺席的伦理境遇下的命名方式。在完成这首组诗一年后,张枣在《厨师》(1995)中虚构了一个烹饪的日常情境,其中也写到“不”字:
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
像两个舌头的小野兽,冒着热气
在冰封的河面,扭打成一团……
“舌头的小野兽”可理解为对烹饪、饮食的明喻,对言说的暗喻。这意味着诗中的“不”仍然是元诗的信号,而且与以烹饪为名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这与“知音对话”模式中日常生活的缺席相比,似乎发生了新变。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接下来,本文将梳理张枣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书写,这一工作将呈现那本“荷兰人的书”对于张枣的具体影响,并由此揭示诗人90年代中期这次诗歌转变的内在诗学逻辑。
二、日常生活:从唯美启示到游戏伦理
诗学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诗歌”在整体上强调对历史的介入,但如何认知历史,诗人也有诸多自由,“九十年代诗歌”因此呈现出纷繁的面貌。在张枣这里,“所谓历史,无非是今天鲜活的日常细节”,处理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是处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托所说,“这个巨大的宝藏中有着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区别,使各种现象都富含了多种意义……日常生活中还有昙花一现的‘无名英雄’发明的无数玩意等待着我们去了解,城里走路的人、居住区里的居民、爱好读书者、梦想家、厨房里卑微的人,正是他们让我们惊叹不已”。张枣也格外青睐细微而丰富的日常生活,这构成了他对时代认知的最主要来源,甚至构成了他所信赖的民族传统。这一点,他早在1987年就已经确认:“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分。”对他来说,传统就隐藏在一代代的日常生活中间,但它不会主动“流传到某人手中”,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进入传统的方式,“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此外,张枣所青睐的“生活”是享乐性的,“气场是汉族的”。旅居德国多年,他想念国内的生活,始终难以爱上德国的生活,觉得“住在德国,生活是枯燥的”,“德国日常生活的刻板和精准醒了……一切都那么有序,一眼就望到了来世,没有意外和惊喜,真是没意思呀”。德国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在张枣笔下成了被工具理性压抑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成为其诗歌中理想的对话者,尽管他借用德语作家卡夫卡的题材,写出了《卡夫卡致菲丽丝》这样的作品,但这种对话之达成,是因为德语文学是他理想的对话者,存在于他的知音谱系中,而德国的日常生活,则是他出于诗人的文化使命感而不得不忍受的牺牲,就像坐牢一样:“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不过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
在与《护身符》同时期的、同样让他不满意的《祖国丛书》里,张枣表达了对“生活”的强烈抉择,伴随着同样强烈的牺牲感: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舔”与“被舔”的交换,暗喻了他沟通中西的诗歌对话使命。那一时期,他的抉择是为了这样的使命放弃“生活”,“海底被囚的魔王”般囚禁在德国的枯燥中。“不愿去生活”在抉择上应和了《护身符》中“驮走了你的肉体”式的直接说“不”。而当张枣在《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厨师》中去思考“该怎样说:‘不’”时,这就意味着,旅德多年,经过了“不愿去生活”的“知音对话”阶段,有意思的国内生活重新成为他想在诗中呈现的主题。
对中国的日常生活该如何关注与提炼,张枣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自觉,这实际上是他在“知音对话”模式之前的创作阶段。在为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所作的序言《销魂》中,张枣回忆自己早年的诗歌取径:“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张枣的早期诗歌富于唯美主义色彩,其音调是“楚文化的,抒情的”,充满阴柔气质,且不说《镜中》《何人斯》,就连《楚王梦雨》《卡夫卡致菲丽丝》中的抒情主体,虽然皆为男性,但并不阳刚,这些诗的抒情声音都透着一股南方楚地浓郁的靡丽声息。
而去国十年后,1996年春节刚过,张枣与老友陈东东在上海南京路上闲逛,“大概又见到了少女”,他对陈东东说:“‘……东东我跟你说,我痛失中国啊,真是痛失……’……‘你知道吧,现在我看出去,满眼,全是鸡……只是价格问题。’”在分析了张枣1984年写于重庆的《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中单纯的少女般的唯美气氛后,陈东东对这段往事追加评论道:“十二年以后,张枣从德国回来,面对的已经是另一个时代,当他觉得甚至从少女那儿所见的也只是失落的中国,他点起一支烟来的叹息里,是否又有了那种‘你怀疑它是否存在过’的忧伤?但他早就不再写那样的诗了。但他也许一直都在写那样的诗。”陈东东的这段评论指出了张枣9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所面对的“生活”危机:“少女”从纯真变为“堕落”所隐喻的,实际上是张枣对变化了的国内语境的觉察;对信奉“诗的危机就是人的危机;诗歌的困难正是生活的困难”的张枣来说,当“不愿去生活”的“知音对话”模式已陷入“写不动了”的危机时,他下定决心挣脱德国式的枯燥日常,将目光重新转回国内,却发现面对变化了的国内语境,提取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已经不再是有效的诗歌方法。那么,新的诗歌可能性又在哪里?
这段往事发生于1996年春节过后。正是在这一年,他与《游戏的人》相遇。面对变化了的国内语境,张枣的诗歌方法从提取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转变为营造日常生活的游戏伦理。我们可以从他在1998年9月12日给好友钟鸣的一封信里找到证据,该信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我内心对事物的融联之幻觉越来越强,越来越稳定。我想更偏重更阳性的语调说话,以超越或包容我的精致。总之,更游戏一点。”
《游戏的人》究竟如何启发张枣找到了“该怎样说:‘不’”的崭新方式,至此可窥一斑。面对国内生活的变化,张枣的写作在音调层面发生了由阴性到阳性、在伦理层面发生了由唯美到游戏的转变。纵览张枣1996年以后的诗歌,无论他身在德国与否,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同步于国内的景观与事件,他对景观的营造、对事件的讲述,清晰地呼应了本文开头从《游戏的人》一书中提取出的“游戏”的定义。面对“痛失中国”的危机,“游戏”的意义是:从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生活情境,由此敷衍出游戏般的乐趣,这构成了诗的崭新可能性。此后,在张枣看来,枯燥的日常之所以枯燥,因为它是个“无词讲述的艰辛故事”。若想把这份“艰辛”转化为“好的故事”,就需要找到“那些讲述的词”:“如果有了那些讲述的词,那么,我们的日常就会有一种风格,而如果有了风格,我们的日复一日就不再只是重复某种幸存,而会跳跃升腾,变成节日的庆典和狂喜。”转向游戏的张枣,正是要追求一种将日常转变成“节日”的写作。它脱胎于日常,但又必须有着与枯燥的生活不同的面貌与姿态,宛如一个狂喜的野人:
你猜那是说:“回来啦,从小事做起吧。”
乘警一惊,看见你野人般跳回车上来。
“野人”的形象构成了张枣“回归祖国”的方式与起点。在游戏中消遣了“乘警”这一能指,即解构了枯燥驯顺、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这场景分明脱胎于日常,但张枣给予我们一个迥异的逻辑和游戏规则,相比于此前“不愿去生活”的姿态,我们清晰可见此时张枣对“生活”之理解与言说发生了何等的转变。这首《祖国》仅仅透过其标题的修辞意图,便可视作张枣“返乡”之作的开始。面对“乘警”所隐喻的日常之法,“野人”般的“你”不啻是一个冒犯者,它对权力构成了挑衅与消解。然而读到这个形象,我们并不会感受到他如同日常生活中冒犯者般危险,而是觉得颇具喜感,仿佛庆典的嘉宾,凸显出冒犯、否定了日常逻辑的主体形象。实际上,这一“野人”形象,正是在元诗意义上构成了对张枣90年代中期诗歌转变的隐喻,它第一次揭开了“该怎样说:‘不’”的谜底:作为现代主义书写方式的核心,张枣在诗中说“不”的方式,不再如《护身符》那样,以概念性的言说来完成,而是从日常生活中为其找到一个个经验性的赋形。“野人”便是张枣这次诗歌转变中的第一个“不”字。由此,张枣这一阶段的诗歌呈现出变与不变的辩证情态:依然围绕着说“不”这一否定性诗学展开,且依然坚持用词讲述“好的故事”这一与语言之间发生本体性追问的语言观念,这两点处变不惊;面对变化了的日常生活,诗歌的音调由阴性变为更偏重阳性,诗歌内在景观与日常生活之间由提取唯美启示变为提取游戏伦理,这两点则是因时而变,力图突破生活的变化所造成的诗的危机。这种辩证昭示了张枣诗歌转变的意图与努力所在:依然坚持西方现代主义的书写方式与语言观念,但结束“不愿去生活”的“知音对话”模式,返回日常生活,并面对变化了的语境,为其在内在观念与文本面貌上找到新的回应方式。诗人的创作,也由此开启了后期阶段。
实际上,在张枣后期的一系列诗中,“不”字以“野人”式的形象,一次次得到经验性的赋形与命名。这些诗也由此被诗人塑造为一个个有趣的游戏景观。接下来,我们便要深入文本,对这些诗的游戏伦理进行细致的分析。总体而言,这些诗可被归纳成一个个说“不”的游戏,它包含了两个主要角色:罪犯和立法者;还有一个游戏规则:特赦。
三、说“不”的游戏
伴随着说“不”的调整,在张枣后期诗歌的游戏景观里,“不”从《厨师》中依旧略显抽象的“舌头的小野兽”被赋形成《祖国》中具体的“野人般跳回车上来”的“你”:“你”犯禁,让“乘警”受惊,构成日常之法的罪犯。这一形象也成了张枣后期诗歌中的主要角色。《祖母》中的“小偷”与《枯坐》中的“一对夫妇”是三位更加突出的罪犯。先看《祖母》:
四周,吊车鹤立。忍着嬉笑的小偷翻窗而入,
去偷她的桃木匣子;他闯祸,以便与我们
对称成三个点,协调在某个突破之中。
圆。
这里的“小偷”是个典型的罪犯,入室盗窃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常见的犯罪形态,它构成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祸事”。如果说这里的“小偷”是底层罪犯,那么《枯坐》中的夫妇则是一对携款潜逃的“社会精英”: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像一对夫妇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炒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要读懂这首《枯坐》,我们需要参考张枣的同名随笔,里面记录了这首诗的写作动机:“我想写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揣着偷税漏税的钱,隐姓埋名地逃到海南岛去了。他们俩特搞得来,待在一起很贴心,很会意,很好玩。比这个时代好玩多了,悠远多了。”这首诗里的犯罪在法学界有专门的学术研究,名曰“白领犯罪”(W hite Collar Crime),它由美国社会学教授E.H.萨兰瑟于1939年提出,目前已成为社会学、犯罪学及刑法学的专业术语。萨兰瑟给出的定义是:“‘白领犯罪’可以大体上界定为由具有体面身份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实施的犯罪行为。”《枯坐》中的“一对夫妇”与“小偷”虽然有着不同的法学意义,但与后者一样,也是当时中国日常生活中典型的罪犯。
从这样的日常认知中提取说“不”的赋形,正是后期张枣诗学的努力所在。在法学上了解过这两种罪犯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两首诗就会发现,张枣对他们的书写,虽然极具现实意义,但并非现实主义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仍是以现代主义书写方式表现出对当下语境的符号学指涉。张枣诗中的罪犯非但没有现实生活中危险贪婪、为祸社会的精神气质,反而让人亲近和喜爱,比如有学者在评论“小偷”时就说他是个“喜人的形象”,而《枯坐》中的那对白领夫妇,也给人一种怅惘情调。“小偷”“夫妇”作为能指,在诗中的所指恰好是“喜人”“悠远”这类含义,并非现实意义上危险的罪犯这一参符的含义。这就意味着,这些诗虽然极具现实指涉性,但书写方式上仍是现代主义的自律性命名。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命名在张枣诗中是否有方法论的信号呢?这便引出了说“不”游戏的规则——特赦。张枣后期诗歌中,明确出现“特赦”一词共有两处:
是的,无需特赦。得从小白菜里,
从豌豆苗和冬瓜,找出那一个理解来,
来关掉肥胖和机器——
我深深地
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移到窗前。
——《春秋来信》
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
那些否认对话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
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只笛子,这只给全城血库
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
一切都得仰仗它。
——《大地之歌》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枣对“特赦”的态度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在《春秋来信》中,诗人枯坐室内,虽然已经在蔬菜的隐喻中耐心寻找着“返乡”的可能,但“特赦”并未最终被抉择为游戏伦理中的具体规则。因此,这首诗笼罩在一种抉择的迷惘和等待的神往两相缭绕的精神氛围中,深深的矛盾感就凝聚在诗中。而在《大地之歌》里,诗人通过否定“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明确了自己的伦理抉择。并非巧合的是,与罪犯极具现实指涉意味一样,特赦也与当时中国的法制状况有着紧密的呼应。
特赦是赦免制度的一种,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中,都曾或繁或简的设置有赦免制度。另一种赦免是大赦。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历史看,从1959至1975年共实施了七次赦免,且都是特赦,对象是国民党及伪满洲国官员等战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只规定了特赦,未规定大赦。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未曾再执行过特赦,以致该制度逐渐被虚置。可以说,赦免制度作为“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乃至弥补法律不足之有效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既无实体规定,也无程序规定,赦免制度已被完全边缘化了”。
考察了这些背景后,我们会发现,张枣在后期最清晰、成熟的作品,比如《大地之歌》,对特赦的态度冥冥之中非常切中时弊:它如此边缘,在当时中国,“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大有人在。因此,后期张枣诗歌的生产性就在于,面对现实生活的缺失,他在游戏逻辑中说“不”,即宽容、施行仁政,将“特赦”设置为游戏规则,他的游戏伦理实际上是“特赦伦理”,现实中不能被容忍和赦免的罪犯,在他的诗歌里被及时赦免。正因为设定了“特赦伦理”,“小偷”“夫妇”在诗中才得以发生了参符的断裂,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危险,相反变得或喜人或悠远,成为张枣后期诗歌中的动人意象。在元诗意义上,如果说罪犯是“不”在张枣后期诗歌中的赋形,那么“特赦”则构成了说“不”的动力学。
至此,说“不”游戏中的最后一个角色就浮出水面了:立法者。它所携带的问题是,在说“不”游戏中,立法者如何呈现自身,拥有怎样的品质和能力,并引出了怎样的诗学问题。与罪犯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不同,立法者形象在诗中往往是缥缈的、高度象征化的,只在“特赦”发生的瞬间闪现:
我们得发明宽敞,双面的清洁和多向度的
透明,一如鹤的内心;
学界对张枣诗中“鹤”的理解,通常认为它要么是汉语性的象征,要么是纯诗的象征,总之隐喻了一种至高、缥缈、清洁而又精致的诗歌语言境界。如果联想到“笛子”的形象和声音,我们会觉得二者具有同构性。然而,研读过张枣后期诗歌的特质,并参照他给钟鸣信中要“更偏重更阳性的语调说话,以超越或包容我的精致”的说法,我们有理由判断,上文所引的“鹤”“笛子”所包蕴的意涵,在这一时段绝不仅限于张枣早期汉语性与纯诗的“精致之瓮”,它们在“特赦”的意义上,还代表了最高的善与正义,增添了政治哲学的维度。它们既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需要“发明”和“仰仗”的境界与对象,又是说“不”游戏的逻辑中,罪犯的注视与同情者,“特赦”的制定与执行者,即立法者。
本文将这些超凡脱俗、空白缥缈的意象视为说“不”游戏中的立法者,是有其政治哲学上的依据的。对于立法者这一身份,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专章讨论:“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这一职务缔造了共和国,但又决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可见,卢梭心目中的立法者为人类工作,却超越人类,在精神气质上呼应了张枣诗中的“鹤”“笛子”等意象。按照西方古典学的观点看,立法者蕴含着某种神学的意味,正像化鹤的吊车一样,其目光足以俯瞰众生:“这种超乎俗人们的能力之外的崇高的道理,也就是立法者所以要把自己的决定托之于神道设教的道理……”
对于张枣诗中的立法者,还需一点分辨:无论是西方古典学意义上的立法者,还是卢梭笔下的立法者,二者皆具有神圣性。而在现代主义写者这里,神圣秩序消解了,唯一悖论性地残留着神圣性之物便是空白本身。现代主义写者在对空白保持“反身性”(reflexivity)的信仰中才得以一次次完成写作。在后期张枣这里,立法者一方面在“特赦伦理”的层面具有现实指涉意义和政治哲学维度,另一方面,其书写模式仍然隶属于现代主义,立法者是对神圣的空白的命名。因此,后期张枣的说“不”游戏每次到了终结的瞬间,立法者总会显现出来,神一般地俯视一切,并转瞬即逝,比如《祖母》中的“吊车鹤立”,而《大地之歌》的结尾,“鹤”则又飞了出来,它作为神圣的空白,在显现的瞬间组织起世界的秩序:
飞啊。
鹤,
不只是这与那,而是
一切跟一切都相关;
……
这一秒,
至少这一秒,我每天都有一次坚守了正确
并且警示: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与《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结尾那个“此刻”相同,“这一秒”也是参符与能指、所指之间最终断裂,命名完成的现代主义时刻,但不同的是,这里的“这一秒”是遵循说“不”游戏完成命名的时刻。“这一秒”,罪犯得到赦免,立法者俯视世界。“这一秒”的正确性,在《祖母》结尾被命名为“圆”,在《大地之歌》里则是“至高无上”,但无论如何,对它的信仰只可能是反身性的,因为它的立法者是神圣的空白。在后期的另一首诗《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结尾,张枣写下这样的诗句:“源自空白,附丽于空白/信赖它……”
作为现代主义诗学之核心的否定性,在张枣后期的诗中依然延续着,但以说“不”游戏的崭新命名方式得到文本上的实现。围绕着罪犯、立法者与特赦,说“不”游戏挪用了日常生活的图景与经验,但以游戏的逻辑进行了重构。说“不”游戏是后期张枣延续他所信赖的现代主义诗学策略,是针对当下语境之转变而发明的新型元诗姿态。
四、“好的故事”与“游戏”的限度
按照卢卡奇、赫勒、列斐伏尔等日常生活学派的观点,日常生活貌似混乱随意,充满了狂欢化和偶然性,但作为“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也是被权力的操纵所充斥和压抑的对象,相比于显性的权力范畴,它以更隐微的方式对所有生活着的人构成威胁与压制,其中不断制造生存的缺憾与困难。或许正因如此,游戏才得以为许多人提供了弥补之机。抛开以“拟像”理论分析当下日常与游戏之间日益模糊的界线这一点暂且不谈(这实际上更能揭示游戏逻辑的当下限度),游戏与日常生活的差异一言以蔽之,身处游戏能获得某种想象性的圆满。循着这游戏的逻辑,张枣后期诗歌的结尾往往如下:
泪的分币花光了,而泪之外竟有一个
像那个西湖一样热泪盈眶的西湖,
黎明般将你旋转起来。
——《西湖梦》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枯坐》
正如这些结尾所暗示的,后期张枣致力于构筑一种神往与圆满,这正是针对他“痛失中国”的命名危机,针对变化了的语境,针对日常生活的不圆满。由此,张枣后期诗歌正如他在散文《枯坐》中所讲,“从枯坐开始,到悠远里结尾”,要讲述一个个“鲁迅似的‘幽静美丽有趣’的‘好的故事’”。《好的故事》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张枣在分析这篇散文诗时的观点也颇似对自己后期诗歌的夫子自道:“生存的缺在是通过文本来弥补的,而通过这种弥补,又会让我们向往一种实在的生活场景,这就是《好的故事》的意义。”可见,张枣对鲁迅《好的故事》的理解侧重于对完美梦境的执迷,并以想象性的方式弥补“生存的缺在”,与现实达成和解。而张洁宇对这篇散文诗的解读却与之不同:在分析文中的梦境之前,张洁宇先谈论了比《好的故事》仅仅晚八九天而作的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著名的“十景病”与悲剧、喜剧论断。鲁迅原话是:“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关于“十景病”,张洁宇认为:“所谓‘十景病’,只是传统中国文化心理痼疾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代表着一种自欺、一种对‘大团圆’式的‘精神胜利法’的沉迷。”“若非破除‘十景病’,‘睁了眼看’,看到那些‘毁灭’与‘撕破’,并借此真正认识它们背后的‘有价值’或‘无价值’的人生,中国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深刻的艺术和文学。”经过如上梳理,张洁宇对《好的故事》的解读是:“把二者相联系起来看,‘好的故事’正是在另一种体式中以一个更加直观、感性、形象的方式,‘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二者的分歧无疑是重要的。在张洁宇这里,鲁迅笔下这“好的故事”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显现是为了“撕破”的需要,并由此揭示现实的不圆满。而在后期张枣那里,“好的故事”则是以游戏伦理打碎现实的符号秩序,由此努力重构一种命名上的圆满,最终弥补“生存的缺在”。并不是说“撕破”一定是更深刻的文学形式,而是说既然后期张枣希望将当下日常纳入诗学关切之中,以促成其元诗姿态的新变,那么当下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与真实性,其内在观念构造、情感实践以及权力机制等,理应在新的元诗姿态中得到转化与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后期张枣受到“荷兰人的书”的启发,将与现实逻辑迥异的游戏伦理作为其元诗姿态的崭新言说方法,其内在限度便值得注意。游戏伦理固然能以“参符的断裂”这一命名方式对现实说“不”,也能完成对诗人既有元诗模式的突破,作为一种诗学方法它并无问题。问题是,它对于后期张枣希望克服“痛失中国”的危机、将当下性纳入追问的抱负来说,有太多局限。“小偷”“夫妇”在游戏中被立法者特赦,诗歌被改写成“好的故事”,“生存的缺在”被想象性地弥补,在这些诗里,当下性一次次被视作有待重构的对象,并且被游戏性地重构,获得圆满。如此,将当下性纳入元诗的意义又是什么?
朱朱在写给张枣的悼亡诗《隐形人——悼张枣》中说:“我惊讶于你的孩子气,膨胀的甜蜜。”很多回忆文字也提及张枣日常生活中“孩子气”的细节。然而作为一位极有头脑的诗人,张枣并非没有注意到“生存的缺在”与语境的变化,否则,“痛失中国”一类的意识便无从出现,也不会说“现实都挫折了,为什么诗歌就该成功呢”这样的话了。而且,张枣也自觉地希望能面对变化了的语境,发明出有效的诗歌方法,否则,他继续提取80年代的“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就好,无须在“荷兰人的书”的启发下推演出游戏伦理这一新型元诗姿态了。但问题在于,既然要将当下语境纳入命名,那么当下语境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便有必要成为决定命名形态的内在元素。也就是说,后期张枣既然希望在元诗姿态与当下性之间发展一种追问关系,就不应将“生存的缺在”本质化为某种抽象的命题,而应该追问这样的结构性问题:“生存的缺在”在当下究竟如何发生与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讲,《醉时歌》中的两行诗便值得深思:
那醉汉等在那空电话亭边,唱啊唱:
“远方啊远方,你有着本地的抽象!”
“醉汉”的唱词,颇能构成对后期张枣诗歌中当下语境的隐喻:本该具有特殊性与具体性的“本地”,在游戏伦理中却成为抽象的“本地”,同构于那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远方”。换句话说,当下语境在后期张枣游戏伦理的书写中,明里是从当下性进入,暗地里却又从“远方”出来。这一过程中,围绕着当下性原本丰富的诗歌可能,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消解掉了。于是,张枣后期的诗往往呈现为“孩子气”的圆满与“醉汉”的唱词,现实的挫折作为追问的初衷,则得不到有效的回应了。尽管这些诗在审美性上往往无可指责,比如《醉时歌》这两行诗有着完美的腹韵和尾韵,正因如此,其局限也才更加遗憾。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张枣的元诗姿态依次体现为提取“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与构建“知音对话”两种模式。它们要么从集体主义的时代话语和音调中脱离出来,完成“对封闭的语言机制和为这语言机制所戕害的我自身”的反叛,要么克服孤悬海外的枯燥,完成汉语性与现代性的文化沟通使命。这说明,有效的元诗姿态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语言风景的内面化与模式化,而是需要诗人针对个人境遇与整体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命名的模式。因此,90年代中期的张枣在“荷兰人的书”的启发下,将元诗姿态自觉调整为游戏伦理后,这一选择的内在得失限度便值得反思。“好的故事”如何可能、如何以更为深入当下性肌理的方式去追问,而不只是以命名上的圆满来想象性弥补“生存的缺在”?汉语性也并非本质化的概念,其中哪些资源更能与当下性构成对话,从而突破“远方”与“本地的抽象”?到了更为当下的网络虚拟时代,游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某些新变,这能否突破张枣游戏伦理的限度,为元诗提供更为开阔的追问逻辑?凡此种种,都是探究张枣90年代中期这次诗学转变时值得反思与打开的面向。他的追问“圆梦”之处,正构成了当代新诗有必要继续说“不”与追问的起点。
① 臧棣:《可能的诗学:得意于万古愁——谈〈万古愁丛书〉的诗歌动机》,《名作欣赏》2011年第15期。
②③ 约翰·赫依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第131页。
④ 颜炼军:《张枣生平与创作》,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页
⑤⑦⑧[34]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张枣随笔选》,第176页,第172页,第174页,第192页。
⑥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⑨ 参见詹明信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24—245页。
⑩ 亚思明:《张枣的“元诗”理论及其诗学实践》,《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11] Zhang Zao,,PhD Dissertation,Tübingen:Eberhard-karls-Universität Tübingen,2004,S.34.这是张枣的德语博士学位论文,第二章研究鲁迅的《野草》。译文出自张枣:《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上)》,亚思明译,《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6期。
[12] 张枣:《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上)》。
[13][19] 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第232页。
[14] 张枣:《护身符》,《张枣的诗》,第192页。
[15] 张枣:《今年的云雀》,《张枣的诗》,第198页。
[16] 张枣:《空白练习曲》,《张枣的诗》,第200页。
[17] 张光昕:《茨娃密码:张枣诗歌的微观分析》,《诗探索》2011年第3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8][20] 黄灿然:《访谈张枣》,《飞地》第3辑,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
[21][43] 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第88页。
[22] 张枣:《厨师》,《张枣的诗》,第239页。
[23][36][37] 张枣:《庆典》,《张枣随笔选》,第18页,第17页,第17页。
[24] 米歇尔·德·塞托、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日常生活实践2:居住与烹饪》,冷碧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337页。
[25] 张枣:《一则诗观》,《张枣随笔选》,第59页。
[26][41][61] 张枣:《枯坐》,《张枣随笔选》,第1—2页,第6页,第6页。
[27][32][33] 陈东东:《亲爱的张枣》,《我们时代的诗人》,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第133—134页,第135页。
[28] 张枣:《祖国丛书》,《张枣的诗》,第185—186页。
[29] 张枣:《海底被囚的魔王》,《张枣的诗》,第213页。
[30] 张枣:《销魂》,《张枣随笔选》,第28页。
[31] 黄灿然:《张枣谈诗》,《飞地》第3辑。
[35] 张枣著,钟鸣编:《鹤鸣瘞:张枣致钟鸣书简》,未刊稿。
[38] 张枣:《祖国》,《张枣的诗》,第242页。
[39] 张枣:《祖母》,《张枣的诗》,第247页。
[40][60] 张枣:《枯坐》,《张枣的诗》,第289页,第289页。
[42] E.H.萨兰瑟:《白领犯罪》,赵宝成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44] 张枣:《春秋来信》,《张枣的诗》,第262页。
[45][48][56] 张枣:《大地之歌》,《张枣的诗》,第270页,第271页,第272页。
[46] 郭金霞、苗鸣宇:《大赦·特赦:中外赦免制度概观》,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47] 阴建峰:《现代赦免制度论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9] 参见颜炼军:《祖母的“仙鹤拳”——读张枣的〈祖母〉》,颜炼军编:《化欧化古的当代汉语诗艺:张枣研究集》,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349页;张伟栋:《“鹤”的诗学——读张枣的〈大地之歌〉》,《化欧化古的当代汉语诗艺:张枣研究集》,第369—382页。
[50] 张枣《大地之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德国作曲家马勒的交响曲《大地之歌》,该曲歌词七首取自汉斯·贝特格(HansBethge)中国唐诗集德文版《中国笛》,故张枣笔下的“笛子”,灵感应出于此处。
[51][53]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第56页。
[52] 参见路易斯:《城邦诸神及其超越》,张清江译,林志猛编:《立法者的神学——柏拉图〈法义〉卷十绎读》,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
[54] “反身性”概念,意味着现代性对秩序保持修正的敏感性。联系到本文,则与否定性、永恒的追问意义相关。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5] 后期张枣笔下以“鹤”为代表的立法者,在现代主义书写的意义上,与晚期里尔克笔下的“天使”具有同构性。二者在以“空白”为秩序的书写模式中,都代表了“最高的位格”。参见张伟栋:《“鹤”的诗学——读张枣的〈大地之歌〉》,《化欧化古的当代汉语诗艺:张枣研究集》,第380页。
[57] 张枣:《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张枣的诗》,第281页。
[58]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59] 张枣:《西湖梦》,《张枣的诗》,第252页。
[62] 张枣:《〈好的故事〉讲评》,《张枣随笔选》,第157页。
[63]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64][65] 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页,第154页。
[66] 朱朱:《隐形人——悼张枣》,《我身上的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59页。
[67] 张枣:《论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的发展与延续》,颜炼军编:《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45页。
[69] 张枣:《醉时歌》,《张枣的诗》,第283页。
[70] 钟鸣:《笼子里面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71] 参见邓剑:《中国电子游戏文化的源流与考辨》,《上海文化》2020年第12期;欧阳友权:《多维视野中的网络游戏》,《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