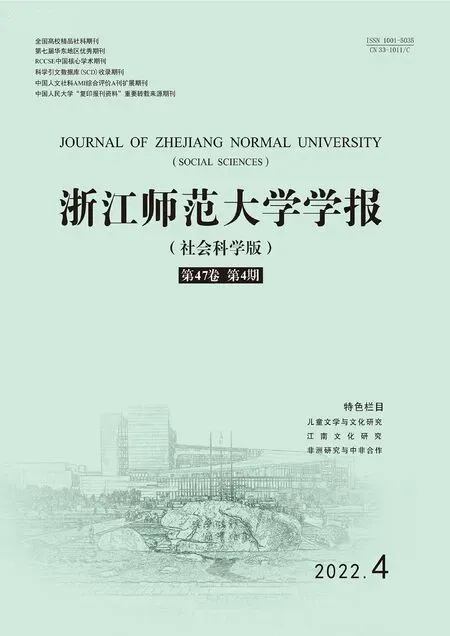音韵与气韵:宋代韵书的文化意涵
黄金灿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宋代韵书是中国传统音韵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更是音韵文献史上绕不开的高峰。作为一个整体,宋代韵书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俗语云“尝一脔之肉,可知一鼎之味”,宋代韵书文化是宋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将宋代韵书的文化意涵发掘出来,有助于更具体地感知宋代文化的气象和神韵,推动“宋韵文化”研究的深入。目前学界关注宋代韵书,主要还是看重其语音史研究价值。其实宋代韵书的价值远远溢出于语音研究之外,从宋代韵书看宋代文化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正如李文泽先生所言,宋代政治、学术、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成就了宋代音韵学,“音韵学的发展又积极推动了宋代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代学术风范”。[1]论中强调了宋代音韵学与宋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颇具启发性。不过,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①虽然类似的宏观认识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但是宋代音韵学与宋代文化互动的具体情形和路径仍有进行更细致展示的空间。本文尝试通过描述宋代韵书的特色,发掘其文化意涵,为相关研究的推进提供一点参考。
一、宋代韵书文化面面观
宋代韵书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具有承前启后、接力递修、精益求精等鲜明特色,形成了意蕴丰富的宋代韵书文化,具有从多方面考察、阐释的价值。
(一)承前启后
关于承前启后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广韵》上。《广韵》上承《切韵》《唐韵》而来,继承了隋唐时期一众音韵专家的研究成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广韵》撰人的著录就体现了这一点:
隋陆法言撰。开皇初,有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共为撰集,长孙讷言为之笺注。唐朝转有增加。至开元中,陈州司法孙愐著成《唐韵》。本朝陈彭年等重修,《中兴书目》云不知作者。案《国史志》有《重修广韵》,题皇朝陈彭年等。[2]89-90
这本是《广韵》的解题,却题曰“隋陆法言撰”,显得颇为突兀,且“与下文‘共为撰集’句弗贯”,[2]89-90令人怀疑是否存在文字脱误。实际上,只要比对《广韵》卷首文字就会发现,从“隋陆法言撰”至“陈州司法孙愐著成《唐韵》”数语乃是陈振孙对《广韵》卷首文字的直接概述。《广韵》卷首景德、祥符敕牒二通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陆法言撰本,长孙讷言笺注。仪同三司刘臻,外史颜之推,著作郎魏渊,武阳太守卢思道,散骑常侍李若,国子博士萧该,蜀王咨议参军辛德源,礼部侍郎薛道衡,以上八人同撰集。郭知玄拾遗绪正,更以朱笺三百字;关亮增加字;薛峋增加字;王仁煦增加字;祝尚丘增加字;孙愐增加字;严宝文增加字;裴务齐增加字;陈道固增加字。更有诸家增字及义理释训悉纂略备载卷中,勒成一部进上。[3]
这里提及的人物都是对《广韵》的前身《切韵》《唐韵》有关键贡献的学者,刘臻、颜之推等八人为最先敲定《切韵》体例者,陆法言为撰《切韵》定本者,长孙讷言为笺注《切韵》者,郭知玄以下为拾遗绪正、增加字者。在增加字者当中,又有单独成书者,例如王仁煦本的《切韵》全名为《刊谬补缺切韵》,孙愐则在《切韵》基础上增添更多释训内容,直接编成《唐韵》一书。《广韵》编纂者所做的工作就是将上述各家成果都适当吸收后“勒成一部”,这样看来,陈振孙的著录不但并无不妥,反倒更能体现《广韵》继承前人的渊源统绪。
上承《切韵》《唐韵》而来的《广韵》,其后又为《集韵》的编纂奠定了基础。《集韵》十卷,《直斋书录解题》曰:“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比旧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2]91这里“比旧增”的“旧”字,是指旧《韵》,即在《集韵》之前成书的《广韵》。因为在《广韵》卷首有“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单指所收韵字的总数,不包含其注释字数)的说明,这个数字正是《集韵》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的基数。刊于《集韵》卷首的《韵例》也有说明:
先帝时,令陈彭年、丘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戬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4]
这里“法言《韵》”即是《切韵》,陈彭年、丘雍因之“刊益”而成的则是《广韵》,它是宋祁、郑戬等人“同加修定”的对象,修订成的新《韵》就是《集韵》。随后《韵例》还列举了“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说者取之,不然则否”等共“十二凡”,来表明其在体例上的创新;最后又有“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的说明,所谓“新增”,也正是基于《广韵》所收韵字的总数而言。[4]以上这些足以表明承前启后确实是以《广韵》为代表的宋代韵书的一大特色;尤为可贵的是,这种“前”“后”并不是韵书间简单的时序相次,而是有着明确的文献记载与切实的文本关联性作为证明。
(二)接力递修
关于接力递修这一点,《礼部韵略》体现得最为明显。《直斋书录解题》曰:“《礼部韵略》五卷、《条式》一卷。雍熙殿中丞丘雍、景德龙图阁待制戚纶所定,景祐知制诰丁度重修,元祐太学博士增补。其曰‘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2]91陈氏以《礼部韵略》为“字书声韵之略”,表明是书并不像《集韵》一样“务求该广”,而是旨在体现“举子诗赋所常用”的实用性与时效性,这就势必需要对它进行接力递修。据陈氏记载可知,《礼部韵略》自丘雍、戚纶编定后,又先后经历了一次重修和增补,其实只是众多递修中时代比较靠前且规模相对较大的两次而已。陈氏著录时未明言“元祐太学博士”为谁,这一点《礼部韵略条式》中有记载:
元祐五年……准都省送下太学博士孙谔等状:“朝廷近颁贡举法,经义之外添诗赋一场,窃惟贡举条制,诗赋格式该载或有未尽者,今举人初习声律,动多疑虑……谨采摭经传及《广韵》《礼部韵》校对得字,及诗赋式,各具解释……今将孙谔等所申事理并于逐项内勘当讫,伏候指挥。七月九日三省同奉圣旨,依礼部所申,仍先次施行。[5]1a-2b
可见孙谔这次修订也是很详细的,而且修订程序也极为严格。通过这次修订,进一步缓解了“虽主司考校,亦无定论,临时率以私意去取”与“往往收平凡而退优异”等科举弊端。[5]1b-2a《礼部韵略条式》所载的递修事件一直持续到南宋宁宗朝,嘉定十六(1223)年嘉兴府府学教授吴杜进言:
今《礼部韵略》虽已经元祐五年太学孙博士陈请校勘一次,及后来间有增附而多疏略,疑贰相传,无所折衷。今幸以小官,职城阙之学,日课月试,朝夕与士子接,又得以商榷订正,尽去其隐僻不该押韵,而遴选其词赋中引用者,才六十七字,目以《韵略续补》,谨具状申,伏望详览。[5]64b-65a
吴杜进呈《韵略续补》后,由国子博士钟震等人聚议、看详,由于“吴杜所申《韵略》六十七字,若广引训释及添入不紧要字,即与《广韵》无异”,[5]65a最终决定只允许将其中的三个字修入《礼部韵略》。这一次修订也颇具代表性,且对孙谔以降接续递修《礼部韵略》的历史有所回溯,值得重视。虽然吴杜的《韵略续补》篇幅不大,但能够看出他一开始有意将之视为相对独立的著作,只不过最终只被国子监采用了三个字,似乎也就没有了独立成书的必要。
在宋人对《礼部韵略》进行接力递修的过程中,尚有不少独立成书的成果出现。例如杨伯嵒撰有《九经补韵》一卷,《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〇著录有伯嵒《自序》及俞任礼《后序》各一篇,分别有云:
《礼部韵》一书,政为声律举子设,绍兴间三山黄进士尝补选进上,乃亦阙略。如《礼记》“敛,般请以机封”,《毛诗》“鳣鲔发发”之为“鲅鲅”,《周礼》“舍采,合舞”之为“释菜”。或音义未顺,或非韵语可押,岂可任后学之传讹?乃即经释搜罗,萃为一编,于嘉定十七年冬而书成焉。
《礼部韵》以“略”言,多隘之而议欲增,自元祐国子博士孙谔随乞添收,其后黄启宗有《补韵》,吴棫有《韵补》《补音》,毛晃有《增韵》,张贵谟有《韵略补遗》,近世黄子厚、蒋全甫各有论。泳斋先生《补韵》,凡九经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订分汇,各疏其下。[6]
可见此书实为增补《礼部韵略》而作,以《九经补韵》为名,意在强调其以“九经”所见之字补《礼部韵略》之未备的特色。《自序》《后序》皆回溯了《礼部韵略》的接力递修历程,尤以俞任礼之《后序》所言最详,孙谔之后,黄启宗、吴棫、毛晃、张贵谟、黄子厚、蒋全甫的贡献皆为拈出,实为《礼部韵略》接力递修特色的有力佐证。
类似的著作还有不少,不妨再举5部:
1.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
2.欧阳德隆、易有开《押韵释疑》五卷。《直斋书录解题》赞其“凡字同义异、字异义同者皆辨之,尤便于场屋”。[2]95本书适用于“场屋”,表明其“释疑”的对象实际就是作为官韵的《礼部韵略》。
3.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五卷。《续文献通考》曰:“《押韵释疑》,宋绍定时庐陵进士欧阳德隆所撰,至景定甲子,守正增修之。”[6]此书是对《押韵释疑》一书的“增修校正”,其接力递修的特色更为显著。
4.《附释文互注韵略》五卷。《直斋书录解题》曰:“以监本增注而释之。”[2]95此书是《礼部韵略》的又一修订本,所谓“监本”,是指国子监刊本《礼部韵略》。
5.刘孟容《修校韵略》五卷。《直斋书录解题》曰:“以《说文》《字林》《干禄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佩觽》《复古编》等书修校。”[2]94此书亦是为“修校”《礼部韵略》而作。
需要强调的是,接力递修并不等于接力递增,更不等于递相求奇。秦昌朝有《韵略分毫补注字谱》一卷,将文字形体之学融入《礼部韵略》中,就受到陈振孙的批评:“窃谓小学当论偏傍,尚矣,许叔重以来诸书是也。韵以略称,止施于礼部贡举,本非小学全书,于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尽天下之字,而欲使科举士子尽用篆籀点画于试卷,不几于迂而可笑矣哉!进退皆无据,谓之赘可也。”[2]95陈氏所论甚允。《礼部韵略》是因科举考试的实际需要而编,其本意欲求“略”,非求“备”,以之为基础来研究字形,确实难免捉襟见肘、进退失据之讥。当然,如果不考虑科考实用性,仅将之当作个人学术兴趣钻研之,也未尝不可。正如陈耆卿《代跋钱君韵补》所言:
学者例以《监韵》为师,《监韵》所不载,不之味也。溪南钱君,味乎世之所不味,旁罗周抉,根括蔓引,足以鸠棼纫阙,与前人分功。甚矣,其志完而力富也。其老犹尔,而况其壮之日哉!余与君别三年,吏氛压首,览卷心目为开,颇恨路远,不能效汉人载酒之问,而徜徉其间也。[7]
陈耆卿认为真正的学者不应“例以《监韵》为师”,更应求知于“《监韵》所不载”。他推崇的是“味乎世之所不味”的学术个性和通过“旁罗周抉,根括蔓引”的努力获得“鸠棼纫阙,与前人分功”之成绩的治学过程。用这种态度来研究《礼部韵略》固然无益于科举士子,却足以答同道之人的“载酒之问”,获得“徜徉其间”的学问之乐。这种自得其乐的治学态度与宋代文化精神也是极为契合的。
通过上述举证可见,虽然《广韵》主要体现宋代韵书承前启后的特色,但也能体现接力递修的特色;同样,虽然《礼部韵略》主要体现宋代韵书接力递修的特色,但也能体现承前启后的特色。
(三)精益求精
在承前启后与接力递修的合力作用下,宋代韵书精益求精的特色也就很自然地被体现出来。宋人在韵书领域的持久经营,不仅创造了韵书的繁荣,还进一步将整个韵学推向精深化。两宋时期先后出现的韵学著作颇多,例如:
1.旧题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是书为图解韵书反切而作,接近等韵学。
2.张有《五声韵谱》五卷。张有还曾撰《复古编》二卷,是其字学代表作,与此书可互补。
3.吴棫《韵补》五卷。《直斋书录解题》曰:“取古书自《易》《书》《诗》而下,以及本朝欧、苏凡五十种,其声韵与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讲多用其说于《诗传》《楚辞注》,其为书详且博矣。”[2]92吴氏此书主要价值在于滥觞古音之学。
4.杨中修《切韵类例》上下篇。《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切韵类例序》曰:“科别户分,著为十条,为图四十四,推四声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语不合之讹,清浊轻重,形声开合,梵学兴而有华竺之殊,吴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释象,纤悉备具。”[8]302此书后世不传,其以《集韵》为基础,“推四声子母相生之法”,颇有特色。
5.王宗道《切韵指玄论》三卷。《郡斋读书志》认为其最大特色在于“论字之五音清浊”,[9]卷一下,16a可知此书亦以审音见长。
6.僧宗彦《四声等第图》一卷。是书乃“《切韵》之诀也”,[9]卷一下,16a《续通志》曰:“《崇文总目》载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僧宗彦《四声等第图》一卷。横有三十六母,纵有四等,即《七音韵鉴》所由昉也。”[10]478又曰:“古人切字不分等第,自僧宗彦撰《四声等第图》,而切韵字因之,因立类隔、交互诸门法。”[10]537可见此书亦为等韵学著作,对后世影响颇大。
综上,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宋代韵书,不仅推动了宋代韵学的深入发展,还凭借其承前启后、接力递修、精益求精的鲜明特色,彰显了包容性、连续性与精深性等鲜明的文化意涵,这些意涵与宋代文化的整体精神无疑是同频共振的。
二、宋代知识体系中的“韵书型”类书
笔者提出“韵书型”这个概念,是用以描述宋代知识体系中本身不被视作韵书却具有韵书的框架结构的文献类型,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韵书型字书与韵书型类书。这两种文献类型很好地展现了宋代韵书文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韵书与宋代知识阶层的文化生活关系密切,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日常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韵书的指导与辅助。这就使韵书的普及程度、受重视程度相对高于同样具有工具书作用的字书与类书,促使它们将知识的组织形式向韵书靠拢,从而产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韵书型字书与韵书型类书。
宋代的韵书和字书在知识的组织形式上差别很大,但在功能上却高度互补,故而二者经常配套施行。宋代字书的代表《类篇》与韵书的代表《集韵》之间就是这种关系。《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曰:“丁度等既修《集韵》,奏言今添字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乞委修韵官别为《类篇》,与《集韵》并行。”[2]91顾野王《玉篇》原与《切韵》相参协,甚至仍大致可与《广韵》相参协,但丁度等人既修《集韵》之后,增字繁多,故必须新修能与之相参协的《类篇》。《类篇》按部首排列,《集韵》按韵部排列,可以分别满足“因声求字”与“因字求声”两种不同需要,具有极高的功能互补性,这是宋代韵书与字书关系的常态。
(一)韵书型字书
宋代另有相当数量的字书,直接采用韵部分类,用韵书的框架容纳极具字学专业色彩的内容,形成非常典型的韵书型字书。据笔者考察,此类字书有:
1.夏竦《新集古文四声韵》五卷。莫友芝曰:“黄伯思《东观余论》云‘政和六年冬,以夏郑公《集古韵》及宗室克继所广本二书参写,并益以三代钟鼎彝器款识,及周鼓秦碑古文印章碑首,并诸字书有合古者益之,以备遗忘’云云,是宋人《古文篆韵》有三,今唯英公集者有新安汪启淑刊本,赵、黄二本则皆无传。”[11]可知是书为一部依四声韵部顺序编次古文篆字的韵书型字书,且有前人两部著作作为新编的基础。
2.薛尚功《钟鼎篆韵》七卷。元熊朋来《钟鼎篆韵序》云:“《钟鼎篆韵》,自琱戈、钩带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称钟鼎,贵彝器也。……政和中,王楚作《钟鼎篆韵》矣,薛氏承龙眠之旧图,其帖始于琱戈,因王楚之成书,其韵谓之重广,乙卯癸亥,一再脱槁,宜无遗字。……临江杨信父,参订旧字,博采金石奇古之迹,益以奉符党氏《韵补》,夏、薛所未收,征余为序,其篆则夏商周秦之篆,而韵则《唐韵》也。”[12]可知是书为依《唐韵》编次夏商周秦之篆字的韵书型字书,且经过多次重广、增补。
3.陈天麟《前汉古字韵编》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取《汉书》所用古字,以今韵编入之。”[2]94编者将《汉书》中的古字“以今韵编入”,可见也是一部韵书型字书。
4.刘球《隶韵》十卷。洪适《书刘氏子隶韵》曰:“予初见刘氏子《隶韵纪原》,凡隶释碑刻无一不有,惊其何以广博如是。及观其书,乃是借标题以张虚数,其间数十碑,《韵》中初无一字,至他碑所有,则编次又甚疏略。”[13]卷六十三,11a是为一部按韵编排隶字的韵书型字书。
5.洪适《隶韵》。《隶韵序》曰:“篆古钟鼎款识皆已有《韵》,独隶刻世所艰得,后学提笔辄书,增点减画,变易偏旁,漫不求是。予家藏汉代庙中之碑、幽堂之铭、墓门之阙与遗经断石,凡百有九十二种,惧难聚而易失也,因辑以为《韵》,与我同志者,必有取焉。”[13]卷三十四,9a按洪适《隶韵》或未成书,然据自序可知亦为韵书型字书。
6.谢雩《正字韵类》五卷。陈傅良《谢季泽正事韵类序》题此书名作《正事韵类》,又目此书为“字学偏旁训故”之作,[14]可推定此书亦是按韵编排之字书。
7.林春山《草韵》。黄仲元《题漫翁林春山草韵序》引林氏语曰:“韵二百有六,字一万七百有奇,世间万书,横写竖写,词人墨客,长歌短歌,尽在个里。”[15]此书是一部将草书字体按韵编排的韵书型字书。
8.黄邦光《群史姓纂韵谱》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谱牒类曰:“永福黄邦先宋显撰。凡史传所有姓氏皆有韵,类聚而著其所出。”[2]230可见此书是专录姓氏字并按韵编排的韵书型字书。按此书编者《直斋书录解题》曰“黄邦先”,误;据宋梁克家《三山志》知当作“黄邦光”,名“邦光”与字“宋显”相合。
上述诸书的编者,已经通过题名的“韵”字,标示出了韵书型字书的形制特征。但也有只在题名中标明为字书,实际是韵书型字书的。例如娄机的《汉隶字源》与《班马字类》就是如此。《汉隶字源》六卷,《直斋书录解题》曰:“以世所存汉碑,三百有九韵类其字,魏碑附焉者仅三十之一。首为《碑目》一卷,每字先载经文,而以汉字著其下,一字数体者并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从出。”[2]94可见是书为按韵编排的字书。《班马字类》二卷,《直斋书录解题》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韵类之。”[2]94也是一部韵书型字书。宋楼钥与清四库馆臣对此书都有较高评价:
古字不多,率假借以为用……而缀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资华藻,片言只字,施之铅椠,自有一种风味,故《诲蒙》《汉隽》等书,作者不一,此书更取《史记》之字,合为一编,从韵类分,粲然可睹,娄君之志勤矣……(楼钥《攻媿集》卷五十三《班马字类序》)[16]734-735
其书采《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以四声部分,编次虽与《文选双字》《两汉博闻》《汉隽》诸书大概略同,而考证训诂、辨别音声,于假借、通用诸字,胪列颇详,实有裨于小学,非仅供词藻之挦撦……”(《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一)[17]351
楼钥认为古字、奇字不仅有字学价值,还有文学价值,即“缀文之士”可以“摘取奇字以资华藻”,只需将“片言只字,施之铅椠”,就可“自有一种风味”。对于此书“从韵类分,粲然可睹”的简捷高效的体例,楼钥也颇为赞赏。而四库馆臣虽然也认同其“供词藻之挦撦”的文学价值,不过更看重的是其因“考证训诂、辨别音声”而“有裨于小学”的文字、音韵价值。楼钥和馆臣对《班马字类》价值的总结相当准确,可以说“资华藻”“裨小学”是所有宋代韵书型字书的共同价值。
(二)韵书型类书
如果说宋代的韵书型字书还主要以征实的知识性为主,那么宋代的韵书型类书则在知识性之外,又多了不少文学性、趣味性。张孟《押韵》一书,是宋代出现较早且影响较大的一部韵书型类书。《郡斋读书志》曰:“右皇朝张孟撰。缉六艺、诸子、三史句语,依韵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9]卷一下,17a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四曰:“张孟《押韵后序》曰:‘《押韵》肇自颜鲁公,迄于圣宋。’盖孟在天圣中,准宋《韵》重编集也。”[18]可见此书是以宋代官韵为框架,将“六艺、诸子、三史”中的语句,依韵部、韵字的顺序逐次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乃是用韵书的框架排纂类书的内容,为典型的韵书型类书。此书颇受宋人重视,王楙《野客丛书》就曾频繁引述(见卷十一“借书一鸱”条、卷十二“痟消二义”条、卷二十九“不磷不缁”条),可见至少在王楙生活的南宋前期,《押韵》一书在读书人中已流行。又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乾道癸巳冬,有大理人至横山采购,所列购书清单中,张孟《押韵》与《切韵》《玉篇》等书并在。[19]9067-9068即便是当时的“化外之地”,也希望购得张孟《押韵》一书,其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韵书型类书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韵类事”,不过根据“事”的不同又可细分为不同的小类,像张孟《押韵》就属于经部、史部、子部材料都收的一类。类似的还有袁毂《韵类题选》一百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类书类,曰:“以韵类事,纂集颇精要,世所行《书林韵会》,盖依仿而附益之者也。”[2]426另,《通志》卷六十九艺文略第七有《续韵类选》三十卷,不著撰人,其前为《韵类题选》,后为《庆历万题》,当是宋人补续《韵类题选》之作。又有王百禄增辑《书林事类韵会》一百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类书类曰:“《书林韵会》一百卷。无名氏。蜀书坊所刻,规模《韵类题选》而加详焉。”[2]428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子部曰:“考宋学士《翰苑别集·韵府群玉题后》云:‘《韵府群玉》乃因宋儒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钱讽《史韵》等书而附益之’云云,则是书乃百禄所增辑也。”[20]可见,后世声名甚著的《韵府群玉》正是承袭此书及《回溪史韵》而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又,或云宋许冠所编《书林韵海》一百卷。《郡斋读书志》曰:“右不题撰人。分门依韵,纂经史杂事以备寻阅,或云皇朝许冠所编。”[9]卷三下,24a这些韵书型类书动辄百卷,且多“纂经史杂事”,收事范围都非常广泛。
此外还有专门收录某一类材料的。例如,郑潾《经语韵对》收录的都是经语,而钱讽《回溪史韵》则专收史部材料。《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附志》小学类曰:“《史韵》四十九卷。右回溪钱讽正初所编也。依唐韵分四声,而以十一史之句注于下。”[9]卷五上,13b《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类书类亦曰:“《史韵》四十九卷。嘉禾钱讽正初撰。附韵类事,颇便检阅。”[2]427宋濂《韵府群玉后题》曰:“《韵府群玉》一书……乃因宋儒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钱讽《史韵》等书,会粹而附益之,诚有便于检阅。”[21]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一《回溪史韵二十三卷提要》曰:“宋赵希弁《读书附志》以为‘依《唐韵》分四声,以十七史之句注于下’,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其‘附韵类事,颇便检阅’。盖宋人兔园册,类摘双字编四声,以便寻检,而回溪独采成语,多至三四句,未尝割裂原文,洵著书之良法也。”[22]《回溪史韵》与《书林事类韵会》一起成为元代著名韵书型类书《韵府群玉》的前身,其“未尝割裂原文”的体例又被阮元赞为“洵著书之良法”,足见其影响之大。又据范镇《羲叟检讨墓志》载,刘羲叟曾撰《刘氏辑历南北史韵目》,观题名也当是一部收录南北朝史事的韵书型类书,不过后世罕见著录,影响不大。
在专门收录某一类材料的宋代韵书型类书中,尤以专门收录诗歌文本的一类数量最多且具有很高的诗学史研究价值。其中杨咨《歌诗押韵》二十四卷成书较早。杨咨约与苏轼同时,《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类书类曰:“裒集古今诗可以为矩矱者,编为《押韵》。”[9]卷三下,25a《文献通考》子部类书类作“《歌诗押韵》五卷”,并云:“鼌氏曰:皇朝杨咨编古今诗人警句,附于韵之下,以备押强韵。”[19]6264据清人萧穆《跋善邻国宝记》载,明成化、景泰时,日本所求中土书籍中,此书与《北堂书钞》《史韵》《诚斋集》《遁斋闲览》《石湖集》《老学庵笔记》等书俱在列,[23]可见其影响之久远。在宋代专门收录诗歌文本的韵书型类书中又可再细分出博收众家类、专收数家类与单收一家类。《歌诗押韵》就属于博收众家类。
属于专收数家类的有:
1.李滨老《李杜韩柳押韵》二十四卷。孙觌《押韵序》述其体例与价值颇详:“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韩吏部、柳仪曹四家诗,以礼部四声之次,集而录之,以类相从,号《李杜韩柳押韵》,凡二十四卷,以示余。余曰:‘……师武摭取四家韵语,类聚群分,会而分一,不待劳搜博采,开卷了然,尽于一睹,如观武库之兵、宗庙之器,粲然毕陈于前矣’。”[8]314-315所言“以礼部四声之次”云云,就是指依《礼部韵略》的韵部排列顺序来编排诗歌韵句。
2.裴良甫《十二先生诗宗集韵》二十卷。《郡斋读书志》卷五上小学类曰:“裴良甫师圣编杜甫、李白、高适、韩愈、柳宗元、孟郊、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无己之诗韵也。”[9]卷五上,14a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六经籍考将是书置于子部类书类,最能体现其韵书型类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七曰:“用宋《礼部韵》标目,盖犹旧本,然采摘诗句,依韵分截,颠倒割裂,又削去原题,使览者茫然,殊无义例,不足取也。”[17]1162-1163此论未能体会韵书型类书的体例与功能的特殊性。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子部五类书类曰:“按《礼部韵》每韵字下分载其诗句,采摭颇详。古人押韵,意匠可参观而得。”[24]瞿镛所论较能反映其体例特点与文学价值。
3.楼君秉《三家诗押韵》。楼钥《三家诗押韵序》述其体例曰:“取欧阳、苏、黄三家诗集,类以声韵,细字楷法,凡四十万字。”[16]727是书取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三家诗,按其韵句所属之韵部重新类编之。
4.汪大猷《唐宋名公诗韵》。楼钥《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载:“取唐宋名公诗集编为《诗韵》四十册。”[16]1204周必大《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汪公(大猷)神道碑(嘉泰元年)》曰:“有……《唐宋名公诗韵》四十编。”[25]楼钥《行状》、周必大《神道碑》俱言大猷有此一书,虽未详述体例,殆亦是将唐宋名公诗以韵类编者。
属于单收一家类的有:
1.传为孙觌所撰《杜诗押韵》。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辨杜诗闲殷阑韵”条有“俗传孙觌《杜诗押韵》”之语,[26]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卷八“避讳”条有“麻沙传孙氏(觌)《杜诗押韵》”之语,[27]周、彭都曾引其所录杜诗为考证之资,知其亦有相当价值。
2.陈造《韵类诗史》。陈造《题韵类诗史》曰:“予读子美诗能上口,来房州多暇,创以韵类之,庶便歌诵。”[28]卷三十一,22a此书为专收杜诗韵句的韵书型类书。
3.陈造《韵类坡诗》。陈造《题韵类坡诗》曰:“东坡仙伯之文,韩、欧伯仲,其于诗,迈往劲直之气溢于言外,而其严密腴丽,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学者与子美表里可也。……创以韵类其诗,为五策,凡一千三百九十一首。”[28]卷三十一,21b此书为依韵编次苏诗的韵书型类书。
综上,韵书型字书与韵书型类书作为宋代知识体系中一般韵书文献之外的具有韵书框架结构的文献形态,反映的是韵书文化对整体知识体系中其他模块的“入侵”。“韵书型”文献形态并非宋代才有,但直到宋代才形成较大的规模与相对完整的系统,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宋人对其“附韵类事,颇便检阅”的实际功用有更深的体验,另一方面更与宋人在同韵书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韵书型”阅读习惯甚至“韵书型”思维方式有关。尤其是这种“韵书型”思维方式,是宋代韵书文化对整个宋代文化思维范型的深刻拓展,强化了宋代文化的独特神韵,其存在价值与后世影响都是值得继续深挖的课题。
三、宋代韵书是宋代学术的增长点
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到什么样的高度,具有什么样的品格,是判定该时代文化发达程度的关键指标。宋代韵书文化的繁荣对宋代学术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宋代韵书、字书之学的发达,为宋人汲取知识提供了巨大便利。通过韵书、字书来获取知识,并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门径,这在宋人中已经成为共识,即便是著名的文学家也不例外。例如东坡每逢出行,“必取声韵、音训文字复置行箧中”(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十七载李廌语);[29]晁说之也曾津津乐道“昔稽叔夜喜音韵学,谢康乐疲于译梵字,颜鲁公老于《韵海》”(《文林启秀序》)的前贤事迹;[30]杨万里也曾说自己“无事好看韵书”(《鹤林玉露》乙编卷五“识字”条),[31]于此可见韵书在宋代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性。《湘山野录》载有宋人一件与韵书有关的趣事:
余杭能万卷者,浮图之真儒……时儒皆抱经授业,师居常喜阅《唐韵》,诸生长窃笑。一日出题于法堂曰《枫为虎赋》,其韵曰:“脂入于地,千岁成虎”。诸生皆不谕,固请之,不说。凡月余,检经、史,殆百家会最小说,俱无见者,阁笔以听教。师曰:“闻诸君笑老僧酷嗜《唐韵》,兹事止在东字韵第二版,请详阅。”诸生检之,果见“枫”字注中云:“黄帝杀蚩尤,弃其桎梏,变为枫木,脂入地千年,化为虎魄。”后诸生始敬此书。[32]
能万卷平日喜读《唐韵》,而诸生经常窃笑之,因为他们觉得《唐韵》不是《礼部韵略》,对科举无直接用处。而真正爱好学问的人则深知其广博渊深。能万卷与王钦若同时生活于真宗、仁宗时代,其时《唐韵》的宋代版即《广韵》已经问世,此处《唐韵》很可能就是指《广韵》;且“黄帝杀蚩尤……化为虎魄”之句,《广韵》东字韵“枫”字注亦见载,位置也大致“在东字韵第二版”。即便就是指《唐韵》,此则材料也可证明宋人很早就认识到韵书的学术价值。又,《嬾真子》卷三“赋桐始华依次用韵满场曳白罢举”条曰:
天圣中,邓州秋举,旧例主文到县,乡中长上率后进见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职官,年老,须鬓皓然,既贽见,有轻薄后生前曰:“举人所系甚大,愿先生无渴睡。”既引试,赋《桐始华》,以“姑洗之月,桐始华矣”依次用韵,满场阁笔不下。乃复至帘前启曰:“前日无状后进辄以妄言仰渎先生,果蒙以难韵见困,愿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来日再见访。”诸生诺而退。是夜,主文遂遁去。申运司云:“邓州满场曳白。”[33]
按“姑洗之月,桐始华矣”典出《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桐始华,由鼠化为鴽,虹始见,蓱始生。”[34]《桐始华赋》的用韵“姑洗之月,桐始华矣”,因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故曰“姑洗之月”,“桐始华矣”前三字乃《月令》原文,“矣”字为当日主文之老先生为了凑足八韵而额外添加。诸生若知《月令》此文,此赋题、韵自不难理解,即便不知《月令》有此段文字,若熟读《广韵》,亦不致见困。《广韵》释“桐”字曰:“木名,《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华。”[35]明确载有《月令》之名,所引虽与《月令》原文不同,然“清明”即是“季春之月”,亦即是“姑洗之月”。于此亦可见《广韵》在“知识化”的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南宋初年乱离之后,连国家典章制度的重建也离不开《广韵》《集韵》:
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诵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质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方大驾南渡,典章一切扫荡无遗,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祠祭但称庙号而已。又因讨论御名,礼部申省言:“未寻得《广韵》。”方是时,性之近在二百里内,非独博记可询,其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尽护致剡山,当路藐然不问也。(《老学庵笔记》卷六)[36]
至宣和中,册府所藏,充牣栋宇,而禁中藏书尤盛。设官校勘,谓之御前书籍。中更变故,丧亡略尽。至高宗巡幸至吴中,虽祖宗谥号亦亡之,但称庙号。建炎三年,因考求字训,而有司言:“止有《广韵》,俟求访得《集韵》,乃可尽见。”其散亡乃至于是。(《会稽志》卷十六“求遗书”条)[37]
此二则记载颇有助于观照两宋之际《广韵》《集韵》之盛遇。据陆游所记,当时礼部因“未寻得《广韵》”,连“讨论御名”亦无从入手;据施宿所记,当时虽已寻得《广韵》,因尚未“求访得《集韵》”,故考求字训仍未能详密。二人的记载,颇给人一种宋代文化一线之传赖《广韵》《集韵》以存的印象,足见二书所载知识的丰富性与可靠性。
《广韵》《集韵》收字多、注音全、训释详,故而其学术价值也极高。宋人书目对《广韵》《集韵》的绍介不遗余力,宋人注前代典籍引用《广韵》《集韵》比比皆是,宋人注当代文献亦常常引用之,即便宋人自著专书,亦须不时参考。这些都促进了宋代学术的增长。尤值一提的是,宋人在揭示韵书与字书的关系时,往往体现着明显的辩证色彩。例如,苏辙《类篇叙》曰:
今夫字书之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既已尽之以其声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书之变曲尽。[38]
由于韵书和字书都收有大量文字,故苏辙在这里将二者统称为字书。他认为《集韵》所收是“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类篇》所收是“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分而言之,二者各司其职;合而观之,则既能“尽之以其声”,又能“究之以其形”,使“字书之变曲尽”;这样的观点无疑是颇为辩证的。李焘的《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及《后序》也是如此。李《序》主要讲述《类篇》《广韵》《集韵》《玉篇》等书之关系,条分缕析,颇为详明;《后序》主要介绍《说文解字韵谱》之“新编”新在何处,其中论及《集韵》《类篇》之关系曰:
盖楚金先生本志,止欲便于检阅,故专以声相从……然偏旁一切都置,则字之有形而未审厥声者,岂不愈难于检阅乎!此宝元所以既修《集韵》,必修《类篇》。修《类篇》,盖补《集韵》之不足处也。《集韵》《类篇》两者相须,则字之形声,乃无所逃。[39]170
其中“《集韵》《类篇》两者相须”的观点也辩证地道出了韵书重声、字书重形、声形相济为用的客观事实。魏了翁引申之曰:“夫字有六体,而编次检阅必本形声。《说文解字》《玉篇》《类篇》,始一终亥,则其形也。《广韵》《集韵》,始东终法,则其声也。”[39]17魏了翁的论述虽仅寥寥数语,却也道出了《集韵》《类篇》的共生性与互补性。可见,宋人在韵书与字书关系研究中体现了可贵的辩证思维,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推进整个宋代学术的全面健康发展。此外,宋人也善于利用韵书多维的学术价值来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王之望《看详杨朴礼部韵括遗状》一文有云:“《礼部韵》止为场屋程文而设,非如《广韵》《集韵》普收奇字,务为该洽。”[40]表明《广韵》《集韵》的学术价值已为宋人普遍认可。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又名《群书考索》)曰:
订周思言之《音韵》,质刘秋孙之《释名》,以《声谱》而定平、上、去、入,以《玉篇》而参古文、篆、籀,以《指微韵镜》而别唇、齿、舌、喉、牙之音,以熙宁《集韵》而究僻、俗、用假借之字,又安有“伏猎”“雌霓”之失?[41]
可见章氏不仅对字书与韵书、韵书与韵书的不同作用等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对它们形成的避免误认字、误读音的强劲合力也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韵镜》“别唇、齿、舌、喉、牙之音”的功能、对《集韵》“究僻、俗、用假借之字”的功能的强调表明,宋代韵书的学术价值是多维的,只要善于利用,即可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孙觌《切韵类例序》曾详叙《集韵》纂修之全过程,并言杨中修《切韵类例》乃是“即其书科别户分”而成,可见《集韵》深刻影响了宋代其他韵书的编纂;楼钥《答赵共甫书》指出吴棫《诗补音》主要以《集韵》为据,其《跋赵共甫古易补音》则指出《易补音》多以《集韵》为证,也表明《集韵》已被宋人广泛运用到了研究中。
需要强调的是,宋代韵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与疏漏。不过,这些缺憾与疏漏也能成为宋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增长点。《集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宋代不少著作都对《集韵》中的知识点进行过补正。笔者所见有:
1.司马光等编《类篇》补正7则。例如卷三下“弑”字有异体字,光曰:“《说文》失收,故《集韵》今不载。”[42]
2.罗泌《路史》补正4则。例如卷二十四《国名纪·黄帝之宗》曰:“儇,与嬛同音……《集韵》音旋,非。”[43]
3.方崧卿《韩集举正》补正3则。例如卷二释韩诗《寄崔二十六》“视物隔褷”之“褷”时曰:“不知《集韵》何以不收入?”[44]
4.楼钥《攻媿集》补正1则。卷六十七《答杨敬仲论诗解》:“俗谓坠下曰覃,徒绀切。而《广韵》《集韵》无此字音。”[16]893此则可并补《广韵》《集韵》之阙。
5.王观国《学林》补正2则。例如卷九“勑”条曰:“《集韵》本朝所修,当明言用勑字之非,而不能决判,反有相承用之说,《集韵》误矣。”[45]指出《集韵》未能严格辨别正体与俗体。
6.吴曾《能改斋漫录》补正2则。例如卷十五曰:“《集韵》引《山海经》以惠为车,惠车(車)字相类,岂传写失其真欤?”[46]

8.孙奕《示儿编》补正2则。例如卷二十三曰:“《集韵》乃景文撰定,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去声既出朴字蒲候切,入声又出朴字与樸字同匹角切,则与《笔记》所谓‘朴无樸音’者不同矣,岂景文而自为矛盾乎?”[48]指出了宋祁观点的自相矛盾处,也使人注意到《集韵》可能不妥。
综上可见,宋人补正《集韵》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在补正过程中,宋代学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增长。
宋代韵书还加强了宋代诗学的知识化取向。在韵书与学术频繁互动的大背景下,韵书自然会对宋代诗学产生影响。宋人先是参考前代韵书进行创作,接着自己编纂韵书辅助创作,后来者又根据韵书对前贤的创作进行解读、分析——这是宋代韵书与宋代诗学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基本面貌。而在这一过程中,《广韵》《集韵》发挥的作用颇大。在《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宋代知名诗学文献中,经常可以看见引用宋代韵书佐证诗学知识的情况。例如:
苕溪渔隐曰:“裴虔余云:‘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襦湿,疑是巫山行雨归。’《广韵》《集韵》《韵略》垂与归皆不同韵,此诗为落韵矣。……又《学林新编》谓:‘字有通作他声押韵者’……然则字通作他声押韵,于古诗则可,若于律诗,诚不当如此。余谓裴虔余之诗落韵,又本此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八“五纪杂记”)[49]127-128
苕溪渔隐曰:“……其语虽协韵,然《广韵》《集韵》于庚、清、青三韵中不收此‘箵’字,并于上声迥字韵中收之。苏子美《松江长桥观渔诗》:‘……拟来随尔带笭箵。’黄鲁直《雨晴过石塘诗》:‘……渔父晒网投笭箵。’秦少游《德清道中还寄子瞻诗》:‘……支港泛笭箵。’皆于青字韵中押,真误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四“苏子美”)[49]176
上述两则材料,论述的是韵字使用正误问题及诗歌押韵规则问题,都引用了宋代具有代表性的韵书作为论证依据,宋代韵书在宋代诗学中的作用被很好地体现了出来。这种情况在宋代诗学文献中普遍存在,增强了宋代诗学的知识化程度。宋代韵书对宋代诗学的影响,学界一般都是以《礼部韵略》为中介,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切入来谈。上述材料的大量存在表明,宋代韵书已经直接参与到宋代诗学的建构之中,其所包含的丰富知识内容,已经成了宋代诗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宋代韵书承前启后、接力递修、精益求精的特色,加强了宋代文化的包容性、连续性与精深性;因宋代韵书的繁荣而形成的“韵书型”思维方式,拓展了整个宋代文化的思维范型,强化了宋代文化的独特神韵;宋代韵书作为宋代学术的一个显著增长点,增加了宋代学术的专业性、思辨性与知识性,彰显了宋代文化的求实、求是精神,使宋代文化在博大与精深两个方面的特色都显得更加鲜明可感。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化研究领域很早就流行着“宋型文化”的提法,近年“宋韵文化”的提法也方兴未艾。前者学术意味更浓,后者似更具文化审美意味。虽然二者产生的时代语境不同,应用场域也不完全一致,但无疑都有助于推进宋代文化研究更加多维、立体地发展。宋代韵书既是文化知识的载体又是诗歌创作的参考,因而也兼具学术价值与诗性智慧。探索宋代韵书的文化意涵,不仅对“宋型文化”与“宋韵文化”概念下的宋代文化研究具有推进意义,更可以成为沟通二者的媒介,为进一步考察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注释:
①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子君:《宋代韵书史研究——〈礼部韵略〉系韵书源流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罗积勇、肖金云:《〈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