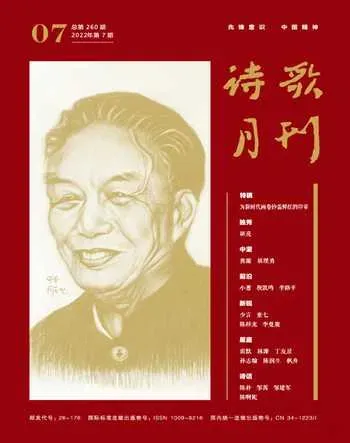陈梓龙的诗
陈梓龙
春天的修辞学
太阳慵懒地趴在树上
望着从南国飞回的新燕
是如何叫醒,沉睡了一冬的花朵
烟雨不请自来
它们说,要为这些娇贵的春花沐浴
梅花、桃花,甚至是不善言辞的苦杏子
都曾邂逅一场迷人的春风
这是三月最大的馈赠
满城喜鹊执迷于一面镜子
还未找到,河面上就漾起了句点
水的肋骨开始逐渐柔软
那些被雪隐藏的脚印,全部重新显现
春天变成精妙的修辞
所有词语,都隐喻美好的人间
穿行人间的雪
天空一直注视人间
知晓寒风是把刻刀,割裂的树皮
形似祖父额头深硬的纹路
这些曲折,就像身体里遍布的肿块
永远无法消散
以隐秘的方式传承,在人间
留下通往冬天的路
还未学会行走,雪里就有行走的足迹
宛若天空用持续的省略
叙述空旷的心事,让真相成为谜底
让单薄的雪花流浪人间
并告知:晓色将至,春天的马蹄奔涌而来
良宵引
沿着长满薰衣草的河岸,一直走
河岛中偶尔惊起几只水鸟
我们迎山而坐,垂钓空旷的黄昏
灯火阑珊处,水墨色的瓦屋点缀几棵梅树
迟暮的爱人住在那里
修补逝去的光阴。花苞落入碗中
剔透如月,你唤我归家,夜色如此妖娆
仿佛我已完成一生的证词
认领手中的命数。夜寒逼人
我们默默无语,任凭唇在黑暗中相触
柔情似蜜,“大洋彼岸骤起了风暴”
一个人去海边
平静的生活在蜀中,除了山
就只有山,这些心中的高墙直入云霄
即使身处浩瀚的夜空
总有一处柔软,不属于自己
那就往南方走,一个人去海边
摘蔚蓝色的浪花献给爱人
捉鱼、拾贝壳,用贝壳建一幢房子
就住在这里,远离未来,更远离过去
成为一座岛屿,海洋的符号
用这种伪装的命运,一瓣一瓣剥开自己
蝉语
漆黑的村庄,只有一盏灯在心中
如果没有蝉语
我只能与黑暗独白,月光之间
有一条无法窥视的河流
向我传递温度,而深秋的寒刃太急
割伤了一只蝉的半生
像岁月划过,母亲的脸颊
当灯火消逝,月色沉溺
人群散尽的村庄微缩成一个句点
只有蝉声不曾停止,继续讲述,这失语的人间
归去来
心中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声音:
“归去吧,归去吧”
但归往何处,旧友,年华,慈祥的眼神
已风干成杂草丛生的瓦房
除了比酒还深沉的暮色,我什么
也不曾拥有,阴雨落在南昌
我行走在洪湖东路
这一刻,夜晚疼痛而神秘
无人知晓,一枚雨滴蕴藏了多少盐分
喻
桂花香铺散开来
清晨的太阳,慵懒趴着
在我昨夜留下的,不忍拭去的泪痕之上
长椅上坐着的姑娘,用木梳
捋弄怀里的那只,湿漉漉的麻雀
温柔的模样,像极了,抚摸爱人的头发
这时蝉声戛然而止,风不再奔跑
落花坠在湖面,漾起层层波纹
而我,也不再想飞。即使这心儿像天空般辽阔
一碗茶
在斑鸠的歌声里,泡一碗浓茶
躺在摇椅上,品味生活中细微的苦
茶色微黄,小小的碗里似乎藏有秋天
隐隐倒映着后山枯瘦的树木
当燃烧的叶子零落成泥
一棵树就完成了安静的一生
而我体内,还有尚未数清的年轮
在鹅毛大雪中虚构消解的生命
冬日,是一场离别送行另一场离别
有太多事物,我们不忍揭示隐秘的疼痛
其中包括漂泊他乡,只有寒风
张开双臂拥抱我,和这碗没有饮尽的苦茶
草木集
万物有灵,一株植物也有疼痛的内心
风拂过原野,我看见
乌桕和黄昏交换金色的火焰
烧尽最后一片叶,体内的年轮
叙述着被雨珠惊动的湖面
直至灌木枯萎,留下多褶的面容
时间被喻以更深刻的含义
那些活在人间的草木
被迫在四季的刻度中端举墓碑
生长,结籽和枯黄,重复本无意义的轮回
从消逝走向永恒,终于赶在雪落前
埋藏装有天空的弦月
所有承受风雨之物,都像替我而活
大雪终将把自己还给土地
这种汹涌的平静,是十一月最疼痛的部分
现象学
霓虹陷入沉睡,黑夜的称谓不曾改变
只是人间因此闭上一扇窗
剩下的火种,能否引燃星辰的眼睛
指引流浪者回到故乡
它还有隐喻的含义,即便是光明本身
也掺有阴暗,如同天空
不能容忍一枚孤月,悬挂在雨露湿润的内心
生命具有不能承受之痛
无法用零碎表象,掩盖命运的卜卦
即使残缺这个形容,已变成动词
让岁月遗漏最为重要的部分
却无论如何,也没能抹去
风来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