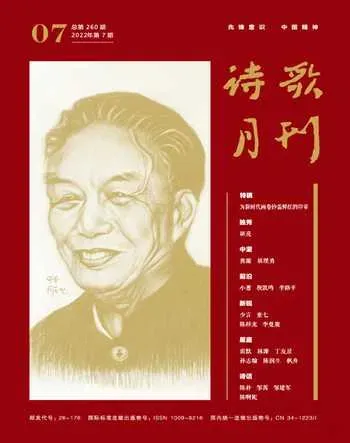片羽(组诗)
胡亮
六月
苜蓿花特别擅长紫色,而微型蓝蜻蜓
则精通短暂。几米外的小河
反复练习着清澈,以便娴熟地
洗去我双颊的土尘。
紫色像微澜那样悦耳,而短暂像锦鸡
那样将最长的尾翎也缩回了灌木丛。
我特别擅长转动群山,而你则精通蔚蓝。
凭窗
我的近视眼再次受教于落日。一列火车逆行,
驶离了暮年,停靠在中年。
这是中年新家:所有窗户都朝西。
这是中年涪江:在铝合金的方格里豁然开朗。
万神殿
铁角蕨又多又密,好像是湿地的汗毛。
八角金盘略高于铁角蕨,风车草
略高于八角金盘。锈毛苏铁,
海桐,龙爪柳,芭蕉,槐树,还有
金叶水杉,搭建着青黄相接的天梯。
我的惊愕步步高,
翻越金叶水杉,仍未企及那最高的真实。
巨人传
如果麻雀的羽毛有点丑,如何才能获得
锦鸡的羽毛?……聆听!
如何才能获得鹰眼或马蹄,
还有翠鸟、野花或青藏高原的肺腑?
……聆听!
我像蕨类植物那样聆听着大地,
又像大地那样聆听着掉落的绣花针!
无尽
解开一丛丛巴茅的发辫,从这个野湖的耳垂
走到额头。我们环行小半圈,
止步于眉间。湖变得越来越大,
剩下了越来越多的发辫和幸福。
得闲
我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额头冒出了
一层细汗。楠竹做的笔筒,
柏木做的抽屉,橡胶木做的书架,
复仇般地消化了房间里的一切
铁器。一盆绿萝从书架的第五层
垂落到木地板,
就像司空图的二十四个妙谛
或飞瀑。是的,我要找到那把小剪刀,
我要剪掉从绿萝上溅出来的一片黄叶。
小树林
“植物才是遗物!”——很少有人能领会
这句话的绿意。两棵蓝花楹,
一棵黄葛兰,几棵香樟,
以及若干丛斑竹,哪里还具有什么
“当代性”?绿意勾兑了秋意,
秋意勾兑了古意。就在这条葱茏之路,
我们会碰上张船山,过一会儿,
还会碰上苏子瞻。小树林圈住了小茶亭,
小茶亭圈住了十二平方米的南宋,或
三个小时的东晋。诗人们,
青年们,明天就是白露,
快让我们临摹每棵树,临摹它们的绿意!
不要羞愧于笨手笨脚,
而要羞愧于“当代性”结出的老茧……
分寸
我抓住一只花脚蚊,它又从指间飞走了。
可见——
它的前生:一条赤链蛇,一只短尾鳄,
或一只黑盾胡蜂,当初对我绝无恶意。
魔术师
我要把刚摘下来的一颗葡萄,拆分成
一百颗。要把葡萄上的一克新雨,
拆分成一千毫克。我要在更慢里求得
最慢,要在两匹砖的细缝里发掘出
一吨享乐主义。我要把五亩葡萄园
拆分成无边无际,要把
尝到甜头的一个下午拆分成今生今世。
丰收
秋天像一个可以伸缩的榫头:对少年来说,
是夏天的长尾巴,对中年来说,
是冬天的短脖子。夏天我没有训练
潜水,冬天也没有计划滑雪。
西风如车,娴熟地搬运着从银杏叶
尖端滴落的一克理想——从这个身轻
如燕的金色密封舱,我该不该尝试
向外跳伞?秋天已经派来一株
双荚决明,在我上班或下班的中途,
一边开花,一边挂果,一边无言
答疑,像一个双手合十的鹅冠花和尚。
无言,就是五千言。再乘上
几次过山车,我或能习得上乘的孤独。
小团圆
第一轮明月不断撤退,有时撞上了隧道口,
有时游过了桉树林,有时跳上了
兽脊般的小山丘——被我和一辆绿皮
火车无望追赶。就在这些时候,
第二轮明月高悬于涪江左岸,一动
也不动——被她无理纠缠。
两处清辉好无赖,拧紧了两个身体的发条。
我的急性子与绿皮火车的慢性子
强行签订了协议:
时速要提高到一百六十公里,
两轮明月要遇合成一轮明月。
沈府君
汉代的无名工匠雕成了一对墓阙,守护着
沈府君。春风吹过渠县,
沈府君早已四散为一片两三亩的野草花。
朱雀已无实用性,白虎亦无
实用性。无名工匠早就以伟大的迟疑
预言了艺术的独立日——
两只石兽把春风送出了沈府君的领地。
捷报
我看过高仓健主演的两部电影:今天,
看了《兆治的酒馆》;儿时,
看过《追捕》。高仓健还是那么年轻,
仿佛六年前离世的只是
他的替身。那么,迄今逍遥的反而
是本尊?这样的错觉令人着迷。
诗从来就不会输给电影——
我将比高仓健更老,也将比他更年轻。
无休
四天算不算是阔别呢?今天我徒步上班,
发现银杏加速变黄,而水杉
开始变红。是谁调配着红黄两种颜料,
就是谁让小诗冒出了白发。
我驻足于涪江之畔,在永恒中小憩了
两分钟,然后就匆匆赶赴一个会议室。
围城
两只刺猬,从一开始就没有吮到棒棒糖,
而试图用舌头,
怀柔那遍体竹签。
而在郊外古战场,无数刺猬备好了云梯。
恍惚
十六头亚洲象离开了西双版纳,向正北,
走过了普洱,
折而向东北,走过了墨江、元江和石屏,
继而向正北,走过了峨山、玉溪
和晋宁。巨腿移动,
玉米倒伏。如果它们继续向前,
就将横穿昆明靠近成都,折而向正东,
就将途经我的五亩孤独,
还将用鼻子大大咧咧地碰碰重庆。
求诸野
鹧鸪的叫声被一个山头分了岔,就像被甩到
山腰的鱼尾巴。麻雀的叫声很圆,
似乎要用滑轮放下一座天堂来。
看看吧,这座天堂的建材如此普通——
一条小河正在转弯,一片草地齐茬茬,
一块地毯小得刚好够宽,
几杯红茶,几个皮蛋,一碟葵花籽,
几句真心话的下午。蝉的叫声织补了
构树与枫树因交叉而形成的各种
不规则夹缝。哪里有什么亏本生意?
我赚到的嫩黄和新绿
足以把天堂铆接于任何一片水波。
交通
接下来,朋友,你开始吹奏印第安木笛。
我很快听到了树状的南美洲和北美洲,
听到了十只奥奈罗鸟,
——它们动身飞越太平洋,其中九只
就要停上你的肩膀。此刻,
灯笼花红得羞涩,斑竹绿得谦逊,
紫葳正在搭建一个音乐的凯旋门。
一只本地画眉鸟作为临时替补,
与木笛互相问答。朋友——
请记得用音孔的专列,运走这紫葳,
这斑竹,这灯笼花和画眉鸟;
请记得用尺八
把它们吹奏给与我暌违的鼓浪屿。
若尔盖
你弹了几首名曲,半即兴。又弹了一首
心曲,即兴。在半即兴与即兴之间,
隔着一座昨天下午的鹧鸪山,
而在羊角花丛里面,又藏着一条直通
即兴的隧道。当你收起琵琶,
露珠就从皮制琴囊上滑落。露珠,
白河,黑河,收到了同一封密件
——加入黄河的喋喋!这个时候,
所有星星突然低于并略大于
核桃,北斗用银勺子从黄河舀起了
一大把没有听过瘾的耳朵。
最尖的一只耳朵乃是月亮的倒影,
这倒影加盖了波浪的暗花。岸边,
几棵沙棘在与寒气的谈判中
不断收缩,它们羞愧于既不能留下
黄河,又不能割赠草原。
也无妨,我们已经确信——
如果沙棘办不到,就寄望于音乐。
即物
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孩。
她的小腿上纹着一个什么图案:动物,
植物,或抽象符号?六七十公里,
恰是夏天的时速。他们驶离了这个
秘密补给站——
小路两旁长满了枇杷,
树下长满了斑茅,
地面长满了鸭跖草;不远处的一小块
废地,长满了黑心金光菊、陈艾
和鬼针草。一对中年散步者交换了
眼神,两只手自然相牵,
就像火棘由青转红。所有葱茏
都见证了他们内心的摩托车,所有
葱茏都把他们的系列眼神译成了
秋天的短序,译成了野蜂蜜的续集。
悟空
一匹流水,两匹流水,漫过了剪刀——
那个剪刀手颧骨
高耸,并没有得到一匹丝绸。
流水和剪刀在一棵法国梧桐下举行了
一轮和平谈判——
流水比剪刀更硬,剪刀比流水更软。
左岸
我把双眼租给了一只鹭鸶,在十七楼,
可以看得更清楚——涪江向右拐了
一个弯,就像一小截圆周。
如果难眠,我就不能赊来一尺波浪,
就不能把波浪折成一只鹭鸶,
就不能让它飞往右岸,歇在某家
医院窗口,并向某个圆心致以
比护士服更白的表白。如果入眠,
以上种种岂是问题?《瓦尔登湖》
从我的手里滑落,即将胜任
孤枕,“可以测出天性的深浅”。
九月
雨丝那么新,那么细,那么尖,身手
那么曼妙,穿过了针鼻子,
拉出了线状的凉意。芭蕉一边
减肥,一边撰写夏天回忆录。
某人一早办结了出院手续,下午
就急着换上了草绿色
长裙。小病的山顶就是哲学,
哲学的山脚就是秋天。当银杏逐渐
变黄,剪指甲就会成为一门艺术。
当涪江逐渐变瘦,水落石出,
我们就会挑出一只很小的勺子
而不是一只巨杯
来品饮身体之间的任何一束静电。
钻石胃
箭镞的成分检测报告,已经从实验室
送到一张梨木书桌——其含量,
百分之一为稀有元素,或未知元素;
百分之四为小误会;百分之十五
为有眼无珠;百分之二十三为嫉妒,
秒胜了青柠檬对酸的积极性;
百分之五十七为仇恨,硬度和亮度
略低于榄尖钻;其与韭菜的相似性,
为零。我饿了,狼吞十万箭镞
——为了把它们消化成一小堆废铁。
无遮
书房外面就是一个狭窄阳台,也是理想
花园的一个次品或残品——
两盆蓝色绣球花,一盆栀子花,
两盆铜钱草,一盆茉莉花,
茉莉花的一根长枝条挑逗着两盆多肉。
都没有开过花。我挨个儿浇水,
摘掉黄叶,剪去枯枝。在平静
与平静之间的一个尖刺状空隙,忽而
念及一个人。很快,我生出了
羞愧。而在花园的一个角落,一盆
天竺葵在预期以外,在几棵凤尾蕨
的干扰之下,冒出了羞愧般的红苞。
惊艳——致Virginia Woolf
伍尔芙!伍尔芙!你的两只大眼睛组建了
美之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你的白银忧郁
接通了良知。不管是用鹅毛笔,
还是用蘸水式钢笔,你定然会写出
这个句子——
在斑斓花朵的中心,总有一只蝎子,
在问:
“为什么要活着?”
鸡尾酒
索道的语速比盲人更快,还没说完
草甸、冷杉和油松,已然跳到
落叶松。过了三千八百米海拔,
史诗快要进入紧要关头——
寒冷开除了大部分植物,被反复
叙及的唯有黑黢黢的乱石堆,
无序,
而有序,像一群群团坐的怪兽,
就读于一个湖的深蓝。嘘——
索道咬断了舌头——大哥已就绪,
达古冰川进入了变声期。体力
急需想象力来接力,我——我们
——从来没有见过大哥——
我——我们——顿时信服——
必定有一张齐天的大嘴巴,
能一口饮尽群山环抱的鸡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