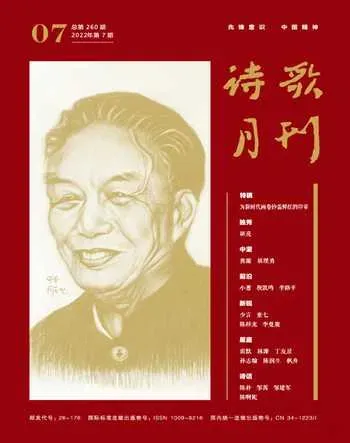语象的智性与古典艺术的交锋
——傅荣生诗歌考察
陈啊妮
傅荣生的诗写得很轻,短小精悍,行神如空。这种轻是语言的简洁干练,精神的通透,以及情感内蕴的有力填充。返虚入混阔,积健为雄思。从文本开篇,傅荣生的诗歌就有立意和聚力于思想性拔高与净化的写作动机。在他的 《辩护》《结绳记事》《湖心岛》《南方来信》《戒律》等作品中,诗人已然对自然质朴的生命体验和抽象的精神刻画彰显出其不可多得的语言造诣。
俗常中的事物,意象和隐喻都是傅荣生随意撷取的天然写作资源,诗人在创作中善于建立个体象征的独特塑形,对于细节的挖掘是经过深度思考的。这些深度思考的过程在诗中甚至是完全透明的过程,对于事物表象的审视,诗人更加侧重它们的象征深意,而在剔除常规审视和自然抽象的选择中是智慧的,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语言果断的行动力。“一滴雨/在枝条上发呆/鸟在微漾中走神/百年银杏/看守着村落/锈迹斑斑的寂寥/和此时的迟疑/在风里/我看到了/紫阳花的纠结”(《殇》)。从某种意义来说,傅荣生在整体象征与局部象征的平行运思中侧重于反论式象征,就如《殇》中“紫阳花的纠结”,诗人以意识形态话语位移诗绪的高涨,无疑“殇”的整体象征不断在分解情感的疏离,才使“纠结”具有不必迟疑的隐痛。
将自然万物人格化移情呈现,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启迪,诗人傅荣生的诗歌给我们带来了两种显著的美学效果和精神价值。其一是傅荣生诗歌的古典审美自觉,以及直朴诗意的素描体系呈现,全力以赴在短诗中展现博大壮阔的万物象征和精神内蕴。傅荣生的诗歌大多在七行到十行,与古典节数贴近,对一个意象的语言陈述拓展,诗人独创的诗歌体制在韵律和谐的追求上,是向古典诗歌致敬和拓新的双向奔赴。首节铺垫,第二节主旨揭示,后节收尾烛照全诗,都是承上启下的自然过渡。“窗外/虫吟断断续续/那节奏/像在替我们分配时间/醒着的/或梦着的人/都领走了属于自己的部分/在鸣叫的间隙里/有人怀揣云梯/跟着起伏的群山彻夜奔跑”(《声声急》),在短短几行之内运思,生发出更高的主题意蕴。“窗外”是语境推衍,“虫吟”“云梯”都是时间的浮游姿态,“跟着起伏的群山彻夜奔跑”是层层铺叠的情感跃升,无疑“声声急”在末节陡然增强的诗歌回音是剧烈的,最终为诗歌主旨营造了足够的氛围。
傅荣生对命运形而上的思考是深度的,一种沉静、睿智、禅意的古典审美运思像烙铁一样灼疼我们的神经。如在《成子湖的芦苇》一首:
被诗词反复伤害过的
这片芦苇
拒绝成为任何比喻
他们安静地站在自己的莲花里
我来,没有带上纸和笔
只带着泊在传说里的一座桥
和隐隐约约的水岸
把荡里的落日,引渡
作为一个被重复使用的经典意象“芦苇”,诗人开始倾听它们作为喻体的魂之所系,“被诗词反复伤害过的/这片芦苇/拒绝成为任何比喻”。对“成子湖”这片土地致以深切的情谊,“芦苇”似乎是无法回避和不可剔除的象征,而诗人反作用于一种惯性的形象设象,“我来,没有带上纸和笔”,对自然抽象的深爱是博大的,被虚幻统摄成一种涤荡着风之气息的“芦苇”,在某种隐喻的思想行走中复活了。而诗人“把荡里的落日,引渡”,则是构成了生命情感的持重释放和消泯。一个立体的、多维思想元素的“成子湖”的芦苇是竖立感的,亦是诗歌艺术审美下排他的苍莽呈现。这里不得不说,傅荣生的语象画风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些司空见惯的意象“芦苇”“落日”是经典的重塑,是古典另类的唯美,具有修辞骨感的精神厚意。
傅荣生有学者的洞察耐心,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情感抒发和理趣哲思都有较为固定的语言基调,是一种睿智、飘逸、静默的东方审美,一种富于沉潜和勃发的语言心态。其实诗人对短诗的整体思想见地的营造是难度最大的。长诗有足够的思想语言舒展空间,越长越好,傅荣生的短诗却反其道而行之。“河岸柔软起来/浅水照出万物的模样/溪边/一只白鹭/抖掉身上多余的影子/把脖颈往尘世里伸了伸/振翅/消失在天际/——就像不愿融化的雪/又返回天空”(《白鹭》)。在此诗中,诗人诗绪的回潮起落是精微而空灵的,前两节的托举结构出于修饰的刻意,也追求吟诵的语言实用性,对于艺术化推衍的诗意架构,傅荣生摒弃文字的拖沓,内容的繁复,无疑这短短的行数为“白鹭”贡献了语言象征的自励。“抖掉身上多余的影子”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写意,着力强调和阐释诗歌的思想空间。而在结尾的断裂中,“就像不愿融化的雪/又返回天空”,用“雪”烘托“白鹭”的圣洁写意,寄寓引申一种介乎精神边界的思索,这是一种未经教化的野性的唤醒,也是诗人一种直觉和惯性的思想行走实践。
可以确定的是,傅荣生对于生命深度考察的意义在于,在精神意向上对于生命真切的感受和觉知,在诗歌文本中成为思想显像不可回避的佐证。诗人不是完成某种人类的精神救赎,就是对于生命深深地怅惘和赞美。在傅荣生诗歌中,哲学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他的语言活水,是潺潺流动的价值认同。如《结绳记事》的文本呈现:
当我们试图用文字
解开一根绳子上的死结
才知道语言已经荒废多时
我们只能顺着平滑的部位
往前,或往后探寻
死结,只是时间较劲或停顿的地方
多年以后,我们才会明白
绳子上如果没有死结
许多事情往往无从谈起
“结绳”首先是诗人自我思想的一个“结点”,这是一个谜之“死结”,当诗人将膂力倾注于人类命运的深刻意味,那么无常如雪就不再是一种语言的渲染,而是一种理性客观的观照,“死结,只是时间较劲或停顿的地方”。在“结绳”用作象征去派生厚重的生命现实体验中,无疑这是一种疼痛的语言出鞘,闪着命运无常的寒光和晦暗的沉重思想。诗人貌似不动声色,而情感的走向是价值的最终固定,“许多事情往往无从谈起”,这一不断强化的否定之否定不断增值着个人生命的自足、丰盈以及释放,而不仅仅是一种自醒的体悟。“结绳记事”其实是完成了一个思想完全打开的运思过程,诗人以平缓的语气导出思想的症结,这是一首有着生命哲学意味的“绳索”。
古典铺排,理趣哲思渗透,以传递日常自足现实经验为审美基底,在智性的语象气质里,傅荣生的诗歌艺术表述是有着深刻思想与情感的。以诗歌体式传播自我生活觉知,傅荣生在突破现代诗语与格律束缚中做出了成功的尝试,生命自由的形式与诗歌自由意志力的强劲结合成为语言的化合剂。“要多少春风/才能吹绿一个人的空白/长出莲花和粮食/顺便长出一片竹林/为此/我曾叩问过一条/解冻的溪流”(《空白》),傅荣生在细腻的诗思迂回中肆意挥洒深刻的诗歌思想内涵:空灵、禅意、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