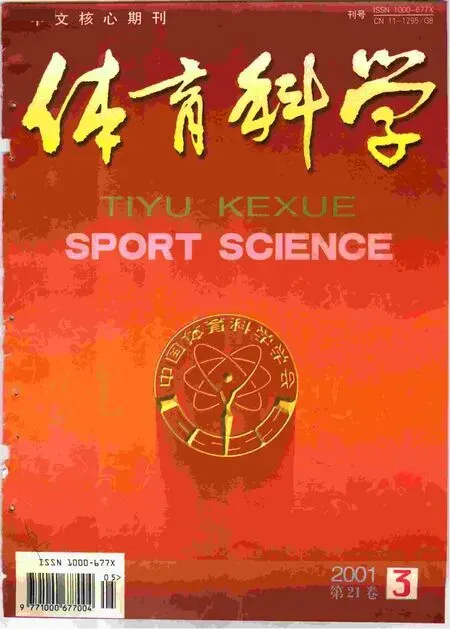运动训练学的学科属性和基本定位
贾潇彭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1866年,英国学者Archibald Maclaren著述了世界上第一本运动训练理论著作,一个世纪后,东德学者Hans-Dietri‑ch Harre在1969年撰写的《训练学》()标志着现代运动训练学(以下简称“训练学”)概念的正式确立(王雷等,2017)。2019年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在南京召开,此时恰逢运动训练学诞生50周年,于会之际陈小平等学者尝试总结了目前我国训练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基于原创性理论进步停滞、学科发展陷入瓶颈的行业事实,有学者认为我国训练学发展的主要困境在于既往的研究范式建立在近代科学的简单性范式基础上,范式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困局的形成,未来应积极研究和应用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兴起的复杂性科学范式(诸葛伟民,2009)。仇乃民、李少丹等学者是这一提案的主要支持者,自2009年至今其团队已多次撰文论述复杂性范式在运动训练领域推广应用的潜在契机(杜长亮等,2009;仇乃民 等,2011;胡昌领 等,2020),从经典理论的重新解读到研究方法论的反思重构乃至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展望(金成平 等,2016;仇乃民 等,2013,2015),逐步描绘出一系列复杂性科学的建构方案(仇乃民等,2016,2019)。杨成波(2019,2020)在近年也分析了近代训练学的科学范式,并将其总结为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下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所形成的一种脱胎于科学主义的产物,这一观点与此前两位学者的解读略有不同,但杨成波(2020)也表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运动训练领域中数据信息与训练决策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复杂性科学将会是未来发展的出口。
分析“复杂性科学”这一概念本身,尽管它一直强调“混沌理论”“不确定性”,但实际上其范式的理念框架并非彻底脱离传统科学。从内涵上理解,与其说它是追求“不确定性”,不妨说是追求新的“确定性”(赵俊海等,2013)。时至今日,其贡献也多体现在概念的“隐喻”层面而非硬性成果的“涌现”,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对于训练学的“传统科学范式局限”以及“经由复杂性科学改良”的论点且不妨“悬置判断”。据此重新考究训练学发展困境的归因原点,直接围绕学科的实际知识性质以及人们赋予该学科的基本定位问题寻找突破口是更为效率化的做法。本研究通过拆解不同科学名义背后的实际含义,重新梳理、考察运动训练领域所涉及的各类知识的生产方式,从具体的知识性质这一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我国训练学的学科属性,为未来学科建构过程中的定位取向提出新的辩护,也为破解当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新的切入点。
1 既往的学科认识和路径选择
1.1 训练学的社科情缘
在我国,训练学从属于教育学。起初对它的解释为:研究运动训练的特点,以探索运动训练的客观规律,提高训练的效益(过家兴,1986)。目前,国内通用教材上将训练学定义为研究运动训练规律以及有效组织运动训练行为活动的科学。田麦久(2017)指出,训练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运动训练活动的普遍规律,并指导各专项运动训练实践,使各专项的训练活动建立在科学的训练理论基础上,努力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纵向比对来看,训练学的定义视域总体上并无较大出入,但并不难发现人们在叙述过程中对于科学的强调日益增多,科学、科学化以及揭示训练规律就是当前运动训练学科的主旋律。反映到学术成果上,项群训练理论、双子模型等经典理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双子模型是在整合了“木桶模型的短板效应”与“积木模型的优势补偿效应”的基础之上总结提出的竞技能力结构模型,该模型的建立在形式上对经管领域早期的模型范本多有借鉴(张克峰等,2019),母学科的“科学”性是其主要支撑;项群训练理论是我国学院派训练学理论独立性的旗帜,最初它被解释为揭示不同项群竞技规律与训练规律的理论(田麦久,2017),近年来已被进一步拓展为项群理论,并认为已经从一个狭小的学科概念发展为宏大体育学领域中得到普遍应用的科学概念,具有积极的科学价值(田麦久,2019)。
在科学话语持续走高的今天,如果不求甚解地体察词义或只从行政划分的角度来看,学界似乎已经给定了科学的实体范围,然而一旦问及“科学本身究竟是什么?”其仍然是萦绕在科学哲学家心头的晦涩难题。古希腊时期,柏拉图通过理念论“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的二分建构起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后诸多学者传承并发扬了这一理念,直到Isaac Newton撰写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后才真正促使了“科学”这个集数学演算、形式逻辑、实验实证于一体的新型学问声名鹊起。逻各斯中心主义先从本体论认可了“可知世界”的隐秘真理,又分别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通过先验演绎(尤其是数学)和经验归纳(尤其是后期的实验体系)建构了“因果甄别”的论述基础,从而衍生出“理论具有未来预测力”的实践效力。据此,将项群理论和双子模型归为科学俨然有些失格,且不论二者的研究范式中并未见数学的痕迹,实验实证和形式逻辑也都多有残缺。项群理论是面向于人定规则的建构物,双子模型提供的辩证语境作为一种学术解释条件尚可,而如果将其反映到实际操作层面,则会使大量的训练决断陷入模棱两可的地步(潘政彬等,2019),其知识性质既不符合形式逻辑的推演要求,也与科学最基本的预测性特质相去甚远。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理想的,或许真正的“Logos”只存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所以科学的名头并未被一口说定,加之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传播本就容易引起混乱,科学的“横蛮生长”并不难料想,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头衔的后进者,它的出现就是语言混用的典型。Auguste Comte(王幼军,2010)最早奠定了社会科学“习其表而非其神”的宏观基调,由于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还原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抗拒,导致本体论的束缚先行错乱,进而促使社会科学的因果解释始终“踉踉跄跄”,相关代替因果、概率论替换决定论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理核心。Paul Rudolf Carnap和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至后来的Karl Pop‑per都曾想作出些捍卫,但Thomas Samuel Kuhn的相对主义将科学范式解释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某种共同信念——“是科学家最终决定了什么是科学”(吴国盛,2016),这就等同于把科学含义的解释还原到了经典的“知识之辩”。尽管这种假借科学家认定的知识范式来为科学提起辩驳的做法本算不上对科学实在性作出的解释,在“科学”没有被实在性的界定之前也本无标准来界定“科学家”,但受到Thomas Samuel Kuhn的影响,哲学领域整体对科学理解的态度产生了一种从“辩护”、“批判”或“解构”到“审度”的转变(赵俊海 等,2013),关于名义的话题实际上已经被搁置了。进而受制于这种模糊的科学辩护范畴,科学名义在现实的社会构建中将要持续引发的误会自然也就无从了结。训练学学者何曾料想,科学之名义有如斑驳变化的忒修斯之船。与其先入为主地以“社会科学”语境来引领叙述,倒不妨坦诚地接受训练学的科学名义本就是从对科学的崇拜中衍生出的科学主义产物。理解了科学含义的流变,认清了自然科学之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科学的本质差别,再对过去的训练学理论提出批判便不难发现:将理论体系层面的不足映射到实践应用层面的失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性质的知识本就不是某种科学真理,它只不过在自然语言的环境中与科学“齐舞”,并最终以文化的形式影响了人们的行动。
1.2 生物学范式的影响和局限
回答“为什么”是学术安身立命之基本。但训练学的期待若只是局限于学术化地提供一种解释,便难以形成体系化和繁荣发展,毕竟训练研究的初心在于指导实践应用。相比于社会科学,生物学在Francis Galton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更加系统化的模仿传统科学的道路,而且往往也能够提供更加现实有效的实践方针。于是站在社会科学的视角之外,另一类训练学科学性的捍卫者往往会选择“投靠”生物学阵营。苏联以马特维耶夫为代表的训练学系统深刻影响了我国训练学的发展(黄淡伟等,2017),其中最为我国学者广泛吸纳的周期训练理论就是在生物学范畴的超量恢复和应激-适应等假说的基础上酝酿形成的。
超量恢复作为最早引起训练学领域注意的生物代谢机制,是一种从能量代谢的角度引申出的概括性总结。而后Hans selye提出的应激-适应理论尽管更贴近运动训练的宏观生物学基础,促使训练学领域内对生物学基础背景的取向性作出了调整,但并没有扭转这类理论在底层架构上缺乏大量、具体的实验数据支持的局面,也无法从根本上对人体运动能力进行量化解释和论证(陈小平,2017;李捷等,2018)。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创建的周期训练理论是实证性较弱且抽象的,其本质就是在某种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教育学方法论而对竞技训练过程提出的解释和归纳(曹锦飞,2013)。论科学名义,其做派并不是直接关注真理问题的纯粹科学,将其定位为传统科学范畴是不妥当的。这也促使了很多学者认为,针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和定位,训练学应进一步着眼于生物层面的基础研究,从而提高训练学的科学性(陈小平,2010;黎涌明 等,2020)。
可生物学是何性质?通常而言,生物学被理解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也由于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核心框架同传统的自然科学高度相似,生物学受到了许多科学统一论者为其“科学”名号辩护。它相比社会科学命题具有更高确定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生物学命题不完全等同于人和社会双向构建的社会问题,生物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实验甄别单向度的因果关系;二是生物学的哲学起点不在于回答自由意志构建出的问题,如神经科学,其本就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解读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李夏冰等,2020;肖根牛,2018)。但遗憾的是,现阶段生物学所认定的规律也并非完全像是牛顿经典力学那样具有高度现实还原性的规律法则,生物学结论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取得了实验室意义上的统一。一方面,生物学是典型的“科层科学”,当研究得出了某个生物现象的发生机制,并不代表同时掌握了该现象的高层因果关系,因为现象通常是一般的,而机制则是个别的;另一方面,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利用数学推导,数学方程的转换大大降低定律之间的壁垒效应,有利于系统有效性的维系,而生物学中的这些机制与其核心理论进化论(乃至其他学派)之间却并不存在像经典力学那样(如牛顿定律与其他定律之间)通过数学互相转换的确定性关系(董自立,2017)。因此,严格来说,生物学的因果“咽喉”仍被还原主义紧紧“扼住”,其学理身份尚未分晓。
科学作为学术利益的重要标靶,被各学科领域追捧称为大势所趋。对于因果闭环未能有效成立的知识范畴,定论科学其名仍需谨慎。毕竟科学的预测性首先要求实现实践检验层面的完整闭环,模型本身的系统质量达不到实际应用情景的标准,就绝不能纵容打着“科学”旗号的妄想。在已知生物学无法满足因果闭环的前提之下,借以行之的训练学并不能直接冠以“科学”的名义,即便现实的发展早已面目全非。不只训练学,包括和训练学视角最为接近的现代医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代医学是典型的入世显学,通常也被宽泛地冠以“科学”之名,但从现存的学术成果来看,一些模型的实际质量(如先验程度及相应的置信水平等问题)缺乏仔细斟酌,许多发现在随后的研究中根本无法复制,有些甚至在重新分析原始数据时也无法得出相同的结论,以至于大量既存证据的实际有效性备受质疑(Goodman et al.,2007;Kafkafi et al.,2018)。
2 学科属性的分析论证
2.1 分析前提
对同样作为入世之学的训练学来说,现代医学的众多科学化成果是不容忽视的。况且在推动运动训练学形成的早期,学者群体就普遍具有医学背景,是医学的视角构建了现代运动训练的发展基础(王雷等,2017;杨群茹等,2018)。因此,本文并不反对运动训练的“生物科学化”提案,但由此也将要引申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生物学基底究竟能给训练学提供多大的空间?训练学问题和医学问题在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即“干预”方面存在核心差异。医学干预主要采用药物、器具、手术等需要被动接受的外源性手段达成目标,这类干预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因果联结大多可以简单对应,而且每一种干预方法在正式取得合法化地位之前都需要通过系统的检验,所以总体上为科学这种严苛的论证策略留有足够的余地。比如医生在应对某一病症时总是直接提取经科学核验后的专门化处方,倘若出现科学一时无法给出答案的局面,可以宣告已尽最大努力但暂且无计可施,这是信守科学本身所需要遵守的。训练干预的核心立足点在于人体运动,其实质是一种主动的内源性激发过程。“人体运动”问题在本质上至少包含了动作结构的排列组合以及作为其支撑的能量代谢两个层面(黎涌明等,2014),粗略地来看,训练就是把一系列的“人体运动”问题有计划地编排组合并且持续给予调控的过程。更进一步来说,“人体运动”本就是直接嵌入生活的一部分,训练除了要处理在狭隘语境内被称作“训练”的专门性时段中的人体运动,还要处理渗透在专门性时段以外的人体运动(体力活动)。与此同时,诸如营养状况、休息节律、情绪心理等一系列本就从属于生命活动的、不容许被肢解孤立的行为范畴也是训练所必须要考虑的要素。故训练的终极含义是一种面向生活方式整体所实行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行为筛选和主动调节。同样作为一种“价值实现过程”,训练的每一个干预部分都与其最终目标之间保持着因果的间接对应,这就导致训练所需要涉及的复杂程度和为了维持科学性所需要达到的系统精细化程度远远高于单一的医学问题,训练干预的内源性难以给予科学合适的自由度。
训练计划中的任意一个细分环节都可以设计随机双盲实验,即科学能检验干预A、B、C等独立变因的有效性,验证同一变因模板下不同干预水平的A1、A2或A3的优越性,但由于训练作为贯穿生活的一部分,不仅仅是由一个或简单的几个干预方法构成的,实际训练是将各种各样孤立的科学干预方法交叉串联后形成的复合体,其最初的形态就已经属于庞杂的“鸡尾酒疗法”。人们越是渴望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的训练,就越需要增加干预变因,而每增加一个变因,想要进一步证明这一整体的有效性是否仍然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就会更加困难;反过来,如果忽略细分环节的变因科学性,参照整体训练范式设计双盲实验可以检验成套计划的科学有效性或优越性,但对整体性计划的简单信赖本就潜含着对奥卡姆剃刀原则的选择性无视,如此一来就无法判断整体训练设计的各个环节究竟是在切实地发挥价值还是制造冗余。真实的训练情景是存在不稳定因素的,训练难以参照预先给定的科学证据制定出计划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必须普遍地、及时有效地根据具体情形调整决策判断,倘若刻板地遵从整体主义的科学证据就会失去计划调节的自由度,无从应对训练中的偶然性问题。
究竟哪些变因是核心的?哪些变因是附属的?变量之间如何扭合?扭合之后是保持线性叠加还是效应制衡?各个变因在时间序列中的交互反应如何?变因之间又潜藏了哪些次生问题?这些最为基本的因果论证才是真正重要但又非常难以回答的训练“科学”问题。简单地凭借“机制主义”给训练学冠以科学的名号并不能解决实际训练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事实上盲目地吹捧科学无异于对实际问题含糊其词地掩盖,假借零散证据宣扬一种在语境中被无限泛化的科学,很难说这究竟是在提供科学证据还是在提供新的偏见。真实的训练情境中,教练员在应对基本因果问题时仍不得不基于既往的执教经历而作出直观经验判断(或者说一种带有抽象演绎意味的先验判断),最后更是会凭借比赛成绩或达到预设目标的程度来审视训练的整体实效性,评价既往干预的科学正当性。而这时答案的求证条件显然已经被推进了追验(后验)范畴,训练学实质上就会变成训练史。所以,只要各种主观主义倾向的方法论无法抹消,训练学就注定难以走出所谓“社会科学”的框架,更难以成为具有稳定预测功能的“科学”。
2.2 训练发展的终局论证
言之将至,究竟要如何断定训练学的学科性质?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引入的视角是:运动训练发展的尽头在哪里?倘若未来系统生物学或某一复杂性科学领域的发展达到极致,人类破解了生命甚至社会的“密码”,生物学足以像物理科学那样使用定理转换,此时的人体问题已变得清晰可控,问题的消解会宣告知识的终结,也就自然不再有进行训练学研究的必要,训练研究的尽头很可能是由某一门训练学以外的学科来决定的。甚至,训练学存在的必要性可能仅仅发生在这一科学“爆炸”之前,正是由于科学真理的未完成性,人们才需要借助科学以外的知识框架来实现工具理性,若狭隘地认为只有那些事先经过“科学”验证的结论才能被合法地视作训练学成果,则训练学研究和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研究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在实质上就根本没有区别。至于人类最终能否破解生命体的复杂性乃至自由意志等问题,目前无从知晓。在这一命运的转折点到来之前,训练发展的最佳状态可能是研究者以某种技术途径(如AI)整合大量定性、定量证据,进而实现一种无限接近于最佳的实践决策状态。据此反推,如果是某种技术代表了运动训练自身发展的终极形态,其实恰恰就说明了训练学研究的核心性质是要着眼于“技术”本身的。
3 新型定位取向的确立和建构展望
3.1 从科学到技术语境的转变
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吴国盛,2009),基于现代科学所派生出的新技术(即新的存在方式)推动了执教的进步,它促使人类的竞技运动成绩屡创新高并且真正在健康促进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Marinho et al.,2018)。但由于人们既往对科学的崇拜,导致我们给予技术的尊重较少,因此对它的研究也较少。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中最为完整的已知部分之一,一直处在科学的阴影之中(布莱恩·阿瑟,2014)。或许要对科学和技术的边界作出决绝的判定是一种自负的“霸权主义”,但只要在二者的抽象化性质归属层面稍加比较便可以发现,科学建构于技术,而技术是从科学和自身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技术的目的论起点不是“求真”,它最基本的要求是“求实”,这一点同科学相对,也和训练所处的真实境地高度吻合,训练所指代的技术范畴是涵盖了追踪科学证据、总结实践经验、配合社会文化和个体的背景要求而实现的一系列身体治理。
相比于谋求社会科学的美名和生物科学的庇护,大方承认训练学的技术名义本无可厚非。但一提起技术,过去我国体育界的普遍做法是把技术(technology)直接等同于实践操作流程上的技能(technique)和技巧(skill),往往忽视了技术本身的知识性要素,进而导致训练学学科性质的根本解释在逻辑的起点就已经产生了偏差。推及上文已经谈过的所谓科学化发展较好的医学领域也在经历着相似的问题。现如今医学领域内部已有部分学者隐约意识到给医学武断地扣上“科学的帽子”有失妥当,如樊代明(2015a,2015b)指出,医学不是为科学服务的。这不是说医学不具有科学的成分,而是科学并不能指代医学的全部。一直以来,人们在寻常的语境中讨论西医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其指称为科学,而把语境转移到同属医学技术的中医上便不然,与其说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科学与否的真理争辩,不如说其背后的实质更像是打着科学主义旗号的“技术体系”话语权争斗。实际上,反观美国等西医占绝对主导的国家,医学与科学也没有纠缠在一起(赖立里,2017)。
对于技术命题,美国也曾经历过一段“简化解读期”。主要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大批倡导“纯科学信念”的科研人员从德国留学归美,逐步衍生了“技术就是科学的直接应用”这一观念,也由此导致了人们往往不加批判地把技术直接解释为“应用科学”,直到20世纪40年代,“工程研究”才作为一种原创性研究获得普遍承认(陈红兵等,2006)。技术共同体的社会位置和技术学科的构建形式伴随着群体利益的纠葛、价值立场的争斗在历史的沉浮中不断变化,体育领域也不例外。1964年美国体育领域“学科革命”爆发,促使技术性学科逐步转向了纯粹的学术性学科(于涛等,2017),此后带有人体运动控制(技术治理)意味的人体运动学(kinesiology)作为一种上位概念跃上台面,不仅指代了研究人体运动的学术体系,还接纳了与各种体育运动相关的科学、文化、管理类研究者在其名义内开展研究,从而进一步在宽泛意义上成为体育研究聚合体的指称(周建东 等,2017;朱为模,2003),参照我国训练学所处的真实位置(技术研究)则很难再找到相同层级的“等价物”,将“运动训练学”翻译为“sports training science”多少是有些不恰当的。
在命名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种独立的知识结构,邓运龙(2015)解释训练学研究为“philosophy of sport training or training philosophy”(直译为“运动训练哲学”)更加有迹可循。毕竟相比于从其他领域拼凑得来的“科学硕果”,人们从实践中酝酿出的、有关训练技术的哲思、观念才是训练学所独有的知识成就。除了前文所叙述的我国训练学领域的原创观点(项群训练理论),另一个我国独创的训练学成果——一元训练理论——堪称既往运动训练哲学探讨的典范(茅鹏等,2003)。运动训练哲学这一概念在国外的体育学术领域虽略显小众,但也有学者专门撰文讨论其重要性(Caulfieid et al.,2018;Gearity,2010)。实际上,许多教练团体或者个人在现实的训练实践中大多已然默许了某种对于训练的哲学理解,并以此阐述和建构着自己的训练体系。比如NASM(national academy of sports medicine)体系一直着重强调 OPT(opti‑mum performance training)发展模型,这就是在建构主义的思想下对力量发展的次序性原则所提出的一种先验叙述,是典型的技术理念。
不过,当人们讨论哲学时究竟是在讨论什么呢?是爱智慧?抑或一种反思或批判(Edmonds et al.,2010)?哲学本就是一个比科学更难定义的范畴。更为朴素地来说,邓运龙(2015)所述的运动训练哲学是指在训练中所贯彻的一系列理念,它在性质上并非纯粹科学的知识成果,但绝不失为人类智慧探求的结晶。如果接受哲学作为一种理念的解释,训练学的学科性质就很清楚了:它是在科学证据、经验判断等知识条件的基础上,围绕运动训练实践提出反思、审视和批判后所凝练出的一系列技术治理理念。
3.2 技术学科的建构展望
提倡训练的科学化是情理之中,但是训练学这一学科的科学化则应是另一个话题,这是本文致力于澄清的一个误解。实现人体运动控制的最佳策略是高度个体化的,技术探讨的目的除了针对通用化体系的探索,还需要涵盖特异性需求及其解决方案的有效连接。严格来说,每个技治者所秉持的技术原则都应是不尽相同的,那种普适性的、宽泛性的技术原则是新手的“敲门砖”、高手的“裹脚布”。人类行为事务的技术治理,在实现有效创新增长的频数上也无法像传统工程领域那样以“大创新缓慢但小创新不断”的思路加以理解。对训练学处理的问题本身而言,由于每个给定的组织系统所带有的技治独特性将要演化出其特有的默会知识,这类知识的缄默性又导致知识体系的传递困难(就算公度出之后也很难具有实践应用力),所以优质的理论只能是在时间的过滤中沉淀下来的极少部分。对于一门追求应用价值的学科来说,除了考察通用化的治理体系,更多地重视实践中的条件性技术策略和科学本身而不是重视“科学主义”,才是真正有助于学科实在性进步的建构取向。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训练派系虽然不乏技术理念的探讨,但很难同我国既往训练学形式的细分领域实现精准对接。不过当然,并不能因此判定过去我国在训练问题上所作出的理论探索是毫无意义的,其技术理念研究的价值性应得到肯定,毕竟这一重视倾向差异的最终分水岭不过是对实用主义的理解不同而已。就目前的训练学领域来说,改变并不是遥远的东西,改变的第一步是转变观念。选择离开社会科学的语境,直接以技术为学科归属的辩护前提来支撑其名义的正当性,并且以技术的角度审视和传播训练理念才能逐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4 结论
通过解析科学名义背后的实际知识性质,回应了在既往训练学学科性质解读中各类诠释误区的生成缘由,并基于训练实践所提供的条件要素这一实在性基础,分析阐释了训练学的学科属性,认为训练学是在科学证据、经验判断等知识条件的基础上,围绕运动训练实践提出反思、审视和批判后所凝练出的一系列技术治理理念。技术研究合理性地位的确立应当是训练学学科定位过程中的基本面。面向未来的学科发展建设,理清学术逻辑,更加实事求是地传播科学精神与技术思维,或将是真正促进运动训练领域高质量迈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