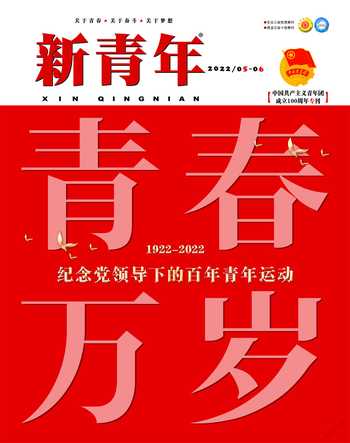叫一声“老团哥儿”,我爱听
韩玉皓


作者(后排右二)在参加铁路分局系统小学少先队辅导员会议期间留影
“五四”前夕,我们几个曾经的团干部又聚在了一起。尽管已经离开共青团近40年,但是每次相聚时的“老话题”还是常说常新。大家都把每年“五四”前夕的聚会当作一年里“盛大的节日”。一声“老团哥儿”,叫得我心里暖暖的。
那是1984年的春天,大兴安岭的达子香开遍山野。当时我是伊图里河铁路分局教育系统的一名普通团干部,迎来了第一个需要组织活动的“五四”,从此有了一段难忘的“团干”经历。
“五四”这天,春光明媚,布谷声声。分局团委组织“青年突击队”标杆和骨干团青,来到牙林(牙克石至林区)线腹地的一个叫道木达的五等小站。
“道木达”是鄂伦春语,即“平坦之地”。它介于牙林线上行方向图里河和伊图里河两大站区之间。山清水秀,丛山列阵,溪水潺潺,四野开阔。
八点多钟,两台“青年号”机车牵引着两地团青乘坐的“专列”, 分别从图里河和伊图里河两个方向相对开来,在道木达站仅有的上下行两条钢轨上停了下来。 各路人马迅速在路基下会师,团旗飘飘,歌声嘹亮,汽笛声声,山谷回响。各队开始向会师总指挥、分局团委书记报告。领队戴着白手套、大檐帽,穿着笔挺的铁路制服,胸前的团徽熠熠生辉。
“书记同志:第 X 大队,集合完毕,向您报告!”
“好,请准备活动!”
“是!”
“一定注意安全,祝你们活动成功!”
“哗……”一阵掌声伴着欢呼声飞向蓝天,青年们跳了起来。
年轻的我被深深感染了,不禁热泪盈眶。五百多人的队伍向原野进发,向馒头山挺进,浩浩荡荡。漫山遍野,是我們的队伍;漫山遍野,是团旗的涌动;漫山遍野,是嘹亮的歌声。
那时,山里的文体活动单调乏味,特别是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就更没什么好玩的了。因此,分局团委决定搞一系列冰上活动。其中一项就是抽冰尜比赛。
说起抽冰尜,一两个人还好办,一大帮人在一个冰场上搞比赛,真是不容易。可越是不容易越要搞,青年人就是有这股子冲劲儿。我们请来学校的体育老师当顾问,帮着制定方案,最后决定分成中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每组人数不限,报名截止时间不定,只要在比赛前能上场就行,按时计算成绩,坚持到最后者为冠军。冰场是分局团委和体育场管理人员起早贪黑浇的。
比赛当天,冰场上被扫得非常干净。冰场周围插满的旗帜被风吹得呼呼响,围观的人冻得直跺脚。尽管天寒地冻,但除了参赛队员以外,工人、学生、家属,还有单位的党委书记、段长、工会主席也都来热情地站脚助威了。
比赛从中午开始,一直比到太阳快落山,大伙抽得是越来越起劲。最后,我们夺得了青年一队和少年组的冠军。你猜奖品是啥?分局团委请工程段团员用桦木旋出的一个老大个儿的冰尜——领奖的时候是被参赛的两个孩子共同托举起来的。
后来,这个大冰尜摆放在了第一小学的少先队荣誉室里。从此,冰雪活动在全分局的学校中一天天兴盛起来。

作者年轻时照片

作者(左一)主持伊图里河铁路分局文艺演出
我们分局所在的伊图里河处在一个山坡上。学生踢足球、打篮球,往往稍一用劲儿,球便被踢到山坡下,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拿回来。
于是,一场自建运动场地的“青年义务劳动”开始了。当时,还没有双休日这一说法,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我们往往是白天上班,挑灯夜战。星期天那就更不用说了,昼夜不歇。
“青年突击队”的旗帜,从山花盛开飘扬到大雪封山;共青团的歌声,从清晨响彻到夜晚。用镐头刨,用铁锹挖,用手抠,靠人拉肩扛,靠用土篮子挑,我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持续干了三年多,在山坡上开辟出“青字号”的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学校的操场。
就这样,我们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就这样,我们在“高寒禁区”创造着铁路运输安全的奇迹;就这样,我们为祖国边疆建设无怨无悔地奉献着青春和力量。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兑现着最初的诺言,并为之不懈努力。
那一年,哈尔滨铁路局团委举办跨世纪青春晚会,我奉命来到哈尔滨,住在招待所里,完成了全部策划与撰稿任务;那一年,哈尔滨铁路局团委编辑哈铁共青团史,我甘当顾问,丝毫未有懈怠。
如今,我退休了,又来到了哈铁关工委的岗位上,这是我未竟事业的延续,也是我青春生命的延长。参加红色场馆建设,担任哈铁史话的执行主编,讲述红色故事,创作文学作品,出版历史文集,成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红色推广人”,由我作的《再穷也要读点书》《国际歌,在哈尔滨是从这里唱响的》报告和相关视频进入了中小学校课堂,开始了我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又一次“会师”。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让青春拥抱时代……”朋友,您还是叫一声“老团哥儿”吧,我爱听。这不只是一个称呼,更是一份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关工委
(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