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娥
史 越
五奶想儿媳妇小娥。
小娥低个儿,圆脸儿,鼻子周围有好多“黑炭沙”。人们习惯把黑炭沙叫成“蝇子屎”。五奶不,五奶说,俺家小娥成天在外头做活儿,黑炭沙是叫老阳儿给晒的,叫风给吹的。
五奶的儿子长富,对于小娥的脸,也说过“蝇子屎”。
五奶对长富说,给你一个芝麻烧饼一个馍馍,你吃哪个?肯定是烧饼吧,为啥,因为有芝麻,香,咱小娥就是芝麻烧饼,好看,好吃。
五爷是好木匠,家里时光比一般人家都好过些。五奶用碎布头缝了个书包,送长富去上学。那时候村里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师,支书本家兄弟王川在学校代课,王川一个人顾了吹笛子顾不了捏笛子眼。支书一趟一趟跑文教局,好话说了一火车,终于盼来一个正式老师——老齐。
老齐报到那天,村里像过年一样喜气,大人把孩子送到学校,说,该嚷嚷,该打打,嚷了打了俺当大人的保准不找事儿,只要孩子学本事长材料。
长富撵猫斗狗拆猪圈掏鸟窝捉蛤蟆,王川罚他站院子,用棍子打他手,用笤帚疙瘩打他屁股,他趁王川不注意,扎破他的自行车胎,还在他的夜壶下面钻眼,还把死耗子放进他被窝,还尿尿浇灭他的煤火。到了晚上,村里的人都躺下了,经常听到王川叫着长富的名字骂娘。
五奶五爷没少给王川赔不是。回到家,长富免不了挨打。不论五爷打多狠,长富从不求饶。有时候,打累了,五爷扔掉手中的家伙,扇自己的脸。
老齐习惯在讲课桌上放根烟,讲课讲到精彩处或者课讲完,划火柴点着吸几口。那天课讲到一半,可能是晚上没睡好,老齐觉得浑身没劲,想吸口烟提提神,划了好几根火柴,怎么也点不着烟。学生谁都不敢吭声,只有长富憋不住,笑了。老齐推推滑落到鼻子尖被长富卸了一个镜片的眼镜,费了好大劲儿,才看清手里拿的是一根粉笔。
学生点煤油灯点蜡上晚自习,一个晚自习下来,鼻子孔被熏黑,吐口痰,痰也是黑的。鼻涕虫李毛孩穿了件新棉袄,长富从本子上扯下几张纸开始画画。第一组:李毛孩的爹死了,李毛孩整天哭得鼻涕连天。数九天李毛孩喊冷,朝娘要棉袄,他娘说,以前都是你爹抱着你暖你,你没有爹了,哪儿来的棉袄?第二组:李毛孩还是要棉袄,他娘站在街口说,谁能叫俺儿穿新棉袄,俺儿就认谁当爹。第三组:老光棍猪医生黄成家有新棉花有布,李毛孩穿上了新棉袄,再也不流鼻涕了,撵着黄成喊爹。
第二天,长富溜进老齐屋偷来糨糊,把画贴到李毛孩后背上,李毛孩背着画晃荡了一上午,见大家看见他都捂着嘴笑,刚开始以为是眼气他的新棉袄,后来觉得不对劲,最后脱下棉袄哭着去找老齐。
老齐跟五爷说,捉弄欺负李毛孩,长富是真该打,但是他画的确实不赖,要能专心学习就好了。
可长富厌学,顽皮得谁都管不了,初中没毕业就不上了。仗凭个头高,他学木匠、学瓦匠,都是学不了多长时间就不学了。
娶了小娥后,五爷五奶问长富到底有啥打算,长富说想去县城学裁剪。
别人都学两三个月,长富一学就是一年。开春进城,年底才回来,裁剪没学会,学会了赌钱。
过完年长富去县城,小娥抱着儿子跟去了。小娥闲不住,带着孩子揽活儿给人搞清洁、洗衣裳,挣钱补贴家用。
这天长富问小娥要钱买烟,小娥说,你见天在师傅裁缝铺子帮忙,一个钱儿也没攒?老实交代,钱都拿去干啥了?
长富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小娥说,爹和娘早就觉得你不对劲儿,才叫我跟来的。你把钱喝酒了?还是赶时髦去歌厅唱歌了?要不就是……小娥停顿了下,又说,要不就是赌钱输了?
赌,长富猛地抬起头,看了小娥一眼,见小娥沉着脸,鼻子旁边的几个“黑炭沙”比平时更显眼,长富慌忙挪开视线。
小娥说,叫我猜着了吧?你肯定赢过钱,要不咋会上瘾?可你要明白,没有谁能靠赌钱发家致富。你不可能每回都赢,就算你回回赢,你赢的钱哪儿去了?你如果回回赢,人家早不跟你当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小娥说罢,拍了拍长富肩膀头。
长富抓住小娥的手,打保证说,我以后不赌了,再不赌了。
隔三岔五小娥就带着孩子回家看公婆,公婆也会坐车到城里来看孙子。
年底要回家,一大早长富攥着一把票子不放,崭新的票子,被汗津津的手揉巴得软塌塌地,没了筋骨。
小娥没好气地说,拿来吧别捏巴了,票子不是鸡蛋,你不是抱窝的老母鸡,暖到明年,你也不能让它们下出崽儿来,赶紧的上街去给爹娘买点年货。
长富支支吾吾,本来说好的,给你交三百,现在剩一百多点,你回家那几天,我,我输了小二百块钱。
小娥说,你可真行,看都看不住你,我说咋的叫我回家那么利索,敢情你早就计划好把我撵回去,好甩开膀子干坏事儿。
长富说,你骂吧,打我也行,这一百多里,还包括有欠师傅的六十块钱,欠账不搁年,一会儿我得给师傅送过去。
小娥脸都白了,以后你要是欠赌债多了,干脆把我们娘俩顶账,我肚子里还有一个,都送人给你顶账吧。
长富像遭了雷劈,说啥呢,咋能叫你顶账呢?那样我还是个男人吗?往后我再也不赌了中不?
小娥哭了,你有个男人样没有?爹娘岁数大了,没花过你一分钱,你整天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还让他们操心。小娥掏出一把钱,哭笑不得地说,我告诉你说长富,以后你就赌吧,大不了输多了用我顶,把这拿着,赶紧去买东西。
过年的鞭炮是五千响的,啪噼啪脆响,长富却觉得闹心。饺子是猪肉大葱馅,包饺子时,五奶把两个钢镚洗干净,说咱马上就是六口的大人家了,包一个毛壳有点少,包俩,谁吃着毛壳饺子,谁有福气。
长富吃到一个,另一个被五爷吃到了。
长富尝不出啥滋味,觉得跟平常的饺子没啥区别,甚至还没有平常的饺子好吃。
五爷高兴得胡子一翘一翘的,一个劲儿地说,今年的饺子比哪一年都香。
第二个孩子是个粉团似的小闺女,闺女会喊娘了,小娥却不声不响走了。
五奶五爷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割麦子时小娥回来,瘦得皮包骨头。干一天活累巴巴的,还熬夜给他们拆棉衣裳拆褥子洗床单做被子,天天晚上给他们洗脚。临回城,小娥把三百块钱给了五奶,说,娘,你和爹想吃啥就买点,千万别亏待自己,你俩身体好了,才能替我带孩子,他们还小,离不开恁。
五奶说啥也不要小娥的钱,小娥打架似的硬给五奶塞到炕席下。
当时五奶纳闷,有长富和孩子在身边,她和五爷又没病没灾的,小娥咋就哭了呢,还哭得那么痛。
问小娥为啥拍屁股走人,长富老牛大憋气。五奶睁眼泪合眼泪,五爷一声接一声叹气。邻居开导五奶,小娥走也走了,日子还得过下去不是,长富年轻长得又不孬,大不了再娶一个。再说你就是把自己急死,小娥也不知道啊。丢下俩孩子,心够狠的,甭想她了。
外人说小娥的种种不是,五奶左耳朵眼进右耳朵眼出。娶小娥进门过第一个年,五奶给小娥一百块磕头钱,叫小娥给亲戚家小孩开压岁钱,其实长富家独门小户,没几家亲戚。小娥知道连翻盖房子带结婚典礼,家里已经垒了饥荒。小娥说我不买啥,屋里啥也不缺,衣裳啥的娘你都给我置办好了,不用给我钱,看看借谁家日子紧,赶快还了。
五爷咳嗽带气喘,整夜睡不着,小娥带五爷去看病,又买了红梨和川贝。她小心地挖去梨核,把冰糖川贝放进去,用白线绳把梨捆好放碗里,续上没过梨身一半的水,搁笼屉上,水开后蒸十分钟,让五爷喝梨汤吃梨肉,过了半个月,五爷的咳嗽好了。从那以后,不管谁家有人咳嗽,小娥都变着法教他们炖梨煮白萝卜水。
长富脑子里过电影似的,晃过一幅幅画面——
那次小娥回老家,长富觉得自己解放了,把家里的钱归拢了归拢,一头扎进牌场。
一共三千多块钱,那是他每天在师傅裁缝铺帮忙挣的,还有小娥给人洗衣裳和打扫卫生挣的。他和小娥已经安排好了这些钱的去处:买个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送回老家,让爹娘每天都有电视看;给爹买个好一点的棉大衣,去年给麦子浇冻水,爹冻感冒了,打了好几天针,爹说过不要军绿色的,太扎眼,藏蓝色的就中;给娘买几盒膏药,娘老是腰疼,上次小娥给娘买了几片膏药,管大用了,只是一片膏药要十几块钱,有点贵,娘说自己好了,说啥也不让买了;给儿子买个电动小汽车,那天,儿子见别的小朋友玩电动小汽车,看了老半天,小朋友走了,儿子还不肯离开,小嘴嘟嘟囔囔,小汽车多好玩呀,爹给我买个小汽车吧;小娥牙疼了一个多月,带她去看看牙,再给她买件新衣裳……
第一天,长富输了八百多,回家挺床上,后悔进了牌场。都说歌厅舞厅是毁人家庭的地方,有的人手里有钱了,嫌自己的老婆不好看不洋气,到歌厅舞厅找小姐。老婆说地里该撒肥料了、孩子该交学费了、孩子生病了,他们说没钱,扭脸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到小姐身上。每每听人说起谁谁谁这样,长富都会骂他们猪,没脑子的猪,不知道香臭,拎不清轻重。老婆不好看咋了,不挡吃不挡喝的,模样差点又咋了,身上又不少一块肉,能掏心掏肺对男人好对孩子好对爹娘好,上哪儿找这样的女人去。再说了,模样差没别的男人惦记,搁家里还放心呢。
牌场比歌厅舞厅好不到哪儿去,自己是有钱了,还是长啥材料了,咋就作起精了呢,比较来比较去,自己还不如这些猪,最起码猪们有几个臭钱,他有什么,除了能背着老婆赌钱输钱,他啥也没有。提起不正干的人,人们常常说还不如喂个猪养个狗呢。喂个猪,到了年底能吃肉;养个狗,知道给主家摇尾巴,养大了还知道看家护院。
长富烙了一夜饼,上午师傅叫他去西街口接学员,他在城墙上转悠了半天,眼看着晌午错了,才想起来正事儿没办,撒腿往西街口跑。
天刚黑,长富就去找经常带他打牌的二胖,二胖说咱甭去了,最近我老输。
长富说,正因为输,更得去,去了才能赢回来,不去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说起二胖,还真有说头,人跟个铁塔似的,喜欢眯眼睛,都说他人憨心不憨,眯眼睛是在想点子。他是做小食品批发的,起早贪黑没白天没黑夜地忙。钱挣多了,买了汽车,盖了两层楼的新房子。有人估摸接下来他该换老婆了,然而,他没有。
他有钱,又喜欢撵时兴,因为胖,买衣裳不好买,只能找裁缝量身定做,他是师傅的常客,一来二去跟长富熟了。长富见过二胖老婆,像个大圆球,说话粗声大气,做事风风火火。有人嘲笑二胖老婆胖,二胖说,胖人七分财,不富也镇宅,你看工商局长的老婆,还官太太呢,瘦得跟个绿豆芽似的,脸没有四指宽,能有啥福气?
长富问他,为啥没有换老婆,是不是老婆厉害,打不过老婆。
他眯起眼,给长富讲了他和老婆的故事:他刚从老家来城里做生意那会儿,城里人欺生。一天,他刚发走两车货,对面和左右邻居眼红了,晚上偷偷在他门市门口挂了一个茅桶,第二天他打开门,被浇了一身粪便。还有一回,他把三轮车装满货,回屋拿了个水杯,轮胎被扎了。有一年过年,又宽又大的白纸,把他贴的红对子遮盖得严严实实。他报过警,警察来了,啥也查不出来。痞子们时不时地来找茬,那天,几个痞子围着他打,他老婆把他护到身子底下,痞子们打累了,临走还骂骂咧咧。他老婆喊住他们,只见她劈手夺过一个痞子手里的烟,撩开上衣,露出捆在腰里的一排雷管,像极了电影里与鬼子同归于尽的女八路,那帮痞子吓得哭爹喊娘,溜得比风还快。打那天起,再没人来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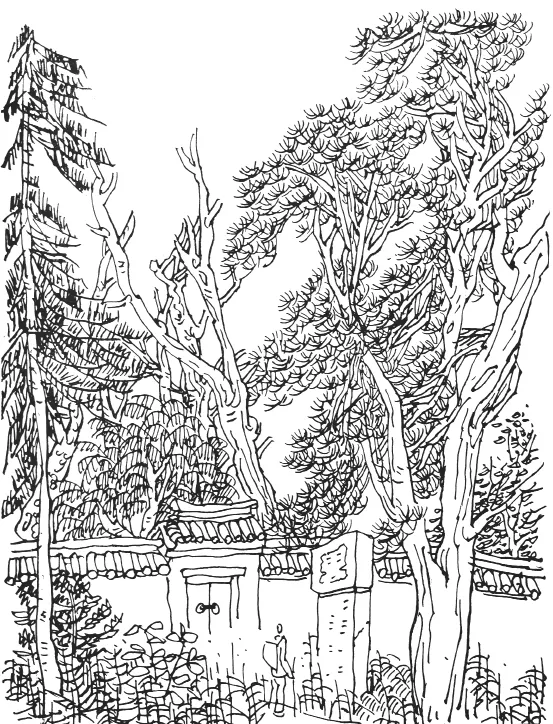
他只有一个闺女,老娘叫他们生二胎,他对老娘说他老婆太胖,怀不了孩子了。老娘说为啥怀不了,叫医生给瞧瞧,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调养调养不就怀上了。老娘的话不敢不听,可老婆更胖了,别人的肚子鼓起来,里头有东西,他老婆的肚子鼓起来,最后放几个响屁,啥也落不着。亲戚怂恿他,怎大的家产总得有人继承,你可以借腹生子,只要是你下的种,只要给够钱,这都不叫事。他说亲戚一肚子坏水。他对长富说,人得知道天高地厚,不管有多少钱,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婆的好。
他和长富进牌场,长富赢了钱,高兴地请他喝酒,他笑呵呵地说,打牌有输有赢,谁也不能一直赢,谁也不能一直输。输了甭着急,赢了也甭瞎高兴,打牌只是消遣,不能误了干正事挣钱。这酒我就不喝了。
有一回长富输了钱,不敢回家。
二胖说,怕输就别再赌了。
长富说,好好的牌咋就赢不了呢?二胖哥你借点钱给我,叫我往回捞捞。
二胖说,我的钱都叫我老婆管着,你要是真圆不了弧,我就给你找别人借点,下不为例。
这回长富又叫二胖给他找人借钱,二胖“嗤嗤”擤了一把鼻涕,抹到身旁的电线杆上,慢腾腾地说,以前借给你钱的肯定不能再找人家了。这回这个主儿,人很仗义,不把钱当钱。
长富好像看见了救命的稻草,眼睛瞬间亮了,忙不迭地说,那咱马上去找他。二胖眯起眼,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根烟,长富赶紧拿打火机点着,二胖吐了一串烟圈,等烟圈慢慢散开,说,这人是有钱,还不把钱当钱,但是你要还不上他的钱,他会卸你一条胳膊,最起码剁你一只手。这样的主儿,你敢招惹?
长富憧憬自己拿了钱到牌场腰杆挺直的样子,他下了赌注赢了钱的畅快,把赢来的钱还给债主,也许会把钱甩到债主脸上,或者扔到债主脚下,总之要多豪气就多豪气。他把钱交给小娥,小娥见多出那么多钱脸上的惊喜,瞧他的眼神往外溢出的全是崇拜,在她眼里,他是神一样的人物,他不仅是她的男人,更是她和孩子的英雄。至于爹娘,将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从此他不再让二老跟人闲谈时说不出口,他们会大声地告诉别人,俺家长富出息了,娘会笑出欣喜的泪来,爹会高兴得胡子一翘一翘。
见长富不回答,二胖推推长富,重复了一句,这样的人还是甭招惹了。
长富回过神来,我觉得我该转运了,就差本钱,二胖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说成啥你也要帮我一回。
二胖说,万一你又输了呢?小娥知道了,会找我拼命。
长富说,你不说我不说,她不会知道。
二胖说,咱先声明,这是最后一回,输了赢了你都别再找我。
偏偏长富灰头土脸地找到二胖,说,又他娘的输了,我点咋怎背呢。
二胖老婆瞥一眼像霜打茄子一样的长富,没好气地说,怪不得别人,怨你不懂黑白。
长富顾不上男儿膝下有黄金有白银,“扑通”一声跪下来,让我从你们家拿五千块钱捞捞,往后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你们没有儿子,哪天你俩死了,我给你们打灵幡摔老盆。
二胖两口子连推带搡把长富赶走了。
长富转头找生人借了笔高利贷。
小娥回城,长富说他欠了几万块赌债,小娥浑身发抖,骂道,周长富,你让我说什么好,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还钱人家剁你一只手,能怨谁,都是你自作的。
他害怕得门都不敢出,每晚噩梦连连,他对小娥长跪不起,爹说手是手艺人的命根子,我是裁缝,不能没有手。我有爹娘没有打发,俩孩子没有成人,如果爹娘知道我胳膊被人给卸了,会打死我,他们也会被活活气死的。小娥,求求你,替我想想办法,求求你想办法救救我。
小娥说,我有啥办法,你该不会真的叫我去顶账吧?
长富鼻涕一把泪一把,不,不是这样的,可你总得想个办法呀,我,我,我现在就剁了我的手,以后再也不赌了我。小娥让长富写了字据按了手印。
过罢年,风多雨少。有天小娥起床扫院子,长富说晚上陪师傅跟学员讲课,叫小娥甭等他。
晚上十点多,小娥出来找长富。师傅的裁缝铺锁着门,她转到裁缝铺后面小北屋的窗户底下,看见亮着灯,这是师傅师娘休息的地方,小娥抬手准备敲窗户,听见师傅连打喷嚏带咳嗽,师娘埋怨师傅不吃药硬顶,咳嗽得不住声,天明必须去医院。小娥整个人僵了,如同十冬腊月屋檐下的冰挂。长富并没有和师傅在一起。
小娥来到城墙根戏园子,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黑咕隆咚的小夹道,听见“哗啦哗啦”麻将洗牌的声音,一排溜六七间平房,都成了麻将场。这里原来是演员化妆的房间,最里面一间是敞开的,由几个台阶连着戏台,里面也摆着麻将桌。小时候,奶奶带小娥来看过一回戏,《天仙配》,坐在靠近台阶的长椅上,七仙女从平房里出来,快步跨过台阶,飘飞到戏台中央,赢得台下一阵喝彩。小娥不错眼珠地打量着七仙女,问奶奶,这是谁,咋这好看呀!奶奶说,仙女能不好看吗?
小娥走进去,听到长富在叫嚷,谁不跟谁软蛋,死全家!小娥忘了她是怎样把长富拽出来的,她在前面走,长富在后面跟,她走得快,跟长富拉开了好长一段距离,两个巡逻的民警看到她又哭又喊,不放心地把她护送到家,开导她想开点。
长富又说再赌剁掉自己的手,小娥捂住耳朵不停地摇头。突然她拱起脊背,双手按住胸口,蜷缩成一团,周长富,菜刀我傍黑就磨好了,在火台上,你去剁手啊,没人拦你。
长富抱起瘫软在地的小娥:你胸口又疼起来了是不是?都怨我都怨我,说完不停地用头撞墙。
小娥闭着眼睛,任由泪水横流,你不是不知道,生闺女的时候就检查出来了。我奶奶食道癌死的,我爹我姑姑也是,遗传的,有什么办法?反正我早晚都得死,还不如临死帮你一个大忙。小娥喘息了好大会儿,接着说,你得答应我戒了赌,老老实实出力挣钱,好好孝顺爹娘,好好把俩孩子养大。
城里的路比乡下宽,城里的人比乡下多,城里的灯比乡下亮得早,灯光色彩缤纷。穿戴一新的小娥,抱着女儿,跟着长富在一辆轿车旁停下。
小娥白白净净的,看不见“蝇子屎”。长富知道,小娥往脸上搽了奥琪增白粉蜜,那是他给小娥买的第二个物件(第一个物件是一个小镜子),这是个红盖子的白瓷瓶,里面是像雪花膏一样的东西。小娥抹了一回,说好东西就是好,味儿香香的怪好闻不说,还能让我知道原来我这么好看。小娥照着镜子热泪盈眶,对长富说,一直觉得你不稀罕我,现在才知道,你心里有我,谢谢你。我不后悔跟了你,给你生了两个孩子。长富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猛戳了一下,他抱住流泪的小娥,跟小娥一起流泪。长富说,一瓶这就叫你幸福成这个样,真是个傻媳妇,以后我铁定不赌了,我好好挣钱,你想要啥跟我说,我都给你买。小娥说,你咋对我怎好?长富说,你是我媳妇,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车玻璃摇下,一个大背头露出脑袋,说好的一个人,怎么来了两个人还带个孩子?
小娥说,孩子还吃奶,离不开我,长富欠你多少钱,你说个数,看俺娘俩够顶债不?
大背头说,长富你输不起就别赌,你老婆孩子还比不上你一条胳膊?
长富灰溜溜地,我爹说过手艺人不能缺胳膊少腿,我是裁缝,不能……
大背头连声呸呸呸,还好意思说你是裁缝,你给孩子老婆挣了几个钱?你老婆都比你像个男人,就算她真心替你顶债,我也不收。说吧,叫我卸你哪条胳膊?
小娥把孩子搁地上,随之从包里掏出刀,对大背头说,我替他中不中?
大背头愣了愣,劈手夺过小娥手里的刀,高举过头顶,继而转握到身后,末了扔进车里,“砰”地关上车门。小娥晕倒在地。
看热闹的人,好像提前撒好的一把草籽,齐刷刷地冒了出来。
大背头骂长富不是个东西,居然叫老婆替你顶债,真是个站着尿尿的娘们儿。骂完,开车绝尘而去。
长富声嘶力竭地喊小娥,号啕大哭。女儿也吓哭了。小娥躺进了医院。
长富第二次去医院,小娥人去床空,医生说是小娥强烈要求出院的,至于出院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她拖个病身子能去哪儿?她怎么生活?会不会挨饿?会不会发烧?会不会饿晕倒在路边?会不会流落街头?会不会遇到坏人受欺负?她胃疼起来,会不会疼晕在路边,被过往的汽车碾压?万一她倒下的那会儿老天爷正下大雨,她会被浸泡在雨水里的。这几年她给人洗衣裳、打扫卫生不嫌冷、不惜力,已经累出了毛病,遇到阴雨天,浑身大小关节都疼,有时候疼起来筷子都捏不住,吃一顿饭,要弯腰捡十几次筷子。不管碰到哪种情况,她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心里会装满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他,深深的绝望。
尽管长富不说,五奶也知道小娥走一定有原因,说到底还是长富不争气,喝酒赌钱,能跟他过还生俩孩子,够意思了,横挑竖挑,挑不出小娥半点毛病。五奶的心被掏空了。
五奶做完阑尾炎手术回到病房,冷得瑟瑟发抖,长富向护士要了几个葡萄糖瓶子,灌上开水给五奶暖,麻药劲没下去,五奶感觉不到瓶子有多烫,等麻药劲下去,才发现两旁肋骨被烫出好多燎泡,燎泡不小心被弄破,剥皮一样地疼。
五奶比任何时候都想念小娥,要是小娥在,会用毛巾包好瓶子,然后再贴着五奶的身子放,她会隔一会儿撩开被子查看,瓶子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五奶有没有被烫着。
五奶渴得嗓子冒烟,护士说暂时不能喝水,长富搓着手干着急。如果小娥在,会用棉签蘸点水,润湿一下五奶开裂的嘴皮。
熬过一个秋天一个冬天,五奶挺了过来,她抖擞精神,照看孙子孙女,喂猪种菜养鸡养鸭,给五爷往地里送饭。
有一次,两个孩子跟着五奶去地里,看到大片绿油油的麦苗,两个孩子兴奋得连蹦带跳,异口同声地说,爷爷种这么多韭菜,奶奶可以天天给我们捏饺子包包子了!
五奶赶紧纠正,这是麦子,不是韭菜。自那天开始,一有空,五奶就领两个孩子去地里,教他们认识麦子、玉米、红薯、棉花、南瓜、茄子、豆角。给他们讲杏花是白的,桃花是红的,油菜花是黄的,打碗花是粉的。告诉他们粮食都是庄稼人出力流汗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吃饭不能浪费。
春天燕子在屋檐下飞来飞去,两个孩子能一眼认出来,它们是去年就住在这里的。
长富开了裁缝铺,冬天地里没活了,给人裁剪做衣裳。过了两年,在镇上开办了裁缝学校,后来又办了童装加工厂,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只是这么多年过来,长富没有再结婚。他经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盖子的小白瓶,一看就是半天。
刚上初中的女儿,给长富叠衣裳,发现了小白瓶,拧开盖子,里面啥也没有。她说,爹,一个空瓶子有啥好看的,每天装身上,鼓鼓囊囊的,弄得衣裳一点也不板正,扔了吧。
长富慌忙说,扔不得!扔不得!这是你娘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我还给你娘买过一个小镜子,你娘当宝贝一样收着,我叫她把我们的结婚照夹到镜子后面,你娘说我自私,咋光想着自己呢,要夹就夹全家福。照全家福时你还小,你奶奶抱着你,跟你爷爷坐前排,你哥哥站在我和你娘中间,脚底下踩着椅子,我们仨在后排。相片洗出来,你娘真把它夹在小镜子后面了。
小镜子呢?
你娘带走了。
五爷去世那年,孙子已经是市中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了,孙女在省城师范大学教书。
五奶耳朵聋了,眼神却好到能穿针引线。孙子的婚被是五奶亲手做的,孙媳妇蒙头红四个角和正中间的钱是五奶亲手缝上去的。
都说五奶命好,五奶笑呵呵地说,命好命好,要是俺小娥在就圆满了。
五奶说得最多的是,小娥,可怜的孩子,娘的傻闺女,你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叫娘看看你,给娘说说话。你知不知道长富在等你,娘在等你,两个孩子也在等你,知不知道娘想你,你不回来,娘闭不上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