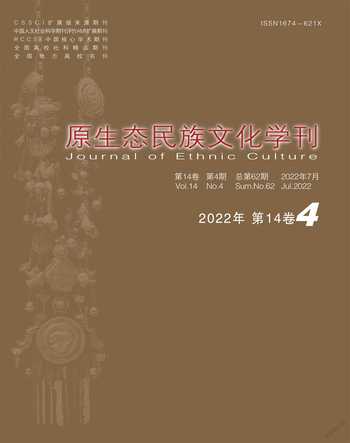佤族社区灾后重建中的利益博弈与文化重构
杜香玉
摘 要:佤族作为山区民族在长期的搬迁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民族文化建构的官方主导与民众参与的“互嵌式”地域灾害文化逻辑。2015年发生于芒卡镇佤族社区莱片村的“3·01”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灾后搬迁、村寨选址、房屋建筑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深刻地改变了当地佤族民众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村寨民众、村寨与村寨之间,甚至是村寨内部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决定着村寨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运转,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并对以文化为载体的一套世俗理念进行协调。深入理解佤族内部文化逻辑的重构,有利于全面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灾后重建及异地搬迁过程的复杂性、递进性,对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佤族;灾后重建;文化重构;莱片村;“3·01”地震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4 - 0044 - 10
佤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沧源、澜沧、耿马、孟连、西盟等地,因其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频发的自然灾害致使当地佤族民众经常搬迁,在搬迁过程中促进了各民族之间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目前,学界关于灾后重建的研究成果颇多,集中于灾害人类学、灾害民俗学、灾害史等领域。基于灾害人类学视角,李永祥认为灾后恢复重建应更多地关注社区需求,以社区文化和社会功能为核心进行恢复重建,才能避免产生新的社会脆弱性,实现灾后可持续发展[1]。基于灾害民俗学视角,王晓葵认为灾后在生活、工作秩序以及社会组织的重建完成之后,遗留下来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创伤往往会变成一种文化记忆沉淀于地域社会的基层,而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通过重构记忆的方式,重建地域社会的认同,这既是一种针对灾害的应对方式,也是社会基本文化逻辑的体现[2]。周琼提出了灾害史的文化转向,应思考灾后重建的措施及相关行为的文化内涵,通过重构某些灾害记忆及书写、表达、宣泄等途径,消解社会创伤,迅速重建地域社会的认同,从而引导积极稳定的社会心态,促进全社会对人性、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思考及应对,顺利渡过灾后社会脆弱期[3]。
从重建的内容来看,灾后重建并非是单纯的房屋重建,而是包含了社会、经济、文化网络等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重建。从重建的对象来看,地方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包括重建地的选址、房屋设计等,灾区民众在整个过程中缺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较少参与其中,继而造成了灾后重建主体缺失,引发社会内部诸多问题,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各利益群体在灾后重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背后隐藏的是一套深刻的文化逻辑。本文立足于灾害文化视角,以佤族社区莱片村“3·01”地震为个案,探讨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这些群体是如何进行沟通与协调而重建新的文化逻辑图示,实现社区的稳定与平衡,这对于今后的灾后重建及异地搬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利于推动边疆灾害文化研究。
一、佤族社区莱片村灾后搬迁概述
在历史上,由于民族戰争、资源掠夺、自然灾害、人口增加等综合性因素影响,佤族民众进行的整体性迁徙较为频繁,为其更快适应新环境以及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社会文化、族际交往的正常运行提供了良好基础,这一基础建立在民众自主选择、主动参与、积极融入的前提之下。佤族主要分布在东经99° - 100°,北纬22° - 24°,山峦起伏、平坝较少,常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干湿分明的山区,属于亚热带低纬度地区,地势复杂,处于澜沧—耿马地震带上,海拔高差较大,垂直气候明显,常年雨量在1 500 - 3 000mm,5月下旬至10月底为雨季[4]3。此种地形地貌、气候条件之下,使得阿佤山区成为滑坡、地震、塌方等自然灾害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和高发区。与城镇相比山区农村居住分散、经济基础薄弱,面临更多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佤族民众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已然形成了一套本土防灾减灾体系。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外来文化冲击、人口增加、与外界交往频繁以及外部生存环境改变,传统的防灾减灾意识趋于淡化,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防灾减灾手段和措施已经逐渐被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灾害管理方式所取代。
(一)佤族社区莱片村概况
莱片村隶属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芒卡镇,地处芒卡镇西南边,距镇政府所在地2公里,距县城108公里,辖岩门上寨、岩门下寨、莱片上寨、莱片下寨等9个村民小组、10个自然村。2017年末,耕地面积3 438亩(其中:水田1 184.2亩,旱地2 254.5亩),人均占有耕地1.4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拥有林地21 400亩,其中经济林果地3 674.2亩,人均经济林果地2.84亩,主要种植橡胶、芭蕉、香蕉、茶树等经济林果。近年来,莱片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有甘蔗、稻米、无筋豆、橡胶、玉米、竹子、沃柑等。1因水稻种植收入较低,村民主要在政府支持下种植甘蔗、无筋豆。从2018年开始还进行了木耳培植,共有2个木耳培植大棚。
历史上,莱片村较为频发的灾害包括地震、滑坡、火灾、风灾、冰雹、疟疾、病虫害(橡胶白粉病、霉病、炭疽病)、生物入侵(薇甘菊),其中造成较为严重影响的主要是地震、疟疾。2015年3月1日发生在莱片村的地震使竹蓬寨进行了整体性搬迁。竹蓬寨原来就有一户人家是因为1998年爆发疟疾时,从公勐胶队搬到竹蓬组的。在佤族的观念中,热的地方容易得疟疾,冷的地方不会得疟疾,所以从山脚搬到了山上①。莱片村是由多个村寨搬迁形成的村落,原名山下寨,佤名为旱谷地寨。原只包括山下寨(岩门寨)、山坡寨两个村寨,后来,山坡寨又分成永果寨(又名山梁寨)和大青树寨(今竹蓬寨)。之所以称为“莱片”,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莱片除之前两个寨子,加上扣勐村、焦山村农户搬迁而来形成湾塘寨(今田坝组),属于两不管地界,民众主要依赖于种植罂粟维持生计,鸦片商贩经常来此收购鸦片,故此取名“莱片”(意为鸦片交易的地方)。②1976年,因原岩门寨人口增加,又分为岩门一、二两组,一组搬迁至上芒卡(今岩门一组)、二组留在原地生活,永果寨也搬迁到因南立线开挖而发展起来的马队寨(今堆堆组)。未搬迁下来之前就已经分成一、二两组,一组是今堆堆组;二组于1978年,改名为专业队负责养猪及种植胶树。1983年,胶树种植面积扩大,二组和湾塘寨(今田坝组)部分农户又搬迁至今供勐胶队,二组剩下农户又自成一组并改名莱片胶队。③莱片村的最终形成源于历史时期佤族民众因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不断搬迁和融合,反映了莱片村佤族民众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二)“3·01”地震时的莱片村
2015年3月1日18时24分,在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芒卡镇(北纬23.5º,东经98.9º)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普洱、西双版纳、楚雄、大理4州市邻近沧源的几个县均有震感。截至21时,地震共造成沧源县芒卡、耿马县孟定两个乡镇房屋受损严重,并造成3人重伤、17人轻伤,地震致使6.2万人受灾;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沧源县芒卡镇,全镇人口1.3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8人[5]。
2015年“3·01”地震的震中是在莱片村,全村共有197户房屋受损,但无人员伤亡。地震发生时,据莱片村村委会的副書记回忆:“发生地震时,打电话联系媳妇,让我的父亲赶紧从屋子里跑出来,但是媳妇说,他父亲不愿意出来,老人认为有天上神灵保佑,房子不会倒,是因为老人原来住的茅草房在面临地震的时候不会倒塌。”④*在采访中了解到,佤族民众尤其是老人对于地震这种灾害并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他们认为地震发生时不要乱跑,仅是在家里坐着,一方面地震时要顺应天命,另一方面是地震时待在家中神灵会保佑,即使有事则是上天的惩罚。虽然2015年莱片村的大部分居民建筑已非茅草房,而是石棉瓦、红瓦等,但老人的观念却并未改变,竹蓬寨的一位村民说:“他们并不会刻意地去跑,而是坐着,因为他们认为地震是大自然和天的地震,是天命,要顺应天命,地震时候老人不往外面跑,他们觉得往外跑和在家里面结果都是一样的。”1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佤族传统民居建筑是茅草房,居民建筑结构有防震功能,而且莱片村经常发生小震,多是房子晃一下,并未造成多大损失和伤亡。
2015年“3·01”地震损失比较严重的是房屋,竹蓬组的房屋建筑大部分是石棉瓦建筑,房屋受损严重。据竹蓬寨的老组长说:“地震对房子的影响很大。”2除房屋之外,此次地震加剧了村寨的地质灾害风险,主要是塌陷与滑坡。据竹蓬组村民介绍此次地震前后情况,竹蓬老寨在地震之前也时常有滑坡发生,但是地震之后更为严重,村中大榕树下的竹林发生滑坡,落下去多处。据了解,地震之后,竹蓬寨的好几位村民都提到竹蓬老寨村子下面的山坡发生塌陷和滑坡,进村口的水泥坡上还裂了一条长缝。地震前的2014年夏季,寨子就发生了滑坡,2015年地震后,在村中大榕树旁的竹林下面这个坡上又发生了塌陷和滑坡,从公路进村的水泥破路上也出现了裂缝,村里操场上面的水池也有裂缝,另外好多家房子的墙面也出现裂缝,水源在神林东边0.5公里的山上,震后出水量有所减少。3关于滑坡的成因,竹蓬组村民认为可能是由于修建公路后,路面排水功能下降,无法及时渗入地面,集中冲刷山体,进而造成滑坡灾害。传统治理滑坡的方式主要是由老人对山沟进行清淤疏浚,减少山坡的水土流失及滑坡;国土部门也对此采取了相应措施,由村干部兼职的灾害信息监测员随时监测。传统的灾害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滑坡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当时地震引起了滑坡,村寨的很多边缘地方都塌掉了,之前地震产生的裂缝,如果有树叶掉落到裂缝里,就能防止雨水过多的渗入到缝隙里,造成滑坡或者塌方,人少,滑坡就会减少,因为落叶也不常打扫,另外种沙松能把土固定起来,不会让土跑,就不会滑坡”。4虽然现代灾害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滑坡危害,但仍存在滑坡风险。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当地人口增加、户数增多、村村通公路、保水性植被面积减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必然导致滑坡灾害的加重和频发。此时,灾后搬迁无疑是杜绝灾害威胁的重要方式,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民众在灾后搬迁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搬迁的场地选择受到官方制约,这种制约对于调和民族矛盾与社会利益冲突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民众缺位一直是灾后重建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灾害管理方式带来的弊端。在当前防灾减灾体系工程建设中,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防灾减灾规划的重要部分,这一规划包括房屋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但在原址原地重建和异地搬迁则存在很多区别,原址重建更易解决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社会网络、经济发展等问题。异地搬迁则存在一定难度,搬迁地的选址、搬迁后民众生计等问题在当前众多搬迁的村寨中仍旧存在,处于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民众更是面临着搬迁之后的一系列问题。灾后重建给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一系列影响,尤其是根植于当地生存环境基础上的民族文化面临严峻挑战。
二、政府主导与民众缺位:佤族社区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利益博弈
灾后重建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的最后一环,意味着让物理环境、社会经济和人都达到灾害发生前的状态,或提升到更好的状态。它是考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体现社会安全的一道基本防线[6]。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整个灾害管理过程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其注重的更多是物质层面的重建,忽视了精神层面的重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出现断裂,在边疆民族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既是资源富集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自然灾害对于这一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影响远高于内地。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前,边疆民族地区面对自然灾害主要是依赖于以民间为主导的各民族传统防灾减灾方式。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抵御自然灾害才逐渐由以民间自救为主转向以政府为主导的救助方式。这一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但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如民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缺位,表现在参与性降低、自主性削弱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主导下的灾后搬迁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缺乏与受灾民众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且较少考虑到搬迁民众未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是否能持续运行。由于中国灾害管理方式自古以来都是自上而下,导致灾后重建过程中民众认可度较低,从而出现民众不愿搬迁、搬迁后抱怨情绪等现象。
受“3·01”地震影响,损失比较严重的是竹蓬组和岩门二组。然而,竹蓬组和岩门二组搬迁的原因有所差异,竹蓬组是主动向政府提出搬迁,岩门二组则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搬迁。竹蓬老寨是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地震加剧了竹蓬老寨滑坡灾害风险。竹蓬老寨在地震发生之前便提出过搬迁要求,但并未落实,地震发生之后,滑坡隐患加剧,竹蓬寨的村干部共同向莱片村村委会提出搬迁的请求。经地方政府请地质专家进行勘测之后,竹篷组与岩门二组都存在地质灾害隐患,为进一步响应“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政府采取“统规统建”方式,开始选址规划。
在搬迁选址过程中,地方政府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专家评估、场地选择、土地价格协商、房屋规划最终建成龙佬组安置点。关于搬迁选址,笔者从沧源县自然资源局了解到,搬迁新地点的选址主要是在原来寨子的附近,莱片村搬迁点也是距离原来的寨子2公里左右,其新寨址的选择一般不会距离原寨址太远,而且也会请专家进行评估,之后才会重建。重建村寨的土地也是由政府专门进行协调,搬迁之后的民房建设一般会保留本民族特色,主要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抗震减震能力肯定高于传统民居。1可见,搬迁安置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综合评估之后进行选择,最终确定将安置点选在澜沧至孟定的交通主干道旁,此处距离芒卡镇镇政府2公里左右,交通便利。地方政府選址之后,再与当地村民进行协商购买土地,由政府统一规划房屋设计,达到抗震6级设防要求。
龙佬组安置点于2015年开始建设,2016年陆续进行搬迁。竹蓬组有20多户于2016年就已经搬到了龙佬安置点,其中5户村民并未按照政府要求搬到安置点,而是搬到芒岗岔路口。竹蓬组搬迁是民众主动向政府反映的,主要是基于“3·01”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也有一些村民表示“3·01”地震之后,村里的水就没有之前多了。岩门二组46户中,有2户在老寨没有搬下来,有2户在堆堆组。由于专家评估岩门二组老寨属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岩门二组搬迁是政府的惠民工程,地方政府是占据主导地位。岩门二组组长介绍:“从老寨搬下来不是因为地震,老寨位于陡坡上,且因人口增加,较为拥挤,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所以政府让搬下来,但是老寨已经有五代人生活在那里都没有发生过灾害。”1岩门二组的另一位搬迁到龙佬组的村民提道:“寨子并不是因为地震才搬迁的,而是因为政府的扶贫工作需要,所以才让岩门二组的人搬下去的;而竹蓬组是因为地震损害严重,所以主动要求搬去龙佬组;岩门二组的大多数人不愿意搬,因为岩门二组的风水、地势很好,年年粮食的产量最高,那里的土地很硬,没有发生过滑坡和泥石流。”2
龙佬组位于澜沧至孟定的交通主干道旁边,相较于之前需要走10多公里路程才到公路旁边而言,交通极为便利。安置点建好之后便是搬迁。据了解,由于佤族迁居需要算日子,佤族不管是出门、婚丧嫁娶、种田、看病等都要看日子,有些是因为日子不合适,也有是因为父母亲过世,还有就是等家中孩子放假回来才能举办“进新房”仪式,再进行搬迁,所以搬迁至龙佬组的村民搬迁的具体时间并不一致。也有一部分村民不愿意搬迁到安置点,特别是一些老人不愿意搬迁,主要是由于搬迁之后给当地民众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竹蓬组、岩门二组的猪圈、鸡、牛、农田及两个组的坟山、庙房都在老寨,往返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给当地民众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不同的人对于搬迁观念不同,也有一些老人认为搬迁还是好的,因为“老寨人少了,树叶和杂草会把地震导致的地下裂痕堵住,水就进不到缝隙里,防止土泡,山体就不会‘跑’”。3
(二)民众缺位导致灾后搬迁过程中的博弈与协调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民众对于安置点的选址有参与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关于安置点房屋的规划设计过程中,竹蓬组和岩门二组并未参与其中,也造成了当前竹蓬组与岩门二组搬迁之后房屋出现的种种问题。
岩门二组之所以全寨搬迁,主要是由于老寨被评估为地质灾害隐患点,经实地调查,老寨位于陡坡上,确实存在滑坡隐患。但2015年的“3·01”地震对其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其搬迁主要是由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因此,岩门二组的很多村民并不愿意搬迁,在搬迁点选址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搬迁的积极性并不高,参与程度较低。
相较之下,竹蓬组村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更高。2015年的“3·01”地震之后,由于竹蓬组存在山体滑坡现象,且较之震前水源减少,村民要求搬迁。竹蓬组作为受灾主体,在灾后搬迁点的场地选择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竹蓬组搬迁是自主提出,并积极选择搬迁场地,但场地选择经政府评估后并不适合于居住,地方政府请相关专家进行搬迁点选址,竹蓬组在灾后搬迁新选址中主动参与其中,有利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协商机制的建立。2015年“3·01”地震发生之后,对于竹蓬组造成严重影响,竹蓬组房屋、道路、水源因地震遭受严重破坏,后经村民代表大会协商,向村委会提出搬迁请求,同时到周边地带选择寨址,村民代表先提出搬到采石场附近距离老寨3公里的王达山,旁边有一座采石场,那个寨址下面是落水洞,政府勘测地层较空,最后政府没有同意,接着村民带政府人员去看采石场对面山坡,那里的地基相对较平,但下公路的坡陡,这个寨址也放弃了,最终选择在龙佬组这个寨址。其中竹蓬组有5户震后搬到南距老寨2公里的芒岗岔路口的山坡上住防震篷,当政府确定将竹蓬组整体搬至龙佬组安置点,村委会均要求这5户与全寨一起搬迁,但他们表示不愿搬迁,要求在岔路口就地建房。在这5户人家看来,岔路口交通方便,吃水不成问题,离耕种的水田和旱地都很近,于是政府便答应了他们就地建房的请求,补助每户4万元钱由其自行建盖房屋。1
从地方政府与民众在灾后重建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应当加强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与协商,避免因搬迁导致的民众抱怨情绪。这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带动作用,让村民积极参与到搬迁选址、民房规划之中,给予民众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利,地方政府在广泛了解民意的情况下开展重建工作,才能更好地让群众参与其中,发挥受众主体作用,形成一套“互嵌式”的灾害文化逻辑体系。
三、“变”与“不变”:佤族社区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文化重构
灾后重建作为一种地方性实践,佤族社区在面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干预时,大量的外界事物渗透到传统文化之中,包括救灾人员、救灾物资、社会意识等加剧了佤族传统文化的解体,形成了灾后佤族文化重构、适应、更新的过程,实现了佤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耦合体。李永祥指出灾害虽然对社会结构造成破坏,但其结构会再次平衡,这种平衡关系的恢复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明显,即原住民社会和文化在反复无常的环境条件下可以获得长期稳定性[7]。佤族村寨人际关系网络、社会经济网络、生产生活网络等都是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得以正常运行的,这套依托于传统文化而形成的逻辑体系是嵌入到佤族生产生活、社会经济、风俗习惯之中的。佤族村寨大到集体的事要通过祭拜神林,小到个人的事也要看鸡卦,这既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不成文的约束条例,保证村寨整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灾后搬迁过程中,这一套文化逻辑体系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关注,导致维系村寨社会文化秩序的传统很难延续,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重构新的文化逻辑体系。
(一)传统社会文化的断裂与消失
首先是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目前,搬至龙佬组的竹蓬组和岩门二组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影响,当地民众主要的生计来源包括种植农田、饲养牲畜,搬迁之后给日常生产带来诸多不便,传统生计方式较难维持。2016年龙佬组新寨建盖好之后,组长、副组长带头搬迁,至2017年12月底,全寨26户搬迁完毕,5户搬至芒岗岔路口,1户搬至道班,至今竹蓬老寨变成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寨。但是,竹蓬组的田地都在老寨附近,距离龙佬组有12公里,部分农田荒废,还有一半的人把田地租出去了,也有少部分人往返于安置点与老寨之间种田。这让他们在路上花费不少时间,加重了他们生产生活的负担。由于龙佬组不允许建盖猪圈,所以一些竹蓬组民众还要回老寨养猪。据调查统计,竹蓬组至今还有10户在老寨养猪,而不会骑摩托车的老人多是喂猪的主力,每天在龙佬组和竹蓬老寨来回一次,光车费至少10元,辛辛苦苦养猪一年是赚不到什么钱的,甚至亏损。时间上稍微空闲一点的老人,早上回去喂猪之后就待到下午把猪喂了再回来,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车费。时间不宽裕的,早上很早出门,喂了猪之后还要赶去地里干农活,晚上再回去喂猪。竹蓬组搬到龙佬以后,活路变少了,没有什么可以干的,大多数人只能打工,冬天还可以帮忙摘摘豆子,工钱为60元/天,没有农忙时只能待在家里休息。年轻人几乎全部出去打工了,没有搬下来之前出去的比较少。1此外,搬迁后,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新寨的自来水需要出钱,每家每户的房屋相较于老寨较为紧凑,没有菜园,未规划建盖猪圈,用当地人的话说:“整什么都整不成。”而且政府统一建的房子并没有规划厨房,有些抽签抽到空间较大的地方可以在房屋旁边搭建厨房,但是大多数人家没有厨房,现在煮饭炒菜都是露天,做飯烧的柴火堆放的地方也很小,到了雨季,生火做饭都是困难。
村民在老寨时,由于交通不便,农业靠种植为生,长期安于现状,但是搬下来了之后,靠近公路,交通方便,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原来的农田种植成本增加,更多人选择做生意,如倒卖蔬菜等。也有很多人开始在道班的沃柑基地和蔬菜冷库务工,帮忙盖房子等,这种方式相较之前的生计方式收益更快,但也增加了妇女的负担。村中中青年男性大多在外务工维持家庭收入,女性承担着种田、教子的重任。据竹蓬组的一位妇女所说:“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得照顾两个孩子,不会开车,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耪田种地,猪也养不了,房子前面的菜是到老寨要别人的猪粪来下来种的,想养猪也养不了,因为政府不准在房子旁边盖猪圈。”2
其次是风俗习惯的改变。搬迁之后,虽然在房屋外观装饰上还保留着些许传统民居特色,但是已丧失了具有佤族文化功能的民居建筑,如火塘的文化功能逐渐消失。在佤族传统文化中,围绕火塘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文化事象,包括各种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以及围绕火塘而展开了一系列宗教仪式活动、风俗习惯等。新民居的文化排异性,导致传统文化的延续出现断裂。佤族传统民居建筑为“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或堆放农具杂物、柴火,室内有主、客、鬼三个火塘,佤族“火塘文化”历史悠久,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火塘是家庭生活的必需之物,更是火神、祖神来往的栖息之地,是家庭、家族聚会的中心,佤族民间谚语常说“炉中不断千年火”。在佤族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中,“火塘”也具有祈福禳灾的功能,佤族每年都会进行“取新火节”,主要是送旧火、造新火。佤族认为:散落在地上的火、烧到根的火,都是旧火、破烂的火,是灾难和不幸的根源,如果不清楚这些旧的、破烂的火,就会受到火神的惩罚,烧毁房屋,烧毁庄稼和山林,使受灾遇难,反映了佤族极为重视防范火灾的习俗。
灾后的民房重建或是“易地扶贫搬迁”所建盖的房屋都是“统规统建”,仅是外形装饰上保留一些给外人看来有民族风格的特色,但实质上这种民房已然不具备佤族传统文化功能,“火塘”的消失意味着许多信仰、习俗、禁忌、祭祀仪式逐渐消失。火塘在佤族民众中发挥的文化功能在逐渐降低,如新火节、火塘禁忌会随着火塘的消失而逐渐被后代所遗忘,火塘文化的断裂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一现象,佤族民众更多的是叹息和在现代化生活接轨中寻找火塘文化,如龙佬组很多村民仍旧在房屋前搭起火塘生火煮饭,吃完饭后围着火塘聊天、烤火;也有一些村民居住空间较大,在新房旁边搭起用木板做的房子,里面搭起火塘。
(二)地方传统文化秩序的重构
灾后搬迁过程中诸多新事物渗入到民众的生产生活之中,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仍会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并在与新事物碰撞的同时进行文化适应和更新。搬迁后,要重新选择祭祀神庙的地方,龙佬组安置点包括竹蓬组和岩门二组,两个组分别有村寨自己的头人、山神、坟山、庙房。在佤族传统文化中,从老寨搬出到新寨,老寨的坟山、庙房就不能再进行祭祀,要选择新的庙房,两个小组合并为一个村寨之后面临着重新选择坟山、庙房,这意味着村寨与村寨之间相互的文化融合与认同。
笔者于2019年1月调研了解到,关于竹蓬组与岩门二组是否共同选择坟地、庙房还在争议阶段,到底是选择共同的坟山、庙房,还是各个寨子分开选择,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据了解,两个组选择共同坟山、庙房可能性较大。佤族的习俗是一旦搬迁出来,就不能到老寨神林进行祭祀,也不能继续在老坟山埋葬亲人,这样村民就难以进行叫魂和其他公共祭祀活动。据了解,竹蓬组搬迁下来之后有一位老人于2018年过世,但龙佬组还未确定公共坟地,经与岩门一组协商,谈妥了1块2亩多一点的地,价格为1.5万元1亩,火葬1了老人,经村寨民主决议确定之后想作为龙佬两个组(岩门二组和竹蓬组)共同的新坟地,但后来因购置土地的价格提高到4.5万元1亩,龙佬组公共坟地选址一事搁浅。2
地方文化逻辑的重构需要一个漫长的交融过程。在佤族村寨搬迁过程中,各村寨之间的文化认同程度较高,相互之间的认同关系便会很快建立,这需要寨中老人3以共同协商的方式进行协调。从竹蓬组搬迁至芒岗岔路口的5户来自一个村寨,在文化重构过程中,更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其协商空间更易包容和理解。据了解,“这五户人家在新寨的东边选择好神林并且盖好庙房,于2019年大年三十那天在新庙房公祭寨神,且5户人家,大家推选最年长的四人作为寨中老人,大家有什么事就一起商量,定下来后大家一起做,今年(2019年)大年三十到庙房公祭寨神,四个老人就开始学着做”。1新寨坟山、庙房的选择和建立反映了搬迁点新的文化逻辑的形成,更好地保证了佤族社区文化秩序的正常运行。
四、结语
佤族社区灾后重建过程中所呈现的地方政府与村寨民众、村寨民众与村寨民众、村寨民众内部之间存在各种博弈。在这一博弈过程中,虽然佤族社区面临着传统文化断裂及消失的风险,但当地民众并未随波逐流,而是通过主动参与、自主选择的方式在地方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灾后重建的选址上,更突出表现在灾后重建社会文化网络的自我调节及恢复上,佤族社区民众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锋中掌握了推动社会文化变迁的主导权,依托传统文化的力量试图重塑新的地方文化逻辑,以此来实现原有村寨社会文化秩序的正常运转。在今后现代化的科技防灾减灾过程中应当更多的吸收融入民族優秀传统灾害文化,通过设计“民族优秀灾害文化”旅游体验,建立“民族优秀灾害文化博物馆”,加大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灾害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性转化研究力度,整合多方资源,形成“互嵌式”地域灾害文化逻辑,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防灾减灾建设进程,构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灾害文化与现当代防灾减灾相结合的共同体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本土化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李永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以云南省盈江县的傣族社区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10):67 - 70.
[2] 王晓葵.“灾后重建”过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以灾害记忆为中心[J].河北学刊,2016(5):161 - 166.
[3] 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J].史学集刊,2021(2):4 - 10.
[4] 赵富荣.中国佤族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5] 沧源发生5.5级地震 李纪恒陈豪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EB/OL].(2015 - 03 - 02)[2016 - 03 - 02].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02/c117005 - 26621585.html.
[6] 王赣闽,肖文涛.自然灾害灾后重建的地方政府行为探析——以福建省闽清县“7·9”特大洪灾灾后恢复重建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7(12):22 - 33.
[7] 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泥石流为个案[M].民族研究,2008(5):35 - 109.
[责任编辑: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