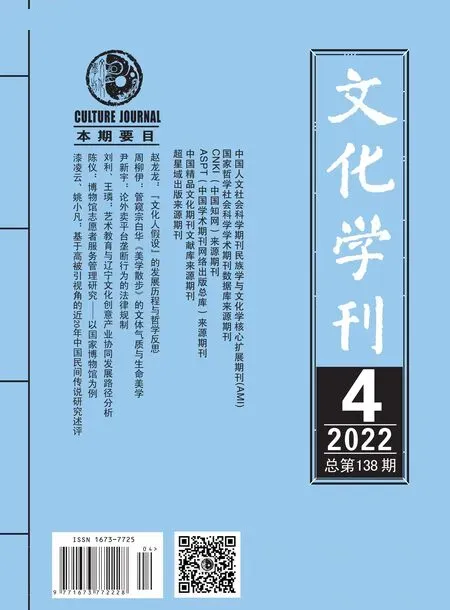纳兰性德“咏史词”中的文化认同分析
闻 锐
在《饮水词》中,“咏史词”作为一类特殊且重要的题材,最能体现纳兰性德身处两族文化挤压下所形成的“背满向汉”的独特民族文化心理。现将《饮水词》中“咏史词”以大概时间顺序录于下表(表中词作皆以赵廷秀、冯统一《饮水词笺校》为依据):

表1 咏史词汇总
由上表可见,纳兰性德的“咏史词”创作主要在入职侍卫后的随驾扈行与奉旨出塞期间。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国内局势渐趋平稳。为了宣扬文治武功来巩固统治,康熙多次出巡与命人出使边塞。对纳兰性德而言,无论是随驾出巡还是奉旨觇梭龙(本文持以张任政、黄天骥等学者“梭龙”即索伦部的看法。)都代表着天子威仪,当展示出高昂劲健的姿态。但这一时期的“咏史词”创作既没有对清朝历史的褒美也没有对昌盛王朝的盛赞,甚至没有胜利者的昂扬心态,取而代之的是对盛衰兴亡的消极感叹,词风不似盛世而更像末代伤吟。
一、“背满向汉”文化心理产生的缘由
为了维护对汉族的统治,清初在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建设三方面均实行了汉化政策。经济上推崇汉族的农耕经济,政治结构上仍袭明朝旧制,特别是科举制度一以贯之。八股取士所阐之理仍是儒家经典,这不仅维护了汉族文士的仕途,也极大地促成了满族子弟对儒家典籍的阅读学习。文化上的汉化主要体现在推崇儒学和吸纳汉儒名士两方面。汉化政策不仅缓解了汉族和满族的文化对立和民族矛盾,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汉族文人和满族文人的接触,汉文化的输入变得更方便彻底。纳兰性德深受时代风气的影响积极投身到汉文化的学习中接受汉化。
带着“留心当世之务,不屑屑以文字名世”[2]人生理想的纳兰性德一心想进入名儒才俊荟萃的翰林院继续经史研究,更期在未来入职宰辅安国定邦,完成人生的不朽盛世。事与愿违,康熙十五年(1676)入选翰林院的失利给纳兰性德带来巨大的打击。名列二甲第七成绩的纳兰性德可谓才学上等,他的落败更像是康熙帝出于文化私心与政治考量而有意为之。在政治上康熙为掣肘纳兰明珠将纳兰性德视作“君臣权势场上博弈乃至维护平衡的一个棋子”[3],这是纳兰性德不能对抗的绝对阻力。而在文化上则无疑是康熙“首崇满洲”观念的体现。清朝统治者一直将“满洲本位”作为“清朝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4],对满人汉化的程度设置了原则和底线。康熙“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和“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5]的言论,都是文化上“首崇满洲”的心理。喜与汉族文士交游唱和的纳兰性德自然引起了康熙的关注,知晓他专注入选翰林的心思,也对他痴迷汉文化的心理起了戒心。搁置一年之久,康熙才亲选他为三等侍卫这一武职。据雷炳炎先生统计:“清代八旗贵族世家大族子弟由侍卫入仕,日后飞黄腾达,跻身为一品、二品大员的为数众多”[6]。可见康熙欲以一条由侍卫升迁高位,享有满人把持特权的道路向纳兰性德重申满族“国语骑射”的文化本位。不幸的是,纳兰性德没有如康熙所望回归文化上“首崇满洲”的观念,而是在不自由的侍卫生活中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儒家理想的破灭:“更那堪、冰霜摧折,壮怀都废。”“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平生诗友,尽在兹邦,左挹洪厓,右拍浮丘。此仆来生之夙愿,昔梦之常依者也。”(《与顾梁汾书》)[2]265能够参与到皇威浩荡的南巡中,纳兰性德不以为傲,反将随行作为远离知己亲朋的苦差,甚至直言自己“梦中常依”的“平生夙愿”正是摆脱身份制约,陪伴汉族友人的诗酒生活。这些作品流露出的悲观心态既是纳兰性德理想破灭后的真实想法,也表明对康熙阻挠行为的难以接受。在对汉文化的认同上,二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康熙必须保证满族本位,对汉文化实行学习与防备兼有的复杂态度。纳兰性德则不必考量政治因素,真诚地学习汉文化而没有“首崇满洲”的戒心。“背满向汉”的文化心理正是纳兰性德对汉文化认同的结果后“身陷异质文化撕扯的两难境地”[7]的表现。由于对汉文化的熟稔推崇,无法认同统治阶级尊满鄙汉的文化政策,所以纳兰性德的“咏史词”中没有作为胜利者的优越意识,又因为康熙的强制干涉造成其理想破灭的人生体验,所以纳兰性德在“咏史词”中又表现出浓浓的悲剧色彩,以兴亡满眼的消极话语寄托自己人生失意的哀情愁绪。
二、“背满向汉”的文化心理在“咏史词”中的表现
(一)创作模式对汉文人的继承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韩愈“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创作理论明确了汉文人诗歌创作富含悲剧意味的创作心态。晚唐词作沿续了这种创作心态,确定了词柔婉纤细的语言风格和感伤幽微的悲伤情调。无论是创作实践上“哀感顽艳”的创作风格,还是创作理论上“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2]46的批评文字,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了纳兰性德对悲剧意味创作心态的接受。
借助陈水云先生的著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8],我们不难发现感慨深邃的后主词对纳兰性德的“咏史词”影响巨大。相似的人生苦难使纳兰性德更易与李煜产生情感的共鸣,更容易接受李煜词中熔铸兴亡之悲、家国之叹的创作模式,只不过相比于后主词,纳兰性德的“咏史词”褪去了后主词中浓郁的情感色彩,以一种更深沉的哲理感叹兴衰。另外,当时词坛的创作风气也影响了纳兰性德的创作。生活状态逐渐稳定的汉族文士在词作中的情感宣泄亦渐趋平复,悲慨激宕的亡国之痛渐被悲哀无奈的兴亡感叹所取代,陈维崧和朱彝尊便是最好的代表。二人在词风上虽有雄豪、清婉之别,但在情感上因国破家亡而抒发的兴亡之叹皆感人至深,富有深韵。如陈维崧《凤凰台上忆吹箫·秣陵怀古》“悠悠,南朝风景,看几遍桃红,白了人头。算刘郎易老,嬴女难留。三十六宫何在?斜阳外、隐隐离愁。”与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同是战争风云消散后再游南京之作,虽风格不同但其中借南朝以喻故国的悲戚情感,历史兴亡的思考都郁结着作者的无限哀思,是明末清初汉族文人民族文化心理的典型写照。陈、朱二人作为当时的词坛领袖且又与纳兰性德交游相友,他们在“咏史词”中咏叹兴亡的文化心理自然影响到《饮水词》中的咏史怀古类作品。至于顾贞观和严绳孙等与纳兰性德十分交好的江南失意文士,他们在咏史怀古中吟咏兴亡、自伤怀抱的创作心态对纳兰性德的影响更加直接,如《望海潮·宝珠洞》中“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直接仿效严绳孙《望海潮·钱唐怀古》“吴颠越蹶,玄黄战罢,无多钱赵兴亡。”中的亡国愁绪;“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也近于“一道愁烟,三分流水,恼人惟有斜阳。”中的个体愁情。
(二)创作意识的去满人化
既然熟知了词体写作“以悲为美”的创作模式,又无法认同清朝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文化观念,纳兰性德在随驾扈行与奉旨出使的背景下也就没有了作为满族八旗的那份骄傲与自豪的创作心理。再加上他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咏史词”创作便不以主人翁的意识去观照历史,也没有尚武的骁勇气息,而是在创作中用一种悲观的视角去咏史怀古,以汉文化中兴亡有数的历史观寄托自己人生失意的哀感情绪。如《浣溪沙·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定三藩”之乱后在扈驾东巡途中曾宿至小兀喇。平叛得胜,清朝贵族们的心态应当是开怀欣喜的,如康熙所作的《松花江放船歌》:“浪花叠锦绣縠明,彩帆画鹢随风轻。”“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观兵。”在悠游明媚的风景中,康熙帝心中的畅快不言而喻。“貔貅精甲”和“旌旄朱缨”精简地传递出清朝威武的军势,康熙以一种主宰者的角度审视山河。反观同时期纳兰性德的词作,在言及小兀喇地区的民族旧俗后亦将目光聚于松花江上。大鱼翻滚,浪花排空,空将腥味弥散。看着天空自由遨游的海东青,处处不自由的纳兰性德多么渴望如猎鹰一般任逍遥。下阙转入怀古,作为叶赫那拉氏的一员,纳兰性德来到先世海西女真的故地必是思绪万千。遗迹依稀但海西已亡,远处寂寂的钟声传来,思绪万千的纳兰性德想到曾经的海西和明朝都已经亡了,现在的清王朝虽兴但又何尝不会与前朝一样。“莫将兴废话分明”饱蕴了作者多么深沉的兴亡慨叹!分明处在王朝盛时,却没有康熙诗中昂扬激奋的豪情,也没有他那种山河主人翁意识的观照。纳兰性德始终将自己游离在胜利者的队伍之外,用自己的悲戚心态去感叹兴亡的命数。同是在随扈东巡期间所作的《南乡子·古戍》中,纳兰性德更直接以议论的方式感叹兴亡:
古戍饥乌集,荒城野雉飞。何年劫火剩残灰,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
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
戍营和城墙被战火焚烧后荒芜不堪,只有食腐肉的乌鸦和野禽在这里聚集。战场遗迹下又不知埋了多少兵士的鲜血。前朝军营的旧址仍在,但曾经于帐中吹笳的人已消逝。虽是春天,但在如此萧索破败的遗迹面前作者亦不免感从心来,发出兴亡定数的感叹。
“觇梭龙”期间,纳兰性德面对边塞风光和历史古迹也创作了诸多吟咏历史人生和兴亡感慨之作,没有建功立业的豪情与蔑视敌人的气概,无不以儒家兴亡观为视点,具有悲剧意味。如《满庭芳·堠雪翻鸦》:
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宵起舞,无人处、那有村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
作者在边塞寒冷寂静的深夜难以入眠,唯听阴风铜笛,唯见冰雪鬼火。词的上阙以对边塞景物感官描写为主,又透露出“堪悲”和“泪沾衣”的伤感情绪。下阙以议论直言堪悲的原因。世事的运行如下棋的胜负,兴亡总是在由胜到负再由负至胜中转换。可叹人类的纷争在天数的盛衰轮转中就如同蜗牛角上的蛮、触两个那样渺小。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朝代又落下,换来的只有在青史上留下短短几行,而那些王朝的过往也只会在“断碣残碑”上找到痕迹。没有谁可以永恒,年华如同江水只去不回。通过对过往的历史与现存王朝的审视中,纳兰性德在这首词中既有儒家的兴亡观也体现出消极的空幻思想。古今之变的兴亡律既是纳兰性德熟读经史后的文人哲思,也是深受儒家影响后自觉产生的忧患意识,而佛老思想的空幻观则是想要摆脱痛苦的解脱工具,更何况爱妻亡故、亲友离散对这位多情公子更是雪上加霜。
可以说在这类扈行与出塞背景下的“咏史词”中,纳兰性德完全抛开了本族胜利者的身份和统治阶级“首崇满洲”的文化政策,以汉文人的哲思与心态去感叹历史兴亡的规律与人生在世的渺小虚幻,又处处流露出自身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和哀感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