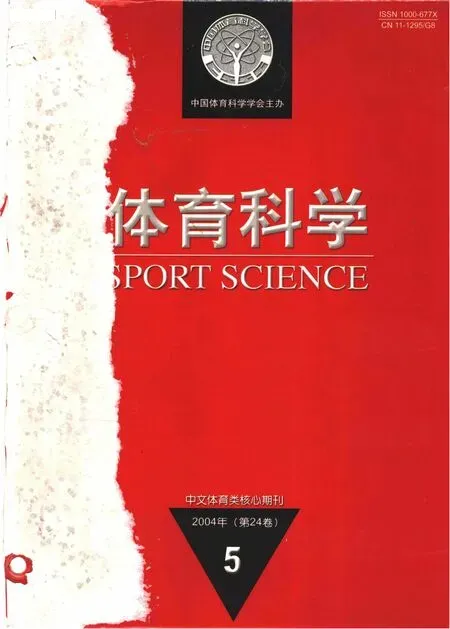论兴奋剂违规处罚抗辩中的非故意证明新路径
周青山,梁 婧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最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WADC)已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实施。对比2015版WADC,现行条例给第10.2.1.1条之体内发现禁用物质的禁赛期规定增加了新的释义,指出“虽然在理论上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可以在不说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自己体内的情况下证明其兴奋剂违规不是故意的,但在条款2.1的兴奋剂违规案件中,运动员在没有证实禁用物质来源的情况下,这是基本不可能的”。这表明WADC制定者承认了运动员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not intentional)的理论可能。该释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反兴奋剂实践中,尤其涉及非特定物质的兴奋剂违规中,禁用物质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导致的运动员非故意证明困难现象,已成为兴奋剂案件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由于主观非故意的成立会直接决定运动员禁赛期的减免,与运动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该问题不仅影响了WADC相关条款的修订,还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引起了广泛争论。尽管WADC制定者对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方法运用于兴奋剂违规案件的可行性仍持保留态度,但该证明方法在CAS已有成功实践的先例。本文将在梳理WADC规定和CAS相关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当前运动员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时应注意的要点,并对中国反兴奋剂实践提出相应的建议。
1 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的产生背景
出于严厉打击兴奋剂使用行为的目的,2015版WADC改变过去首次违规基准罚一律为2年的做法,将故意作为确定基准罚的首要标准;并且,为了让反兴奋剂组织能更高效地惩戒兴奋剂违规,WADC借助推定规则来认定运动员对违规是否存在故意,并根据兴奋剂禁用清单中特定物质和非特定物质的分类来区分证明责任轻重(宋彬龄,2015)。禁用清单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发布,用于确定兴奋剂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其中,禁用物质又可分为特定物质和非特定物质,相比非特定物质,特定物质主要因治疗行为进入运动员身体,为提高竞技成绩而故意使用的可能性较小(宋彬龄,2014)。非特定物质对竞技比赛公平和纯洁的损害更大,因此,体内存在非特定物质的运动员将面对更为严厉的处罚,洗脱其兴奋剂违规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也更重。
2015版WADC第10.2.1条规定,运动员被发现体内含有禁用清单中规定的非特定物质,即推定为故意违规,首次故意违规者将被禁赛4年。根据第10.2.3条,条例中的“故意”是指运动员明知其行为构成或有构成违纪之风险,仍然实施该行为。其之所以使用“故意”一词,目的是将“作弊”违规的运动员和其他违规运动员相区分,让前者受到严厉处罚而让后者免遭不公平的对待(于洋,2019)。因此,运动员能够推翻故意推定的,违规处罚可以从原本的禁赛4年减少至2年,甚至还可以根据过错程度获得进一步减免。运动员要想免受4年禁赛处罚,就必须竭尽全力证明自己并非故意摄入禁用物质,根据2015版WADC,证明非故意的途径主要有:1)根据10.2.3条,证明该禁用物质是赛内禁用物质但在赛外使用,且与成绩提升无关;2)根据10.5.1.2条,在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前提下,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或无重大过错;3)无法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时,根据10.2.3条对故意的定义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证明主观非故意(杨春然,2017b)。若运动员成功推翻故意推定,禁赛处罚不超过2年,最轻仅给予警告且免于禁赛。
WADC第2.1.1条规定,运动员有责任确保无禁用物质进入自己体内。这要求运动员对所摄入的食品和补充剂等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通常,运动员都会保持谨慎,仔细记录自己摄入的食物、补充剂和药物,并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近期使用过的产品。因此,在大多数非特定物质导致兴奋剂违规的案件中,运动员能够通过途径2,即说明体内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证明自己主观无重大过错而获得禁赛减免,这也是2015版WADC第10.5.1.2条所明文规定的主要证明路径。但在实践中该路径存在明显缺点,即当运动员无法说明体内禁用物质来源时,他就不能证明自己无重大过错,因为前者被认为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运动员无法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由于实践经验的积累,CAS对禁用物质来源的说明要求不断提高,运动员必须提出切实的证据,以证明禁用物质来源于他使用的某个具体的产品(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06),并且要能够说明该物质进入自己体内的方式、剂量和时间(Taylor,2020)。尽管运动员为避免摄入禁用物质保持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其举证可能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如果仲裁庭认为禁用物质来源不确定,运动员就不能用前述途径2证明非故意。其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运动员体内残留的禁用物质能够被更精确地检测出来。对于无意中接触了被污染产品的运动员而言,尽管其体内禁用物质的水平远低于那些故意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但在现行规则下,这些不知情的运动员仍然构成兴奋剂违规(WADA,2019)。此时,运动员难以通过说明物质来源证明主观非故意——因为他(她)无法确定禁用物质究竟从何而来。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在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发生(Yonamine et al.,2004)。
面对CAS对物质来源说明愈加严格的要求,许多运动员因无法说明禁用物质来源而难以履行证明责任,不得不承受禁赛4年的处罚。但无法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窘境并不是2015版WADC生效后才出现的。为了让无辜的运动员有机会挽救他们的职业生涯,有学者对2015版WADC的处罚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他们注意到,根据运动员过错程度的高低,2015版WADC所规定的非故意与无(重大)过错之间属于包含关系,前者涵盖的范围要大于后者;且如果运动员不主张自己无(重大)过错,只证明违规非故意,条例并没有明确要求他说明物质来源,仲裁庭可以根据第10.2.3条之内涵判断违规是否为非故意(Rigozzi et al.,2015)。借助WADC规定本身的模糊性,该观点为运动员指出了推翻故意推定、争取禁赛减免的新思路,即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
2 CAS的仲裁实践
从2009版到2021版WADC,运动员通过故意的定义证明自己主观非故意的新路径逐渐发展并得到认可,这一过程与CAS的仲裁实践密不可分。在CAS仲裁实践中,新路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2.1 第1阶段: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是获得禁赛减免的唯一途径
由于2009版WADC中没有明确给出故意之定义,因此,严格意义上它并不在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就非故意证明路径的形成与发展而言,2009版WADC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它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理解仲裁庭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源头,也能够为非故意证明新路径的完善找到方向。
如前所述,2009版WADC没有根据运动员过错程度高低来区分基准罚,首次违规禁赛期一律为2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09版WADC无视了故意与过失违规的本质区别,其对故意的惩处采用的是加重处罚、延长禁赛期的方式:根据条例第10.6条及其注释之规定,若反兴奋剂组织可以证明运动员对违规存在故意,那么禁赛期应长于常规处罚,最多可以延长至4年。不过,由于反兴奋剂举证证明运动员故意难度较大,实践中适用加重罚的案件寥寥无几,对2009版WADC的关注,应集中在禁赛减免的规则上。
2009版WADC第10.5条规定了运动员争取禁赛减免的途径,该规定对运动员在因药检阳性成立兴奋剂违规的案件中证明自身主观非故意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后来的“无重大过错条款”(No Significant Fault or Negli‐gence,简称“NSF条款”)之雏形,10.5.1和10.5.2条分别规定了运动员无过错和无重大过错的证明方式。根据这2条规定,在因体内发现禁用物质而构成兴奋剂违规的案件中,如果运动员能证明自己无(重大)过错,则可获得禁赛期的减免。但是,运动员必须提交相应的证据说明该禁用物质如何进入自己体内,否则就不能减免禁赛期。当时,证明无(重大)过错是运动员根据过错程度获得禁赛减免的唯一途径,但只能在仲裁庭认可的“特殊情况”下适用。
虽然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是证明无(重大)过错的必要条件,但实践中无法查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的情况绝非个案。对此,CAS仲裁员没有“墨守成规”,而是灵活适用了第10.5条的规定,代表性案例就是加斯奎特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09)。理查德·加斯奎特(Rich‐ard Gasquet)是一名法国网球运动员,2009年3月,他在参加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ATP巡回赛(ATP Tournament)期间去俱乐部观看表演,第二天接受药检后被告知检测出体内含有可卡因,为赛内禁用的非特定物质。本案经国际网球联合会(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ITF)的独立反兴奋剂裁判庭(Independent Anti‐Doping Tribunal)审理后,被ITF和WADA上诉至CAS。上诉审中,因禁用物质进入运动员体内的路径无法确定,ITF提出了包括故意吸食、运动员饮用的俱乐部提供的饮料中掺有可卡因等可能的进入路径;加斯奎特则认为自己体内的可卡因可能来源于当晚他曾亲吻过的女伴,且这名女伴已被证实是一名“瘾君子”(宋彬龄,2012)。仲裁庭认为,为了确定运动员在摄入禁用物质时过错程度的大小,首先需要说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运动员举证时应当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如果关于来源的几种说法中,运动员提出的说法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可因此认定运动员达到了优势证明标准。也就是说,当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无法确定时,只要能证明某一种进入路径比对方提出的现实可能性稍大,仲裁庭就会采纳。本案中,仲裁庭认为加斯奎特提出的接吻说法能够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比起其他进入方式更有可能发生,因此,视其履行了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举证责任。
根据该案,虽然CAS在禁用物质来源无法确定时允许运动员以变通的方式完成举证,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说明禁用物质来源”这一要求的范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仲裁庭处理兴奋剂案件的经验有限,尚未总结出说明确切来源的方法和要求,因此,只要运动员能说明最有可能的来源,即视其达到证明标准。不过,说明了禁用物质来源并不代表运动员证明无(重大)过错的举证已经完成,在国际自行车联盟与WADA诉康塔多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2)中,运动员虽然成功证明了自己的说法比上诉方提出的说法更有可能发生,但他没能证明自己无(重大)过错,仲裁庭因此对其处以禁赛2年的处罚。
2.2 第2阶段: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的出现与摸索
2.2.1 规则变化
因“使用了受污染产品”是运动员证明自身无(重大)过错时最常使用的理由,制定2015版WADC时,WADA新增了第10.5.1.2条“受污染产品”规定,将这一理由作为适用NSF条款的一项特殊情形固定下来。该规定是前述非故意证明途径2在2015版WADC中的具体表述。根据受污染产品规定的内涵,如果运动员认为违规是因为不慎使用了被污染的产品,他必须举证证明自己声称受污染的产品中的确含有该禁用物质(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6),否则就视为举证失败。也就是说,只有在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可以确定的案件中,运动员才能通过途径2证明其非故意。
2015版WADC对运动员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导致无法确定禁用物质来源的运动员在证明违规非故意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障碍(Rigozzi et al.,2015)。对他们而言,因为途径2不能在非故意证明中发挥作用,寻找不需要说明禁用物质来源即可洗脱罪名的证明方法至关重要。在条例的适用过程中,“故意”和“疏忽”“过错”概念之间不相对应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这也为运动员打开了另一扇窗——“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以获得禁赛减免”和“证明非故意以避免禁赛4年”的意思存在区别(Duval et al.,2016),证明非故意并不以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为必要前提。即使只能说明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仲裁庭仍应给予运动员推翻故意推定的机会。过往判例中“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为证明非故意必要条件”的观点因此发生了动摇。为了让无法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的运动员有机会证明非故意,途径3——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无须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的证明路径,开始在实践中出现并得到运用。
2015版WADC对故意的定义规定在第10.2.3条中。根据该条,“故意是为了界定作弊的运动员,为此,该术语要求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明知该行为已经构成兴奋剂违规或知道该行为具有构成或造成兴奋剂违规的高风险,但仍忽略该风险实施该行为”。此处“作弊”应当理解为“企图使用兴奋剂提高比赛成绩”(王倩倩,2019),仅指直接故意的情形;但要求运动员在实施行为时已认识到其行为构成违规或有构成违规的风险,又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内容(郑志磊等,2016)。实践中取后一种理解,即故意包括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运动员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使用兴奋剂,或者漠视风险而导致禁用物质进入体内的,都会被视为故意(杨春然,2017a)。在不说明禁用物质来源前提下,从故意定义出发,运动员仅反驳作弊的嫌疑尚不足以证明违规非故意,他必须通过其他事实让仲裁庭相信自己的过错程度较低。
作为兴奋剂违规处罚案件上诉机构,CAS处理了大量运动员试图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来减轻处罚的案件,其裁决能直观反映CAS在是否承认非故意证明新路径上态度的转变。从已公布的案例可以看出,该证明路径起初仅被承认具有理论可能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CAS仲裁员由开始的一致否定其现实可行性逐渐分化为支持和反对两派,并呈现出相互对立的姿态。在观点的激烈交锋和运动员的不懈尝试下,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之路径由理论逐步落实到现实。
2.2.2 WADA诉费尔南达案: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仍是证明非故意的必要条件
受以往经验影响,2015版WADC生效之初CAS并不接受运动员根据故意定义证明自己非故意的做法,新路径使仲裁庭难以判断运动员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证明责任。运动员的辩解可能只是一种推测,而仅仅如此就让他们得以减轻处罚无疑会违背WADC打击运动员服食兴奋剂、维护体育纯洁的目标。在WADA诉费尔南达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6)中,仲裁庭就明确指出:运动员必须说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她体内的,否则就视为没有履行证明责任。
费尔南达(Yenny Fernanda Alvarez Caicedo)是哥伦比亚国家举重队的队员。2015年5月6日,她在参加泛美青少年锦标赛时接受了兴奋剂检查,结果显示她体内存在勃地酮(boldenone)代谢物,该物质为赛内外均禁止使用的非特定物质。2015年11月在国际举重联合会(Interna‐tional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IWF)举办的听证会上,费尔南达辩称阳性结果是队内理疗师注射所致,该治疗行为在队医的指导下进行,因此违规是非故意的。IWF接受了她的解释,处以5个月零21天的禁赛处罚。WADA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CAS提起上诉。在向仲裁庭提交的意见中,WADA指出,没有证据显示运动员的药检阳性结果与理疗师实施的注射行为有关,费尔南达没有履行说明自己非故意的证明责任,因此应当受到4年禁赛处罚。仲裁庭支持了WADA的主张。
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写道:“运动员负有证明违规行为不是故意为之的举证责任,因此,她自然要证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体内的。”只有非故意的辩解不足以证明运动员的无辜,CAS的一贯立场和以往裁决形成的惯例已经表明,禁用物质如果来源于运动员在相应时间段里无意中摄入的某种补充剂、药品或者其他产品,运动员必须提供确切证据以说明禁用物质可能来源于这些产品之一。仲裁庭认为,本案中运动员关于违规是由理疗师注射行为导致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费尔南达提交的证据只说明她本人相信这一辩解,却无法说服仲裁庭。因此,仲裁庭认为费尔南达没有履行证明责任,不能证明自己非故意,应当受到4年禁赛处罚。
费尔南达并不是唯一因未能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而被认定没有履行举证责任、进而未能获得禁赛减免的运动员。在WADA诉埃尔萨拉姆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7b)中,仲裁庭重申了上述立场:“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是获得禁赛减免的先决条件,因为运动员有义务确保没有禁用物质进入自己体内。如果运动员不能以仲裁庭感到满意的方式证明禁用物质如何进入她体内,她就不能排除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使用该物质的可能性。”
2.2.3 比亚努耶瓦诉国际泳联案:CAS首次认可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路径
尽管CAS刚开始并不接受运动员根据故意的定义证明违规非故意,但在诸多运动员的不断尝试之下,这一局面开始被打破,标志性案例就是比亚努耶瓦诉国际游泳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FINA)一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7a)。本案中,仲裁庭首次对比分析了两种观点,并认为理论上运动员有可能在不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前提下推翻故意推定。
比亚努耶瓦(Mauricio Fiol Villanueva)是一名秘鲁游泳运动员,并于2015年7月14—16日参加了泛美运动会。比赛前他接受了泛美体育组织兴奋剂检查,随后参加了比赛。7月16日下午他被告知7月12日采集的兴奋剂检查样本中检测出了一种叫司坦唑醇(stanozolol)的非特定禁用物质。FINA兴奋剂处罚机构(the Doping Panel of 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于2016年3月14日作出了处罚决定,但比亚努耶瓦表示不服并上诉至CAS。在提交给仲裁庭的意见中,比亚努耶瓦表示自己的行为既不是作弊也不是故意违规,他不知道也没有理由相信自己使用过司坦唑醇。他辩称自己体内的禁用物质来源于出发比赛前在秘鲁当地食用的、被当作牛肉出售的马肉,而该肉制品受到了污染。同时,比亚努耶瓦还指出,FINA要求他必须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以证明自己没有作弊意图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对本案,仲裁庭在裁决书中专门讨论了证明非故意是否要说明禁用物质来源,并分别列举了支持正反双方观点的理由。最终,仲裁庭选择了“说明禁用物质来源并非证明非故意的必要条件”这一立场,并引用了学者观点进行说明:“2015版WADC未明确要求运动员在证明违规行为非故意时必须说明禁用物质的来源。虽然禁用物质的来源能在评价运动员过失程度的事实依据中成为一个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但仲裁庭可以根据10.2.3条对案件的主客观情况进行灵活审查以判断运动员是否确为非故意违规。”(Rigozzi et al.,2015)仲裁庭认为,运动员有可能仅凭借自己在兴奋剂问题上的清白历史和品格证据证明违规非故意,但这是极为罕见的特殊情况。本案中,虽然仲裁庭认为运动员有可能根据故意的定义证明非故意,但其并未支持比亚努耶瓦的主张,因为无论是否需要说明物质来源,仲裁庭都认为比亚努耶瓦没有充分履行自己的举证责任。
2.2.4 阿德米诉欧足联案:运动员首次成功运用新路径证明非故意
比亚努耶瓦案中仲裁庭对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的认可,促使CAS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其他案件该路径的可行性。当大多数仲裁庭仍然坚持将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作为必要条件时,阿德米诉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UEFA)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7c)实现了运动员根据新路径成功证明非故意案件的“零的突破”,对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阿德米(Arijan Ademi)是一名效力于萨格勒布迪纳摩足球俱乐部(GNK Dinamo Zagreb)的职业足球运动员。2015年9月16日,在其所属俱乐部与阿森纳俱乐部的比赛结束后,阿德米接受了兴奋剂检查,之后他被告知自己的样本中检测出了司坦唑醇代谢物。UEFA道德与纪律委员会(the Control,Ethics and Disciplinary Body of UEFA)决定对阿德米禁赛4年。由于UEFA申诉机构(UEFA Ap‐peals Body)维持了原处罚决定,阿德米将该决定上诉至CAS。阿德米辩称自己体内的禁用物质来源于自己为减轻背痛而使用的补充剂,且该补充剂经过俱乐部医生检查,确认标签上的成分不含有违禁物质(王倩倩,2018)。他将自己使用过的补充剂送往多个实验室进行检验,但不同实验室给出的检测结果大相径庭:有的实验室检测出了司坦唑醇,有的则只检测出了可疑峰值(suspect peaks)含量但不能确认产品中是否存在司坦唑醇。因无法提供同批次同包装的补充剂进行检测,阿德米难以说明体内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UEFA则认为,在将补充剂送去检测的过程中,容器处于非密封状态,阿德米有足够的动机和机会去操纵检测结果。
本案仲裁庭认为说明禁用物质的来源并不是运动员证明非故意的必要条件。仲裁庭指出,尽管阿德米无法确定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但结合阿德米提交的关于补充剂可能受到污染的证据、理疗师和俱乐部医生的证词及其本人的证词,可以认为他达到了推翻故意推定的优势证明标准,阿德米方提出的补充剂被污染比UEFA方提出的操纵行为更有可能发生。因此,阿德米证明了自己违规是非故意的。不过,在考虑阿德米违规是否属于无(重大)过错时,仲裁庭认为,阿德米忽略了一般运动员为了避免误服兴奋剂而采取的诸多预防措施,例如,他没有上网查询产品成分表,也并非从有执照的药店购买补充剂,因此很难认定其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由于阿德米没有证明自己无(重大)过错,无论他是否说明了禁用物质来源,仲裁庭都不会根据NSF条款减轻处罚,更何况没有证据证明禁用物质确实来源于阿德米声称被污染的补充剂。最终,仲裁庭裁定阿德米应就其兴奋剂违规受到禁赛2年的处罚。
阿德米案是运动员在没有说明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下,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首次成功实践。作为适用新证明路径的典型案例,它意味着运动员即使只能提出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也有机会推翻故意推定,获得禁赛减免。尽管本案的仲裁庭被认为破坏了CAS判例的一致性,但无法否认的是,阿德米案让对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开始关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一证明方法。
2.2.5 阿卜杜拉曼诉埃及反兴奋剂组织与WADA案:根据故意一般证明非故意也需举证说明具体情形
比亚努耶瓦案的裁决结果表明,CAS仲裁员在“运动员必须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才能证明非故意”这一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阿德米案加深了这种分歧。但是,这两个案件都没有回答这类案件中运动员如何履行证明责任等问题,导致在实践中尽管有不少仲裁庭认可它们的立场,却不知如何适用,也担心难以判断运动员是否履行了证明责任。而阿卜杜拉曼诉埃及反兴奋剂组织(The Egyptian Anti‐Doping Organization,EGY‐NADO)与 WADA一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7d)提出了运动员在无法说明物质来源时,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所必须满足的要求。
阿卜杜拉曼(Ihab Abdelrahman)是一名埃及标枪运动员。2016年4月17日,阿卜杜拉曼在埃及接受了赛外兴奋剂检查并填写了兴奋剂检查表。检测结果显示,阿卜杜拉曼的样本中含有内源性同化雄激素(Endogenous 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这是一种赛内外均禁用的非特定物质。埃及反兴奋剂处罚机构(the EGY‐NADO Doping Hearing Panel)决定给予阿卜杜拉曼禁赛2年的处罚,理由是他没有谨慎地对待自己认为可能已被污染的补充剂,反而继续使用。阿卜杜拉曼和WADA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分别向CAS提起上诉。
阿卜杜拉曼主张禁用物质来源于自己写在兴奋剂检查表上的名为“GH Freak”的产品。该产品有两种版本在市场上销售,一种含有违禁物质而另一种不含,但它们都出自同一生产商,且标签和包装几乎完全相同。阿卜杜拉曼知道两种不同版本的“GH Freak”存在,并且总是与自己的医生一起检查包装以确定使用的产品是不含违禁物质的版本。以往的多次兴奋剂检查中,他都通过检查表报告自己使用了该产品,但从未出现阳性检测结果。因此,他认为该产品在生产环节就已经受到污染,自己对由此造成的兴奋剂违规不存在故意。
本案仲裁庭承认,证明禁用物质来源是证明非故意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当摄入途径已经确定时更容易证明非故意。但是,如果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背景能够支持运动员的非故意主张,那么仲裁庭也有可能被说服,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运动员不能仅就违规事实进行辩解,他还需要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自己不是明知故犯,也没有忽视可能构成兴奋剂违规的重大风险。仲裁庭重申,尽管规则并不强迫运动员说明禁用物质的来源,但他提出禁用物质可能来源的猜想后,应当举证证明这一说法具有现实可能性。既然阿卜杜拉曼认为产品在生产环节就受到了污染,他应当举证说明在生产过程的哪个环节有可能发生这种污染。仲裁庭认为阿卜杜拉曼的证明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因此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
阿卜杜拉曼案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案件中,仲裁庭难以判断运动员是否履行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仲裁庭观点,在这些适用新路径的案件中,运动员即使无法说明确切来源,也要根据情况说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其体内,并且要有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有可能发生,仲裁庭的裁决应建立在证据之上。如果运动员提出的猜测没有以任何方式加以证明,仲裁庭就会认为这种解释不足以推翻故意推定。这说明,无须说明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不代表运动员可以逃避说明来源的责任,即使关于来源的说法只是一种可能,运动员也要积极举证,才有可能说服仲裁庭认定违规非故意。
2.2.6 劳森诉国际田联案:运动员运用新证明路径免除禁赛处罚
除阿德米案外,另一件成功在未说明禁用物质明确来源的前提下、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案件是劳森诉国际田径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IAAF)案(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20)。贾里奥·劳森(Jarrion Lawson)是一名美国田径运动员,2018年6月2日他在一家日本餐厅吃了牛肉饭,并在19个小时后接受了兴奋剂赛外检查。6月14日,检测结果显示A样本中含有群勃龙(Trenbolone),属于赛内外均禁用的非特定物质,但直到8月3日劳森才被告知该检测结果。临时停赛后劳森要求对B样本进行检测,结果与A样本一致。2019年5月24日,IAAF纪律仲裁庭(Disciplinary Tri‐bunal)作出裁决,对劳森处以禁赛4年的处罚,劳森表示不服并上诉至CAS。在上诉审中,劳森坚称自己体内禁用物质来源于在日本餐厅食用的牛肉,自己的违规是非故意的。但是他只证明了当时自己确实在该餐厅用餐以及自己体内的禁用物质含量很低,但无法提供IAAF要求的餐厅牛肉采购单据及相关信息。
本案仲裁庭认为,为了证明非故意,运动员通常需要说明禁用物质的来源,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不满足这一要求,运动员也有可能证明非故意。在肉制品污染案件中,追查肉类的具体来源和证明肉类被污染的可能性都是履行证明责任所必须做的,因此,仲裁庭首先从科学角度对劳森提出的、禁用物质源于肉制品的说法进行了考量,结论是结合已有证据,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极低。劳森的举证没有达到标准,未能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但是,仲裁庭认为,本案属于特殊情况,劳森可以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其认为,劳森之所以无法提供可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证据,是由于IAAF没有及时告知他检测结果,导致他错过了收集证据的最佳时间。综合劳森的清白历史、其教练和经理的证言、测谎仪结果和头发检测结果,仲裁庭认定其违规确非故意,甚至不存在过失,并因此取消了对劳森的禁赛处罚。
上述案件反映出,从不被认可到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之路径是在CAS主导的体育仲裁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CAS关于证明非故意是否必须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分歧,促使持不同立场的仲裁员不断地探索新证明路径,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同时也丰富了需要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非故意证明内涵。CAS和运动员就2015版WADC非故意证明路径完善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21版WADC相关条款的制定。
2.3 第3阶段:WADA承认非故意证明新路径
由于2015版WADC不强制运动员证明非故意时必须说明禁用物质来源,CAS支持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声音愈加强烈,加上该路径的两次成功实践,在WADC修订时,条例制定者不得不有所回应。2021版WADC第10.2.1.1条之注释写道:“虽然在理论上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可以在不说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自己体内的情况下证明其兴奋剂违规不是故意的,但在条款2.1的兴奋剂违规案件中,运动员在没有证实禁用物质来源的情况下成功证明其行为是非故意,这是基本不可能的。”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但条例制定者不得不承认,尽管通过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以证明主观无(重大)过错仍然是最主要的非故意证明路径,但运动员的确可以不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仅凭个人主张和其他证据来推翻故意推定。
同时,2021版WADC对“故意”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删除了“为了界定作弊的运动员”的要求。删除这一表述是对实践经验的吸收。在实践中,反兴奋剂组织和CAS在对初次违规的运动员进行处罚时,无论其是否有作弊嫌疑,只要运动员不能证明自己违规非故意,就会被认定为故意并因此受到条例规定的4年禁赛处罚。例如,在埃尔萨拉姆案中,独任仲裁庭认为运动员虽然不是“作弊者”,但是她不能证明自己非故意,因此认定该运动员构成故意违规并支持了WADA要求对运动员禁赛4年的请求。2021版WADC的修改使条例规定与仲裁实践保持了一致。
经过对WADC相关条款的梳理可以看出,WADC的制定者正逐步接受和承认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并通过让条文保持一定的模糊性,让各反兴奋剂组织和CAS仲裁庭能够在个案中根据需要灵活解释和适用。而且,对非故意证明新路径的探索还进一步推进了故意定义的修正和原本通过说明禁用物质来源证明非故意之路径的完善,体现了WADC与时俱进的优点。但是,与实践相比,2021版WADC的改动依然保守,制定者仍刻意回避了某些问题,如个案在满足哪些条件后即可成为“特殊情形”,并根据第10.2.1.1条注释证明非故意,条例并未规定;对故意定义所进行的修改只是“小修小补”,故意与非故意之间如何划分依然没有答案。在维护无法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的清白运动员利益方面,2021版WADC仍存在改进空间。这种做法会使运动员继续面对沉重的举证责任和较大的败诉风险,尤其是在药物检测技术提升、食品安全问题愈加突出而导致无法查清禁用物质来源的兴奋剂违规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不利于维护清白运动员的利益。
3 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前提和要求
涉及非特定物质的兴奋剂违规中,不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根据故意的定义证明非故意的路径在比亚努耶瓦案中得到确立后,经过多个CAS案例的讨论和实践,最终得到2021版WADC制定者的认可。通过上文对WADC相关条款和CAS案例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WADC制定者在非故意证明问题上一直态度暧昧,但CAS的仲裁员们却在实践中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结合学者观点灵活适用规则,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裁判观点。这些裁判观点中的一部分成为2021版WADC相关条款的修订基础,一部分或将在日后同类案件的裁判中成为被不断遵循的判例。两相结合,可以总结出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前提和举证要求。
3.1 适用前提
第一,无法说明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如前所述,3种非故意证明途径中,第2和第3条途径与禁用物质来源有关,这两种非故意证明途径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CAS案例给出的回答是:当运动员因不确定禁用物质来源而无法根据NSF条款获得禁赛减免时,可以视情况给予运动员机会。也就是说,两种非故意证明途径之间存在适用上的先后顺序,运动员应优先选择确定禁用物质来源、证明自己无过错或无重大过错来推翻故意推定,只有当这一途径无法实现时,才去尝试根据故意的定义证明非故意。
这种顺序安排并非没有道理。首先,由于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途径的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制,而且适用与否完全取决于个案中仲裁庭的判断,运动员在兴奋剂违规案件中主要还是通过说明禁用物质来源、援引NSF条款给自己争取禁赛减免。其次,即使运动员竭尽全力仍不能确定体内禁用物质的来源,努力也不会白费。根据2021版WADC第10.6.1.2条的释义,运动员除了说明禁用物质来源,还要证明自己是无(重大)过错。运动员可以借这个过程向仲裁庭反映自己对违规结果缺乏可责性或可责性很低,并以此来说明自己主观非故意,这实际上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来博取仲裁庭的同情(杨春然,2017b)。最后,运动员援引受污染产品规定证明非故意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比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时要轻——证明自己过错程度低的主客观因素可以从先例中归纳。但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时,运动员面对的失败风险很高。这不仅是因为故意与非故意边界不明确——虽然否定了“明知故犯”,但因无法证明非故意而仍需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依旧存在;而且根据故意定义主张自己“无罪”时,运动员能从先例中获得的指引远不及前者。
第二,仅适用于特殊案件。当运动员经过努力仍然无法说明体内禁用物质的来源时,仲裁庭可以根据案件其他事实情况判断是否给予运动员机会,让其根据故意定义证明自己非故意。虽然认可了这一证明途径的合理性,但为了避免实践中运动员利用该方法逃避处罚,CAS一直将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特殊”案件中。2021版WADC吸收了CAS的观点。遗憾的是,成为“特殊”案件应满足哪些条件,无论是条例本身还是CAS案例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阿德米案和劳森案也许能够提供些许线索。在这两个案件中,尽管运动员努力举证,但已有证据均无法就禁用物质的确切来源得出结论。如果运动员不能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是因为缺乏关键证据,但该证据的缺失很难归责于运动员自身,仲裁庭认为继续纠缠这一问题会导致案件调查陷入僵局的,仲裁庭就有可能考虑认定当前案件为适用新证明途径的特殊案件。
3.2 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时的要求
阿卜杜拉曼案为想要通过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运动员确立了履行举证责任时需要满足的3点要求:1)运动员应根据兴奋剂违规的客观情况及自身的行为(包括其行为、人品和历史记录),表明存在可反驳故意违规的情形;2)对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作出切合实际的解释,并且要与前述情形相关联;3)上述解释应当有证据支持(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7d)。
上述要求的提出,让通过故意定义推翻故意推定的方法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在实践中具备了可操作性。它解决了此前不支持该方法的仲裁员的担忧——离开了禁用物质来源说明,仲裁庭难以判断运动员是否恰当地履行了证明责任。在上述条件指引下,运动员在提出非故意的主张和解释时,也需要说明体内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并不是一种臆想。只要运动员提供的证据能够让他的说法比对方更具有说服力,他就完成了证明责任。
在上述3项条件中,第1项和第2项容易实现,不存在争议;关键在于是否必须满足第3项条件,运动员才能被视为履行了证明责任。有学者认为,当运动员满足了前2项条件时,仲裁庭就已经预设了立场以判断运动员违规是否非故意;第3项条件的存在是徒有其表,尽管提出相关证据确实能够进一步增强运动员说法的可信度;如果第3项要求是强制性的,那么运动员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未免太过沉重,几乎没有履行的可能(Nuriev,2019)。CAS的案例目前也无法就该问题提供明确的回答,显然,仲裁庭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运动员是否提交了足以支持主张的证据完全由审理个案的仲裁庭判断。
4 完善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途径的建议
4.1 明确适用条件
因受污染产品规定对说明禁用物质来源的要求愈加严格,为了保护无意中接触了禁用物质、但无法说明来源的无辜运动员的权益,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路径应当尽快明确适用条件,以使这部分运动员有机会自证清白。明确新路径的适用条件,不仅能帮助仲裁庭判断案件是否落入适用范围,而且可以指引运动员更有针对性地调查取证和举证。2021版WADC只承认特殊情况下运动员可根据故意的定义证明非故意,但并没有说明何为特殊情况,因此在实践中CAS需要注意对案例进行分类,总结出最常落入特殊情况范围的案件情形。目前,运动员最希望争取仲裁员同情以适用新途径的情形主要有两类:1)无法确定禁用物质是否来源于被认为受到污染的补充剂;2)认为禁用物质可能来源于肉制品。CAS可以先从这两类情形中确定某一较常适用新途径的类型,总结出其落入该途径适用范围的特定条件;同时保留对该途径的一般规定,以便其他特殊情形出现后,运动员仍有机会根据故意定义自证清白。
4.2 界定履行举证责任所需要的证据种类
前文提到,即使在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案件中,运动员仍需要就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进行举证,才能被仲裁庭认为履行了举证责任。一般而言,运动员举证证明违规非故意需要满足优势证明标准。根据以往CAS案例中对该标准的阐释,只要运动员能够说服仲裁庭认可其提出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有可能发生,就视其达到了标准。虽然CAS要求运动员就禁用物质污染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进行说明,但运动员基本只能提出污染发生的可能说明而难以提供切实相关的证据。由于对禁用物质来源不确定,运动员通常会借助专家证人证言来支持自己非故意违规的解释,但CAS更愿意采信反兴奋剂组织方提供的专家证言,运动员能否凭借专家证言证明非故意因案而异。在尚未建立第三方专家库的背景下,CAS应当明确哪些类型的证据可被用于支持运动员的主张,让运动员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有较为清晰的目标,如产品制造商此前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过污染的不良记录、当地有关部门对兴奋剂禁用物质滥用情况的报告和能够证明运动员说法有现实可能性的其他兴奋剂违规案例。
4.3 证明非故意后禁赛期的确定
证明非故意后就要确定对运动员的处罚。除作为运动员证明非故意的主要途径外,NSF条款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确定运动员的禁赛年限。一般认为,NSF条款中关于禁赛年限的规定,不能在根据新途径证明非故意的案件中适用,因为运动员没有说明禁用物质来源,而这是援引NSF条款减免禁赛的必要前提。根据WADC第10.2.2条之规定,运动员非故意违规的禁赛期为2年。也就是说,运动员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应禁赛2年且不得根据NSF条款进一步缩减(Rigozzi et al.,2015)。但是,无论是阿德米案还是劳森案,仲裁庭都认为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后,仍然有可能适用NSF条款为运动员进一步缩减禁赛期。阿德米案仲裁庭认为运动员只证明了非故意,其行为与通常应尽注意义务的行为表现不符,因此认定其没有证明自身无(重大)过失而裁定禁赛2年。劳森案中,仲裁庭将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过程与无过错的认定合二为一,在认定运动员非故意抗辩成立后,直接得出运动员无过错的结论,没有对运动员施加禁赛处罚。这两个案例反映出,在NSF条款能否与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途径合并适用的问题上,CAS内部存在不同意见。本文认为,根据新途径证明非故意的案件,在NSF条款的适用上也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如仲裁庭综合案件全部证据和实际情况,能够认定运动员主观上对兴奋剂违规的确无过错也无疏忽的,可以根据NSF条款取消禁赛处罚。
5 启示
5.1 对我国运动员的启示
由于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而WADA又尚未出台调整阳性结果报告阈值的措施,我国运动员很有可能因使用了受污染产品而陷入体内禁用物质含量低却被认定为兴奋剂违规、又无法找出该禁用物质来源的窘迫局面。倘若发生这种情况,运动员在为自己争取禁赛减免时,可以考虑将通过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辩护思路纳入应诉策略中。
根据前文分析,当运动员无法通过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而证明自身无(重大)过错时,应努力举证让仲裁庭认为本案确属“特殊”案件,并因此给予运动员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机会。此时,运动员除了通过自己清白历史和良好品格支持自己违规非故意的主张外,还需要对禁用物质的可能来源进行合理解释。这种解释不能只是运动员的个人猜测,需要举证证明其有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才具有说服力,提供证据时,运动员应注意说明产品的污染可能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哪个环节、于何时何地发生、污染的原因和路径等。
5.2 对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启示
WADC要求成员国对条例的主体内容不得进行实质性修改,但并不阻止在条例框架内灵活应用规则。对于我国的反兴奋剂工作而言,既然2021版WADC已经承认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的可能性,那么在条例实施过程中就应积极探索该方法的实际运用。
我国的《反兴奋剂规则》最新版由国家体育总局根据2021版WADC的内容制定,属于WADC第23.2.1条规定的签约方实施条例的可行方式。根据WADC对签约方实施条例的要求,《反兴奋剂规则》关于兴奋剂违规的类型和对个人处罚的规定应与实施中的WADC内容保持一致。出于文字表述简洁的需要,《反兴奋剂规则》省略了WADC中的注释,但根据《反兴奋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WADC中注释对正文的解释不仅适用于WADC本身,也适用于该规则,规则视为已纳入释义并参照执行。因此,《反兴奋剂规则》适用2021版WADC第10.2.3条释义中关于非故意证明新途径的内容,当合适的特殊案件出现时,不得以《反兴奋剂规则》中没有规定为由拒绝运动员使用该证明途径的请求。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规则》和《兴奋剂违规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对违规运动员的处理程序为:中国反兴奋剂中心通知运动员及其相关方确认阳性检测结果并告知申请听证的权利;运动员申请听证的,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委员会组成听证专家组,负责具体案件的听证工作;听证结束后,专家组形成听证会结论,内容包括确认阳性检测结果或运动员涉嫌的其他兴奋剂违规是否成立、衡量当事人过错程度或责任轻重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对运动员的处理建议;结论作出后,通知运动员、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有关单位,将资料移送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相关项目协会或机构,由后者根据听证会结论作出处理决定;运动员拒绝听证的,由有关单位直接作出处理决定。在整个过程中,运动员证明自己违规非故意的机会主要出现在听证程序环节。在听证程序环节,运动员可以就涉嫌兴奋剂违规的诸多问题进行申辩和质证(李静,2020),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违规非故意的主张和证明。听证活动应当按《反兴奋剂规则》的要求进行,由于《反兴奋剂规则》是WADC在中国的具体实施形式,根据前文所述,听证程序中如果无法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运动员可以请求根据故意的定义证明非故意,听证专家组应当认真考虑运动员的请求,并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进行判断。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实施新的《反兴奋剂规则》时,可参照CAS案例决定是否允许运动员通过此途径证明非故意,最好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取得经验上的突破。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肉制品受污染情况值得关注,对于禁用物质可能来源于肉制品的案件,听证机构相对于CAS可以适当放宽适用新途径的要求。对运动员而言,这无疑为其争取禁赛减免增添了希望,也是实质公平的必然要求。
6 结语
2021版WADC在第10.2.1.1条的注释中承认了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之路径的价值,这一修订对于运动员争取禁赛减免、早日重返赛场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无法说明禁用物质确切来源的清白运动员。尽管该证明方法尚存在诸多等待完善的细节,但CAS通过案例为该方法的应用积累了经验,使之不再仅仅有理论上的实施可能而具备了实际运用的基础。根据对CAS案例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兴奋剂违规者在无法证明禁用物质来源时,可以从故意定义出发,通过说明违规的主客观情况证明自己非故意,这种证明方法已经得到WADC和CAS的认可。
第二,实践中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时,需注意:1)在适用顺序上,说明禁用物质来源以证明运动员无(重大)过错的非故意证明方法仍处于第一顺位,只有该途径无法实现时,才考虑根据故意定义证明非故意;2)新证明途径只适用于“特殊”案件,不具有普遍性;3)即使不需要说明确切来源,运动员仍要举证支持自己关于禁用物质可能来源的解释。
第三,该非故意证明新途径仍需继续进行完善,完善的内容包括:1)明确“特殊”案件的标准;2)界定运用该途径证明非故意所需要的证据种类;3)建议根据该途径证明非故意后,适用WADC第10.2.2条将运动员的禁赛处罚缩减至2年,综合案件情况能够认定运动员主观上确无过错和疏忽的,可根据NSF条款免除禁赛。
第四,考虑到我国反兴奋剂工作面对的压力,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反兴奋剂组织,都不能忽视WADC的这一变化。运动员可以将该证明方法纳入自己的诉讼策略,灵活运用以减免禁赛处罚;反兴奋剂组织的听证机构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允许运动员使用该证明方法。
- 体育科学的其它文章
- 我国体育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机遇、挑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