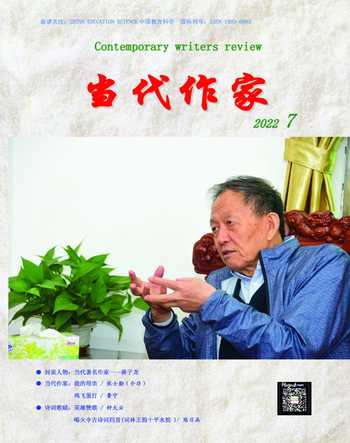故乡的柳树
从我背上行囊,远走他乡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故乡已被我装在了旅行袋中。
而今,屈指算来,我离开故乡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其间每每思乡情切,泪眼迷蒙的时候,老家门前那七棵柳树总是最先涌向我的脑海,垄断我对故乡的思念。
还记得小时候故乡的一个春天,柳条青青,我们几个顽皮的小家伙专拣嫩长的柳枝折下来,做成“盐老鼠”,直奔自家盐缸里钓“老鼠”,到头来,“老鼠”没钓着,盐倒是“钓”出了不少。父母一回来,对不起,你跑得快可逃此一劫,跑不快——小心脑袋“凿顶箍”!而我,却又偏偏是那跑不快的。于是,直到现在,当我偶尔看见有些小调皮鬼玩这些早已过时但趣味不减当年的“游戏”时,我还不由自主地替他们担心——可要小心脑袋“凿”的疼啊!
当柳枝也因我们的顽皮而快速变硬时,夏天到了。嫩柳枝是找不到的了,但不用担心,我们自然有玩的“绝招”。
嘿,你瞧,我們几个男扮女装全副“武装”的“荷花仙子”来了 ——衣服嘛,是三片大荷叶组合而成(即把每片荷叶掏个洞往身上一套,衣服就成了),再折几根粗柳条,编绞成一个圆形,在头上盘成一个圆圈,圆圈周围呢,插上我们采的五颜六色的野花,仙冠就诞生了,再配上耳环,项链(全是原生态的就柳取材),我们一个个就变得“花枝招展”了。
再然后,我们就要变成“神仙”啦!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神仙”是个什么概念,但听爷爷奶奶讲是神仙是那能够腾云驾雾会飞的……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在每两棵柳树间系上绳子,我们就这样拉着绳子飞过去飞过来过“神仙瘾”——运气不好的,摔下来,也顾不得疼痛,拍拍灰赶紧再去打荷叶做衣服。首先还会为“仙装”的破损而难过。
也许是我们玩得太过份了,柳树很快就力不从心了,她变老了,叶子都发黄了。
秋天到了。
大人们日夜忙着收割,我们几个调皮鬼也不闲着。一到夜晚,家家门口都点上一盏大油灯,人们都忙着趁好天气打谷。我们几个一吆喝,来到柳树下,“兹溜”一声,我们几个就都到了柳树上。拣个稍粗点的枝丫,再用绳子把自己和柳枝绑在一起——一闭上眼睛安心睡到被父亲一巴掌打醒。睁眼一看,天刚亮,心里不免要埋怨父亲的“粗鲁”,但听说母亲跑遍整个村子都找不到我的焦急时,心里又不免一阵自责:开这种玩笑也确实没有理由怪父亲那一巴掌。
当我们傻呼呼地为不能给每片落叶都建一座高级“坟堡”而悲伤的时候,冬天又匆匆地搭上了岁月的列车。
大雪掩盖了一切,枯黑的柳枝也像是擦上了雪花膏。看不到半点苍老的容颜。
顾不得暖暖的被窝,我们都早早起床,聚在一起打雪仗。也许当你正专心致志地打着“敌人”的时候,你的后脖子不知被哪个“叛徒”塞进了个雪球,但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童年本来就是像雪那样纯洁,那样美丽的啊!
走过岁月的四季,我们最终还是失去了童年,太多的不舍与留恋,都被柳条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承诺所冲淡,当年的小伙伴也都如我一般因为生活而远走他乡,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的相交点仅限于在那几棵杨树下,但我们在那几棵柳树下结下的情谊却值得我们回味几生几世。
九十年代初,老家门前的几棵柳树因为要扩建公路而被伐倒了,我听后心里徒感一阵失落,我不否认我对故乡的思念并非仅仅只是由那七棵柳树所支撑,但那七棵柳树确实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现在,它们被伐倒了,我在痛惜之余又不免想起了过去的种种。故乡的柳树啊,要是那时候有相机……不!我的眼晴里、脑海里、心窝里存着你!比相机更先进;柳树带给我的童年快乐永远可以回放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简介:
吴雷,男,七零后;毕业于湖北大学,从小对古藉、古诗词楹联及古色古香的民居、摆饰、陶瓷、化石、器皿等特别钟爱并专注搜寻、研究;吴雷不是雷军(小米科技创始人),但有着与雷军同样的韧劲与执着。从不熟识汉川文化到成为汉川的“活词典”、“活地图”、“活百科”、“汉川历史文化研究者”;吴雷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还在专心研读,他的积蓄大多用来购置书籍,用来加深对汉川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盛誉之下,饱含着他的韧性、坚持,和一如既往的热爱与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