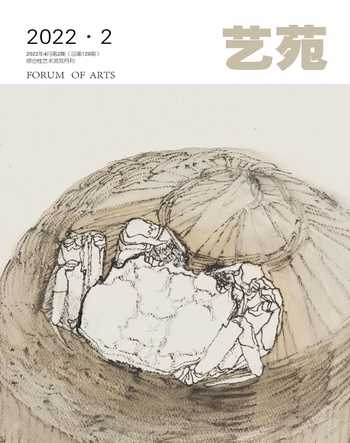谍战剧中的“双重文本”与“角色-观众”间的隐性置换
周粟
摘 要: 借用约翰·费斯克的受众主体性理论分析,在以《潜伏》为代表的经典国产谍战剧中,存在着一对相互对立的“双重文本”:观众在表层意识文本中解读出了“信仰”,同时在深层无意识“潜文本”中解读出了当下自身的现实生活困境与内心渴望,这种内心渴望转而在谍战剧中获得替代性满足。这种于潜文本层面的“隐性置换”,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的转化公式,即无论观众在谍战剧的“显性文本”中解读出了“信仰”“理想”还是其他的“上层建筑”,他们在“潜文本”层面永远会不自觉地解读出更深一层的“渴望”,这两种极端的转化公式取决于一个变量,即观众在潜文本中看到的对象是弱者还是强者。对经典谍战剧文本特征和题材特性层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挖掘当年“现象级”谍战剧引发收视热潮的深层原因,进而对当下国产电视剧的创作与研究产生启迪。
关键词:电视剧;谍战剧;《潜伏》;约翰·费斯克;屏幕理论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谍战题材电视剧,主要指以间谍活动为表现主题,以极强悬念、较快节奏和严密逻辑为主要创作特征的电视剧类型。谍战电视剧的题材优势,决定了其既不同于家庭伦理剧中充分贴近观众熟悉场景的现实性,也不同于古装武侠片中彻底远离观众认知范畴的奇观感,也即优秀的谍战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往往能在电视文本生产者和观看者之间建立一种符合观看主体产生意义的“适当场所”[1],进而通过谍战剧特有的“脑力游戏”特质征服观众,使他们在产生“智商提升”的象征性快感后,形成对剧集中沉着冷静智力超群的魅力角色的高度崇拜,进而获得由谍战叙事这一“高级思维游戏”引发的特殊审美意趣。
本文选择考察谍战剧《潜伏》,主要考虑到其在观众中的特殊影响力。从受众角度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谍战题材电视剧呈现出广泛的传播趋势;而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对于观众的受众研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以下试图批判性地从约翰·费斯克的观众主体性理论角度切入,分析以《潜伏》为代表的21世纪国产谍战题材电视剧受众心理、身份价值等观众主体性因素及其效果,进而考察观众在读解过程中如何创造意义并建构自身价值,剖析《潜伏》文本在受众传播中的内在驱动力,从而为理解21世纪中国谍战剧的社会影响力状况提供一种解答。
一、费斯克的电视受众主体性理论特征
以约翰·费斯克的电视屏幕理论看,观众在观看情节紧张、故事离奇的电视剧时,往往会获得隔绝于家庭之外而又保留家庭主体性的“生活在別处”的审美快感。观众于熟悉的家庭环境中,边忙手头事边对屏幕内谍战剧惊险情节的随眼“一瞥”,可能就决定了电视文本与观看者之间恰当“共谋”关系的瞬间生成。回顾21世纪的头十年,国产谍战题材电视剧的播映热度曾一直居高不下。这其中,《潜伏》作为当年“霸屏”的谍战经典,时至今日仍“潜伏”在众多谍战迷的作品排行榜之中。探讨谍战剧《潜伏》中的受众主体性特征,首先需要就电视主体性理论做出必要的特征辨析。
在斯图尔特·霍尔与大卫·莫雷的研究基础上,约翰·费斯克重点提出了观众主体性的概念,其通过对电视文化的研究方式进行分析,亮明自身的观点:电视观众是具有积极性的意义生产者。综合来看,费斯克对于电视受众的主体性理论,重点贡献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费斯克是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基础上,明确观众主动性地位的电视研究开拓者。费斯克强调受众“积极”地构建与电视文本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建构自身意义的自主权力。费斯克对于受众主动性的重视,是对之前电视研究理论中过于强调文本力量的重要回应。
其次,费斯克指出电视受众获得快乐的深层原因。相比之前的电视研究理论,费斯克关于电视受众如何理解电视文本,以及如何从中获得乐趣的观点十分新颖。费斯克指出,观众对电视文本的解读立场,来自于电视文本的意识形态代码,以及这些文本代码传递给观众所形成的电视代码。当观众所运用的解码方式与电视文本编码者所持的意识形态相符,受众立场就容易倒向电视文本的常规道德立场。
费斯克指出,以电视文本的多义性也即意义的多样性为根基,电视受众在观看电视过程中具有“生产”出多样性的潜在意义的可能性,而这种被生产出的“可以实际体验的意义”[1],也依托于不同观众主体的社会特征。综合来看,费斯克的观众主体性理论对于挖掘电视剧受众的主体性特征、展现电视剧文本输出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凯尔纳对于费斯克的批判所指出的那样,费斯克的理论具有“膜拜受众”和“膜拜抵制”的倾向,这导致其在文本研究中漏掉了诸如社会体制、文化生产语境、政治体系等影响因子,从而这种过于强调接受者的受众理论,难免具有形成“新教条主义”[2]的倾向。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后文将力求避免费斯克主体性理论中“唯受众是举”的立场,兼顾谍战剧《潜伏》受众的同时,客观论述电视剧文本生产者的作用与地位。具体来看,后文将沿承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对于“心理分析与主体”的论述方式。[1]费斯克在“心理分析与主体”部分的论述具体方式是,既承认体验电视文本的主体是多种社会主体(而非单一接受者的心理分析主体),又指出电视文本建构了这些主体。他在论述心理分析与主体的关系时强调家庭中的电视观众是社会化之后的产物,因而需要获得由“社会转化而来”的一种主体理论。[1]以下将尝试将电视受众主体性理论与以《潜伏》为个案的谍战剧分析进行内在结合。
二、从主体性角度看《潜伏》受众的五点特征
在统计当年《潜伏》的诸多受众反馈数据时,笔者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何当时数量众多的剧迷,似乎普遍对于《潜伏》中的反面角色关注度高于正面角色?为何当时网络上形成了众多针对四位反派角色吴站长、李涯、陆桥山、谢若林的“二创作品”?为什么不是余则成所代表的象征崇高信仰的正面英雄人物,反而是吴站长所代表的反面人物赢得了相对更高的关注度?或许,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入叩探21世纪头十年谍战剧收视火爆的深层社会心理缘由。
通过应用受众主体性理论对《潜伏》受众进行初步分析,本文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五方面思考:其一,受众特别是《潜伏》的年轻观众,对于传统意义上“男性气概”包含的“信仰”“坚韧”等精神力量充满期待;其二,具备“迷”特质的观众会对剧中所迷恋的角色产生二度“创作”的冲动,体现出麦特·西尔斯所述“創造性自我表达”的粉丝特性;其三,观众会通过辨认电视文本中自身“熟悉”的话语,感受到《潜伏》对于自己的话语“尊重”,进而获得影像文本的解读快感;其四,在观看《潜伏》时,受众通过“权力”“信仰”等内在符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商与碰撞过程,获得身份的彰显与意义的“再生产”成果;其五,《潜伏》所特有的压抑情感,与中国人传承下来的压抑记忆产生了“共谋”,“压抑”成为获得了观众同感的《潜伏》成功秘诀之一,也即《潜伏》中特有的剧场式的安静基调氛围,与谍战环节紧张刺激的叙事节奏反差,使得费斯克所述的“快乐”源泉得以产生。谍战剧电视观众的快感,就来自于这一反差张力达成统一的程度和情节弥合荧屏内外思维鸿沟的力度。正如费斯克理论指出的那样,电视观众通过辨认出他们熟悉的内容,在电视文本的解读中获得了文本“尊重”他们的熟悉“话语”,由此获得了快感,并获得了继续积极创造自身社会经验以及“再生产”“再编码”的动力源泉。
例如,在相关学者所论述的“泛俗化”卡里斯马幻象这一概念中,吴站长这一角色形象,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现实社会话语体系中观众眼中的“卡里斯马”幻象。在如今男性特征式微的社会现象下,吴站长、李涯、余则成这样具备男性魅力、权威感、神秘感以及已有或者具备潜在权力属性的角色,成为观众对于传统男性形象呼唤的复归。
三、《潜伏》中“潜伏”的“双重文本”
不妨这样来看,《潜伏》好比是一部包含“双重文本”的电视剧文本:它的表层意识文本的主旨在于“信仰至上”,这以余则成为突出代表;其深层无意识文本的主旨在于“活着至上”,这以吴站长为代表。“信仰至上”,要求为崇高信仰而敢于牺牲一切;而“活着至上”,则相反要求为活下去而可以牺牲道德、义务、责任、承诺及信仰等。如果这种假定是有合理性的,那么可以看到,观众在收看这部谍战剧的过程中,已经身不由己地投射进自己的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在意识层面,他们可以为余则成等人物的崇高的牺牲精神而深深感动;而在深层无意识层面,他们则会不知不觉地为吴站长等人的生存行为及其法则而深切地投入。而这种深层无意识心理颇为耐人寻味:观众已经于不知不觉中将自身的现实生活情境投射进电视剧的角色中,并且完成了一次银幕与现实之间角色的隐性“审美置换”[3]。
进一步看,《潜伏》的影像文本层面,实际上存在着一对相互对立的“双重文本”(也即“双重本文”),正如有学者所述,“双重文本”不仅可以作为“一切本文共有的特性,也可以被视为文化的一种修辞术……文本总是由意识文本(表层结构)和无意识潜文本(深层结构)组成的”[3]。观众在谍战剧《潜伏》的表层意识文本中解读出了“信仰”,又同时在其深层无意识“潜文本”中解读出了自身的当下现实生活困境与内心渴望,这种内心渴望转而在《潜伏》中得到替代性满足。双重文本之间具有一种张力结构,可以令观众产生“信仰至上”还是 “活着至上”的选择困境。对于《潜伏》来说,上述双重文本之间是结合得如此紧密而又融洽,以致观众常常会忘记掉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这种紧张关系。这部谍战剧的美学成功就在于,它巧妙地让上述双重文本融合于叙事结构的多义性构造之中,让观众游刃有余地在其中投入地观看,既可以投射进崇高的理想主义信念,也可以投射进现实的享乐主义情怀。
四、“双重文本”背后的“隐性置换”
更进一步,在观众的无意识潜文本层面,也存在着两种渴望。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述,“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分别代表这两种渴望的两极:一极为意欲“取代对方”成就自身欲望的“最低需求”,另一极为“同情对方”帮助他人崛起的“崇高道德”。[4]两者相互转化,互为因果。例如,反面人物中,观众普遍对于吴站长的关注度很高,这体现出观众在无意识潜文本层面,为“活下去”而宁愿放弃道德、承诺与归属感的“本我”式渴望:观众在潜意识中渴望“代替”吴站长进而“化身”吴站长,他们在观看《潜伏》时下意识地将自身生活情境中的困苦与无奈的身份,与荧屏中深谙生存之道的吴站长形象进行了对调,完成了潜文本层面的隐性“审美置换”;与此同时,观众在潜文本中也饱含着“同情弱者”的“超我”式“崇高道德”,根据相关调查可知,不同性别观众对《潜伏》中女性角色晚秋呈现完全相反的态度,男观众最喜欢的女性角色就是“晚秋”,而女观众最讨厌的女性角色恰好也是“晚秋”。
具体分析,在潜意识层面,男性眼中的晚秋是绝对的弱者,他们面对荧屏中晚秋这一类型角色激发出潜意识中强烈的同情心与保护欲,渴望成为她的宽厚的肩膀,因此,男性观众在解读《潜伏》的潜文本层面,实际已与剧中那些配得上晚秋的强悍男人完成了身份对调,形成了“隐性置换”。而温柔的晚秋在女性观众眼中,则被下意识归为可憎的竞争对手,她们眼中的晚秋是具备“温柔”这一女性杀手锏的“强者”,因此女性观众内心那份“本我”层面的“不择手段”被强烈激发,“马斯洛最低需求”中最原始的“情欲”需求开始肆意生发。在潜意识中,女性观众更喜爱对自身不具有威胁感的“傻大姐”翠平,她们在观看并“解码”《潜伏》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与傻大姐翠平角色的“隐性置换”,因为在潜文本中她们渴望打败翠平的情敌“晚秋”,为“情欲”需求这一马斯洛理论中的最低层次需求去不断奉献自己的“本我”本能。
《潜伏》提供的这种观众在潜文本层面的“隐性置换”,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学上的转化公式,即无论观众在谍战剧的“显性文本”中解读出了“信仰”“理想”还是其他的“上层建筑”,他们在“潜文本”层面永远会不自觉地解读出更深一层的“渴望”,并且如上文所述,这种渴望包含着两个极端,即对“超我”般高尚道德的追寻以及对“本我”式“活下去”本能的诉求。这两种极端的转化公式取决于一个变量,即观众在潜文本中看到的对象是弱者还是强者。
总体而言,正因“当代影视媒介覆盖面广、信息传递快捷、生动多维,它是以具体直观的感性情态进入千家万户的”[5],所以《潜伏》为代表的21世纪谍战剧,在恰到好处地满足了观众对于潜文本层面上的心理补偿的同时,也更加提升了21世纪头十年,电视剧对当下电视剧创作理念与发展实践的“经验反哺”。
五、经典谍战剧对当下创作的启发
综合来看,国产谍战题材电影已经取得丰硕的成绩,比如《风声》《秋喜》《东风雨》《听风者》,以及《触不可及》《密战》《悬崖之上》《兰心大剧院》等,在电影题材类型表现上得到观众的喜爱。相比而言,尽管国产谍战电视剧的发展时间不如谍战电影那么长,但近年来谍战电视剧也形成了诸多优质的内容呈现,满足了大众的内在文化与心理需求,且不时会出现“爆款”谍战剧。
例如,近期播映的《对手》别出心裁、 跨越时空与《潜伏》形成了模式与结构上的相得益彰。《潜伏》描述的是我党潜伏人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谍战,而《对手》表现的是敌特长期潜伏于我们和平建设时期的间谍活动。作为国民党间谍,《对手》中的主角生活看似司空见惯,其内里却“潜伏”着跌宕起伏的丰富的身份挪移和情感变迁,也许这种呈现正反角色间“隐性置换”的新形态也是吸引当下受众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经典谍战剧进行文本特征和题材特性层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挖掘当年“现象级”谍战剧引发收视热潮的深层原因,进而对当下国产电视剧的创作与研究产生新的启迪。如何敏锐把握和利用好这一观众解读中的“隐性置换”公式,使其为电视剧的创作者所用, 这正是以《潜伏》为代表的21世纪早期优秀谍战剧作品群带给当下电視剧创作者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陆道夫.文本·受众·体验——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8.
[3]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周安华.询唤当代影视批评的价值感和美学蕴含[N].中国艺术报,2021-09-08.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