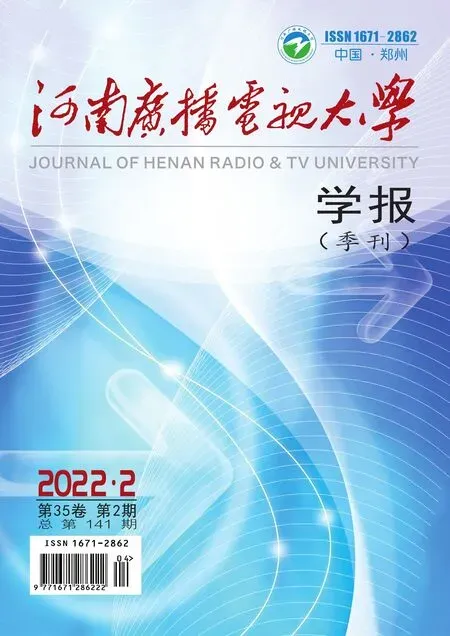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现状与思考
王真真
(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 河南 开封 475000)
开展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是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均衡发展,破解基础教育公平、效率等问题的重要措施。随着互联网、脑科学快速发展,信息整合、呈现方式,以及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对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冲击和深化,亟须寻找一种“适宜”的教育信息化评价方式。基于以上考量,本研究通过查阅教育部等政府网站关于教育信息化的相关论述,以及在中国知网以主题“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评价”等为检索条件,检索CSSCI论文70篇,博士论文69篇,并对以上论文中涉及主题进行重新检索和分析,尝试对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和回应。
一、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后,基于追赶甚至超越世界一流强国的愿景,我国积极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其中教育也不例外。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可以认为是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开端。1986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成立了“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正式启动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成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1998年,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教育部开始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随着《教育信息化“十五”发展规划(纲要)》和《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发布,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进入发展快车道。2012年启动了“三通两平台”建设,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三全两高一大”的信息化教育发展规划。其中,“三全”是: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两高”是: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一大”是: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已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进入了深度应用、全面覆盖、融合创新的时代。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教育资源配置已初具规模,效果显著。以河南为例,截至2020年,有多媒体教室的学校比例提升到98%,多媒体教室占教室总数比例提升至90.4%。远程互动教研平台已覆盖到18个省辖市、81个县区教研室、3所师范院校和440多个中小学校,初步完成了各级教研室、高校、优质学校、乡镇学校、教学点的全省布局任务。2021年举办全省性教研活动140多场,区域教研40多场,共同体活动20多场,专项支教30多场。
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估的研究与实践基本与以上历程同步。2000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管理信息化相关标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2014年、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各省市也积极回应,在各地教育部门组织中小学校和各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展自我检查。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教育部于2015年至2016年发布了《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等一系列工作报告。为了让整个评价工作更加顺畅,2013年,教育部建立了教育信息化工作月报制度和月度视频调度会制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落实,关键在基层部门的落实,为此,教育部等在各项文件中都强调省市在信息化水平评价中的责任,各省市也围绕此制定系列评价标准,并开展常规性的评价工作。从2006年开始,浙江(2006)、河北(2011)、广东(2011)、山西(2013)、安徽(2014)、江西(2016)、辽宁(2016)等都制定了详细可行的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标准。
根据中国知网文献可视化分析发现,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研究进程与政策推进相对一致。在2007年以前,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主要是借鉴国外经验、政策解读等。随着评价的不断深入,2007—2010年,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等方面,表现在实证研究中,更多的是在于揭示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的现状。2010年到2013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信息化评价开始转向优质与均衡取向的评价。2013年到2016年,信息技术在这一时间内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发展,数字学习也成为当时的研究热点。数字学习反映在学校教育中,主要领域是相对微观层面的教育教学,这一时期,针对个体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内容开始出现,研究信息化中“评估的教与学内容是什么”“如何开展教与学的评估”,以及“为谁评估”等问题,以实现个体教与学的效益最大化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2016年之后,我国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渐完成了发展的起步阶段,如何在继续完善教育信息技术基础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育信息化质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赶超国外教育信息化发展,成为研究者的愿景,表现在研究中,“变革”“挑战”等成了关键词汇,中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侧重点逐渐向优质、公平、人文等方向转型。
二、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分类
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必然带来三个问题:谁来评价、评价什么、评价结果如何应用。围绕以上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评价分类。
谁来评价方面,主要集中在国家、地方和第三方三个方面。在我国,国家层面主要是教育部,通过政策规定和委托机构对各地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第三方机构,主要是承接和从事全国性质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地方,包括省、市、县,是信息化评价的主要执行者,各地以省级为单位编制相应评价标准,制定评价计划,开展常规性评估,市、县进行具体的评价工作。作为实际执行者的学校,一般不会主动制定信息化评价标准,而是根据已有的标准进行建设、对照、调整等。整体看来,所有主体开展的评价都离不开教育质量的提升问题,但是在国家和地市层面,还有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在实践和研究中,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从2013年开始,每年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建设水平以及应用现状,发放相应的全国调研问卷,对全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发布了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有关的评估机构,也适时发表相应的调查报告,特别是2005年发表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状况的调查研究》,基本上确定了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评价基本指标体系。[1][2]
宣小红等以育人为本的视角设计了评价问卷,并通过对3省市215所学校进行了评价指标的验证。[3]张屹等采取应用水平、人才培养、资源建设、环境建设、管理、保障体制六维度设计评价指标,使用问卷调查法进行了X省信息化水平研究,提出了对中小学教师信息化应用水平影响较大的是教师对应用信息化的态度、电子备课的能力。[4]吴砥教授等对我国中部地区5省开展教育信息化水平研究,发现各省之间,数字资源整体差异较大,绝大部分中小学校未建有校本资源库,且优质数字资源与教材配套情况较差;省会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远高于一般地市,省域内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差异明显。[5]董爱智等结合河北省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实际,利用SWOT分析框架分析了河北省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提出了优化河北省信息化发展布局的建议。[6]赵欣等对辽宁与全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相比较,提出了加大投入、队伍建设、评估协调等应对措施。[7]
郑朝晖针对洛阳市中小学部分区(县)教育信息化调查结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提出改善条件、优质共享、加强评价的建议。[8][9]黄焱磊等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佛山市部分中小学校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了佛山市中小学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各校之间差距较大的事实。[10]同样是佛山市,岑健林等研究在印证他人成果的同时发现存在投入过剩,设备效能发挥不足的现象。[11]杜明明以浙江丽水为例,提出基础教育资源存在校本和校际两种循环,校内发挥设备效益,校际加强资源共享和流动。[12]张立国等通过对信息化建设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信息化教学创新的关注点逐步转向学生和学习,实践的边界由学校逐步向校外拓展,但也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难题。[13]
就评价什么内容而言,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主要是在借鉴国外评价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实际,设计出相应的标准。因此,研究者简单回顾一下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启动了教育信息化评估指标项目,指标体系的内容涵盖政策(内含7小项)、信息化基础设施及其可用性(内含9小项)、信息技术课程(内含6小项)、教学与教学支持(内含6小项)、学习过程与成果(内含5小项)等5个方面。[14]该指标体系基本成为后来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基本依据。“信息和传达技术”(ICT)教育则根据其信息化教育目的和特征,提出了课程整合情况,课程教学情况,规划及举措,生机比,网络、多媒体系统的分布情况,学校连接互联网情况,不同学科所用教育软件,教师对ICT应用的自信及专业发展,信息素养水平,管理者的专业能力等。这一指标被更多的研究者使用。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的STAR评估量表,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网络连通性、教师专业发展、数字教育资源、学生成绩。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评价内容,经常被我们国家借鉴使用,但是借鉴最多的还是以上3个量表。
在我国,由于评价内容主要是由教育部来制定,各省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所以评价的内容相对是一致的,评价的内容涵盖以软硬件为主要特征的环境支持、教育资源的来源和存量、资源的使用以及使用效果几个方面。一些学者进一步总结出了六要素:基础设施、教师专业发展、数字教育资源、学生成绩、学校信息化领导能力和社区参与度。
相对来说,评价结果的使用就相对比较单一,对我国来说,主要用于考核评价,作为单位的绩效考核内容和未来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在此不再详细分类。
三、研究方法
李枞枞研究发现,研究方法对于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具有敏感性[15],因此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对于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评价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个研究方法中,有一些是通用的研究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法、调查法等,并已延伸出使用NVivo、Citespace等软件进行文献分析。当然通过编码和最基础的Excel也可以完成相对复杂的文献分析。一般来说,采用这些研究方法的,主要集中在对于教育信息化的最基本的描述统计方面,较为高级的是通过对词源、词频等分析,梳理研究的主题、热点、前沿等等。比如,于晓丽通过Citespace分析,得出了乡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当强化公平研究、队伍建设研究、跨领域合作研究和研究方法的研究。[16]
在构建评价指标和分析指标的过程中,一些复杂的研究方法开始出现,比如基于博弈论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法、差异系数法、层次分析法、CRITIC法、组合评价等综合评价方法开展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利用回归分析法探索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李葆萍博士通过对我国2001—2010年10年来基础教育信息化主要建设指标进行整理分析,编制了包含投入均衡、基础设施建设均衡、应用水平均衡、人才培养均衡4项一级指标和24项二级指标,并发现我国城乡间在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多个指标间存在较大差距。[17]周自波等也发现了相关研究结论。[18]刘成新教授等以山东省“十五”期间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为例,从基础教育信息化硬件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山东省城乡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城乡基础教育信息化硬件资源配置情况存在明显差异。[19]一些学者针对城乡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思考。其中,熊才平教授等认为城乡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普遍将关注焦点放在城市重点中小学校;信息化建设仍然以基础设施为重点内容,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思路较落后,停留在传统资源建设思路上。[20]
祝智庭等从视角、发展、角色等不同维度建立三维评估模型[21];焦宝聪教授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对调研学校按照其工作效率进行综合排序[22]。张进宝副教授构建CIPO模型,分析了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效率[23],仍然是以提高教育信息化工作效率为目标。解月光教授等构建了效率评估模型,专门针对农村中小学校信息化发展设计了指标体系。[24]结合综合评价理论其他相关文献,对现有教育信息化评估方法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归纳和总结,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研究方法比较
四、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
指标体系是整个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和热点。与国外相对偏向微观的指标体系相比,我国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研究,主要偏向于宏观,在内容上差别不大。
2005年,中央电教馆给出了设施、资源、素养、管理、应用5个一级指标,下设26个二级指标,从而为我国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设置了大致框架,并使用该评价指标对我国中小学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评价,这是一种宏观的基于国家层面的评价,后来的各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都有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子。2017年,复旦大学牵头制定了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基础应用、教育科研信息化、管理信息化和信息化保障体系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和72个三级指标。
曹卫真教授从成功案例的共性出发,提出了构建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化评估指标的原则和依据,指出了中小学校信息化评估指标的设计思路。[25]黄晓(组织管理、信息化环境建设、信息化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5个评价维度)[26],杨军(基础设施、软件平台、教学环境、教学资源、管理机制、教师队伍6个一级指标)[27],高吉草[28]、肖玉敏(环境、管理、教学、发展)[29],蔡亲鹏(重视程度、队伍、资源、资源、应用等)[30],吴琼[31]等,都给出了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但是无论何种指标体系,基本都是围绕条件、队伍、资源、效果等开展。
在实践中,信息化水平评估的指标也是如此。以河南省为例,包括设施应用、信息技术应用、教师队伍、信息安全等方面,这一点其他省份也是如此。
由于各个指标在整个信息化建设中的地位不同,研究者还经常给与指标赋权。例如,通过采用德尔菲—模糊绩效评价模型,谢幼如教授等确定了教育技术工程绩效评价中的指标权重,同时解决了评估过程中需要定性考虑的问题。[32]杨军运用模糊聚类分析、集值迭代等方法构建了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33]利用灰色区间熵权法,孙德梅等建立了灰色区间关联评价模型,用于评估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34]
五、讨论与思考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研究,已经在框架指标、实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相对国外的有关研究,我们还存在着以下明显问题。
一是研究和实践相对偏重于宏观。由于我国中小学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一直处于基础建设阶段,所以设备的投入、人员素养的养成,也自然成为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从信息化建设发展的阶段来说,前期重视硬件和基础条件,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很难进入到信息建设的教育内涵部分,这必然造成与国外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正是基于该考虑,教育信息化2.0才提出了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事实上,在国外的一些研究和实践中,我们也早就发现,教育信息化的研究和实践已经从硬件、软件、资源等这些外围因素,转向课堂、教学、师生关系这些教育内核因素。[35]Ertmer发现,教师领导力与教育信息化效果呈正相关,提高教师的TPAC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能力,有助于改善教师的信息化领导能力。Tsai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教师的创造力和设计思维,是提高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未来的教育信息化,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是关键。一些研究者更是关注到了性别在教育信息化使用中产生的不同影响,并提出设计基于不同性别的教育信息化使用方式。Aoki更是发现教育信息化存在所有的资源效益阶梯模型,在该模型看来,信息化的硬件建设并不会直接产生明显的收益,只有到了一定的积累和规模,信息化投入才会产生爆发式的收益。教育信息化,本质是教育,而非信息化。在不断加大投入,改善信息化软硬件条件的同时,对于教育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研究,特别是基于课堂、教学、课程、师生关系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加强。
二是研究上过于以“政策演进”为中心。按照时间顺序推演,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的有关研究,都是围绕着政策的发布而开展的。围绕政策去开展信息化评价,自然有其道理,符合党和国家办教育的基本方略。但是党和国家对教育信息化评价的要求,从来都不是教条式的,都是要求在不违背教育为了人民的立场上,开展丰富多样的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上,更应当是提出个人的观点,甚至是百家争鸣也不为过。但是目前已有的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过于偏重政策了。政策不同于教育信息化自身发展的学术脉络,它的产生既有基于客观事实的时间探讨,也有基于教育内在机理的回应,但是更多的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博弈最终达成平衡的结果。因此,任何政策,必然是一种“均衡”,内容必然是“全面”,发展也必然要求“结果”。在这一思维模式下,所有的研究都容易陷入大而全的困境,看似面面俱到,却难以深入。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宏观政策,基本上二三年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而学术研究的周期一般都是10年以上,特别是在微观上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导致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像在原地画圆,一直无法深入教育本身。因此,未来的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在研究信息化硬软件与教育发展关系,投入多少、多大规格的硬件资源已达到教育信息化的规模效应时,就要回归教育本身,去分析教育信息化是如何影响教育教学方式、如何改变师生关系等等。
三是研究的理论基础不足。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在评价领域的反映,不同的价值理念,评价的方式各不相同。已有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中,基本都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评价思维方式。其中,一部分学者默认为教育是成本最大化的组织,教育的目的是追求最大的产出价值,至于投入多少,或者用经济学的视角去考量成本收益比值,并在它们的考虑之内。基于这种观点,所有的评价体系指标基本都是面面俱到的,基本都是硬件、软件、资源、应用、保障等内容。但是以上内容,他们的度量标准并不一致,一些不可度量的指标,比如只能用语言描述的定性内容,即使在可测量的指标中,他们的测量单位也千差万别,这很难在未来的计算中进行统一计量,最终导致整个评价要么是生硬的拼凑,要么难以具备参考和使用价值。成本收益视角作为一种经济学分析方式,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作为教育,是以人为立场的,它具有价值,内在要求需要从一种理论基础去设计教育信息化的测量标准、指标。而这些目前是整个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中相对缺乏的部分。
基于以上考虑,研究者认为,未来在加强宏观研究的同时,政策上,要为教育信息化走进课堂创设软硬件条件和文化环境,研究也应当主动走向课堂。同时应当加强研究理论基础的建设,不断深化教育信息化的评价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