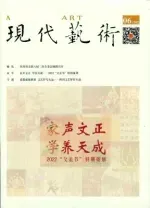我心中的传承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民族,姓氏和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最具核心意义的文化,“家”是人之于这个世界的出处,也会是人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留言,这个留言就是“传承”。“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在我看来,“传承”是家族文化的核心,但其所传承的并非财富、名望,而是通过言传身教、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气质、道德品质、审美格调的家族风貌,是给后辈树立的价值准则,也就是“家风”。
每个人都来自多个家族的组合,我也不例外,我的祖父出自川南乡绅家族,民国时期祖父曾在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图工科”,后长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并坚持绘画。我的祖母出自川南革命家庭,民国时期她的寡母带着年仅14岁的祖母,在乡村开设私塾,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祖母又前往师范學校进修,也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我的外祖父是解放军南下干部,我的外祖母曾是大学生地下党员,解放后他们由组织介绍组合为家庭,外祖母也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因此我的家庭氛围是严肃而浪漫的,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同时也注重人的自由与天性,我就是在这样的“家风”中长大的。
当然对我的职业选择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父亲。因为曾祖父习画的缘故,我的父亲也从小习画,这为他能在文革后期考入四川美院奠定了基础。后来父亲不仅继续坚持绘画,又在西南大学(当时叫西南师范大学)学习了中文,我出生后,他又前往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了文艺理论。他不断扩宽专业广度、加深学术厚度的行为,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从小也喜欢艺术,不仅是创作本身,对于艺术欣赏、艺术活动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我的学术背景是艺术学,后又对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传播与交流等领域有过兴趣,对视觉艺术设计也曾有所涉猎。而我现在所从事的策展人工作,是艺术行业中最“泛”的工作,需要承担展览的学术定位、策划与实施等诸多职能,这一岗位与艺术家不同,更注重在创意、研究的基础上有足够的落地能力,同时也需要与艺术家、观众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策展人也从来不是个体的创作,他需要仰仗于整个工作团队的并肩作战。因此我常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博览的人,要对所有未知的领域保持好奇和学习的动力,这或许是父亲传承给我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除了博览,父亲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他从事过很多领域的工作,但都围绕艺术与文化展开,他的职业选择几乎与金钱无关,更多的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在我几次重要的人生抉择时,他都会鼓励我遵照内心而非关乎外物的限制,他常说他可以做我的退路和靠山,这让我能以更坚定的信念去做出更独立的选择。但其实父亲从不干涉我的发展,也不会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对我进行“规劝”。我们常常保持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互相为对方的艺术事业指出不足、提供建议,甚至互相交流对当下热点问题的态度和见解。独立清醒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是父亲传承给我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我所感受到的“家风”是丰富的,所传承的不是族谱中的家训,也不是祠堂上的警句,而是长辈用他们的人生,为我书写的生命灯塔。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或许会有非常多的选择,得失取舍全在一念之间,而此般家风,将为我每一次的抉择、每一次的迷茫指引方向。
对 话
M=现代艺术 F=曹念 D=曹筝琪娜
M:请问您的艺术启蒙源自于谁?您的父母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F:我的艺术启蒙来自我的父亲。他是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最后一届毕业生,据说学校任教的老师是当年四川省最优秀的艺术教师群。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父亲也学成毕业,回到老家后,他从一个老乡绅家庭走出来,投身乡村教育工作。他的时代,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但无论周遭如何变化,他从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在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带我们去田地里挖泥巴,教我们做泥塑;带我们在乡间写生,画农民劳作和田园风光。五岁时,我画了一些轮船、飞机以及乡村田间的画,父亲把这些稚嫩的画作贴在学校的墙上,办了我最早的“画展”。从此,艺术的种子在我心中开始生根发芽。文革初始,他突然把珍藏了多年的书画作品拿给我(有他读书时的任教老师罗文谟、钟道泉、周伦园、张采芹及一些书法家的作品),让我偷偷地、认真地看了两天,然后便把这些画烧了,让我至今十分惋惜遗憾。但是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父亲还专门给我讲,做人不能做那样的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母亲的先祖是四川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龙鸣剑,外婆是荣县有名的中共老党员,因此母亲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父母亲的相爱在当时是十分不易的。母亲本来是组织培养的优秀苗子,因为坚持自己的婚姻选择,放弃了城镇中心校校长的职务,跟随父亲到偏远的乡村从事平民教育,直到退休。他们对事业的坚守、对爱情的选择、对家庭的付出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
M:您的子女和您的创作差距大吗?能谈谈她的“继承”和“反叛”分别是什么吗?
F:在文艺评论创作中,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问题发生分歧(主要是我不懂当代艺术)。至于“继承”和“反叛”,倒也没有特别突出的体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只要她行进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有想法是好事。并且她对当代艺术进行探索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传统艺术的研究。而就所从事的工作而言,她的“策展”和我的“策划”虽有差别,但也能经常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M:在您的眼中,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他在从艺和为人方面都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D: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杂家”,他在绘画、文艺评论、视觉设计、工艺美术、策划、文史研究等很多方面都有所涉猎,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他还非常“新潮”,无论是9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还是现在的微信公众号或新媒体技术,他都乐于尝试,并能有效用于自我的“输出”。从小,父亲就有意培养我对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兴趣,他陪伴我参观了上千座博物馆和美术馆,为我今天的职业选择奠定了基础。还在高中时期,他就有意地引导我学会了PS等设计软件,后来又鼓励我用开放的态度去探究各种学科,大学时期在艺术学科之外我还喜欢人类学和民族学,他就尽可能支持我去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后他也鼓励我不要只专注于工作所划定的方向,业余时间我们会共同打理研究地方文化的公众号,还一起对自贡桓侯宫进行了调研并形成专著。他的这些态度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能在学习和生活中,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并做出行动。
M:您认为“家学”是什么?您将如何传承和弘扬?
D:在我看来,家学是一种氛围,是对人生和所从事的职业所持有的态度。我记得小时候,爷爷就经常教导我要尊重知识,还给我讲过“字纸篓”的由来,和“焚字塔”的意义,以此来传递家中对文字的尊重。再大一点,就经常看到爷爷将全年的《美术报》《书画报》等装订成册,并妥善编目存放。而父亲更是爱书如命,家中存书足有上万册,以至于儿时的我以为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一面墙是存放书籍的。但是无论是爷爷还是父亲,从未要求我必须从事艺术行业,也从未对我所阅读的书籍内容有所要求,父亲常说阅读可以只“随便翻翻”,但要用一生去做这样的功课。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影响下,我一直把“博观而约取”作为我的治学态度,我也相信,只有广见博识,才能取其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