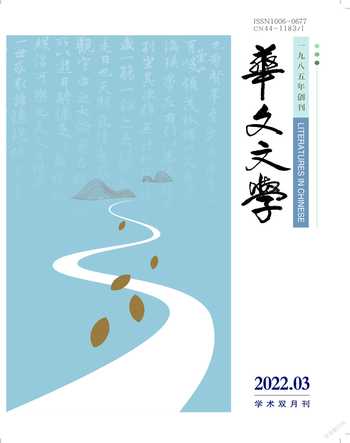并非只有“时差”的香港新文学:《铁马》综论
王芳
摘要:香港新文学与大陆文坛之间仅有“十年时差”已成定论,这种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香港文学的在地性。通过《铁马》几位作者的回忆,可见在香港真正引起回声的不是鲁迅,反而是胡适的白话文论点,这与香港的殖民地境遇息息相关,同时,此时香港新文艺界的都市趣味决定了他们主动关注和接收的是上海带有都市气息的文化辐射。此外,本文具体探讨了《铁马》和《岛上》刊物无法维持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亦关注到《铁马》“咖啡店”栏目中一直被目为“宣言”的文章,其实呈现的是一种大陆和香港文化的错位和混杂。
关键词:香港;《铁马》;新文学;胡适;上海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005-09
一般认为,1927年鲁迅来港作《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之后,新文化和新文学在香港生根萌芽,虽相较大陆文坛有十年“时差”,但亦成功拓荒。这种论述以大陆文坛为中心,关注到中国文学的整体性,香港文坛和大陆文坛的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香港文学的在地性。事实上,在抗战全面爆发、大量文人作家南下之前,新文学在香港始终是边缘的,鲁迅演讲的影响力不可高估;在香港真正引起回声的反而是胡适的论点及其到来,这与香港文化环境有关。
《铁马》等诞生的政治文化土壤与大陆差异颇大,作者们面对的现实情况也不同,本文着重考察“岛上社”成员的经历背景,结识情况等,以串联起《伴侣》《铁马》《岛上》等刊物,赋予“岛上社”的文学活动一个整体面目,并将其置于香港文化整体状况之中。另一方面,通过《铁马》几位作者的回忆,也可见当时香港新文艺界主动关注和接收上海的文化辐射,两者在生活方式、人员往来、文学生产、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
本文探讨了《铁马》和《岛上》刊物无法维持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同时,关注《铁马》“咖啡店”栏目中一直被目为“宣言”的文章,其实不能很好匹配香港文艺青年的心声,反而呈现一种文化错位和混杂。值得一提的是,《铁马》中的插图多由侣伦绘制,与每篇作品相配合,颇为用心精美。
一、《铁马》的出版环境与失败原因
1928年后,香港出现新文学萌芽,新文学期刊《伴侣杂志》出版①,张吻冰和侣伦等是刊物的主要作者②。1929年1月《伴侣》停刊后,其主要作者创办了“岛上社”,随后“岛上”成员之一的张吻冰主编杂志《铁马》,只出一期即停刊(1929年9月)。侣伦在回忆中叙述了此事:“《铁马》是岛上社最早主办的一种文艺期刊,原来张吻冰是香港青年会日校校友会会员,因他的关系,该会学艺部答应帮助岛上社出版《铁马》,但负担以出版一期费用为限,由张吻冰负责编辑。《铁马》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第一期印了二千册,岛上社打算将第一期出版后的收入,用来维持继续出版下去,但所得的收入,用来支付出版第二期的费用,距离很远,所以《铁马》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现存该刊第一卷第一期当时定价每册一角五分,全期共一○四页。”③此后“岛上社”成员又出版了两期《岛上》杂志④。
与此前大报的文艺副刊相比,《铁马》是同人性质的刊物,虽然只出了一期,但因为被视为“青年宣言”,有研究者认为其重要程度超过了被称为“新文学第一燕”的《伴侣》。譬如《铁马》中侣伦的小说《炉边》,揭示了香港本土青年作者写文章讨生活的不易,以及背后发表机制的原因。香港青年作家提倡的“新文艺”,直接对抗的是香港社会的“万皆庸俗”,以及作為资本家的报社对青年作者的压迫剥削,“香港有了算盘是因了做生意,香港有了笔墨也因了做生意的!”这与“五四”新文学初期着重批判封建思想观念不同,提示二者并非只有“时差”。
1. “国语文学也该统一”:香港新文学艰难的第一步
要理解《铁马》等刊物所处的环境,首先需要了解此时香港的人口构成结构,受教育水平,学校设置,知识分子群体思想风貌等基本状况。早期香港文化人主要是南下的清朝遗老遗少,他们以香港为“净土”保存国粹,对1920、1930年代的大陆文化充满敌意,“卫道之心如此坚决,构成其排拒或自别于内地政治、文化情境的心态。”⑤《铁马》诸人面对的“旧文坛”和“旧文化”状况也与大陆不尽相同,一方面香港传统文化或曰“国粹”仍占据文化主流地位,同时,港英政府对新思想的警惕,使得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提倡始终处于弱势,“在英中二国旧士的旧势力相互结合下,导致新文化不能兴起的局面,纵有驱新者鼓吹新文学,又或者是虽然有个别人士有文学觉醒,但始终难以引起社会回响。……香港的文学气氛转变,并不是随着鲁迅南下讲学发生变化。”⑥迟至1935年胡适来港才引起了较大的回响。
的确,种种资料显示,是胡适而非鲁迅(包括他们的主张),引起了香港文化界较大的“回声”。平可回忆自己的“受窘经验”,“有一次一位在教育界很有地位的老先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我是台下听众之一。他大骂胡适之,说胡氏改革文学的建议简直是胡说。又说胡氏散播胡言毒害青年,是个大逆不道的人……他在结论中说:提倡白话文的人是以‘夷为师,跟认贼作父差不多。他的演说赢得全场掌声。”而“我”则没有勇气站起来斥责他。⑦另一个例子是在宴会上一位“热心公益的长辈”诋毁白话文,“我”也不便反驳,可见像平可这样认同白话文的人始终是小众,而冲突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即“白话”还是“文言”,尚未触及思想层面。
同样,《铁马》编者提倡的是“国语文学也该统一起来”⑧,可见“国语文学”才是他们此时关心的问题。“五四”新文化的第一步在香港尚未迈出,鲁迅的思想革命更无从说起,“香港社会对鲁迅的话并无反应。文化教育界的重心人物只把鲁迅的话视作离经叛道者的例行怪论,不屑反驳。他们深信‘见怪不怪,其怪自毙的道理。因此,‘无声的香港依旧是‘无声的香港。”⑨没有双簧信的新文化倡议,在香港落入无声。
不仅没有“双簧信”,也没有“北京大学”,此时香港的学校教育不能为国语文学提供助力,“早期香港没有知识群体”,1920年代的香港,只有一所大学,就是“不重视中国文史的殖民地大学”——香港大学,“1927年的港大中文系是纳入政府制度的现代学术机构,然而其所授科目并未与时俱进,还是传授旧式经史、辞章学科。”⑩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中缺少新文艺新文学的位置,也是导致新文学写作和阅读群体增长缓慢的原因。EFF0A64C-8A90-4699-AE8A-3AC9FB0C644B
2. 大报副刊与同人刊物:受众与《铁马》停刊的逻辑
陈学然认为,《铁马》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编辑作者大多从大陆来港,他们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更体现出民族情感,寄望政治统一、经济统一、国语统一,这可能是“港英政府和旧派绅商、翰林学士对新文学更为警惕的原因,致使新文学在香港难以开花结果”{11}。这当然是新文学第一步都难以迈好的深层原因,至于直接原因,则侣伦和平可等的回忆的更为现实,也更为寂寞。
赵稀方在《报刊香港》中通过侣伦和平可(卓云)的回忆,从书店、报纸副刊等角度关注了彼时新文学在香港的生长土壤。平可自述,1925年省港大罢工是香港青年精神生活的转折点,此后,他在萃文书坊买了很多新文学书籍,如“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华盖集》,郭沫若的《星空》《女神》《落叶》,郁达夫的《沉沦》,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的一夜》,汪静之的《蕙的风》,穆时英的《南北极》等等。”{12}而1927年后尽管香港报业的主流依然是较为守旧的《循环日报》和《华字日报》,但也出现了很多刊载新文学作品的报纸副刊,“若干小规模的报纸已辟专栏刊登用白话文写的作品,并采用标点符号”了,平可着重提及《香江晚报》,他的第一篇白话文作品就是在《香江晚报》副刊上发表的,而据侣伦回忆,“1927年前后,香港新文学开始滋长,表现是本地报刊新文艺副刊的出现,这些报刊有《大光报·大光文艺》《循环日报·灯塔》《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南强日报·华岳》《南华日报·南华文艺》和《天南日报·明灯》。”{13}香港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较为保守,市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新文学读者群体并不大,但大报副刊之增多,一方面鼓励青年们写作投稿,一方面也在培养读者的阅读趣味。
《铁马》的出现,就是新文学青年作者数量增加,要求有更多的发表园地,试图在大报副刊之外辟出更为自由发声的园地,靠售卖刊物生存下去的尝试。据侣伦说:“不管《铁马》的文艺气息如何比过去的《伴侣》更纯粹(至少是没有后者的商业气味),但是在当日香港的文化环境,差不多读文章的人就是写文章的人的情形,杂志的销路是说不上的。当然杂志是卖去了一部分,可是能够收回的钱却与一期印刷费的数目相差很远。”{14}的确,相较此前《伴侣杂志》的定位还是家庭读物,有服饰、家装等栏目,《铁马》的的确确是纯文学刊物,受众寡少是必然的,这也是文艺青年们面对的“无物之阵”。
不过,当年侣伦在《铁马》上发表的《炉边》一文并没有涉及读者群体的问题,主要是描画被大报报社把持的恶劣发表环境。他借主人公之口分析青年作者难以安身立命的原因,一方面他投稿给大报,理论上就有可能靠笔养活自己和妻子,说明并不缺少发表园地,但另一方面却必须面对大报无故拖欠稿酬,发表机制的不公平,充满了无助和无奈:“本来照当地这么众多的报馆看来,靠笔墨去找点饭吃,也并不是困难的事。而以这样众多的报馆每月发出的稿费,扯均来给养就算更多的穷作者,也是在可能内的。然而现实却偏不如此。当地上穷作者并不少数,靠着笔来偿他们无了期的稿酬的计算起来,怕有惊人的结果。然而所谓发表地盘的,多数却给少数人占去了。那些和主编者像有什么关系的自然登得劲,就那些善于巴结逢迎的也只要能够写两句字出来,今天写,明天便可以刊登。於是那穷的,无法巴结的,越是没落了。这样,他便时常陷到极危险的境地,吃面包多于吃饭,有时竟连面包也吃不成。这是个普遍的现象,也许不少穷作者都同遭厄运,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只好化几个署名分投到各报纸去,一个月才勉强捱得过去。”{15}乃至像小说结尾那样,“我”辛辛苦苦写就的稿子飘进了编辑的火炉,后者却毫不在意,毕竟一大堆稿子在手上,看都看不过来,少了一份又有什么要紧呢,全然没有想到这意味着青年的心血和生计——在新文学作者看来,这是庸俗而缺少理想的资本家对自己一群的压迫。
大报副刊把持文坛,青年作者寸步难行,侣伦的《炉边》痛诉了文艺青年们办《铁马》等刊物的现实动因,却不能解释《铁马》《岛上》创办后又为何“短命”。事实上,大报的倨傲态度也是与新文学读者群狭窄相辅相成的,前者吃定了作者们无以自立——和大报开辟刊载新文学的副刊不同,大报有稳定的读者群和收入,增加新文学副刊不过是收揽一个新的读者群,即使是暂时“养着”副刊,也并无太大损失,而作为缺少资金支持的同人刊物,《铁马》《岛上》等只刊登新文学,完全依靠小众的读者群支持,很难汇集资金,支撑刊物运转。
根据侣伦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类似的同人刊物想要存活下去,不能靠售卖所得,必须寻找赞助人,日后《岛上》的出版就是例子。在《铁马》失败后,“岛上社”成员并不死心,“事情既然开了头,总是要继续搞下去才舒服”,于是自费出版《岛上》,百般筹措印刷费,1930年4月终于如愿,不过,“杂志名称虽然不同,香港还是那样一个香港;因此,《岛上》的命运决不会比《铁马》好多少。第二期的稿件虽然集好了,却没有办法付印。”还是资金问题,不过这一次卓云在香港精武體育会遇到了爱好文学的高级职员林君选,“知道《岛上》要继续出版的困难,慨然的表示愿意支持”,林君选担了“社长”的名号,还将《岛上》的稿子带到上海去印制,于是1931年《岛上》第二期得以面世,“杂志本身不但印刷得好,而且篇幅还增加了四十多页”。侣伦觉得,如果没有遇到什么别的问题,《岛上》是可以继续办下去的,不幸的是,“九·一八”接着来了{16},这一切也就戛然而止。
二、香港与上海:文化辐射、
都会想象和文学生产
平可1985年在《香港文学》里说:“用现在香港人的眼光去看二十年代的香港,当时的香港只是个中等规模的都市,人口只有几十万。”{17}此时的香港尚未具有世界港口的规模和地位,港人在心理上未将自己视为独特的一群,学习和就业也考虑大陆的广阔可能性,譬如,平可当时就读偏重英文的育才书社,被戏称为“番书仔”,社会大众普遍更重视中文,考虑的就是去大陆就业的可能,“半途退学的学生很多,这个现象跟当时的环境和风气有关。一般家长有如下的观念:中国人必须通晓中文,不通中文无以立身处世,至于英文,它只是谋生的一种工具,诚然可贵,但可容中国人谋生的区域很大,不限于香港。比方说,中国人可自由来往香港和中国大陆,青年人将在何处生根是不可料的。”{18}这种观点也并非多么“爱国”,不过是出于谋生和实用的考虑,因为在第五篇回忆中,平可就叙述了当时香港的另一种风气:“当时的香港社会迷信什么都是英国第一,包括教育在内。香港所培植的学生,虽稍逊英国本土的,也必胜于其他国家。”{19}以英国教育为最优,又以扩大谋生区域为考量学中文{20},恐怕是彼时香港种种矛盾心理之一种。EFF0A64C-8A90-4699-AE8A-3AC9FB0C644B
这一矛盾心理也体现在对大陆文化的接受上,当时香港人自觉接受大陆文化的辐射是以上海为首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者1920年代末与巴黎等相似的浪漫大都市风貌引发了在港青年的憧憬,“黄:……二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仍是相当保守,居民当中大部分是华南式教育程度很低的本地小市民,另一小部分上层的知识份子,他们从国内流亡到香港的。香港自太平天国开始至中华民国前后,一直都是收留遗民、流亡份子的地方,香港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成份,很难在上层知识份子中找到一些支持新思想的人。因此多只由青年吸收一些新思想。由于年青人不一定有丰厚的学识,所以也不能与中国大陆真正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接上。当时的文艺青年未必充分理解鲁迅来港的意义,却可能从上海、广州、等地接触到带有浪漫、感伤色彩的作品,从而引发青年人朦胧的憧憬及理想,于是带起香港新文学的开端。卢:这一点肯定是的。因为鲁迅来港,只作了两场演讲,逗留时间不长,而且有听众甚至听不懂他的话,靠许广平来翻译;所以来港的影响力虽然可能很深远,但在当时来说,却不是立即可以引发出火花。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那群爱好新文学的年轻人在摸索中,才开始接触到上海大都市浪漫式的都市文化,如看到上海的杂志等。谢晨光先生便觉得,他虽然自己在香港办刊物,但总要向上海的杂志投稿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身份,才觉得威风。又如侣伦先生最早发表的小说便是由叶灵凤在上海编的杂志上刊登,他们的订交也源于此。因此,我觉得黄先生说得对,大部份喜欢文学的年轻人,不喜欢传统八股一类的文学;而他们最容易接触到,或者说他们最向往的,是与香港这殖民地都市风貌近似的大上海。”{21}这一判断值得重视,的确,对于香港的文艺青年来说,鲁迅的思想还是过于艰深,能够引发他们的共鸣的,是兼具“唯美”与“愤怒”的海派文艺风格。
如陈子善指出的,上海文化对于香港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其都市形态,也因为大陆文坛本身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刊物中心也都挪至此处,吸引了香港青年的投稿:“随着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相继定居上海,随语丝派、创造社、新月派等新文学社团相继以上海为活动据点,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上海已经取代北京成为新文学活动的中心。因此当时香港一些在新文学创作上摸索前行的年青作家从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吸取营养,向上海的文学刊物踊跃投稿,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22}侣伦回忆:“《铁马》是卅二开本的小型杂志,一百页,文字横排,毛边;形式和风格多少是受着当时上海出版的《幻洲》杂志的影响。”{23}侣伦和谢晨光在《铁马》上刊稿之前已经颇有成果了,他们的作品最早都是在上海新文学刊物上发表。{24}陈子善具体列出了谢晨光1927年5月到1931年10月在《幻洲》《现代小说》等上海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并且说明谢晨光作品的风格与叶灵凤所编《幻洲》的上部“象牙之塔”非常契合:“《幻洲》半月刊由叶灵凤、潘汉年合编……上部‘象牙之塔专刊小说、散文和诗,唯美色彩浓厚,由叶灵凤负责;下部‘十字街头专刊杂文和文化评论,观点激烈,措辞尖锐,由潘汉年负责,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谢晨光的小说当然都是在‘象牙之塔刊出的。”{25}有此前情,我们会发现刊载在《铁马》和《岛上》的谢晨光作品,如《尽献》(散文)、翻译的诗歌《入梦》(诗)和《去国之前》(散文)等,“唯美色彩浓厚”,也是一以贯之,血脉有自的。
文学风格而外,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也具有召唤性。谢晨光在1930年《岛上》发表的《去国之前》中说到自己一群的生活,“和思源,我们就爱在剧院中和咖啡座中消磨岁月……”{26}《铁马》最末,编者(应该是张吻冰)的话透露出他对大都市小资生活的向往:“在香港,慢些说及文艺罢,真没有东西可以说是适合我们这一群的脾胃的,有许多应该是很艺术的地方都统统给流俗化了;小之则如咖啡店,你想在薄寒的晚上,一个儿坐在咖啡店的角落,喝罢了娉婷的女侍们端来的绿酒,靠了椅优游的吸着纸烟,瓦斯墙灯的朦胧光线底下,斜睨着曳了阔裙随着简单的乐声,轻盈慢舞的舞姬们的旋影,听听窗外夜游者们的渐去渐远的歌声,一直到疲倦的夜阑,才又一个儿的拖了外褸,穿了消沉的石街,酡了醉颜,归途中带着写不出来的诗意,你想领略这些情味,在这样的充盈了立体方形的建筑物和烟突与汽车的香港,就唯有永远的失望着的……‘贫穷点又算什么呢?如果能够有酒钱,能够住在巴黎的Latin Quarter!”{27}这一时期居于香港的青年们亲近新文艺,其写作冲动的根底还是在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且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殖民性并无察觉。
也难怪《铁马》的闲谈栏目定名为“咖啡店”。作为西洋公共生活方式代表的咖啡馆,对于彼时的国人而言新且有符号意味,况且在当时的中国大概只有租界中才常见,更带上一种殖民色彩,鲁迅在到上海之前从未提及过咖啡馆,到了上海后,咖啡馆成了他眼中上海青年作家生活方式和创作的一种符号。不过香港的这一班青年似乎从没有用这么沉重的文化眼光看待咖啡馆,后者已经自然成为青年们相聚相谈的地方,岛上生活方式的某种必然,和茶馆之于北平类似。平可回忆他们这群文艺青年的交往情况,也提到了在咖啡室聊天是常态:“我们一群青少年,包括谢晨光、侣伦、张吻冰、陈灵谷、麦思源、黄显骧、刘火子,常常相约去咖啡室聚谈。参与者有时数人,有时十余人。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算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不过,大家的共同兴趣毕竟是文艺,所以文艺始终是主要话题。每经一次聚谈,大家都晓得谁最近读过什么书籍刊物,写过什么文章,向什么报刊投过稿,等等。”{28}侣伦在《炉边》的开头写道:“普亚街是冷静极了。在夏天,这街上还有不少店户的伙计们在门口纳凉,或铺了席子在门边露宿。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听见他们像牧童的山歌对答似地,你来我往的打牙花。或者一班班从咖啡店,茶室的半掩着的门户出来,归家去的女侍,走过街心时,伙计们向她们调笑的声音,遥遥地呼应。”{29}文中叙述者居住的普亚街居民大多贫穷,但也有咖啡馆,可见其在香港的普及。
由《铁马》的整体风貌看来,香港文艺青年并不直接言及“革命”,更接近早期创造社的主张:承认主体凭直觉追求“生存”和“唯美”的合理性。不过,即使不考虑文化审查的因素,“岛上社”内部思想趣味的参差也并非无迹可寻。1929年丘东平和陈灵谷赴上海拜访创造社和太阳社,颇有象征意味,但就目前看到的材料而言,交流似乎不及革命——当然,这也有可能回忆者有意无意的遗忘或忽略,毕竟到沪的是参加过革命的丘东平和陈灵谷,在“岛上的一群”中,他们二人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从1926年丘东平在海丰陆安师范加入共青团开始,到1935年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参加东京‘左联活动,整整十年间,除了间中几次暂时分开三几月,陈灵谷和丘东平都在一起活动:一起在海丰参加大革命,一起流亡香港成为‘岛上的一群,一起参加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30},而非在《幻洲》上发表作品的谢晨光和侣伦——目前常见的回忆材料来自侣伦:“一九二八年,小提琴家马思聪由法国学成回国,道经香港到上海去准备开演奏会,但是他对国内情形不熟悉”,因此陈灵谷和丘东平“便因同乡关系,以随行人员的身份,伴同马思聪北上,替他安排生活和登台事务。”到了上海,陈灵谷其实是自己一个人活动的,“他拜访了在上海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文艺界人士,相互联络。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由香港来的文艺界青年,我们是无名的;但是我们愿意跟前辈们学习。……这件事被当作文坛消息登在上海一本杂志上面。”侣伦和岛上社的成员也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岛上的一群在香港看到这段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高兴和鼓舞:因为‘香港文艺界青年这字眼第一次在国内的文坛消息中出现了。”{31}从侣伦的回忆来看,“香港文艺界青年”为自己一群的名号和声音出现在国内文坛感到兴奋,这种文化向心力也能够解释《铁马》编者所说的“国语文学统一”的心愿了。而2010年许翼心对陈灵谷的访谈文章是更直接的材料,对于侣伦的回忆多有纠正和补充,更透露出不同的思想质地:“在上海的筹备机构中有位叫杨邨人的左翼作家,是太阳社的(当时创造社已停止活动),他说太阳社有好几位潮州人,其中戴万平曾在海陆丰参加農民运动,是我认识的。于是杨邨人便安排我和东平到一家书店拜访太阳社,在场的除了戴平可(按:应是戴万平之误)、洪灵菲、林伯修(杜国痒(按:应是杜国庠))好几个潮州人,还有钱杏屯(按:应是钱杏邨)……当时,我还陪马思聪去拜访鲁迅先生,可惜没见到。”{32}陈灵谷的回忆纠正了侣伦的在上海陈灵谷单独活动的说法,更重要的是,陈灵谷说当时其实是想要拜访鲁迅的,而上海文坛对香港新文学的影响力不止于海派文学,还有革命文学,也由此坐实。EFF0A64C-8A90-4699-AE8A-3AC9FB0C644B
这一时期香港文艺青年阅读的书籍和刊物也大多来自上海。在平可的回忆中,作为读者的他最早通过上海的刊物《幻洲》接触到了香港作家谢晨光的作品,后来又买到了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谢晨光专集,这些回忆都可与陈子善《一瞥集》中的考证对照来看。因为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的设立,以及上海逐渐成为大陆文坛的中心,上海和香港的文化互动很多。平可自述1925年省港大罢工后精神生活大转折(平可出生于1912年,此时不过13岁左右),“齐天大圣让位给孙中山”,读书方向自然也要求变化,只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书籍,后来终于找到了“理想的读物”,即《少年杂志》和《青年杂志》,这两份刊物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3}而《青年杂志》“所介绍的小说集当然少不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其中《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内文更常被引用,但我没有办法在香港买到那两本书”,后来平可交往一位来自广州的朋友叶君,“他有一位弟弟在上海念大学,常常寄书给他”,因此从他那儿借到了鲁迅的《阿Q正传》,很快看完,但因年纪尚小,自言“对鲁迅小说的深度还未能领略”{34},不过也可见鲁迅的文坛影响力也通过上海和广州辗转至了香港。
侣伦回忆《岛上》第二期的出版是在上海完成的,即林君选带着《岛上》的稿子到了上海,为的是获得更优质的印刷条件;而在“《岛上草》胎死腹中”一节中,侣伦还谈到1929年岛上的一群本想出版一本同人合集,“但是大家都一样穷,那里来的印刷费呢?只有一个碰运气的方法:把稿件寄到上海去。……那时候,曾经是香港新文艺刊物《伴侣》主编者的张稚庐,正在上海和友人搞出版事业,并且准备开办书店。《岛上草》的稿件便寄了给他”,可惜因为篇幅太大被婉拒。对于香港的文艺青年而言,上海是一个充满名家前辈、出版机遇,更加开放包容的大都市,不仅仅是印象,更是一種文化生产的现实。
三、不能代表的“宣言”和
青年共同的心声:《铁马》“宣言”辨析
侣伦回忆:“‘岛上社没有什么组织形式;只是一群爱好文学、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结成一伙;是一种精神上的组合。这一群人中,除了谢晨光、张吻冰、岑卓云(平可)和我,是一向生活在香港之外,其余的包括谷柳在内,都是因当时国内的政治关系,从外地流亡到香港来的。”{35}《铁马》的创作者很多与大陆有联系。譬如陈灵谷是广东海陆丰人,第一次大革命后逃往香港,而卓云和侣伦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后者1927年曾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回港。
平可(即卓云)则具体描述了他和“岛上”一群主要成员的相识相交过程,他最早认识的是张吻冰,{36}平可说自己和张吻冰都是“番书仔”,因其就读学校都偏重英文,前者在育才书社念书,后者在圣约瑟书院念书,圣约瑟书院创立于1875年,是一所天主教男子学校,无怪乎张吻冰在《铁马》上发表的小说《费勒斯神父》是宗教题材。后来平可和陈灵谷成了邻居,平可只介绍了一个人给他认识,就是张吻冰。而陈灵谷则是促成平可投稿《大光报》的人,陈灵谷“是海陆丰人,因政治上的牵涉而逃难来港,他比我大两三岁,喜欢阅读新出版的书籍,我跟他很谈得来。……他开始用‘灵谷的笔名投稿”,说的就是投稿给《大光报》副刊,而在灵谷的鼓励下,平可也给《大光报》投了一篇短篇小说,并被刊登出来,邀请赴宴,在宴会上,平可又认识了“星河”,也就是谢晨光。当时《大光报》的副刊主持人来自广州。{37}在认识谢晨光和龙实秀之后,他逐渐认识了侣伦和黄天石(杰克)。从平可的角度,“岛上”一群,或者说《铁马》的作者群,相识是偶然也是必然,香港早期爱好创作新文艺而又有一定水平者(被报纸副刊筛选过),所以,尽管侣伦和平可都强调岛上社没有组织,但无形中他们是必然结识的。换言之,1929年的《铁马》是集合了当时香港最为优秀的一批新文艺作者,同时,他们的共同点也就是“新文艺”而已,各人有各人的文化教育生活背景。
与侣伦一样,平可也否认“岛上”同人有什么具体的共同诉求和组织:“上述包括我在内的一群青年纵各自有自己的愿望和志向,共同的雄心壮志却是没有的,因为也没有什么组织,只是一群气味相投的青年,常常聚在一起,闲谈大家都感兴趣的事物而已。想不到后来却出现了‘岛上社。”{38}的确,即使仅仅阅读《铁马》上的文章,我们也能明显体会到《铁马》作者群的“同人”性质,在于其处境的相似,而非思想层面有怎样高度的共鸣。在《铁马》最末被视为“宣言”性质的文章中,使用了很多经典的“五四”语汇,但在香港文化的语境中,又显示出不同的意思。这一具有“五四”色彩的“宣言”常常被研究者引用,以说明“五四”的连续性,香港与大陆仅仅有“时差”,而无根本上的差别,但真的如此吗?
在《铁马》中,“咖啡店”栏目中的文字在话语层面大量借用了大陆新文化的经典语言,譬如“呐喊”“古董”“国语文学”等等,其中1927年鲁迅来港演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有意思的是,“宣言”的作者“玉霞”“川平”等反而很少被提及,在卓云(平可)和侣伦的回忆中,也未出现他们的身影。看来,他们相当于岛上一群请来的“外援”。如果将他们的文章当作香港文艺青年的“宣言”,在未能确定这些作者的身份之前,还是存疑。
譬如《第一声的呐喊》的作者玉霞,编者在文后说,“玉霞君听见我们铁马有咖啡店之设,因此,他就写了这篇文章来,我们接到玉霞君这篇文章,恰是铁马将近出版的时候了”{39},由这句话看来,玉霞很可能并非“岛上的一群”的核心人员,而只是与他们交好的朋友,不过,他关于香港文坛的叙述还是有一定的在地性:“虽然,香港已经有了新文艺的作者,已经出了一些杂志,可是终于不能鲜明地标起改革的旗帜,终于被根深蒂固的古董们暗暗地陨灭了。他们抱了文坛的老资格,转移了许多有为的新文艺作者,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老板们的金钱,把一些容易诱惑的青年作家诱惑了去。有许多,却是穷苦地在他们的蹂躏下,把一切的聪明与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埋没了去。这是我们怎样觉得可怜的事?”{40}玉霞了解香港的新文艺刊物出版情况,对于香港文艺青年的困境也有体会,可惜的是侣伦、平可的回忆文章都没有言及其身份。EFF0A64C-8A90-4699-AE8A-3AC9FB0C644B
而“咖啡店”第二篇是杂文《从艺术家到世故》,作者署名川平,显然他与大陆文坛的联系更为紧密,其文章似乎有些脱离《铁马》的“香港语境”,尽管同样充斥了不满和愤怒。首先,川平受鲁迅影响很深,“自从入世以来,就知道吃饭这功业并不容易。……有些吃饭的艺术是渊博的,便挣来许多饭碗。这类,我们便叫做‘英雄。所谓‘英雄也者,大概吃得饭稳,而且可以随便抓着奴才们的碗来摔破若干者也。”文风是尽力模仿鲁迅杂文,而“奴才”“给正人君子之流挤倒”等话语也来自鲁迅。同时,川平看起来是从北京南下香港:“胡大师还统治着北平的时候,不准‘乱谈国事,所以茶楼上全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帖子。现在张大帅虽然‘身终路寝,但在这年头儿,老百姓还是不敢乱谈国事。在这不能乱谈国事的大时代里,而妄想做艺術家这不是疯子狂徒,而且该打者几希!”{41}浓浓的京味和语丝气息,给《铁马》带来一丝混杂的文化质感,提示着香港新文学和“五四”文学的联系,也提示着彼此人员往来和交流的自由密切。既然在此刊登,则鲁迅式杂文即成为香港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它与其他追求唯美的、呼吁生存的、表达愤怒的文章是平等的混杂,而非谁代表谁的关系。
论述及此,可见的是“岛上的一群”正如侣伦和平可共同指认的,最多只是“气味相投”。他们的共通点大概就是青年人对于固化文坛和不公社会的天然愤怒。陈灵谷的《蕾莲之死》最可以体现这种愤怒。小说中十五岁的姑娘被爱慕她的作家炸死,“炸死”是一种极度暴力的行为,与纯真唯美的蕾莲形成鲜明对比。他爱慕蕾莲纯真不伪的艺术(歌舞),而痛恨她身边包括她父母在内的丑陋势利之人,“蕾莲是天赋自然界的花朵,她被一部分人独占她要从此失了真价。”他无法获得她,就想要毁灭她,因为若不如此,“她的纯真不伪的艺术,怕就要逐渐受了环境的包围而转变”{42}。这显然是一则关于艺术与世俗矛盾的隐喻之作。而其价值,正在显现作者对于庸俗的极度愤恨——而革命者陈灵谷所表达的痛苦和愤恨正是一种无法明言的殖民地症候,尽管可能因为审查等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在字面指向“革命”,却不应该被忽略。
《铁马》和《岛上》如短暂的流星划亮天空,但据侣伦说,一九三四年夏季,“一家报纸的副刊发起举办半月一次的‘文艺茶话会。参加茶话会的文艺工作者在‘岛上的一群的基础上有了发展:他们中包括了刘火子、温涛、李育中、戴隐郎、杜格灵、张弓……等人。‘茶话会并产生了定名《新地》的文艺双周刊;由杜格灵和侣伦主编。‘寂寞的岛上不再是寂寞的了。”{43}《铁马》和《岛上》虽然告终,但这批新文艺作者的交游创作并未停歇,香港的新文学也只是开始,而非结束。
① 赵稀方在《报刊香港》一书中辨析了《伴侣杂志》是“香港新文学的第一燕”的说法,后人都是对侣伦说法的延续,其实相较于定位为家庭杂志的《伴侣》,作品质量更高的1924年初刊的《小说星期刊》才是香港新文学的前驱。(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② 张吻冰在《伴侣》第5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四月十一日》,侣伦在第6、7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殿薇》。
③ 杨国雄:《清末至七七事变的香港文艺期刊》(连载),《香港文学》第14期,1986年2月5日。
④ 有文学辞典写成“三期”,应是对侣伦《向水屋笔语》中“该社的作者中虽然个别已经在香港或上海出版过几种单行本,但是杂志却只出过三期。”(侣伦:《向水屋笔语》,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7页。)一句的误读,侣伦所说的三期是包括一期《铁马》和两期《岛上》。
⑤⑥⑩{11} 陈学然:《五四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79页,第191页,第174页,第190页。
⑦⑨ 平可:《误闯文坛忆述》,《香港文学》第4期,1985年4月5日。
⑧ 玉霞《第一声的呐喊》编者按:“我们知道国语文学在中国已经被人共同承认了十余年,现在,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国语文学更该普遍于全国了,而香港这里的文坛,还是弥满了旧朽文学的色调,这是文学的没落状态,以后,我们甚愿如玉霞君所希望的将古董除去,建设我们的新文学,——新的文艺。我们中国的政治统一了,经济也要统一了,同时,国语文学也该统一起来。”见《铁马》,1929年9月。
{12}{13} 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年,第56、57页,第58页。
{14}{16}{23}{31}{35}{43} 侣伦:《向水屋笔语》,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16页,第16、17页,第16页,第33、34页,第32页,第34页。
{15}{29} 侣伦:《炉边》,《铁马》,1929年9月。
{17}{28}{36}{37}{38} 平可:《误闯文坛忆述》,《香港文学》第3期,1985年3月5日。
{18}{33} 平可:《误闯文坛忆述(一)》,《香港文学》第1期,1985年1月5日。(“忆述”系列只有第一篇标题中标注了(一),其后六篇皆未标注。)
{19} 平可:《误闯文坛忆述》,《香港文学》第5期,1985年5月5日。
{20} 陈学然关于当时香港居民构成的叙述也可以作为佐证:“从当时香港居民的构成来看,“香港本土出生的居民在1921年时只占全部人口的26.7%,1931年上升至32.5%……活在1920年代一段长时间里的港人,他们尽管寄身殖民地,但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毋需质疑,也不会动摇。港人大部分都来自珠江三角洲、东江沿岸一带,香港于他们而言只是暂居之地。再加上香港只有极少数华人代表或后来的英籍华人才能参与社会政治,港人的‘香港意识遂难构成,致使港人时刻注目中国内地。”(陈学然:《五四在香港》,第167、168页。)EFF0A64C-8A90-4699-AE8A-3AC9FB0C644B
{21} 郑树森,黄继持,庐玮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27-1941》,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页。
{22}{25} 陈子善:《一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第3页。
{24} 据陈子善考证,“侣伦在上海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伏尔加船夫曲》刊载在《北新》上……谢晨光的作品主要是在《幻洲》和《现代小说》上发表”。(陈子善:《一瞥集》,第2、3页。)
{26} 谢晨光:《去国之前》,《岛上》,1930年,第56页。
{27} 編者:《Adieu 告别之辞——并说几句关于本刊的话——》,《铁马》。
{30}{32} 许翼心:《寻访陈灵谷,忆述丘东平》,《文学评论》(香港),2010年第8期。
{34} 平可:《误闯文坛忆述》,《香港文学》第2期,1985年2月5日。
{39}{40} 玉霞:《第一声的呐喊》后编者按,《铁马》“咖啡店”栏目。
{41} 川平:《从艺术家到世故》,《铁马》。
{42} 陈灵谷:《蕾莲之死》,《铁马》。
(特约编辑:江涛)
New Literature of Hong Kong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Only Have Time Difference:A General Review of Iron Horse
Wang Fang
Abstract: Its a conclusive view that there is only a time difference of ten years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of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of letters on mainland China. But this view, to a certain degree, ignores the 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Memories on the part of a number of writers who wrote for Iron Horse help one see that it is not Lu Xun, but the views expressed by Hu Shi in his vernacular essays that caused reverberations in Hong Kong.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Hong Kong as a colon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urban taste in the world of new arts and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pre-determined that theyd be concerned with and receptive to the cultural radiation with the urban airs of Shanghai.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direct and deep-level reason why magazines like Iron Horse and On the Island were not able to maintain themselves while also paying attention to articles consistently deemed ‘declaration in a column, called ‘Cafe, in Iron Horse, which, in fact, shows the dislocation and mixture of mainland and Hong Kong cultures.
Keywords: Hong Kong, Iron Horse, new literature, Hu Shi, Shanghai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9ZDA278。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EFF0A64C-8A90-4699-AE8A-3AC9FB0C64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