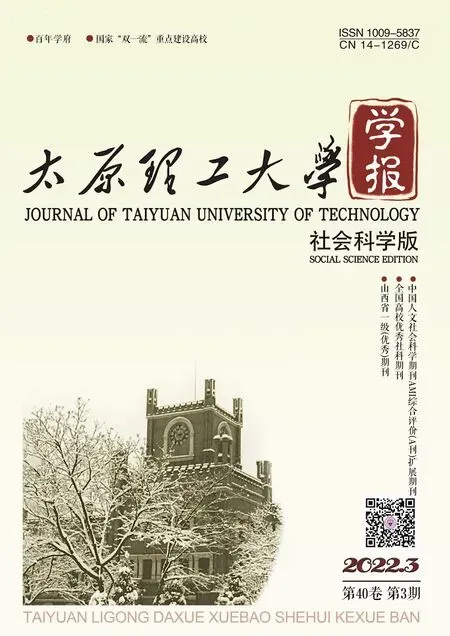重释马克思的权利理论
——基于《哥达纲领批判》中“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考察
张 超,杜玉华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一个翻译引发的理解难题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针对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合并预备会议上拟定的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批判》所写的批判性文章,马克思告诫两派需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合并,批驳两派合并时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且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在这两个关键阶段和一个动态转变过程中,马克思重点论述按劳分配和按需两种分配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包含了一个关键术语——“das bürgerliche Recht”。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32,即新见解的科学性体现于对术语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进行深入研究。
“das bürgerliche Recht”出自德文版MEGA2第1部分第25卷收录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词所在的段落原文是:
“DasgleicheRechtist hier daher immer noch dem Princip nach—dasbürgerlicheRecht,obgleich Princip und Praxis sich nicht mehr in den Haaren liegen,während der Austausch von Equivalenten beim Waarenaustausch nur imDurchschnitt,nicht für den einzelnen Fall existirt.”[2]14
对应的中文翻译:“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3]434
“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中国历次翻译的版本中意思不尽相同,如表1所示。围绕“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中文翻译,对“Recht”和“bürgerliche”(1)bürgerliche Recht的符合语法的正确表述为das bürgerliche Recht。根据德语语法,bürgerliche的词根是bürgerlich,因bürgerlich前面的定冠词“das”而在词尾增添了“e”。但是定冠词“das”对于本文的分析无实质影响,因此被隐去。该解释经由郑永流先生提醒而增添。的理解分别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争议。

表1 “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不同版本中的翻译(2)表格内容参考了两份资料汇编文献:其一是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资料汇编第1辑(1983);其二是贺团卫.《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8.
从1922年5月熊得山在《今日》第一卷第四号翻译《哥达纲领批判》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到1949年5月何思敬和邢西萍在解放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das bürgerliche Recht”中“Recht”一直被翻译成“权利”,然而到了1955年,根据俄文本唯真校订的版本“Recht”却被翻译成“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最早来自于仓木(陈昌浩)于1949年翻译出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3)康闪金认为将“Recht”翻译成“法权”与陈昌浩的苏联教育背景有关,即与其接受了法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权力的工具思想有关。参见康闪金.“资产阶级法权”:一个革命政治语词的历史考查[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1):84-94.。“Recht”同时具有“法”和“权利”两层意思,译者在某一具体语段时该如何翻译,生造出“法权”一词。陈忠诚在50年代初便对这种模棱两可的译法提出质疑,即从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角度批判:如果“Recht”可以翻译成“法权”,那么不翻译成“法义”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他认为在1949年5月何思敬和邢西萍翻译的版本中,“Recht”第11页被翻译成法(权利)是一种严谨的译法[16]。接续陈忠诚的思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形成了“权利—义务”的框架结构,是一对矛盾体。如果将“Recht”翻译成“法权”,那么必将有一个词可以被翻译成“法义”,然而在马列著作和法学经典中都找不到这样一个词。因此,“Recht”翻译成“法权”是不准确的。令人惋惜的是,陈忠诚的质疑虽然使得中国人民大学在有关教学、课程和教研室名称中将“法权”改成了“法”,“国家与法权理论”改称为“国家与法的理论”,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扩大到马列译著和一些政治书籍。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74年成仿吾的重新校订(4)据考证,陈忠诚是第一个对“Recht”在马列著作和法学领域的翻译提出质疑的。成仿吾是第一个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中“Recht”的翻译提出质疑的。,成仿吾于1977年10月指出“Recht”具有“法”“权利”“正义”“公道”四层含义,译者对前两者的简单合并,不仅造成理解上对“法”和“权利”的似是而非,而且还丢掉了“正义”与“公正”[17]185-186。1977年12月,中央编译局在《人民日报》发布《“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声明。至此,从1995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哥达纲领批判》“das bürgerliche Recht”中的“Recht”均采用了“权利”的翻译。我们不禁追问,将“Recht”翻译成“权利”是否准确?此处的“权利”是何意?这两个问题须与“bürgerliche”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解答。
一直到2005年魏小萍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中“bürgerliche”提出质疑之前,不同译者对“bürgerliche”的翻译都指向资产阶级。具体翻译依翻译年限排序有:“有产阶级的”“资本阶级”“资产阶级的”“资产者的”“资产阶级式的”和“资产阶级的”。
“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属于同一含义,自不待言。资产阶级,亦称“资本家阶级”[18]176。“资产者的”与资本家也应属同一意思。资产阶级是由凭借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的资本家构成。因此,除“资产阶级式的”以外的四种翻译都可以统一为“资产阶级(的)”。
魏小萍认为,“bürgerliche”指的是“市民”,“das bürgerliche Recht”应指“市民权利”[19]。王贵贤、赵丁琪[20]和宋朝龙[21]认为,如果要指明这个词组的阶级属性,也应属于小资产阶级。将“bürgerliche”准确翻译为“市民”,改变了这个词所体现的阶级属性,从资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是否意味着以往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都失去了意义?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话,那么应该如何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权利形态的阐释?这个问题包含了从1977年将“das 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开始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的意义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须首先厘清从1922年起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翻译各异的原因。
二、“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翻译各异的原因
为什么在中译本中,“bürgerliche”会被翻译成“有产阶级的”“资本阶级”“资产阶级(的)”“资产者的”或“资产阶级式的”?同时,为何“Recht”的翻译从权利到法权,再回到“权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词组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即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任务。
在20世纪20年代,或许是因为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或许是因为国内正值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反目,在翻译过程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理解更具有阶级意味[22]173。
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面临国民党的围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解放战争,战争与革命是主旋律,中国共产党时刻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强化了“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阶级性。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7年以前,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践运动迫切需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支撑。毛泽东将消费资料分配领域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泛化,扩大到了思想政治领域,把“资产阶级法权”同“资本主义复辟”问题联系起来[23]。毛泽东认为体现封建主义特权的社会差别、官僚主义作风、官本位和特权现象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混淆了不同阶级的特权与权利之分[24]。政治挂帅、疾风骤雨似的群众运动等极“左”意识形态和实践表现大大加深了“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资产阶级属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法治建设迈入正轨。资产阶级法权被更正为“资产阶级权利”,体现了对极“左”思潮的否定。此时,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探讨的学术性开始逐渐增强。“资产阶级权利”的翻译直到2005年之前都未有人提出过质疑,这其中包含着理论难题,使得“资产阶级权利”似乎能够不矛盾地与《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相协调。因此,更须运用严格的语义分析方法重新考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论述,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带来的启示,这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将是一项重要而有益的工作。
“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落脚点是“Recht”,对其翻译成“权利”已无较大争论,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属于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即便有的学者认为权利概念也属于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25],但作为法学最基本范畴的权利凝结了法对政治具有确认、调整和影响的作用,因此政治哲学的视角仍应回到法学视角。虽然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政治与法学都不扮演重要的角色,马克思致力于透视其背后的经济基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到了成熟时期就完全放弃了拿出一种国家理论的理论意图。但是,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所说,“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如今,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其过程中民主化、法治化是必经的阶段,因此,从法学视角研究“Recht”是实践所需的。同时,这方面分析研究较少,有必要对其进行扩展。此外,分析权利所蕴含的意味也能够为“bürgerliche”的阶级属性分析提供帮助。
三、“das bürgerliche Recht”中的“Recht”(权利)意涵探讨
马克思认为,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原则即按劳分配是一种平等权利。需要辨析的是:作为不同形式的同等劳动量相交换的分配方式,与权利是否可以等同?分配方式与权利是否属于同一位阶的概念?此处的权利属于经济学概念还是法学概念?
权利释义的“利益说”认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权利乃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马克思同时代的法学家、“利益说”的集大成者耶林将利益作为权利概念的指称范畴[26]27。马克思和耶林的利益概念语意都指涉到耶林所称的“外部可见利益”,即经济上的财产。但是二者分析的路径发生了变化。
耶林认为利益概念还包括未显于外的内部利益,即更高伦理形式的利益,如人格、自由、名誉和家庭关系。内部未显利益是外部可见利益的基础,如果没有内部未显利益,那么外部可见利益将失去根本价值[27]9。自由、平等等精神利益决定了物质利益的价值。
相比较之下,马克思则在经济上财产的分配方式基础上继续深挖,指出不能仅从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看待问题,因为分配方式由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决定,后者又由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决定[3]436。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其中生产关系直接规定生产方式的性质,那么分配方式的性质也应由生产关系直接规定。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反映了物质利益的归属,在法律中表现为所有权关系。马克思清晰地透视出权利后面承载利益的所有制关系。按劳分配与权利因物质利益相联系,体现为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3]435,即在物质利益的分配当中,权利的平等本性要求用同一尺度去衡量人。权利是对利益归属(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分配制度)的反映,它本身具有经济学意味。
由物质利益的分配方式所引发的关于平等的论述是马克思区别于耶林的关键点。马克思的权利理论已蕴含了现实主义法学的精髓。马克思排斥“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3]436现实主义法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美国,马克思于1875年便提出现实主义法学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正如现实主义法学的事实怀疑论与规则怀疑论并非是否定事实与规则,马克思也并非否定权利概念,是批判仅仅谈抽象的“平等的权利”这些空话,而不从现实情境之中考察劳动者是否得到了拉萨尔口中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是从实践中按劳分配引发出平等问题。平等、自由问题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经济基础的矛盾引发出来的,并且这种平等受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权利的平等本性要求与等量劳动交换相符合,此处马克思没有言明这种权利以法的形式所固定,而是根植于分配方式中,因此不属于严格的法学概念,但因其与法学中权利的特点——平等相关联,可以称马克思笔下的“Recht”具有法学意味。
权利的平等性并非是一成不变或者属于永恒的价值,而是本身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从形式平等发展至实质平等,最终走向消亡。
(一)形式平等:权利本性
形式平等指使用同一尺度来计量,这是权利的本性[3]435。在按劳分配中,平等的权利表现为根据劳动的时间和强度来确定劳动者能交换多少数量的同量劳动。然而,劳动者并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劳动者本身不同的劳动能力和不同等的需求[28](结婚与否、子女多少等)导致了即便给予同样的社会消费基金,一个人实质上(事实上)可能比另外一个人更加富有。形式平等用单一角度或者特定方面去看待现实的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9]60用抽象的观点去考察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阶级的等级压迫时具有重要意义,天赋人权、权利的形式平等观念被当作有力武器去冲破封建阶级依靠出身、种族来区分人的落后观念。
然而,形式上的平等还带来“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3]430。劳动的社会化过程在权利层面表现为形式平等,只有借助于此,非劳动者才可以凭借其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权平等地享有劳动者的劳动。如果社会中的某个人不劳动,但是他却跟着劳动者过着一样甚至更好的生活,那么他必然是依靠别人的劳动以获得财富从而生活,同时也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3]429。
所以,抽象的权利观念应转换为“现实主义观点”[3]436,追求实质上的平等。权利是历史的、具体的,马克思告诫我们,平等权利带来的“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35。具有形式平等本性的权利在不同社会中因其各自具有的经济结构和由此制约的文化发展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权利的特殊性。形式平等中包含着事实上因劳动者各方面的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即形式平等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克服这些内在缺陷时产生出实质平等。权利的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权利的一般性则体现在它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是“逐步消除的”[24],并且适用于特定社会的一切公民,一般性也可称为普遍性。马克思在批判地对待权利观念时并不否认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而是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二)实质平等:权利消亡
在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中,生产力的增长使得集体财富充分涌流之后,按需分配才能替代按劳分配。在形式平等的社会中,耶林指出需“为权利而斗争”,即“为被法律所承认的利益而斗争”,在利益遭到侵害之时,必须通过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无产阶级在面临资产阶级的剥削之时,也将为实质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进行阶级斗争,改变不合理的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已不需要通过斗争的形式去保卫自己的利益,权利已无存在之必要,因此权利因失去作用而逐渐消亡。形式平等是政治领域内的平等,它将人抽象化,称之为“公民”;而实质平等追求的是社会领域的经济平等。前者是不彻底的,从现代规范理论的术语来说,是不可欲的[28]。
马克思的权利观念完成了“事实与价值相统一”。从历史角度,马克思的权利观念认为权利观念并非永恒;从规范角度,受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利有其特定情境下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四、回到马克思:市民权利与资产阶级权利之争
“bürgerliche”在词典中有“公民的,市民的”和“合法的,符合社会规范的,世俗约定的”两个意思[30]361。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阐明权利(Recht)时,重点不在于其合法与否,而是权利所处的范围。如果仅从词典中的两个含义二选一,“公民的,市民的”的意思更为准确。从词典出发,暂时确定一个意思是可行的,但若止步于此,便简化了这个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丰富内涵。“公民的、市民的”与《哥达纲领批判》各个版本的翻译均不同,我们不妨先假设这些翻译的合理性,看是否能够在逐步推导过程中发现矛盾。
如果认为“das bürgerliche Recht”是资产阶级权利,那么资产阶级权利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马克思认为:
“nicht wie sie sich auf ihrer eignen Grundlage entwickelt hat,sondern umgekehrt,wie sie eben aus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hervorgeht,also in jeder Beziehung,ökonomisch,sittlich,geistig noch behaftet ist mit den Muttermalen der alten Gesellschaft,aus deren Schoos sie herkommt.”[2]13
对应的中文翻译为“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eben)从资本主义社会(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der alten Gesellschaft)的痕迹。”(5)引用的中文翻译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括号内的德文翻译是笔者对照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25.Berlin:Dietz Verlag,1985:13)添加的。“旧社会”(der alten Gesellschaft)与资本主义社会(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是同义语。根据唯物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属于旧事物,共产主义社会要批判性地继承,将“das bürgerliche Recht”理解为“资产阶级权利”似乎并无不妥。所以
“DasgleicheRechtist hier daher immer noch dem Princip nach—dasbürgerlicheRecht”[2]14。
中文释译为“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3]434。
“Trotz dieses Fortschritts ist diessgleicheRechtstets noch mit seiner bürgerlichen Schranke behaftet.”[2]14
中文释译为“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3]435。
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也是资产阶级权利,即被束缚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然而,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不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权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为公有制和领导力量转换为无产阶级专政两方面发生的变化。
相比较之下,“资产阶级式权利”的翻译更加注重从形式上继承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权利的外壳;实质上,这种“资产阶级式”的权利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权利了,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所共同占有。“资产阶级式”是根据俄文本翻译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在共产主义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权利和资产阶级国家[31]200,在这里区分了共产主义时期存有的资产阶级权利和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权利的关键区别——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中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只是在权力原则和表现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权利”,即“资产阶级式的权利”[23]。
将“bürgerliche”解读为“资产阶级式”似乎能够在“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上下文中得到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分配方式来讲,资产阶级式的权利与按资分配的分配方式相对应,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却是按劳分配;其次,从价值形式来讲,按劳分配的权利是等量劳动相交换,使得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是剩余价值法则[21];再次,从权利的本性——平等来讲,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要求平等地剥削劳动者,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权利显然祛除了剥削的含义;最后,如果按劳分配指向资产阶级,按资分配也具有资产阶级性质,那么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便没有社会主义因素。这种解释的困境在于对“bürgerliche”的理解囿于资产阶级,须回到“bürgerliche”的原本意思——“公民的,市民的”,故“das bürgerliche Recht”应被翻译成“市民权利”。在斟酌“das bürgerliche Recht”是否应该被翻译成“市民权利”时,不能仅看到这个词的表面意思,更要探求这个词是否能够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权利的阐释形成逻辑上的自洽。当然,词的表层意思将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表层意思的误读将会危及对马克思关于权利的阐释的解读、建构与创新。
在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权利已经没有支撑其存在的阶级及相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没有了隶属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权利。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到资产阶级权利,但是对此的批判是运用体系解释(6)体系解释是法学中的一种解释方法,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这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中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在这里,运用体系解释的意思是通过联系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上下文,剖析其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其他叙述的逻辑关系和目的论关系来检验“资产阶级(的)权利”翻译是否准确。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推断得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需在各方面,例如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进行。因为,“它(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7)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旧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该段引文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作者加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从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来看,只有当事物发展到内部性质充分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地认识,再去分析它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用较高社会阶段的权利观念来评判较低社会阶段,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观念来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非人化。”[32]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的意义应被归属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
将“das bürgerliche Recht”理解为“市民权利”体现马克思着重批判市民权利的狭隘性或者局限性。马克思权利理论批判的对象包含资产阶级权利和市民权利。两种权利都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要超越的范畴之列。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仍留有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权利的弊病,在革除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制后,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市民社会并未完全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市民社会填补了资产阶级社会消除后留下的“真空”,市民社会具有更大的适用性。此时需要重构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理论:市民社会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无产阶级专政。
市民权利体现的是有限的自由。“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共有为基础的社会中”[3]433,社会主义社会中整体的自由代替市民社会个体的自由,超越市民社会自私自利的狭隘。以往的理解混淆了马克思权利理论所批判的对象和建构的对象。
“市民权利”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小商品生产者为主体,随着资本主义的积累,市民社会的个体所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狭隘闭塞的小生产被社会化了的大生产所消灭,个体劳动逐步转化为私人的雇佣劳动[20]。由此,市民社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市民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后来成为资产者。在探究权利背后的时代背景时,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究呼之欲出。市民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或覆盖,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而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市民社会的因素,其中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倒退”理论难题亟待解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关涉了社会主义权利理论的构建。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用“社会主义权利”一词进行概括是最为适宜的,即对社会主义权利的探讨不应囿于资产阶级权利和市民权利。但是论证的基点是权利的历史性继承,社会主义权利带有市民权利的特点——形式平等,体现在分配领域是按劳分配。同时社会主义权利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分配领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按需分配。那么仍然将“das 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市民权利在法律意义上是为了强调市民权利具有的形式平等,同时在经济意义上指向原来占有生产资料、后来被剥夺的资产阶级脱离出来的市民所拥有的财产所有权(即产权),“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反思在这方面重视程度的不足。
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将“das 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市民权利”,但马克思鲜明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市民权利”指向的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同义语,我们不能够在今天强调以按劳分配的特殊历史情境去套用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首先,这种观点预设了马克思的阶级立场,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其次,无法解释“das 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时对应的按资分配制度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之间的矛盾。此种观点隐含了对“das 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市民权利”时弱化阶级意味,甚至担忧其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是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分配制度肯定“市民权利”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形式平等的观念将深入人心,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可以推导出对资产阶级权利所体现的按资分配和对劳动者的压迫的否定。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并非消失,而是内在地包含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das bürgerliche Recht”应该翻译成“市民权利”,同时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中内在地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深刻批判(8)在德文原文中,“资产阶级的框框”对应原文是“das bürgerlichen Schranke”。“bürgerlichen”与“bürgerliche”属同一词源“bürgerlich”,从前述分析中可知其应意为“公民的,市民的”,市民权利“被限制在市民社会的框框里”才是正解。。
五、“市民权利”进一步引发的问题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下存有的实质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剖析,即劳动者先天的条件和后天不同等的需求会导致劳动者之间按劳分配的生活资料产生数量上的差异,那么由这种实质不平等所带来的因劳动者事实上的社会消费基金份额的差异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却一直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由差异报酬积累了的剩余劳动……能否并且如何投入社会再生产领域的问题。”[19]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将不会最终变为按资分配,市民权利不会再转变为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将会替代按劳分配,但如何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这是现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理论难题。我国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表明我国已在实践中承认“按劳分配原则下的积累劳动能够转化为生产手段、投入生产领域并且参与分配,从而带来利润”[1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践中,资本祛除资产阶级的属性运行,“按劳分配的结果是一部分人较快地先富起来”[32]。按资分配作为补充的分配方式与作为主体的按劳分配共同发挥作用。
为何按资分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成为分配制度的一个补充环节?可从马克思关于“权利”的叙述来做一个法理分析。权利不是天赋的、抽象的,具有受限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的相对性。“权利的这种相对性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和真实性。”[25]权利的普遍性体现为主体的普遍,权利在未被完全消灭之前(未达到按需分配之前),要以形式平等来深刻影响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所有的公民(在权利语境下,劳动者也是“公民”)和组织依据按劳分配制度获得的合法财产,在不同法律相违背的情况下,能够自由任其处分。权利保障公民和组织自由处分财产的同时,也是对这种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33]:一是自由处分财产不能对国家、社会利益和他人或其他组织的自由处分造成影响,当这种自由处分产生危害时,就要遭受某种不利或者负担;二是当自由处分严重影响社会经济运行时,就要通过《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2021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型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34]。第三次分配是“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35],这种具有道德力量的分配方式是追求共同富裕和按需分配的一个崭新途径,多体现于慈善等公益事业,促进了分配公平,坚定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
再者,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关系如何?“应当注重产前生产资料分配的公平性及产后利润分配的社会化问题”[33],当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按需分配”[20]。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与按需分配同时共存于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的体现及其结果——按资分配是形式平等的产物;按需分配则是实质平等的表现。按需分配不仅在事实层面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并且在价值层面关注现实的人的不同状况,是联系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完全的按需分配的纽带,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向往与朝之奋斗的努力,而这必须通过法治化的手段进行,彰显权利的形式平等性。
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关系隐含了市民权利、资产阶级权利再到社会主义权利的历史发展线索。在分配领域,市民权利以按劳分配为主,资产阶级权利以按资分配为主,社会主义权利以按需分配为价值追求。按劳分配发展至按资分配时,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形式平等被按资本分配的实质不平等所取代;虽然资本是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按劳分配有形式平等的内在合理性,但是必将被蕴含着对现实的人的关怀的按需分配所逐渐取代。这体现的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系。分配方式最终将发展至彻底的按需分配,也是权利消亡之时。
六、余论
马克思认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产品,产品的劳动也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一种设想,在实践中不能教条化,因为这种设想否定了商品经济和权利的经济基础,这不符合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实际情况(9)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非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相结合使得我们过早人为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变革后生产力不能直接改变的现实。参见高远戎.“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J].中共党史研究,2006(3).,要对设想进行“矫正”。区分马克思的设想与精神实质是对待这个问题的切入点,精神实质是毛泽东所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6],或者将其称为“基本原理”。列宁指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15]187。马克思提出的是权利演变的方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任何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某种设想都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在不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时,权利的探讨又开始活跃起来。希望借助于对马克思的权利理论的重新阐述,使得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明晰马克思对权利形态变迁的论证与经济分配制度相关联,最终仍然要回归到生产力的发展之中,马克思的权利理论是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经典验证。